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问题青年Wonderers(ID:openyouthology002),作者:狗毛,编辑:Sharon,原文标题:《爷爷的葬礼上:燃烧的香,燃烧的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夏,我跟着爸爸参与了爷爷的葬礼。作为小孩,在白事前后只能是一个旁观者。我看见了爸爸竭尽隐忍的悲伤,目睹了姑姑是如何被一纸禁令被封在灵堂之外,还有在入棺时才出现的奶奶身上所浮现出的复杂的情绪。
整场仪式,我,我的爸爸、表妹、姑姑、奶奶,各有各的忧心。
一
七月下旬,我们这个十八线城市依然很热,外面几乎每天都是 35℃ 以上。我和我的表妹坐在便利店里,手边放着打折的、冒着冷气的牛奶。我们漫无目的地聊天,目光扫过货架上摆着的巧克力,我忽然对她说:“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爷爷给我们买过这个巧克力?”
伴随着巧克力而来的,还有我小学时关于夏天的碎片回忆。爷爷牵着我的手,我们走到附近的一家影碟店去租碟,一张碟看一次是一块,我们总是租大概两三张,够反反复复地看一整个下午。
我和妹妹从老旧的电视柜下面抠出几块零花钱,跑到便利店买最便宜的杨梅冰,回来的时候,爷爷总会给我们买巧克力,不是那种代可可脂的廉价巧克力,而是入口即化的、醇厚的、一盒仅仅只有几颗的巧克力。
电话响起,是姑姑给我打的,我一接起,她就急切地问我们在哪,为什么不接电话,现在所有人都要出发了。我们被急匆匆地接上车,表妹因为手机静音而被姑姑责怪了两句,但是很快,她问姑姑我们现在要去哪。姑姑说,去殡仪馆,那里的车刚把外公(我的爷爷)接走。
我轻轻地啊了一声,表妹开始顺着这个话题叽叽喳喳地讲她在医院里遇到的趣事,讲她如何好奇太平间,讲她经历的第一场妇产科手术,讲一切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个车上讲的东西。我没法阻止她,也没法完全不回应,在微妙的车厢空气里,我轻轻地把头转向窗外,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渐渐从熟悉变得陌生。姑姑的车开的很稳,她的声音也很平静,她既不对女儿做出回应,也不制止她,她的脸上我看不出任何东西。
但是我知道我爸是怎么样的。
中午十二点,昼夜颠倒的我刚睡下两个小时,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
“什么?”
“你爷爷……”
“他怎么了?”
“你爷爷……去世了!”
二
我混混沌沌的灵魂才从梦里惊醒。在我能够理解我爸的话之前,我已经要求他重复三遍这个事实。到最后一遍的时候,他已经无法抑制住他的哭声,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见他这样说话。他简短地嘱咐我,不用急,吃了饭再过去。
我顾不上吃饭,急忙出发去奶奶家里。不大的客厅里满是男人,他们大致都长得差不多,黑皮肤,短头发,金链子,polo 衫。他们或站或坐,或走或蹲,嘴巴里叼着的烟完全不影响流利的方言,他们是为“一条龙服务”来的。
这边,我爸去开死亡证明,那边,姑姑采买水果、香烟、毛巾、毯子。无数的东西堆放在餐桌上。这里是没有小孩的事的。我绕过人群,走到里间,就看见我的表妹坐在里面玩手机。我又抬头回看,透过绿色的纱窗,模模糊糊地看我爸的脸。他吃力地坐在那里,低着头,双手撑在膝盖上,嘴巴紧紧地抿着。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或者在商量什么。
他突然进来,走到我的面前,问我:“吃了吗?”。
“没有。”
“那你点外卖,顺便给大家都点一点。”
“好。”
我伸手接过他的手机,目光不自觉地聚焦在他难以抑制的颤抖的手上。我再对上他的眼睛时,看见他的眼睛很亮,睁得很大,脸上的肌肉都在用力,那是一种有点骇人的状态,好像下一秒他就要“吃人”,或者参加奥运会。
我突然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我的爸爸,像我在许多猫咪视频里看到的那样,他应激了。作为子女,我能感受到他的无助、恐慌、悲伤。但是作为家庭的支柱,我的爸爸,他面对这种困境又半点不能后退。
我后来才知道,爷爷是在我爸爸怀里去世的。
来了人,他们不断地穿过客厅。
表妹说,“我们一起去看下“那个”房间吧。”
我沉默了,说:“我不敢。”
她说,“没事,不会很恐怖的。”
后来,她带着我去看。我站得非常远,远到几乎是那个房间的对角,表妹拉着我的手,好像怕我会被吞噬进去一样。我只能看到那个房间里有一床红色绣花绒面被子,被子叠成工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下面压着的是什么,看不到,我也不敢仔细确认。
到了殡仪馆,定了花圈柱子,我看着殡仪馆给的手册,真花和假花都好贵,随便一个装饰就是 1000 起,我们选了一个折中的套餐。亲朋好友渐渐来得多了,我们每个人都戴上了白色丝线做的“麻绳”,在房间入口处,请高人算的那一张黄纸斜斜地贴着。
我和表妹仔细研究了一番,上面先是列了爷爷的八字、去世时间,接着列的是禁令,“26 岁的牛免哭”,“52 岁的猪免见”云云,还有几时几刻,我们并不是很看得懂的一些话。
大人三三两两地站在灵堂的外面抽烟、聊天,见我俩守着那张黄纸,也围过来瞧。我想,哪怕是对于大人而言,这个东西也并不常见。我的目光从黄纸游移到人群,我爸、我姑姑,每一个人的表情都镇定如常,也许大家同我一样不能理解这张纸。又坐了一会,大人们决定先把我们送回去,因为他们要在这里至少守孝三天。
这个殡仪馆的房间并不舒服,它没有任何可以躺下休息的地方,殡仪馆外面也无餐馆小吃,如需食物,须得提前向店家预定。可以想见,如果要在这个地方待上三天,那对谁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但是,高人说,香是不能灭的,我们排队供了短香,与此同时第一炷长香开始燃烧。
长香一支能燃十个小时左右,“不能灭”意味着,接下来我爸和我姑姑要交接班,一个人守在那里,另一个人出发回家,匆匆洗澡吃饭。从我的视角来看,换班的人从城里带来新鲜的食物和重新积蓄的精气,换走那个耗尽精力的守夜人,这好似是某种吸食人类为生的鬼怪,靠着人类不间断地供奉而存活。
几天下来,每个在灵堂守过的人脸上都有一种可以细致描摹下来的疲倦和狼狈。我作为白事中的晚辈,无法对此事提出任何一点异议。我在这里见到了一些我素未谋面的亲戚,哪怕是躲在父亲羽翼下的我,也能感受到他和我姑姑必须成为“孝子孝女”的压力。
每一句“节哀”的背后,都有对哀痛的要求。
而守孝、白事的排场,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人们之间相互成全。我既无法询问我的爸爸,孝心是否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也没有魄力对双眼满是血丝的他和他背后的那些东西表达否定。
我和表妹说:“如果我死了,我一定不要这些东西。”
“我也是,想快快火化后葬在大海。”
可是我知道,我们默契地都没有说出口的是,如果我的爸爸去世了,如果她的妈妈去世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上这一遭。
我们只敢在权力和舆论倾倒于我们的时刻,才敢说出拒绝。
三
白事,是我们一家最靠近封建迷信,最靠近长幼尊卑、重男轻女的时刻。白事的核心与封建社会如出一辙,无非就是,广而告之的折磨。
我们要送葬。早上四点半起床,五点半到,迎宾客祭拜,七点准备火化。这一切都紧促地不可思议。我爸,作为大孝子,他背上了草鞋,换上了麻绳。草鞋不知道是多少人曾经背过的,48 码,边缘粗糙,缝隙巨大。
我,作为大孝孙女,戴上了一个叠的像猫耳厨师帽一样的麻布,这个帽子头顶尖尖翘起,好像一个前短后长的巨大口袋。说实话我在看到镜子里我和我爸的那个瞬间,没有忍住扑哧地笑出声来,这样传统的装扮和习俗,明晃晃地出现在一个现代化有电子屏幕显示逝者姓名的殡仪馆,出现在花圈中有罗马柱这种东西结合产物的殡仪馆,出现在白衬衫西装裤黑皮鞋的我爸的身上。
至于我,我蛮喜欢“猫耳厨师帽”的,有一些俏皮可爱。
但是我再看,却发现不对了。同样作为孝女的姑姑,仅仅在手臂边上缠了一圈白巾,跟我爸的配饰比起来,似乎差得非常远。再往下,不论是上香,还是列队火化,总是我和我爸走在前面,姑姑就慢慢地跟在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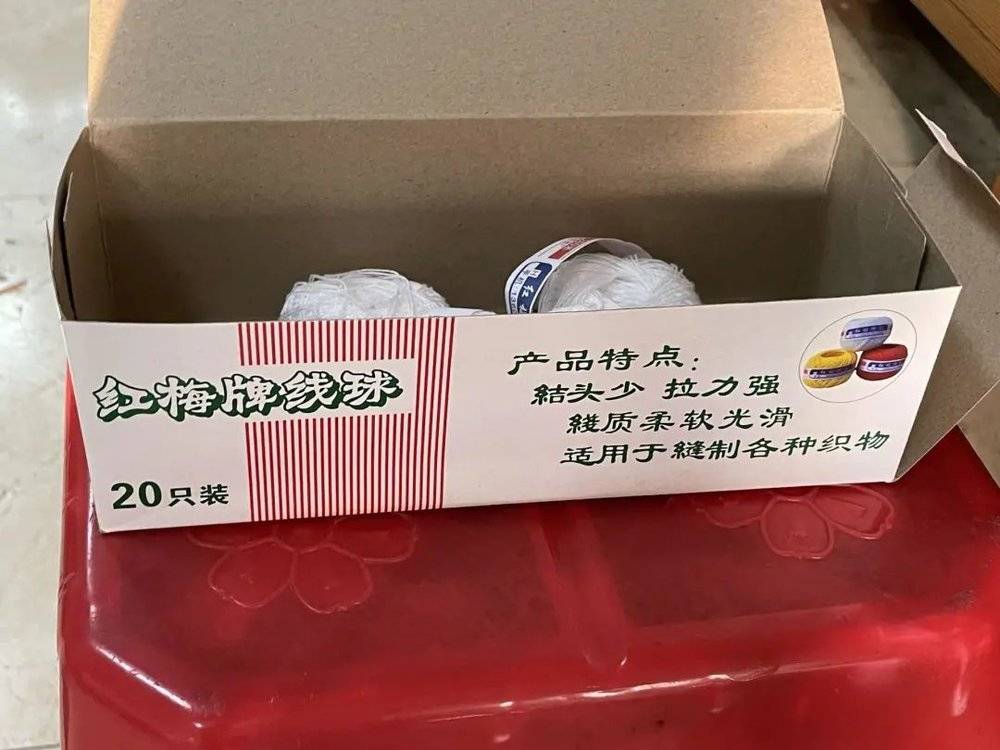
白事似乎对仪式有许多要求,比如谁举照片、谁打伞、谁持香、谁抱骨灰,容不得差池。殡仪馆里,穿黑色 polo 衫的大哥急吼吼地满世界找孝子、孝孙,因为如果没有排好队,送葬队伍就没法出发。我这辈并无男嗣,作为家中长孙女,我自然是代替大孝孙,而作为长女的姑姑,自然是被我爸代替。排队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在这场白事中,我和姑姑谁地位更高呢?
要入棺了,我们作为直系亲属,两两成对去拜。我这才注意到,姑姑是没法见爷爷最后一面的。
那张贴在灵堂门上的黄纸,那高人算的卦,那卦上用行书写着的吉时和吉人,免哭和免见,像是封印,虽朝外告示所有人,但却把我姑姑封在了灵堂外面。她正是,1971 年,肖猪,52 岁。
懵懵懂懂的我们这才明白那张纸的威力。它说几时火化,就必须几时火化,它说谁不能见,谁不能哭,就排除了最后一面和哀痛的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高人算的那一卦似乎只算了今天的吉时,并没有算今天是不是吉日,也许是因为殡仪馆不能停放那么长时间,也许是国家不允许。毕竟高人也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情。
我捧着香和表妹一起走进去,先跪再拜,顺着指引,我们须绕到爷爷跟前,再离开。
我浑身僵硬。躺在那里的人,青黑的脸,死后三天的脸,浮现尸斑的脸。我觉得躺在那里的人似乎是我爷爷,似乎又不是了。燃尽的香灰落在我的手上,我忍不住一个哆嗦。
花,烟,这是殡仪馆里最常见的东西,眼泪倒是没那么寻常,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我走出来,看到隔壁房间那个女孩,看头饰她应该也是孙女,脸上表情凝重。
然后便是吉时到,火化。
四
我没时间到处乱看了,作为孝孙女,我需要抱着我爷爷的照片走在最前面,我的表妹给照片打伞。
我抱着遗像走在人群中的时候,所有人都自动给我让路,大家脸上的表情很微妙,但几乎都是微微笑着的,手上夹着烟的,烟也不抽了,吃东西的,也放下了。我恍惚间感觉自己是在拍电影,身后跟着的不是我爷爷的亲戚,而是数台摄影机。我感觉到每个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爷爷身上,我戴着的猫咪孝顺麻袋子上,我爷爷遗像夹着的白色绢花上。
火化时可以有五名家属在场。作为小孩,我们最好“不见”。于是我和表妹就停在火化室外。我总是觉得这似乎有点怪,作为晚辈,表现出痛苦和孝心,这正是大家希望看见的,但是回到家,不论是谁,见到我脖子上的白绳,总是有些说不出口的别扭,悄悄提醒我要将这东西扔在外面,怕沾染了什么。
我站在旁边看着姑姑,她作为那个唯二不能见爷爷最后一面的人,自然也没有办法参与火化的过程。她自爷爷的遗体被送进去之后就开始颤抖,双手合十不住地哭泣,哀哀地说着一路走好。积压好几天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爆发。这在她心里,大概才是真正的分别。
我这时才有点实感,也有些难过起来。这有点奇怪,我的难过是借鉴而来的,是从姑姑那里传染的,不是我自发的。但是,比起这个,我好像更为姑姑难过,我很难想象如果是我的爸爸,在这种时刻,因为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黄纸就把我隔绝在火化室外面,除了我,其他所有人都可以进去送,我一定很难接受这样的结局。
而在殡仪馆,每个人的身份,和死者的亲疏,只需要瞄一眼他们身上的配饰,不必多言。但有儿子在的时候,总是儿子捧骨灰,有孙子孙女在的时候,总轮不到外孙外孙女捧照片。而我,需要的是在这场白事中,无比准确地表达我是一个长女及晚辈的身份。这其中,长幼尊卑、男重女轻,以及复杂而无意义的折磨,无需赘言。
于是我们去休息室等待骨灰。这个等候大厅像是火车站,里面有空调、排椅,有小卖部,有圆桌,有打牌的人,有聊天玩闹的人,大家在里面,似乎都很自在。我看到了隔壁房间的那个女孩,她正和她妈妈商量买鞋的事情。我没资格嫌弃这个等候大厅像火车站,毕竟我自己也像是厨师,或猫。
烟,到处都是烟。有人抽,有人点,却不止是香烟。干活的人,男人,手持香的人,或者人,每个人的嘴巴里,或者手指上,或者身体上。我从没看过有任何一个地方抽烟抽的那样凶,没烧完的长香横亘在外面绿色的垃圾桶上,有人举着香闲聊,骨灰等候区有共享充电宝,我想我的爷爷也应该被迫抽了很多烟,或者很多香。
燃烧的香烟,燃烧的香,燃烧的人,好像最后得到的东西都一样。

我突然想起入棺之后,殡仪馆的负责人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了一个银色金属台子,看上去冰冷、坚硬,但同时非常像医生用的那种手术台。
等待大概两个小时。
出来了,出来了!大家说,我跟着引路人快步穿梭在灰白而长的走廊,每个人的脸在左或右侧对着我,我冷漠地扫描着上面的每一种情绪,欣喜、漠然、疲惫。如果不是每个人手上点着的香,我恍惚以为自己在妇产科,等待的不是骨灰而是新生儿。
等待。
原来新生与死亡可以用一种词迎接。
十二点,出发去下葬。
烈日当头,我们一路坐一辆空调坏掉的大巴,和送葬哀乐队伍一起赶往爷爷出生的村子。我捧着照片,走在队伍的前列。我仔细观察奏乐队伍,中间似乎有一些乐器人员构成的重复,我再看,就发现队伍里总是有人会小小地偷懒一下,漏过其中几个片段,擦擦脸上的汗,休息下,然后再悄悄加入。
但好像人出生,或者死亡,总是要大张旗鼓地让天下知道。
五
我的爷爷在我大概小学后半段的时候,出轨了。作为一个 “老年人”,却被捉奸在床,很是被人瞧不起。从那时开始,我就很少见到我爷爷。虽然他仍然和奶奶生活在同一个房子里,但是相互不往来,甚至进出房子都不走同一个门,加上学业繁忙,我也很少再见到我爷爷。
爷爷再频繁地出现在我面前,是因为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做小肠气手术时因麻醉昏迷,抢救时失去了他的牙齿。
那几年里,他慢慢地找不到路,从可以骑车跨区上班到只能在家附近走动。他慢慢地讲不清楚话,从可以教我物理到只能反复嗫嚅他未上成功的大学,后来连电话也不会接了。正当我们为此忧心时,他的情况又急转直下,变成了身体上的毛病,吃不下饭,却又贪酒。
我的奶奶恨他、厌他,却又关心他、照顾他。爷爷无法吃硬的东西,她就常做鱼,或者软烂的蔬菜。每回我们去,她总是带着些嘲讽地讲爷爷又忘了什么事情,又连澡也不愿意洗。
在爷爷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饭桌上的气氛越发微妙起来。我爸总是突然间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今天下午去奶奶家里吃饭。除了吃饭的事,其他什么也不说。
奶奶总是把每一餐都做的很丰盛,桌子上永远有不同品种的鱼、虾、蟹,哪怕对于一个沿海城市而言,也过于用心了。饭局的开始往往正常而温馨,老式的电风扇吊在我们三个人的头上嗡嗡地吹着热风,墙上的时钟虽然已经无法正确地显示时间,却一直咔嚓咔嚓地走着。
但是突然间,奶奶就对着我爸说,他最近总是六七点就睡了。他?谁?我听着没头没尾的一句,但是我爸却快速而默契地接话,今天的饭吃了吗?我继续吃饭,直到他们的话题指向越来越明显——我生活无法自理的爷爷。
我在这种时刻通常不敢看我奶奶的脸,或者看了,也马上低下头去。我的奶奶待我一向很温柔,或者说是一种隔辈带来的不假思索的宠溺。我总是要什么有什么,从来不担心奶奶的拒绝。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形容奶奶讲到爷爷时候的表情,有的时候是咧着嘴,有的时候是咬着牙,有的时候讲到最后还会放声大笑,尽管在场除了她之外没有人愿意笑。她好像某种巨大而沉默的暗色生物,只有在天色渐晚的时候才慢慢展露它在海洋下掩藏的部分。
饭继续吃,我的蟹剥了一半。我爸站起来,说他带着饭进去看看,让我继续吃。我的目光由他的脸转向奶奶,然后转向我手里的螃蟹。门开启,又关上。属于爷爷的那个绿色隔间发出细小的动静,然后是模糊不清的争执。奶奶忽然坐不住了,她说她也进去看看,让我继续吃。门开启,又关上。
我终于敢抬起头。我的面前什么都没有,桌子上的菜慢慢地被电风扇吹冷下来,我一个人坐在屋子的中央,感觉坐在一所荒岛上,四面八方的绿意通过那个隔间缓缓伸展进来。我明明是一个人,却觉得手脚僵硬,食欲全无。奶奶进去后,争执的声音逐渐明显起来,我听到爷爷苍老而含糊的声音。
一个人究竟要苍老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觉得声音里都透出了腐败呢?
“……啜饭啊……”(吃饭啊)
“伐啜了,迢西天克啦!”(不吃了,让我去西天吧)
我记起,上一次听爷爷讲话,是他每次酒醉之后必须要讲的,他年轻的经历。他说自己那一年本来一定能考上大学,还说自己那时候作为青年代表一路去了北京,说自己时运不济,怎会恰逢高考取消,说自己如果不是那么倒霉,今天自己就不会这样,也不会在这样的家庭中。奶奶每次听了,都沉默得让我心惊肉跳。
“妳死哦,儿子赞有好估?”(你死了,儿子怎么会好过呢)
我默默地听着里面叮铃咣啷的声音,怎么也没有勇气回头。我虽然仍然坐在椅子上,双眼却自上而下俯视,看见了这一屋闹剧。
入棺的时候,奶奶终于出现,她前面并未露面,我猜想也许是因为她年事已高,身体不便,也许是因为她与爷爷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没有出席的必要。但也许,是因为她这一辈子都和这样一个男人纠缠在一起,她深切地品尝了几乎每一种失望及漠视,却仍然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开始以及最后照料了这个男人。
仪仗队大张旗鼓地走在前面,我和我爸跟着,然后是姑姑,最后才是奶奶。
爷爷去世前,总是忘记换衣服、剪头发。几天没见,身上会有异味,加上讲不清话,所以他之前认识的朋友,慢慢也不来往了。
去世之后,所有相熟的不相熟的,他记得的以及一定不记得的人,都前来祭拜他。光是下葬这一天,我来来回回拜了他四五次。而他下葬,请了礼乐队伍,豪豪气气地从村头走到村尾。
他应该也没有办法想到,这应该是近几年他最受人重视、最受人尊敬的时刻。
好像我们对待离去亲人的感情,正如我们对待土地和历史一般,总是一代一代的。
我的奶奶,我的爸爸和姑姑,我和我的表妹,我们三代人对于爷爷,有着截然不同的印象与情感。我回望我自己的身上,惊讶地发现,独属于我和爷爷那部分真实的、亲密的感情,已经必须追溯到十几年之前了。而我身上更多的,是我作为故事的旁观者的那一份冷眼——我不把他视为我的爷爷,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完整的男人。
我同情他时运不济,没有被命运选择。我同情一个自诩聪明的人,在生命的最后罹患阿尔兹海默症,但我又有时候觉得,许多事情或许是咎由自取。更甚至于,我觉得他其实已经足够幸运,因为他的不幸总体上,几乎全由她人承担。在密密麻麻交织的网中,我没法忽视那些结构性的东西。
再剩下的,就是我继承的,来自我上一辈感情的反噬。因为我的爸爸和姑姑,因为我爱他们,所以我好像自然而然地将爷爷放在了更外层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我是为爷爷忧心,不如说,其实我只是为忧心着他的我爱的长辈忧心罢了。
出葬仪式就要结束。下午两点,下山,去庙里祭拜。下午两点半,到饭店摆酒,下午五点,第二场酒席。
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在庙里守着。这样才终于算是结束了一整个葬礼。这样算来,我爸我姑姑已经四天没睡好觉,七天没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或社会劳动。
在酒店时,我的奶奶问起后几天庙里的事,她说道,五点到确实太早了,你们可以稍微晚点。
我听了,不知道为什么,身上只觉得更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问题青年Wonderers(ID:openyouthology002),作者:狗毛,编辑:Shar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