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内容节选自《风俗与历史观》,原章节标题:《“老爷”和“相公” ——由称呼所见之地方社会中的阶层感》,作者:岸本美绪,头图来自:《海上花》
在古装影视剧,我们常能听到“老爷”这个称呼,富商、官吏、地主,在剧中都被称作老爷。1921年,鲁迅所写的《故乡》中,多年未见的闰土也称“我”为“老爷”,“老爷”这个词把“我”与“恭敬的”闰土深深地区隔开来: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老爷”作为一种高级尊称,是明代中期才开始出现的,这个词的背后是封建社会中的阶层问题,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著称的历史学家岸本美绪观察到了“老爷”这个词的演变,在《风俗与历史观》中,她详细梳理研究了明清时代随笔等作品中关于称呼的记录,为我们了解明清历史提供了一个有趣且琐细的视角。
“毫无疑问,'老爷'等称呼是认识这种势力的重要媒介之一。称呼某人为'老爷',不仅表现了对对方的恭顺态度,而且也向周围的人表明自己已经认识到了对方的势力。人们在听到他人称某人为'老爷'时,也就认识到了此人的势力。而一旦认识到其为有权势的人物,自己也就会随之对其表示恭顺。本文旨在探讨这种依据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形成并不断变化的明清地方社会的阶层关系的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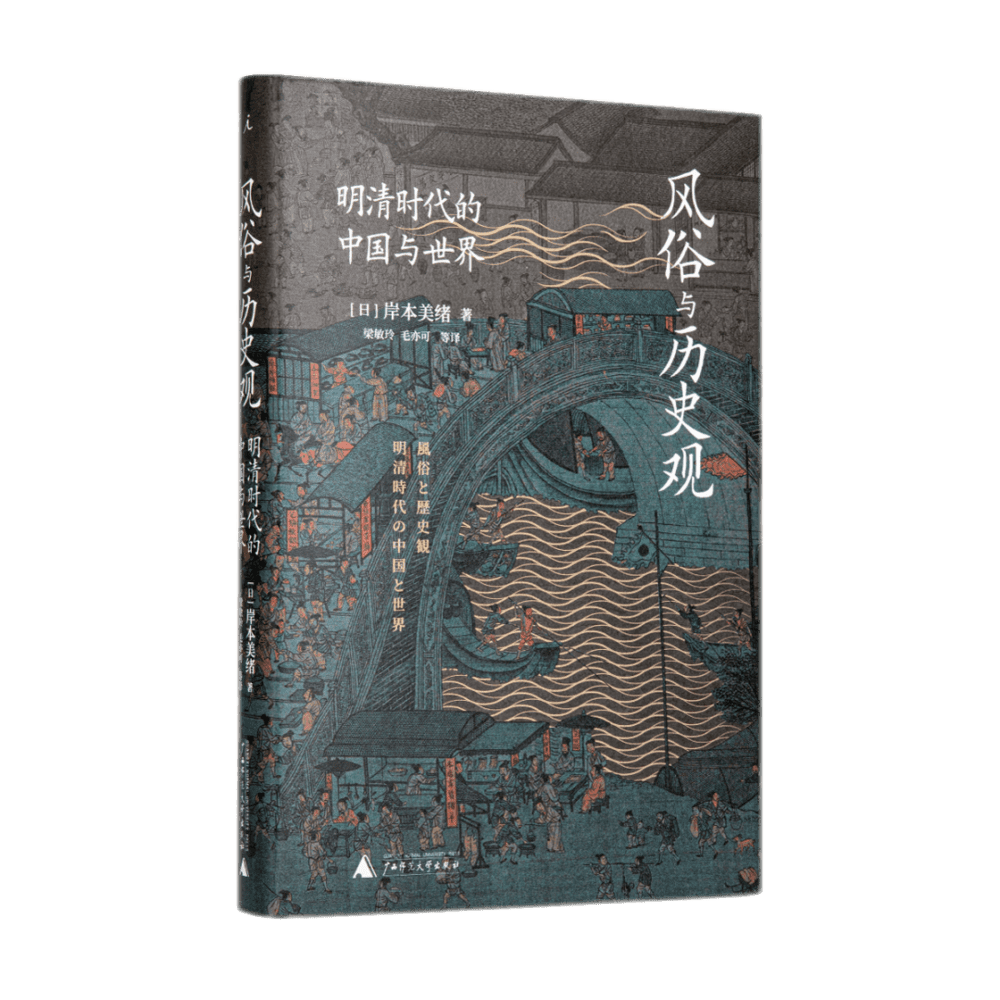
欧洲人看到的“Louthea”
在晚明来华的欧洲人留下的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Louthea”(即老爹)一词。这些早期的观察者对于科举、官僚系统仍缺乏正确认识,因此关于“Louthea”也无法对其科举、官僚系统的制度背景有充分的理解。虽然他们缺少理论性的整理,但正因如此他们在自己的记述中,将当时中国南部老百姓使用的“Louthea”一词所包含的语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中,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就这样记录了1550年前后的华南见闻。
老爷就是我们语言中的“先生”(senhor)。当他们有人呼叫仆人时,仆人答道“老爷”,好像我们说“先生”......服务于国王的重大司法案件的,是由学识经过考察而后产生的官员;但为较小的事服务的,如陆、海的尉官,警长、巡尉、税收官等,在每座城,当然也在这座城,都有很多,是任命的,向大爷要下跪,尽管别的老爷的帽子和名字跟他们—样。
伯来拉将“Louthea”理解为官吏的一种“称号”,是与官带、乌纱帽之类表示身份特征的事物紧密联系的称号。不过,科途出身的上层“Louthea”与未经科考(推测此处应指那些胥吏出身的人物)的下层“Louthea”之间,在实权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上层“Louthea”所享有的权利也给伯来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里应该知道老爷是如何受服侍和敬畏的。如在公众集会,他们一声吆喝,所有公家仆役都吓得发抖......老爷身后有些人拿着牌子,牌子挂在棍头,写着他们跟随的老爷名字、等级和官位。老爷后面他们还拿着与官位相称的伞。
除伯来拉外,根据加斯帕·达·克路士留下的1556年前后的见闻录而编辑成的记录中,也同样能找到“每个在中国据有职位,由皇帝任命的军官或官员,统称老爷”的描述。可见作为当时中国南部用来称呼官僚阶层的当地语言中,欧洲人首先听到的是“Louthea(Louthia)”一词,而官员们所拥有的势力和威信也随着“Louthea”一词印入他们的脑海。

然而,当时欧洲人留下的有关“Louthea”一词的资料信息大抵比较粗略,亦未能对这一语汇的用法提供详细说明。故此,笔者将通过明末清初的地方公文、随笔及戏曲小说等中文史料来管窥“老爷”的用法。
另外,利玛窦曾指出“所有的军职或文职大臣都称官府,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虽然他们的尊称或非官方称呼是老爷(Lau-ye[老爷]或Lau-sie[老爹]),意思是指主人或父亲”,即“老爷”同“老爹”的含义相同。但就中文史料中的使用方法看,华南地区多用“老爹”,而在江南等其他地区则使用“老爷”的情况更为普遍,因此,笔者认为这两者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域上。
被称作“老爷”之人
就明清时代的随笔来看,“老爷”这一尊称的指涉范围,并非全然与“官”涵盖的范围相重合。晚明清初松江人的曹家驹在《说梦》第二卷中这样记述道:
昔年乡宦,凡进士出身者称老爷,以一榜得官者称老爷,若明经如黄仁所(名廷凤,字孟威),官至云南大理太守,仅称老爷而已。近自援纳之例大开,而腰缠五百金,从长安市上归,则乘舆张盖,竞称老爷。
另外,清代中期的常熟人王应奎也在《柳南随笔》卷五中称:
前明时,缙绅惟九卿称老爷,词林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今则内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称大老爷矣;自知府至知县,称太老爷矣。又举人贡生俱称相公,即国初犹然,今则并称大爷矣。此就绅士言之,其余称谓之僭越无等,更非一端也。
尽管这两则记载的内容并非完全一致,但两者都认为“老爷”的称呼原本并不用于所有官员,而是用来指称在科举功名或官职上处于一定级别以上的人物。这些记载颇具意味地显示了时人按“尊贵”程度将官绅区分开来的标准十分微妙,但同时又相当明确。
不过,他们都指出,这一称呼已逐步脱离了本来的用法而被滥用。特别是一如曹家驹所描述的那样,那些靠捐纳获得官职而自视为老爷的人往往成为世人揶揄的对象,比如19世纪中叶的黄钧宰在其随笔《金壶戏墨》卷一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则闻自友人的故事:
又一人援例得职衔,章服而出,四顾其仆曰:此后勿称相公,须称老爷。仆不听,某正色曰:我不与汝戏言,汝不称,自家罪过。
另外,虽然曹家驹等人都将“老爷”的指称范围限定在官僚上层,但是《桃花扇》《清忠谱》等明末清初的戏曲小说类的文学作品在使用这一称呼时就未必按官职、功名而作细致区分,在平民称呼包括文官武官在内有官场经历者的场合,一般都使用“老爷”一词(而且,甚至也有一介平民被称呼为“老爷”的例子。)

而《儒林外史》则颇有趣味地将“老爷”这一用语等同于举人。穷书生范进通过童试进学后决心去参加乡试,并为此向丈人胡屠户开口借赶考旅费,不料却招来胡屠户的一顿臭骂。在这一场景中,胡屠户有如下一段台词:
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
这里,通过童试成为生员,称为“中相公”,而通过乡试考上举人,则称作“中老爷”。虽然无法确定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当时的普遍认识,还是作者特意借此来强调胡屠户的头脑简单、性格粗野,但若就清末山西人刘大鹏的记载来看,一旦成为举人即可被称作“老爷”,在清代已成为一般的风俗。“乡试场中号军称士子皆呼‘先生’,会试场中号军称士子皆呼‘老爷’。名分之不同有如此者。”即尚未担任官职的举人会集会试考场时,都已被称作“老爷”。
如上所述,自晚明至清代,“老爷”一词作为对官绅的尊称被广泛使用,其适用范围也未必有明确限定,可指上层官员、普通官员,也可指举人以上的科举人才,其用法根据时期及地域的不同而各有差异。
不过,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老爷”并不是一个可随便用于任何人的称呼,实际上,人们能够强烈地意识到那些理应被称为“老爷”的人与其他人在名分上的差异。
称呼“老爷”之人
在考虑“老爷”一词的用法时,不仅应注意被称呼方的阶层状况,同时也需要注意称呼方所属阶层。
比如在《清忠谱》中,一般老百姓虽然称呼文震孟为“老爷”,但生员赵伯通却不以“老爷”称呼文震孟,而称呼他为“老先生”。关于“老先生”这一称呼,据16世纪的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描述说:“京师称谓极尊者曰老先生,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门生称座主亦不过曰老先生而已。”
而在17世纪末的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一中记载称:“京官旧例,各衙门称谓有一定仪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称老先生……自康熙丙子(1696)祭告回京,见闻顿异,各部司及中行评博,无不称老先生者矣。”可见,原本仅用于官场部分范围内的这一称呼,自17世纪末起逐渐被广泛使用。
“老爷”这一称呼的使用,不仅与被称呼方有关,同时也与称呼方的地位紧密相连。生员以上的读书人之间的相互称呼的习惯是相当复杂的,这里,仅举例就平民使用的“老爷”等带有“爷”字的系列称呼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清忠谱》中,生员及民众聚集西察院向地方官请愿时,生员同普通民众使用的称谓各有不同。
王节等众生员:“老……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周……周铨部居官侃侃,居乡表表。如此品行,卓然千古。蓦罹奇冤,实实万姓怨恫。老公祖,老父母,在地方亲炙高风,若无一言主持公道,何以安慰民心?”
颜佩韦:“青天爷爷呵!周乡宦若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
生员台词中的老公祖是指苏州知府,老父母则为吴县知县。而老百姓对这些地方官的称呼却成了“青天爷爷”。此处老百姓或许是为了寻求特殊的公正裁决,因而未使用“老爷”,而改用了“青天爷爷”。然而,当巡抚出场时,称呼又发生了变化。
群众:“宪天爷爷,若不题疏力救周乡宦,众百姓情愿一个个死在宪天台下。”
知县、知府:“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言。民情汹汹如此,还求老大人一言抚慰オ是。”
可见,带有“爷”字系列的用语,原则上是普通民众称呼官绅时用的。地方官在称呼上司时,则使用“老大人”等称呼。

然而也并非没有例外。比如,拥有官职或科举功名的人也有称呼官绅为“老爷”的情况。王夫之的《识小录》称:“首领官(地方衙门的辅助官)由科贡出身者,称堂上官(知府、知县等该衙门的长官),亦但曰大人。唯吏员出身者有老爷之称。”即使双方都是官员,但若一方非科途出身而为胥吏出身的,则亦称呼其长官为“老爷”。
另一方面,也有未获功名的读书人面对官员是不以“老爷”相称的情况。比如,在《桃花扇》出场的画家蓝瑛,既是个没有身份的平民,又是个被称作“山人”而无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他在面对上文提到的武官张薇时,一方面强调自己是个“草莽之臣”,另一方面则用“老先生”称呼张薇。
普通民众在称官僚“老爷”时,一般都以“小的”自称。而自认为士人之人,在称官绅为“老先生”时,则以“治生”“治民”(这些是在面对管辖当地的地方官时使用)或“晚生”等自称。值得注意的是,“老爷”的称呼不但体现了被称呼方的权威,同时也反映出了称呼方自身的地位。
“老爷”之称谓的开始
自晚明至清代使用十分广泛的“老爷”这一尊称在15世纪以前,其使用并不那么普遍。根据赵翼的说法,“爷”“爹”原先都是对父亲的称呼,直至唐代才开始用于称呼达官贵人。但笔者认为,明初以前,作为对官绅的尊称,“相公”“官人”或“大人”更为常用,使用“老爷”等含有“爷”字称呼的情况尚不多见。
究竟是何时开始使用“老爷”来称呼官绅的呢?这是颇为有趣的问题,由于目前对资料的调查尚不充分,只能就现已掌握的内容作一阐述。
从记载着书信和诉状等书写格式的日用类书中,可以看到从元到明官僚的称呼方面的若干变化。元代以及沿袭元代内容的日用类书这样记载道:“且如左右相(平章)则云:某官国公。左右丞(参政)则曰:某官相公。以次台部州县官员,当酌轻重,不可过呼。”
朝官、路冠以上“并称为相公”。而一般民众向官府提交的诉状例文中则有“今蒙县官出具榜文”“今蒙县官指挥”的记载。这不仅表明当时称呼高级官员为“相公”,同时也说明了在诉状等公文上却并没有“老爷”这样的用法。
但与此相对,在晚明的日用类书中,作为官吏称呼的“相公”一词主要用于经历、仓官、医官等属官,或千户、百户级别的武官。在诉状的范本中有这样的记录:“某都某人等、今当本县老爷处承认”“有县坊某隅某总居民某今当本县老爷处承保”,可见被称呼为“相公”的社会层次有所下降,而且诉状等公文中“老爷”一词也开始普遍使用诉状公文中所呈现的这种地方官的称呼变化,不仅表现在日用类书中,从实际公文中也能得到证实。
笔者所掌握的能反映明初诉状格式的史料并不多,不过在洪武帝的《大诰三编·朋奸匿党第三十七》里,就有贿赂知县的民众称知县为“相公”的例子。《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收录了1600年以前的诉状和禀词,现将其中的地方官称谓总结如下:
成化五年(1469)——“祁门县大人”
嘉靖五年(1526)——“青天太爷”“爷台”
万历五年(1577)——“本县老爹”
万历十年——“县主爷爷”“爷台”
万历十一年——“大父台”
万历十四年——“爷台”
万历十八年——“本县爷爷”
万历二十一年——“县主爷爷”“府主爷爷”“青天爷爷”
万历二十五年——“县主爷爷”
由于15世纪以前的资料有限,用词的变化并不甚清楚。然而可以确定的是,1469年的公文中用于知县的称呼为“县大人”,至16世纪以后则改成含“爷”字的称呼。至于万历十一年的公文之所以未使用“爷”字,是由于公文作者是当时的乡绅(原任嘉定县训导)或贡生、监生等人。此后,到了万历末年,在有关土地过户的木板印刷的证明书之类的文件中,往往载有“〇〇都〇图遵奉县主爷爷为攒造黄册事”等字样,可见“爷”字称呼作为公文用语已经固定化了。
从戏曲小说中的一些例句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以“老爷”来称呼官僚这一用法出现在晚明以后。虽然不敢说元曲中将官僚称作“老爷”的例子绝无仅有,但至少使用“相公”“大人”的情况更为普遍。《窦娥冤》《铁拐李》《合汗衫》《酷寒亭》《金钱记》《盆儿鬼》等戏曲中出场的楚州太守、廉访使、提察使、府尹等官员,均被仆人、胥吏、普通民众以及士人唤作“老相公”“相公”“大人”或“官人”。

当然,也有称呼“老爷”或“爷爷”的情况,谨举例如下:首先是仆人或差役称呼担任官职的主人,例如,差役张千就以“爷爷”等来称呼自己的主人,而对他人则用“老爷的吩咐”等措辞,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酷寒亭》《金钱记》《盆儿鬼》);其次是公堂上原告或被告向堂上的法官致谢或哀求,例如,“谢青天老爷做主,明日杀了窦娥,才与小人的老子报的冤”(《窦娥冤》),或“告你个青天大老爷,替我这个屈死冤魂做主”(《盆儿鬼》),等等;最后是当衙役因罪行被清廉的监察官员揭发而慌乱求饶时也会使用,如“爷爷不敢了也”(《铁拐李》)。
以上各例中的“老爷”的使用,体现了称呼方和被称呼方之间鲜明的从属或依存关系。要全面探讨元代的官僚称呼法,固然还需作更多的考察,不过即使根据以上的论述,亦应该可以认为:作为对官僚的称谓,“相公”“大人”等较“老爷”更为普遍,而使用“老爷”的场合则特别强调称呼方的从属性及依存性。
晚明以后,“老爷”作为民众对官宪的尊称,使用开始普遍起来。15世纪后半期出版的《成化说唱词话》中,老百姓称呼著名的清官(知府)包拯时仍然大多使用“相公”。相对的,自16世纪末期以来十分流行的公案小说《廉明奇判公案》《新民公案》《律条公案》《明镜公案》及《详情公案》等,作为地方官称谓的都是“老爷”等含有“爷”字的称呼。
这种称谓的变化何以发生在这一时期呢?作为官宪的尊称,“老爷”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在称呼使用方法乃至与人际关系相关的社会心理上出现的诸多变化中的一部分。
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五就记载道:“松江十来年间,凡士夫年未四十即称老翁,奶奶年未三十即呼太太,前辈未有,此则大为可笑者也。”而范濂的《云间据目抄》卷二则有“缙绅呼号,云某老某老,此大夫体也。隆万以来,即黄花孺子,皆以老名,如老赵、老钱之类,漫无忌惮”的记载。可见在16世纪后半期的松江府,出现了“老”字泛滥的现象。
“老”和“老爷”的用词,与本义为宰相的“相公”,以及直截了当表示官僚的“官人”等尊称相比,更具有一种体现存在于家庭间的亲密感,同时似乎也伴有一种基于血缘性的尊卑长幼关系之上的直接支配的从属感。
“老爷”一词原本就是与这种晚辈对血缘性家长以及仆人对拟制血缘的主人具有从属感联系在一起的。浙江海盐县人钱薇是嘉靖十一年(1532)的进士,其弟钱蓘所描写兄长的逸话29就表明了“老爷”一词所体现的家庭内部秩序与官民秩序间的微妙关系。
余兄薇,字懋垣,事兄恭谨,始终如一。初授行人,回乡,人及童仆皆以二老爷称之。因谓曰:“尔之称我,岂不宜?但余有兄在,既以是称我,何以称我兄?我受此称,亦岂能安当?如前日可也。”家庭逊让,一如未第时。
也就是说,“老爷”的称呼并不是官场地位或科举功名简单的机械性反映,而可能与家庭内部秩序相抵触。可以说,在称呼官员为“老爷”的习俗兴起之初,当时人也是在怀有若干抵触情绪的情况下勉强接受的。
笔者曾讨论过,明代末年的16世纪,带有血缘性尊卑感觉的人际关系网已超越了实际的血缘关系而广泛地蔓延至整个社会群体。为结交权势而制作的名片上的自称,在表现与结交对象关系亲近的同时,也多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卑微。这一屡遭有识之士嘲讽的现象实已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特征。
可以想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老爷”“爷爷”这类具有亲昵的从属性血缘称呼,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和地缘框架,而普遍地施用于官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岸本美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