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讲述者:安安,主播:寇爱哲,制作人:Judy,头图来自:电影《美国女孩》

我们学费很贵,一年光学费就要 3 万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活费储蓄账户,生活老师平时会采购一些肥皂、洗衣液这种生活用品,再按照商品定价从我们的账户里划账。学校规定学生自己手上是不允许有一分钱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不允许我们吃任何零食。他们有一种观念,零食里全都是色素,是有毒的,所以我们每次返校首先要被搜身、搜行李,不能有任何零食夹带。
每天有老师统一做大锅饭,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量总是不太够,导致大家会去抢。
你会看到一个很离谱的画面:在一个总是在宣扬“仁义礼智信”、“兄友弟恭”的地方,大家每次吃饭时却都是像原始人一样去抢,大的绝对不会让着小的,学生也绝对不会让着老师。有些男生如果排在你前面,他还会把菜里所有的肉全部挑走,不会给后面的人留一点。
因为很饿,学校又不让吃零食,我们宿舍里面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有时甚至会商量去食堂偷东西吃。我记得有一次,食堂大叔也是比较体恤我们几个女孩子,他偷偷地拿了一瓶老干妈给我们,我们就把它藏在了宿舍里。不过很尴尬的是,我们没什么可以就老干妈的东西。
某一天晚上我就空口吃了几口老干妈,第二天就开始疯狂呕吐,可能是太油腻了。
3. 打手板
在书院,我的确不用再学习数学了,可没想到的是,这里有比数学更可怕的东西。
我们上课就是读四书五经的原文,再没有其他内容。
老师给我们灌输的观点就是“反复地、大量地、老实地读经”。我们每天读、背,当一本书读到 100~200 遍的时候,老师就会要求我们背诵,如果背诵不下来,那就要打手板。
我们这种学校里一般会有一个明星老师,这个老师比较会“忽悠”,就会受到家长的追捧和崇拜。基本上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也会特别听 TA 的,所有人都众星拱月地围着 TA 转。
我们当时也是有这么一个人,因为他在易经算卦方面有一些学识,所以我们就叫他“算卦老师”。
他特别喜怒无常,我感觉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折磨我们。
他会给我们开各种各样的批斗会,我们可能会因为很小的一些事情就受到批斗。比如偷带零食被老师搜出来,那就是“大罪”。又比如我们有固定的早餐时间,如果那个时间你还没有出现在食堂,也会被批斗。
我们的批斗会会在一间大教室进行,一般由“算卦老师”来主导,其他老师做辅助。他们会喋喋不休地数落我们所谓的“罪行”。没犯错的学生坐着听,犯了错的学生要站着听,并且要被打几十次手板。
书院的手板是一种黄色的厚竹板,长度大概有 20~30 厘米,打人的声音可能听起来轻,但如果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力度去打,还是挺吓人的。

在打手板的时候,因为我是低血压,心理上的恐惧会导致全身发凉,控制不住地发抖,所以每当老师过来打我时,基本上只打个几下,我就晕过去了。
但每个人至少几十下的手板份量是必须要打足的,像我这种中途会晕过去的选手,老师会让我先蹲在地上缓一会儿,等我感觉好一点了,再继续站起来受罚。
我在书院的时候特别绝望,而如果心理上很郁闷,其实身体上也会有反应。当时我刚过去的时候,连续便秘了 20 多天,从那之后,我的肠胃就彻底落下病根了,再也没有正常过。
即便我们生病了,老师也是不会管的。他们尤其抵制西药,因为他们觉得西方的一切东西都是坏的、有毒的,就像零食一样。
4. 被孤立
书院的暴力就像个黑洞一样,没有尽头。
因为没有手机、没有钱,甚至出了校门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所以我不敢从书院逃跑。可是我也觉得,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不服从也好,我真的不想让自己彻底掉进这个黑洞里。
广东的夏天很热,虽然我们寝室里有电风扇,但是电风扇是由老师掌管的,我们不可以私自打开。有一天在午休时,我们热得受不了,偷偷打开了,结果就被巡查的老师发现了。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被要求站到操场上去被烈日暴晒,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面对这种惩罚,我其实一开始是不服的,但是老师会一个个把我们“驯服”。很多同学会为了之后少受一点折磨而选择服从、不再反抗。我当时是坚持到了比较后面,但也随之感到更加孤立无援。
因为同学们都已经“缴械投降”了,老师也就没有再那么针对他们,反而是我因为还没有“投降”,所以老师会带动其他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孤立我。
有一天我们在午休的时候感受到了轻微的晃动,所以从那次开始,我们学校就想着搞一次地震模拟逃生演习。在又一次午休的时候,我当时在床上蒙着被子哭,同时用偷带的一个 MP3 听歌,所以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突然,我感觉周围“窸窸窣窣”地不太对劲,就掀开被子一看,宿舍人都跑光了。我想是地震了,也赶紧跑了出去,然后发现大家都在操场上。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只是一个地震演习,并不是真的地震了。
当时“算卦老师”就对我露出了一种非常冷漠、嘲讽的眼神和笑,仿佛在告诉我,“看,就算是真的地震,我们也不会有一个人叫你起来的。”

在书院里,我们只能在父母生日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我当然有跟爸妈打电话说过这些事情,我希望他们能让我回去,其实就等于求救。但我爸妈不太相信这些事,而且觉得“我都把你送过去了,学费交了,你现在还搞什么幺蛾子?”
他们会让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自己。
他们还会对我说,“那个决定不是你自己做的吗?我当时不是问了你的意见吗?”
在我看来,14 岁的自己是一个很蒙昧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去走这样一条路对今后人生造成的影响。我觉得他们作为成年人应该是知道的,但在知道的情况下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没有办法理解。
5. 蔓延的暴力
我记得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她有一些自虐倾向。她会把自己的拳头伸出去大力地捶墙,捶到会哗哗流血的程度。
而我其实在那段跟老师对抗的过程中,因为又不服、又害怕,我自己也有用指甲钳上面的小刀片割过手腕。

我们内部也会互相施暴,我自己就参与过一次。
那次是因为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怀疑有一个小孩子偷了我们的零食,而且是翻了我们的衣柜偷的。
我们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还是把那个小孩叫过来,问是不是她偷的。她虽然说不是,但说着说着,她却给我们跪下了。
她说,“不是我偷的,但如果你们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我们当时觉得,“你都这样了,那肯定就是你偷的。”
于是,我们轮流上去扇她巴掌,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对别人施暴。
但是说实话,我那时隐隐地觉得,施暴这个动作本身是“爽”的,是很解压的。
那个时候真的比较扭曲。
6. “我真的很想学习”
在万事诉诸暴力的书院里,我的喘息时刻是在被窝里用偷偷带来的MP3看电子书。尽管 MP3 的屏幕很小,一次只能看十几个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当时我们不允许私藏任何课外书,所以我们和外界的知识是完全隔绝的。
但“算卦老师”会带一些书到学校来,比如《四书章句集注》之类。他也有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籍,当时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好玩的。我记得有一次上课罚站的时候,他让我站到教室后面去,我就偷偷地拿了一本他的佛教小册子夹在自己的书里面,在后面看得特别开心。
我觉得我那时转变的一个契机,其实也是因为那个阶段有一种对于知识的天然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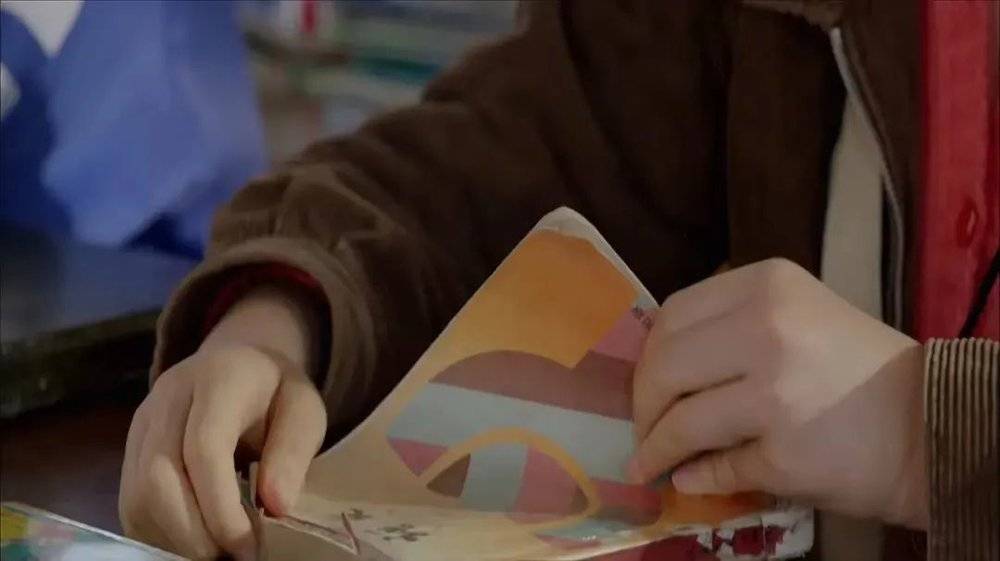
“算卦老师”会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教法,他会多多少少解释一下我们读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因为想要学习知识,我开始对他态度缓和了,也会帮他做一些事情。
因为他是明星老师,我们是要给他办生日会的。我会给他做生日会的主持人,提前安排大家排练各种各样的节目来给他庆祝。
我也会假公济私,在当主持人的时候,顺便跟他说一些“表明忠心”的话,希望他放下对我的成见。
他还搞过一些奇奇怪怪的比赛,有一次是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是在操场上无限地跑圈,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第一。
我记得我跑了 30 多圈就赢了。
基本上在他举办的所有比赛里我都拿了第一,所以他会把我当做是最好的一个苗子,我跟他的关系也变亲近了。我知道他要组建一个七八个人的小班,他会在那个小班里教授更多的东西。而我为了进入那个小班,也变得更加“努力”。
不是有一个词叫“斯德哥尔摩”吗?其实后期的时候,我甚至对他有一点好感。当时确实是挺奇怪的一种状态,我们每天都围着他、哄着他、吹捧着他,只要把他哄高兴了,他就能少发一点火,多教我们一点知识。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战战兢兢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变脸。
7. 更孤独
大概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胆子已经大了一些,于是偷偷带了一部手机到书院。
有一天,老师发现了我的手机,并且把它没收了。当时我很恼火,就怂恿了另外一个同学陪着我去老师办公室把手机偷回来。其实这样做风险挺大的,但当时那个同学还是选择陪我去了,我们俩一个望风、一个偷,就把手机拿回来了。我感觉她蛮仗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共患难的朋友了。
但后来老师会让我协助他们做一些事务,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同学对我的态度就已经变了,因为她觉得我跟老师站到一个阵营去了。
可我当时也很无奈,老师让我做,我也不能不做。但后来我所认为的“友谊”真的就变味了。
当时在书院里交朋友给我的感觉是若即若离,好像上一秒我还感觉我是 TA 的朋友,下一秒就会发现,人家并没有把我当朋友。
成为老师的“亲信”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更孤独了。上一次可能是因为我和老师在做对抗,所以大家要对我避而远之。这一次则是因为我和老师走得太近了,甚至要帮他去盯着同学们,所以大家又一次孤立我。
我并没有因为在书院的时间变长、因为适应了这种生活节奏而觉得不痛苦。
我一直都很痛苦。
学校一般不太愿意让家长来,可能觉得这会“扰乱军心”,让孩子的心情更加不稳定。可我真的很想我爸妈,上课和休息时间经常都在掉眼泪,都在幻想,他们到底会不会来。
但我爸妈就真的从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8. 离开书院
当我在书院待到第三年的时候,我的同龄人也都在上大学了,于是我就又尝试着跟我爸妈沟通,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也觉得我在这里可能呆得差不多了,于是同意了我离开书院。
离开书院之后,“算卦老师”还找过我一次。他想让我去他的一个易经主题的夏令营当助教,并且会给我一两千元报酬。我虽然不太想跟他有更多纠葛,但冲着钱的面子上,我就去了。
结果才去了三五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天晚上,其他学生都从教室回到寝室去了,还剩下一个学生在教室学习,我就跟他搭了几句话。就在那个时候,“算卦老师”突然破门而入,开始质问我们俩在干嘛,为什么不遵守作息时间规则。
当时我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让我回到了当年被他管控的时候,我的所有生理反应都和曾经被他打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浑身都冷、都抖,心慌得不行,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都要晕过去。
在那个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尽管我已经离开他了,但这个人对我的阴影还在,我没有办法在任何情况下与他共事。
第二天早上我就打包行李走了,钱也不要了。从那次之后我也明白了,书院的人会让我条件反射般地产生恐惧的心理,我不能够再和他们有任何接触。
9. 他们只想要我听话
我和我爸妈关系一直都不好,包括现在。他们对于当年这件事情的定义都是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都问过了,是你回答说你可以去的。”
他们还会说,“你学费很贵,我还坚持供你读,我对你已经付出了很多,你不能再来责怪我们。”
这些中年人还有个毛病,他们太希望孩子可以无脑听话了,凡是被送进那种地方的孩子出来之后都会很木讷,不太会反抗了。
我爸妈会觉得这样很好,进去之前那么叛逆,怎么回来就变得这么懂事了。
他们不需要你过得幸福,他们需要你听话。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根刺,要拔掉这根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认为是我的错,他们也不认为是他们的错,我们也不可能给对方道歉,但这件事情也不可能真正从我心里消失。
我记得特别清楚,刚离开书院的那几年,我还是活在阴影之下,经常会回想起那些事情,然后就会哭、会抓狂。
那几年我会像祥林嫂一样,可能刚认识没几天的朋友,我就会开始给对方讲这件离奇的经历,企图博得别人的同情和安慰。
但我觉得这样的自己其实是很可悲的。
后来我就开始慢慢告诉自己,“不要再说了,也不要再回忆了,往前走。”
我会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企图给自己疗伤,但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因为我已经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中,起码它是一个正常的世界,大家都在阳光之下,每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都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和选择的权利。
这让我觉得很安全。
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模拟游戏,开局我已经选错了,参数已经这样了,我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尽可能地再去好好生活。
写在最后的话
我们想给安安的故事留下一个更有希望的结尾,但事实是,在今天,还有很多像安安一样的经历过、或者正在遭受着书院折磨的年轻人,他们被困在以教育为名或是以爱为名的暴力阴影中,这些暴力既不是偶然更不是少数,而是家庭、机构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合谋。
如今,豫章书院的受害者们还在继续上诉,而我们除了围观和叹气,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参考资料:《“豫章书院”案一审宣判!创办者以非法拘禁罪获刑2年10个月》,中国长安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讲述者:安安,主播:寇爱哲,制作人:J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