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面上,我好像是没根的,飘着的,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可依赖的东西。
但这就是我想要的。
北京到底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反正光『北京』这两个字就足够迷人,我就想来!
——《流浪北京》中张夏平说的话
以上这段话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憧憬,然而你可能会想要反驳她说的话,毕竟如今大多数年轻人都想要逃离北上广,到二三线城市去安放青春,在又一个时代的冲击之下,那种一个劲往北京或者是其他大城市冲的劲头,我们似乎已经快要忘记了。
的确,这句话实际上来自那个并不遥远却又十分模糊的八十年代末,出自一位北漂的自由画家张夏平,她是吴文光导演在 1990 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流浪北京》中的一位主人公。
在很多评价之中,吴文光对于中国「新纪录片」的意义,甚至相当于崔健之于中国摇滚。《流浪北京》被认为是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它记录了五个怀抱艺术理想的外地青年在北京流浪的经历,其中包括作家、画家、戏剧导演和摄影师,吴文光也借此间接诠释了自己作为 80 年代北漂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状态。
如今当人们谈及 80 年代,常常用「理想主义」加以概括,它热情、真诚、充满朝气。80 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新鲜事物每一天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空气的松动首先从这个国家最中心的城市开始,伴随着新思潮的来袭,涌现出了一批追求自由、敏感而勇敢的艺术青年,他们自愿从体制内离职,流浪到远方,背井离乡寻找水源。
对于 80 年代的青年来说,北京在他们心中,是那么生机勃勃、充满希望、无法被替代。
影片中那些已经渐渐消失的北京胡同平房与红白条纹的公共汽车都在提醒着我们,那是一个远去的、记忆中的北京,和当下的生活,以及大家对未来的想象,有着迥异的质地。
前段时间,我们有幸和吴文光导演聊了聊,他的影片和讲述,带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逐渐褪色的年代,带我们看了看那个时候,那些将艺术视为生命的年轻人们的真实世界,希望它或多或少能够让你回忆起一些充满激情的日子。
--
我叫吴文光,1956 年出生,今年 67 岁,已经在北京待了三十几年,老家是云南昆明,我出生在那里。
那个年代的人跟今天很不同,都在主旋律里边,跟随着大潮流走。当时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吴文光十几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正统的青年,服从组织分配,积极要求下乡,甚至还加入过红卫兵。
但是,他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正好赶上了 80 年代新思潮的来袭,作为有艺术理想的青年,他想从看得到尽头的生活中挣脱出来。
 ■ 图 / 吴文光,1993年,李晏摄
■ 图 / 吴文光,1993年,李晏摄-1-
我要去流浪
1982 年,我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后分到了一个在中学当语文老师的工作。工作干了一年以后,我就想换一个环境,去一个更远的地方生活。
在大学进中文系之前,也就是我还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我就是文学的狂热分子,当时的愿望就是当作家,发表文章,写作是我的精神追求。
艺术并不会随着时代更迭被彻底淘汰,它永远都会有人喜欢,虽然不一定是很多人,但总有一些人会喜欢。
80 年代初是一个时代的巨变,铁门打开,很多国外的东西涌进来,人们有机会知道很多新鲜的事情,高更、杰克·伦敦、卡夫卡……还有 60 年代、70 年代玩嬉皮摇滚的那一波人,对我这样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不能再循规蹈矩,不能只穿中山装,我要穿牛仔裤,要留长头发,要追求这种新的东西,追求自由。
我生活在昆明这个小地方,到处都是熟人,但我偏偏有一种浪漫主义情结,喜欢去一些陌生的远方,觉得那才代表着梦幻。
在云南昆明的一个文学小圈子里边,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叫陈杰。因为喜欢文学,喜欢卡夫卡,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卡。他也写过一篇小说,叫《铁轨伸向远方》。从小说的名字就能看出我们对远方的渴望。
于是不久后,我就自己开始了流浪。
那时候北京是我们的首选,它对青年人非常有吸引力。地下文学、绘画、音乐,还有电影学院,都只有在北京才有。北京那时候是真正的「唯一」,现在只是作为首都的唯一,作为政治中心的唯一,而已经不再是作为文化中心的唯一了。
1988 年,我坐了三夜绿皮车硬座到北京,没有规划,只攥着一个杂志编辑朋友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甚至还只是对方单位的电话。
我身上带了大概 100 来块钱,已经是我一两个月的工资了,没带什么行李,只想先找个地方住下。
「蹭住」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词,我那会儿反正就是东住一下西住一下,到处蹭住,头几个月根本就无所事事,但是整个人非常兴奋。
那时候北京大学东门外那边的胡同,跟北京二环的胡同很不一样,那儿的胡同似乎更有格局,通常是一家人盖了好几间房,中间还带个院子,然后出租出去几间,房主可能就留一间主卧自己住,也有可能根本不在那住,把整个院子都租给不同的人。这样的一间房,最便宜的一个月只要 30 块钱。
租在胡同里的人,都是从外地来的,而且还没有单位。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就是有的吃、有的住。我们和一群卖菜的、捡破烂的人,保姆等等这样的群体住在一起,像我们这样「搞艺术」的也有,但是非常少。80 年代的北京,并不像后来经历打工潮后有那么多的外地人,后来大家熟悉的圆明园那一带的艺术村,实际上是在 90 年代以后才形成的。
因此在当时流到北京的这批人,都可以说是真正的「盲流」。
这里吴文光提到的「盲流」一词,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到了,但在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专指那些脱离户籍管理,以逃荒、避难或者谋生为理由,自发迁徙到其他城市的人,全称叫「盲目流动人口」。他们没有当地户口、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居无定所。
这个词不怎么好听,它让人自然联想到「底层人口」「破坏治安」这些词。
但「盲流」也是八九十年代来北京流浪的青年艺术家们用来自我调侃的一个词,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意识形态追求。他们觉得,当盲流意味着抵抗和自由。就像片中的自由摄影师高波说的一样,他喜欢当盲流,他希望自己以后还是个盲流,希望自己能一直是一个自由摄影师,拍摄他最喜欢的、最关心的事物。
到北京不久,吴文光就在北京的胡同里,和几位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有着很高教育背景和才华的「盲流」青年,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他们分别是:自由作家张慈、自由摄影师高波、戏剧导演的牟森、自由画家张大力和张夏平。
这五个人呢,之后都变成了吴文光《流浪北京》纪录片的主人公。
刚跟他们在北京认识的时候,虽然吴文光心里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是他觉得,既然大家都能在北京待下去,那他也一定可以,未来会是充满希望的。吴文光很兴奋,非常享受和老家云南完全不同的那种自由的文化氛围,几个人经常会聚在一起喝酒,谈天说地,畅想未来。
我记得想做摄影艺术家的高波,想去一些危险的地方做战地摄影,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奋不顾身,什么都愿意搭上。单是想象这种可能性,都令我们感到美好。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按我自己方式生活,我不要被约束、被困扰。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曙光到来,那就先走着再说,没准好运气就在后头。
在排练的时候,我总是有许多特别感动的时刻。像戏剧这样的东西,总能让我心里产生一种要哭的、幸福的感觉。戏剧它说到底就是一群人在一起,这群人中间有一种东西,他们要一起把这种东西传达给更多的人。
我们是一群选择艺术作为生活方式的年轻人。说到底,艺术就是生活方式本身。
——《流浪北京》中牟森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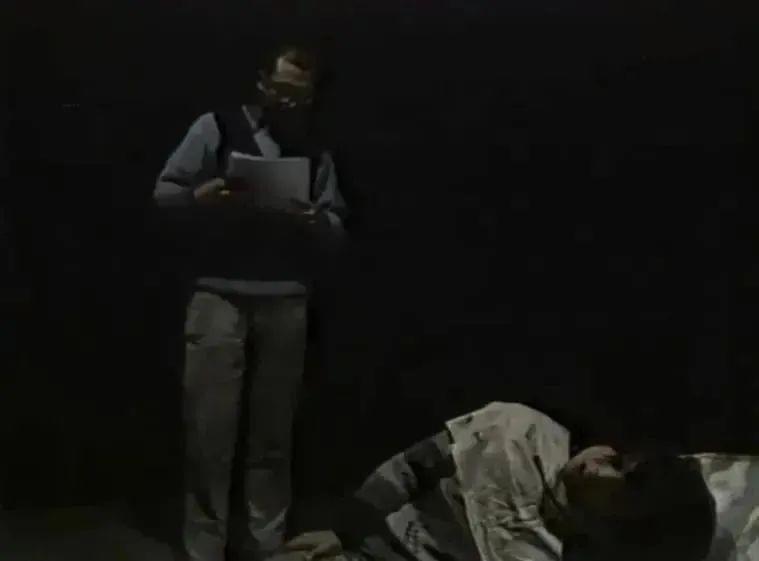 ■ 图 / 排练戏剧的牟森
■ 图 / 排练戏剧的牟森-2-
「飘扬的旗帜上也沾着粪便」
酒后的理想是浪漫的,但酒醒后的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在这些人当中,吴文光算是最务实的梦想家。他也很幸运,在来到北京两个月之后,就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摄制组的工作,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那时候依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在来到北京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盲流艺术家生活中一些被彩虹色泡泡覆盖着的破败生活切片,就开始浮出水面。
在吴文光的镜头里,张慈和张夏平在流泪,牟森从未停止过吸烟,张大力在叹气。牟森在片子中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等待着我们这群『盲流』的无非三条路:自杀、结婚,或是坚持。
 ■ 图 / 镜头前抽烟的牟森
■ 图 / 镜头前抽烟的牟森两个月后我就进了一个摄制组。这个摄制组有招待所和食堂,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再继续「蹭住」了,我的生活完全按照摄制组的方式前进了。
这个摄制组并不是我想要生活的全部,但是我可以去那里蹭拍摄设备,去拍我想拍的片子《流浪北京》。
要拍出什么样的作品当时的我心里完全是朦胧的,只是在跟这些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意思,我们也特别相似。因此,我想记录下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曾经的故事。
第一个镜头拍的是张慈。
张慈跟我一样来自云南,梦想写作,只不过比我小一岁,她辞掉了云南一个杂志社的工作跑到北京来,在北京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大多数是帮人写稿。
她的屋子进门两步就是床,屋子里拢共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非常狭小、凌乱。
我印象很深刻,她用铅笔在墙上涂涂画画了很多自己的印记,还贴了一张红布,上面写着:飘扬的旗帜上也沾着粪便。
这个家是我一手缔造的,去年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天凉了,秋高气爽,天空特别蓝,跟云南的差不多,我从来没在北京见过这么蓝的天。之前小杨说冬天要来了,得把门还有窗户给封死,不然风会进来。我当时没体会到,后来果真好多风刮进去,他就把自己的裤子剪碎,把窗户缝给补上,还弄来了好多的纸板跟木头,把它给封死。
——《流浪北京》中张慈说的话
 ■ 图 / 和平房院子里的大妈聊天的张慈
■ 图 / 和平房院子里的大妈聊天的张慈90 年代的时候你要去北京还可以办暂住证,但80年代末还没有暂住证这种说法,那时候你住北京就需要出差证明,即便是住在亲戚家里边,他们也要提前去跟派出所报告。
我们那时候没别的办法,只能干脆当黑户了,因此每次碰到来查户口的,都特别怕。
高波当时也是黑户,他告诉我,一听到敲门声,下半夜就担心得睡不着觉了。
当时的制度一方面很严苛,没有证明就不许你在这里;但另一方面漏洞也很大,那些警察执行公务的时候就是吓唬你,或者他们有时也会跟你说,暂时借两天住完就赶快走吧,别给他们找麻烦。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能稳定地生存下去,这样就不会有人下个月要赶我走了,我就不用把我的好多画搬来搬去了,我还没有汽车,也不会蹬仅有的一辆三轮车,就只能找朋友帮忙,但是他们都很忙。反正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稳定,能有充足时间去绘画,没有什么太奢侈的要求。
——《流浪北京》中张大力说的话
那时候北京的物价很便宜,几毛钱就可以吃个早餐,一个煎饼果子大概 4 毛钱左右,一个豆花或者豆浆也就 1 毛钱或 5 分钱。一天下来根本花不了一块钱。
我对豆浆价格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复兴门那一带吃早餐的时候,当时我吃的就是豆浆加油条。可能因为太挤,我看到前面一个人的豆浆撒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他们一个北京人,一个外地人,两人开始争执,甚至打起了架来。
北京人人高马大,外地人瘦瘦小小,然后那个北京人就骂外地人,说他傻帽,什么都不懂还来北京干嘛?
我认为绝大部分北京人都非常大气,但北京本地人的优越感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记得在我的片子里边,高波提到过他「蹭吃」的故事。「蹭吃」是我们在北京常用的手段,不仅能蹭到多些饭菜、多些口味,同时也能蹭到一种家庭的温暖。
如果你有个北京的朋友,他家里边有火有炉还有两三个菜,你去蹭吃一顿,比自己一个人吃开心很多。
在我拍的片子里边,张大力说过,那时候他兜里没有钱,每天早上起来就在想今天中午该去哪里蹭吃。
我们住的地方离北大特别近,这样有个好处,我们能用里头的食堂和澡堂。我们有时候会去里面洗澡,有朋友来就可以带他们去食堂吃饭,有时候外国人看到我们这样,他们都挺好奇,觉得挺好。好个屁,一点都不好
——《流浪北京》中张慈说的话
他们的生活水平都非常低,每个人谋生的手段都不一样。
高波会靠他的照片来接一些活,他还拍过挂历赚钱。
张大力没有办法靠卖画为生,就算能卖出去,也卖得很少。于是他就靠帮饭馆在玻璃上画饺子之类的装饰图案来赚钱。
所有这些咬牙挣扎的经历,都是希望自己所做的东西有一天能够被人认可,能够取得成功。
 ■ 图 / 骑车的张大力
■ 图 / 骑车的张大力-3-
也许,最好的艺术作品全是疯狂的产物
流浪北京 5 位主人公中的 4 位,虽然不像吴文光一样,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是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也并没有将务实完全抛在脑后,他们都在想办法接一些零散的活,将自己在北京的盲流生活维持下去。
但是有一个人不一样,她就是自由画家张夏平。可以说,她是那个年代理想主义青年的一个极端。她说,卖自己的画会让她非常痛苦。
在吴文光的镜头前,张夏平很快就「通了」,再来,她就「疯了」。
如果一个人要搞艺术,或者要搞一种真正和人心发生关系的东西,那就应该保持纯粹。如果缺钱,可以干别的来赚钱,让我卖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宁愿当叫花子,甚至宁可去卖淫,也不卖画。
——《流浪北京》中张夏平说的话
张夏平是我在云南的一个喜欢文艺的朋友。
她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也不接活,不屑于接活,她觉得自己能有口吃的、有个床睡就行。
她小时候在文艺学校学跳舞,后来把腿摔折了,就开始改拉小提琴,之后又到文工团里做舞台美术。画画是她喜欢的东西。
她很迷人,随手就可以画出一幅人物的素描。她的眼睛很深情,说话很投入,话里边也经常含着一种哀伤,一般喜欢文艺的男性都很难逃过她的一劫,所以都愿意帮助她。
她从来不租房子,甚至连吃饭都很少掏钱,都是蹭,她就是蹭吃蹭住的大王。
比如在画廊上、展览上碰到个聊得上天的人,如果知道对方有空的房子,她就会说自己的房子房东不让住了,她没有地方去。北京热心肠的人也比较多,就会把空的屋让给她住。
但她总住不长。人家是好心帮她,结果她在人家屋里边开始住得像主人一样,没了分寸,还带人过去玩,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她总是可以找到地方住。喜欢、怜悯、同情、崇拜、欣赏……这些情感,都会在接触到张夏平的人身上发生,让他们愿意帮助她。
张夏平来北京是想做画展的。
对于画家来说,画展就是最高级别的追求。她准备在中央美院的画廊自己举办画展。
画廊的租金当时是几百块钱,她自己肯定拿不出这个钱,都是她家里边给的。
当时,张夏平有两三天的时间来准备展览,那段时间她不吃东西也不睡觉,身体承受能力达到极点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说到时候她做展览,要我拿着摄像机过去帮忙拍拍。等晚上摄制组的机器空着了,我就搬了一台,找朋友拿车子拉过去。
她当时在下面布展,跟我说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但我就发现她的精神状态跟往常有点不一样。
我说,「夏平,你去把画挂上去,我就拍你挂画的场景。」
她就拿着一幅画说,「好。」
结果她并没有朝墙的方向走,而是转过头来,对着摄像机镜头,露出一种非常诡异的神情,开始说,「来,跟我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然后她就在墙角坐下了,我有点懵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这时候,录像机的红灯开始闪烁,表示故障。张夏平坐在地上哈哈大笑说,「我发功了你知道吗?我发功了,让你这个机器拍不了了。」
我一脸懵地在原地愣了一会。后来,我和摄影的朋友提着机器回到了招待所,把录像带拿出来,塞进录像机里一看,里边全是雪花,真的什么都没有拍下来。
坐在招待所里面,我陷入了沉思。我知道张夏平有情感上的精神病,这段时间她又不睡觉、不断地抽烟,什么也不吃,那个时候的她正处在自我失控之中。
之前她发病的时候我也见过,也听朋友说过,我知道她是为了她的画,为了她的展览才走到这一步的,我知道她已经走火入魔了,她想要冲上某个巅峰。
我重新擦一擦磁粉,带着摄像机跑回了画廊。那个时候大家在帮忙挂画,她则开始胡说八道,进入到癫狂状态了。
现在不是我在说话,这是上帝的声音。
上帝是一个女孩吗?
你们说,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世界就缺把火!我就想把火烧起来!
上帝你听见了吗?
上帝你听见了吗?
我是谁?我是谁?
这太可怕了。
我告诉你们,这一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性倒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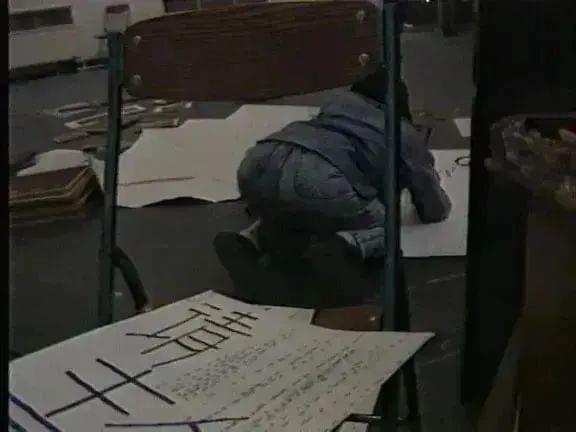 ■ 图 / 趴在地上画画的张夏平
■ 图 / 趴在地上画画的张夏平那天晚上她从始至终都是这样,躺在地上,但就像是站在云端上面蔑视众生一样,觉得所有人都是傻逼,她说,「吴文光你也是个傻逼,你懂什么叫艺术?你根本就不懂!」
大概一天以后,她的展览就开幕了。
结果当天晚上,有个人在前门肯德基打电话打到了我的招待所,「你认识张夏平吗?她在肯德基,现在已经快不行了。」
对面越说越严重,说她站到了桌子上。我就骑车到前门肯德基,把她弄到一个后厨的仓库里,她两眼失神,完全是我不认识的模样,躺在地上又哭又笑,已经进入到了非常极端的状态。
人家肯德基也打了 110,警察也来了,但是看见这样的情况,警察也没法直接弄走,于是就叫了急救车,把她送到了安定医院,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 4 点了。
医院给她用了强制安定一类的东西,一下子把她从那种境界里边拉回来了。
我觉得牟森评价得很准确,艺术需要一种疯狂的状态,但真的疯狂以后,实际上人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画展开幕那天牟森也在,张夏平见了他,就跟他说:「我通了,我什么都通了!」牟森觉得,他明白张夏平在说什么。
我觉得我们在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但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她疯了,而我还没疯。
我不想疯,之后会不会疯我也不知道。
但想在艺术上应该达到那样一种纯粹的状态,发疯似乎是必经之路。
可能最好的艺术作品全是疯狂的产物,没有理智之后反倒能够找到一种流畅的秩序状态。
——《流浪北京》中牟森的话
对于她的情况,我又怜悯又觉得可怕,但这之中还有一丝敬意。
80 年代的张夏平是一个极端,不在乎生活的贫困疾苦,或者是一时的坎坷,他们愿意这样去做。
一个人落到这种状态,可以说是为了艺术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到精神都交付出去了。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到她这个程度的。
可以说,她在艺术上很纯粹,也很挥霍。
 ■ 图 / 展示画作的张夏平
■ 图 / 展示画作的张夏平-4-
飘向更远的地方
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拍摄了两年,从 1988 年到 1990 年。
这两年中,在艺术的追求之外,他们梦中经常听到有人拍门进行人口普查,工作人员大笔一挥,就会把他们扫回「外来务工人员」一栏,日复一日的贫穷和饥饿,北京冬天吹进平房里的寒风,这些最基础的生存需求都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除了创作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似乎都变成了折磨。对于有希望的未来,他们越来越找不到依据了。
这些都慢慢侵蚀着他们的安全感,他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渴望似乎变成了一种浪漫而幼稚错觉,北京变得不够遥远,不够迷人了。
而 90 年代初,正是中国出国潮高涨的时候,那时候的青年人对西方开始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大家开始变着法子地想要结束流浪北京的生活,流浪去更远的远方。于是,这五个「盲流」艺术家的理想诉求都演变成了「出国」。
那个时候觉得国外更好。
在北京,我们还是在一个被管束的环境下生活,还不自由。于是「流浪北京」就变成了人生的站点之一,下一站就是出国。
当时我记得想成为画家的张大力说,外国人才会欣赏画,或者愿意出钱买画,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没有多少人愿意出钱买画的。当然现在情况肯定不一样了。
现在我认识的人比原先多了一些,我可以卖出去的画也变多了,但是想靠卖画在北京生存,还是不太现实,因为卖画只能卖给外国人,中国人好像还没达到水平。如果有钱,他们也不大可能拿来买画,而是可能会拿去买锅,买勺子和炉子什么的。
我有点讨厌这地方的文化气氛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每天不干正事,游手好闲,你搞不清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流浪北京》中张大力的话
要是在今天,大家都知道出国很好,但是会觉得人不一定非得出国,而且出国之后很多人也会想要再回来。但是在 80 年代末,出国成了通向广阔天地的唯一通道。
《流浪北京》里面的所有人在当时都想出国。我也想出国,留下来的人只是因为出不去而已。
不存在什么乌托邦,想象没有办法变成现实,但是我们可以不与现实合流,这就是我在 80 年代年轻的时候所学到的东西。
-5-
逐渐远去的时代
在所有人之中,张慈是第一个走的,她找了一个美国人结了婚,然后顺理成章地去到了美国,过了没多久,张夏平也跟一个奥地利人结了婚,去了奥地利。张大力跟意大利妻子结了婚,去了意大利,而高波的照片被法国一个艺术展选中去做展览,借此机会去了法国。
他们留下的是盲流艺术家对八十年代的追忆和惋惜。
吴文光和梦想做戏剧导演的牟森,没有找到出国的方法,出于无奈,继续留在了北京。
而紧随其后的九十年代,在全球化席卷加速的大背景之下,更多机遇出现了,它比八十年代要更加亢奋。越来越多的青年艺术家流向北京,北京圆明园的画家村和宋庄画家村相继出现。「艺术品市场」「策展人」「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这给留在北京的吴文光和牟森带来了机会。
转年来到了 90 年代,是很多可能性开始出现的地方。
留在北京的我也好,牟森也好,我们都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业。
一部戏接着一部戏找牟森拍着。而我 1990 年接到了新的活,要拍一些企业的宣传片,比在摄制组里面干活挣得多多了。有了钱之后,我就可以在北京安定下来了。
我拍摄的片子《流浪北京》在 1991 年参加了电影节,误打误撞就被人选上了,我因此有机会拍我的第二部片子、第三部片子,后来就顺风顺水地进入到了自己的轨道。
我记得鲁迅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
后来,高波、张大力他们在 1994 年、1995 年也陆陆续续地回国了,毕竟不会外语的话,在国外就是个哑巴、聋子。原来想象的在国外可以有很多艺术发展道路,不能说是死胡同,至少也是很狭窄的一条路。
我特别早就有一种迫切的感觉,那就是新世纪快来了,而且我一想到这个,心里面就特别感动,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强。我不是在说大话,我感觉 60 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将会是整个世纪交替阶段最优秀的一批人。10 年之后,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我现在说的话。
——《流浪北京》中牟森的话
周围的这些朋友,只要坚持下去的,都会有自己的成效,几乎没有所谓失败者,只不过就是做得有声有色跟做得不太大的区别。
像 80 年代,相对于现在肯定是非常的封闭的,那时候的人很「笨」,也很简单,或许是因为没有见过太多东西,大家就会非常单纯地奔着自己想做的东西去做。
张夏平 1989 年在北京的时候精神已经好些了,但还是不断地在说,「我要搞一个艺术中心,那些画画的,写作的,或者搞音乐的,他们没的住、没的吃,这个地方就供他们吃,供他们住,让他们安心做艺术。」当时大家都过得那么狼狈,这番话就像是在画饼充饥。
现在出生的这一代人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有很多现实需要考虑,不像「80 人」那么简单。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依然有什么愿望,还是可以做这个时代潮流中的逆行者。
后来,张大力 1995 年回到了国内,以城市雕塑与涂鸦获得了业内的肯定,成为一名城市艺术家;高波也回到了国内,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成为了一名摄影艺术家;牟森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剧团,是国内有名气的导演;镜头之外的吴文光成为了中国新纪录片第一人。
想要成为作家的张慈和因为画画「疯了」的张夏平没有回来,张慈在美国拥有了固定的房子、车子、职业,有了两个孩子,在空闲之余继续坚持写作。张夏平在奥地利做了一名画家,继续保持纯粹。
他们一定是有才华的,但是也不得不被时代裹挟着向前走。
而后来的北京,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也已经不是年轻人唯一的选择了,很多艺术家们也在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
有些人认为,属于八十年代末的那种激情很美好,但可能永远也无法重复了,而有些人觉得,那种激情是不值得被重复的。无论如何,那个时代都已经带着盲流艺术家们的喜与悲,慢慢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