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0期,作者: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原文标题:《历史的物质转向:专访〈尘暴〉作者唐纳德·沃斯特》,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整个1977年的夏天我都在宿营。我开着一辆老式的大众小厢车,白天奔跑在被太阳晒得焦枯的乡间公路上,晚上随意找一处看似安全的地方在车中睡一晚。有一日,我宿营在一个乡村小学校的外面。你知道的,大平原上有很多那样的乡村小学,小小的一层砖房,孤零零地矗立在某片巨大的麦田附近。
我用小煤气炉给自己煮了一个牛肉罐头,收音机放着比尔·艾文斯(Bill Evans),我最喜欢的爵士乐钢琴家。一阵暴雨袭来,电闪雷鸣,整个厢车都在晃动。第二日清晨,我醒来时,几只斑鸠轻柔地咕咕叫着,两只黑尾鹿在不远处的小树林边缘徜徉,地平线染着霞光。”
45年后的冬夜,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先生回忆起这段田野经历,身在太平洋彼岸,隔着屏幕,我仍然能看到他眼中闪耀的神采。如同大部分“青椒”的经历,沃斯特的早年学术生涯并不平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布兰迪斯大学,一所专门为犹太人创立的学校。当学校遭遇财政困境时,首先失去工作的是尚未拿到终身教职的非犹太人教员,沃斯特正是其中之一。
1975年,他跨越半个太平洋,前往火奴鲁鲁的夏威夷大学任教,那是一个全然不同于波士顿——新英格兰的地方。后者是美国思想传统的中心,而前者则是汪洋中的大岛, 既是美国文化的边缘,同时也是多元文化的中心。
沃斯特入乡随俗,解掉了领带,脱去了西服,穿着印着热带元素的短袖衬衫,教授那些肤色各异、文化不同的学生。在这处远离大陆的地方,他摆脱的远不止服饰的束缚,还有原生家庭的新教传统、新英格兰的精英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美国的同质文化。这段特别的经历让他在重返北美大陆时,具备了世界性的眼光。
1977年至1978年,沃斯特获得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研究金,并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返回他的故乡——大平原,开始撰写一段关于尘土的历史。沃斯特回忆说,“从档案研究、田野调查,到最后成稿,我只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彼时,他未能料到这部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写就的小书,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方向的奠基作之一,成为启发包括中国环境史学人在内的无数历史学者探讨文化与自然关系的经典。
1979年,《尘暴: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以下简写作《尘暴》)正式出版。次年,该书便获得美国历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沃斯特回忆当时道:“就我写的那本小书?我整个人‘傻掉了’。多年后我遇到了那一届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评委,他们才华横溢、不落俗套,也不为当时流行的议题所困。《尘暴》能够遇上他们这样的评委,是我的幸运。”
![《尘暴》,[美]唐纳德·沃斯特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https://i.aiapi.me/h/2022/04/02/Apr_02_2022_16_47_44_35916635015334486.jpeg)
《尘暴》是一部特立独行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此书是第一部带着明确的环境史学科自觉撰写的历史学著作。沃斯特从美国20世纪30年代萧条、压抑的历史中,发现的不仅是经济体系(economic system)的崩溃,也包括生态体系(ecological system)的崩溃。
在他看来,它们是同一场资本主义大危机的产物。“滚滚而至的黑色风暴”将有着“世界面包篮”之称的美国大平原变作“灰碗”,成千上万的农场主破产、抛家离舍,这不是人们所惯常理解的天灾,而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干旱是大平原的常态,但是干旱并不必然导致沙尘暴。
自19世纪后期开始蜂拥而至的新移民彻底破坏了大平原的天然植被,代之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工业农业种植的小麦, 他们犁开了将大平原的土壤凝聚在一起的顽强和庞大的本土草根系统,而后,干旱到来,尘土飞扬。其背后的推手,便是沃斯特所言的“资本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首先,自然必须被当作资本;
其次,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去利用这一资本,以追求利益最大化;
最后,社会制度应当允许并鼓励这种对自然的无极限开发,不应对之加以任何束缚。
在45年前的美国历史学界,该书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征服自然的合法性的质疑,可谓是颠覆性的。其中关键性的思想力量是一种对历史的生态学思考,它启发历史学者发现土壤(soil)、尘土(dust)、野草、驯化的草(即小麦)之于人类历史的重要性,从而将人类文明史放回地球演化的漫长历史当中。
对沃斯特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尘暴本身虽然是区域性的,但其意义却是全球性的,这是激发他撰写《尘暴》的初衷,也成为此书能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原因。毕竟,尘暴并非北美大平原独享的“天赐之物”。
2021年初春,新冠肺炎疫情的幽灵仍然在整个世界徘徊,中国北方的上空更是笼罩在肉眼可见的威胁之下。西伯利亚刮来的大风吹散雾霾的同时,也带来了铺天盖地的尘土。3月15日,中国北方经历了近十年来最大的沙尘暴,北京也未能幸免,海淀四季青站的PM10指数飙至3572微克/立方米。
4月15日,上午的天空并不晴朗,但在灰色中隐隐透着淡蓝,让人看到几分希望。下午则风云突变,天色骤暗,狂风大作,暴雨降临。数十分钟后,风敛雨收,然而天空的色彩仍然昏黄,整个城市如同在泥浆中翻滚一遍,那是一场罕见的泥雨。这一季的沙尘暴让北京在阔别近十年后再次闻到尘土的气味——清晰而辛辣,也令环境史学者忆起沃斯特笔下那个发生在1935年4月14日的“黑色星期日”。
在漫天尘土中,回首近百年前那个在现代道路上一往直前的新帝国在其广阔的生态腹地上所制造、罹受的巨大生态灾难,我们会发现沙尘暴既是当下世界的生态现实,也是生活在相似自然环境下的不同文化群体的生态经历。疫情引发的恐惧令全世界开始反思现代世界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所面对的生态困境远不止健康遭受的威胁,人类的生态过往也远比病毒的干扰更加复杂、纠结。
基于此,我在2022年1月27日的夜晚通过视频采访了《尘暴》的作者——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访谈始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撰写一部书的缘起。
侯深:您为何要写《尘暴》?
唐纳德·沃斯特:对任何一个作者而言,撰写一部书,首先必须是因为他认为他所探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坐落于落基山脉的阿斯彭人文学院(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度过了1974年的夏天,我与其他学者每日讨论的话题都围绕着食物、干旱、饥荒和非洲。
离开那里后,我驱车前往大平原。在那里,我看到了那年因春季严重的沙尘暴而留下的痕迹:从房舍、筒仓到粮仓,所到之处都包裹着尘土变成的泥浆。我当时心想:“嘿,我记得这样的景象,20年前,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这里也曾经盖着泥浆。”大平原不是美国某处穷乡僻壤,反之,它身处现代化农业、生态、粮食议题的中心。那一刻,我惊觉自身的经历同现实世界中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的一切发生了重叠。

在离家15年后,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想念家乡,因此我坚信它必须成为我这本书的主题,它会将我带回这里,探究它的历史、人群、景观和生态。由于那时我仍然在完成我的第一部书,因此我不得不再等三年,才能回到那里开始《尘暴》的调研与写作。如果仅仅因为大平原是我的故乡,却无法让我在其中发现它与整个世界的关联,我仅会热爱它,但可能不会研究它;反之亦然。
大部分人会觉得大平原太平坦、太干旱,过分工业农业化的景观很难称得上美丽。但我不这样想,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所以,在《尘暴》背后,既有私人的兴趣也有学术的意义,我想这应当是所有历史写作的初衷:从强烈的个人兴趣出发,但它应当具有同样强烈的世界性意义。
侯深:“一个浪漫的地方”,的确很少有人会这样描述大平原。能让我们想到“浪漫”的,是高高的洛基山、迷人的加州大瑟尔(the Big Sur),或者壮丽的大峡谷,甚至佛蒙特的田野风光。您为何认为大平原很浪漫?
唐纳德·沃斯特:大平原自然不是传统意义的浪漫,但是它的天空那样辽阔,远景那样空旷。它的景观并不只是农田,它仍然保留着惊人的野性:沙丘、峡谷、河流,游荡的郊狼、野鹿,傍晚出来觅食的火鸡。它的历史色彩斑斓,印第安人、拓荒者、宅地农民纷纷来去。
生活在那里的大大小小的农场主,我曾经与他们中的很多人交谈过,他们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肮脏的30年代”中长大。当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感到热血澎湃。大平原对我来说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它有着一种让我产生激情与幻想的力量。在那里,我感到自由。
侯深:您谈到了那里的人事和自然,二者之中,谁更具有吸引力?谁更让您感到自由?或者它必须是二者的结合?
唐纳德·沃斯特:这很难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渴望做一个早期的“定居者”,前往那片新鲜的土地,那时野生生物处处可见。就像那些早年的宅地农民,他们深深地热爱着所迁徙的那片土地,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去破坏他们所热爱的一切,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
侯深:在《尘暴》之前,您出版了第一部书《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以下简写作《自然的经济体系》),《尘暴》之后,则有《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以下简写作《帝国之河》)。您是否视《尘暴》为您的学术生涯的一部过渡性著作?
虽然《自然的经济体系》研究的是生态学历史,但是它依然是耶鲁大学思想史传统下的自然思想史著作,而《尘暴》与《帝国之河》则远为物质性。在我看来,您在《尘暴》中做出了一个“物质转向”(a material turn),不知您是否认同?
![《自然的经济体系》,[美]唐纳德·沃斯特 著,商务印书馆 1999](https://i.aiapi.me/h/2022/04/02/Apr_02_2022_16_47_53_35916643786453202.jpeg)
唐纳德·沃斯特:的确如此。《尘暴》是一部过渡性著作,是我的早年学术生涯作品。在读博士时,我专注于英美文学、思想和文化史以及科学史,我的第一部书便源自这些主题。我当时的个人兴趣在于理解作为科学和大众观念源头的生态学。我始终保持着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也相信科学对于所有历史学者的重要性,但那时,我希望走出去,帮助建立一门被我们称为“环境史”的新领域。
它不应当仅仅重复旧有的关于自然观念的历史,像利奥·马克斯的《花园里的机器》、佩里·米勒的《自然的国度》或者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而是应当将我们带回物质现实当中,带回在骄阳下劳作的人类身体,带回植物、动物、土壤、气候,带回人类与土地、水、天空、环境的全部物质的相互作用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尘暴》是我第一本真正的环境史著作,后来我又尝试将城市与技术也放入这幅图景之中,但是我认为在此之前,应该在研究中先谈谈人们是如何获取食物和填饱肚子的。
侯深:这让我想起您的那句名言:“人类的历史始于人类的肚子。”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您渴望触及“物质现实”,或者说,您是如何看到您所言的“物质现实”的?
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不应当是思想史或者文化史的某个小小的分支,抑或某些热门的话题。我希望将环境史观带入主流历史研究当中,而非仅仅建立一个有着某套特别技艺的亚领域。当然,环境史从来都不只是物质史,换言之,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等都存在于其中,正如它们在《尘暴》中都有所表达。在那本书中,涉及了如约翰·斯坦贝克、威拉·凯瑟、阿尔伯特·比兹塔特、多萝西娅·兰格等作家、画家和摄影家。
但是,我们需要理解人类同地球之间的物质性相互作用。启发我看到历史中的“物质现实”的力量源于我对当时环境科学和文学的相关阅读,以及对当时环境运动的关注。那场运动并不关心《花园里的机器》或者自然是否是一种文化建构这类议题,它所关怀的是食物、能源、气候、生物多样性这些物质性的议题,关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如何阻止灾难的发生。
侯深:从您读博士到写作《尘暴》的那十余年中,美国社会经历着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您同时代的历史学者大多关注民权运动、女性运动,或者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等,从而开始了美国史学中“种族、阶级、性别”神圣三位一体的思维范式。是什么让您对环境运动、环境权利更加感兴趣?
唐纳德·沃斯特:我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有人关心的都是奴隶制和清教主义,坦白地说,我对两个问题都不感兴趣。我来自堪萨斯,来自大平原,不是南部,也不是新英格兰,我们的经历中没有关于奴隶制的记忆。至于清教主义,大平原人对它有些了解,但是耶鲁大学的清教主义属于新英格兰特有的思想。
我不认为这些是唯一重要的、有意义的问题,对我而言,它们没有个人层面的特殊意义。在政治上,我当然是自由主义者,支持民权运动,拒绝清教主义,但是我来自另一个美国,一个不同于新英格兰的美国。
侯深:谈到个人的身份认知,如果不是种族与性别,您还有另一个选择:阶级。全然不同于您在耶鲁大学的同学,他们大多来自中产或者中产以上阶级家庭,自常青藤学校本科毕业,而您实实在在来自大平原的劳动阶级家庭,父母只接受了高中教育,是尘暴难民。说句不恭的话,这是您身上的阶级印记,为何这样的身份认知没有让您专注于神圣三位一体中的阶级议题?
唐纳德·沃斯特:我确实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但是在堪萨斯,我们并不认为“阶级”有多重要。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对种族、阶级、性别的拒绝。拒绝,正是表达我自身阶级属性的方式。拒绝是一个过于强烈的词,但是我的确无法同新泽西的工人阶级分享同样的身份认知,尽管我们很贫穷,但是对阶级冲突并没有切身的感受和认识。阶级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社会性的,而是私人的。我的那些精英家庭出身的同学们对自身的阶级属性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关注阶级议题的源泉。
迄今为止,我仍然认为自己的某个部分与我所来自的那个群体相通,但是我一直都处于某种边缘地带。在孩提时代,我处于我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边缘,我的父亲从来不能理解我为何宁愿一个人躲在图书馆读书——那里有空调(笑),或者拿着鱼竿去外公家后面那条钓不上一条鱼的小溪边呆坐几个小时。我无法认同大平原的农场主们对土地的掠夺,虽然他们如同我的家人。可能我更重要的身份认同来自我对那片土地的认同。
很多身处环境运动的人可能也是如此,他们的身份认知并不建立在种族、阶级、性别的基础之上,像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蕾切尔·卡森,他们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甚至富裕家庭,但是他们同样站在自己的社会的边缘,并不认同他们所处的社会对待自然的观念。他们是所谓正常道德社会之外的孤独者,然而在政治和经济上,他们(所认同的观念)又同主流社会相一致。
所以当我回到堪萨斯,同我的老乡们打交道,我喜爱他们,无论他们的风格还是态度,我甚至发现他们之中有人同我看待土地和自然的观念是一致的。但是我同样看到很多人前往那里只是为了赚钱,我能够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去批判性地分析他们同土地之间的历史。他们是尘暴的受害者,也是那场灾难的制造者。他们并不邪恶,但是他们在资本主义文化和自身欲望的驱动下做出错误的决定,最终将他们引向巨大的生态灾难。
侯深:当您说希望自己是一个早期定居者时,您显然不希望成为追随资本主义道德和意识形态队伍中的一员。阅读您的著作,一个经常浮现的意象是梭罗在《行走》一文中对美国西部的想象——开放的天空与土地。《尘暴》与《帝国之河》都是在消解这样的西部神话,但是您认为那样的想象本身,对自由和自然的追求仍然有其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定义着大平原和西部。
![《帝国之河》,[美]唐纳德·沃斯特 著,译林出版社 2018](https://i.aiapi.me/h/2022/04/02/Apr_02_2022_16_47_57_35916648001071513.jpeg)
唐纳德·沃斯特:是的,我更像是一个梭罗主义者,而非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侯深: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都会想到您在《尘暴》一书开篇对《资本论》的那句意味深长的引用。自此,您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我知道您一直抗拒这样的标签,很多年后,您强调环境史建立的初衷之一正是为了打破当时美国史学界左右两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那么在冷战仍然胶着的20世纪70年代末,您为何会引用那句话开启全书?
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的引言中,我引用了《资本论》中很短的一句话:“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上的进步。”我为什么这样做?首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确的。同时,我必须承认,我多少想干点儿“捣蛋”的事。
在20世纪70年代的堪萨斯西部和那些当地报刊编辑、商人那里,引用马克思同引用魔鬼没什么区别,我很好奇人们的反应。但是任何一个真正了解马克思思想的人都会迅速地发现,该书并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那本书中没有阶级分析。
侯深:但是您在《帝国之河》中的确对阶级之间的分裂、撕扯有诸多讨论。
唐纳德·沃斯特:是的,《帝国之河》讲述的是社会权力如何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故事,但即便如此,阶级斗争也并非其主题。如何通过统御自然而建立社会统御是我在那部书中讨论的核心,而这并非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在《尘暴》中,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状态和道德哲学,而非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辩证斗争。
在很多方面,马克思看待土地的态度同堪萨斯农场主并无二致,他分享着后者的很多观念:应当将土地视为一种商品,为了人类的福祉使用之、剥削之,土地自身并没有其内在的价值。所以我如何可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我来说,土地首先也始终是一个生态共同体。
现在看来,我当时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应当更详细地阐述我对马克思的赞同与批评。我当时太急于完成那部书,可能我应该强迫自己慢下来,才能做得更好;但是我那时必须回去教书,以确保我的家庭经济无虞,毕竟我有两个尚未入学的孩子。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事实上,我在此后的著作中的确尝试扩展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之有一些更好的分析。
没有将阶级分析作为书的主题,或者没有将种族、阶级、性别作为我思考的核心,并不意味着我不爱人。事实上,我喜欢人,也喜欢与各式各样的人进行各种不同的交流。但是,这个星球上并非只有人类,也并非只有不同人群之间对权力、财富、影响力的斗争,妥协才是历史唯一值得思考、关注的问题。
侯深:对《尘暴》的批评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有意思的是持这些意见的批评者在政治立场上全然不同。
第一类是最可预期的,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的拥趸;
第二类认为您对沙尘暴的受害者,即大平原上的普通人同情不足;
第三类强调沙尘暴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会发生沙尘暴;
第四类则认为您是一个“衰败论”者,相信在白人到来之前,大平原的自然环境是和谐而有序的。
不知您怎样看这些批评?
唐纳德·沃斯特:看来我应当更注意我的批评者都说了什么。一般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是否写出了关于同一主题的更好的著作。当然我知道这样的态度不对,不够谦逊。(笑)但是,他们很多时候的确在刻意地误解一部书。
有些读者理解这一点,虽然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我所写的仍然是我自己的乡亲,那些我喜欢并且尊重的人和我热爱的地方。刚才我一再说道,他们如同我的家人,然而,正是这些农场主而非自然制造了沙尘暴和农业灾难,自然和土地也可能变成受害者,尽管人们最终也要自食其果。
我既不迷信进步,也不笃信衰败,我只是希望展示大平原上的人和自然共同的经历,并解释为何会发生这场灾难。但是显然,很多人并不喜欢这种中立的态度,他们总喜欢将一个作者放入一个固定的类别当中。但可能他们更希望作者告诉他们,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人,特别是普通人,不会做错事。
我对我自己的家庭和大平原上的普通人有更好的了解。假如我指责我的这些乡亲们是种族主义者——仇视原住民和歧视非裔美国人,我的批评者可能会立刻噤声。但是我胆大包天,居然敢说那些最普通的美国人滥用土地且行为无知,在制造了一场世界级的灾难后仍然不愿承认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可着实让我的批评者不快了。
至于批评我对大平原的生态系统想法天真的人,我很好奇他们究竟阅读了多少关于生态学和大平原生态的著作,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在大平原上生活与观察过。
侯深:我想很多历史学者对生态学的认识,对其关于混沌、平衡、秩序的讨论都来自您的《自然的经济体系》。您如何看待尘暴背后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源的问题?
唐纳德·沃斯特:我在书中谈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乌克兰的开发,他们称自己为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将美国的资本主义农业作为学习的范本和竞争的对象。我认为共产主义农业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追寻着资本主义农业的模式,在技术和观念上都很接近。
不过,我并不会那么断然地说资本主义在大平原上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我可以看到一些白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创新精神——他们对如何更聪明地使用这片土地所进行的实验。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风险的强烈接受意愿,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风险导向的文化。
如果我去修改这部书,我会对这个角度做更多的探讨,我会对“肮脏的30年代”之前的一代农场主做更细致的研究,是谁选择了风险,什么样的风险,为何做那样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又如何。我也很好奇女性是否对风险更加谨慎,她们是否可以成为更好的农场经营者。当然,即使我这样做了,我的批评者们还是不会满意。(笑)
侯深:批评者总是存在,可能对您而言更重要的是您对自己的批评。事实上,纵观您的学术著作,您总是在尝试新的维度和议题,尝试超越自己。2016年,您出版了《萎缩的地球:美国丰裕的兴衰》一书,而您现在正在写作一部您所称的行星史(planetary history)著作,这是您在1988年就开始倡导的一个新名词。从《尘暴》到行星史,我很好奇这其中,中国对您的意义何在?因为从2012年开始,您每年会在中国住五个月,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段经历对您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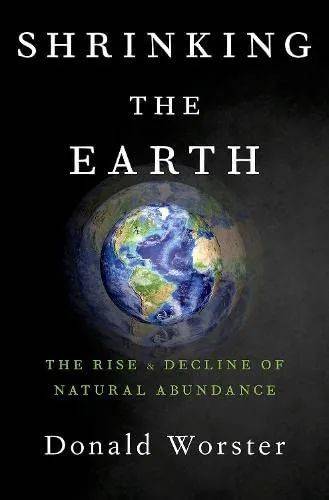
唐纳德·沃斯特:我同亚洲最早的接触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它启发我开始思考亚洲、太平洋,那些美国之外的世界。但是直到1998年,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前往中国,从没有任何一次海外旅行如同那次旅行那样令我兴奋。我一直希望能够回到中国领略它的文化和自然。我感到自己最初的30年学术生涯是那样狭隘和地方主义!我的很多美国、欧洲同行到今天还是如此。
现在,我深知,如果我们不询问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地球和生活于其上的人类的历史。我们需要知道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
如果一个历史学者所知所想仅仅是自己的国家,即使他/她知识渊博、深厚,他/她也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的学者。他/她所产生的所有想法可能都存在问题,因为它们没有经历更广阔的检验。于我而言,在另外一个国家生活并不只是有趣、好玩,同时也极具挑战性和教育性。在我看来,我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同我的博士学习经历一样宝贵,或者更为宝贵。
侯深:如果我所记不错,您并没有经历过中国的沙尘暴,但是每年都会在北京的雾霾中度过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尘暴和霾都是人为的自然灾害,在您看来,除去成分不同,它们有何差异?
唐纳德·沃斯特:看来你认为我如果没有好好呼吸过从蒙古草原吹来的沙尘,我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笑)别忘了,我去过内蒙古,也去过北京之外的很多地方,我对首都之外的中国人在非人类世界中如何生活多少有些了解。
土壤侵蚀当然也是众多污染形式之一,但是比起绝大部分其他形式的污染,其程度更加严重。飞扬的尘土告诉我们,以食物支撑我们生存的地球处境堪忧。与之相比,燃烧化石能源带来的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甚至比尘暴带来的健康损害更广泛,但是其生态危险则较为有限。如果一个国家、政府真正想控制空气污染甚至消灭雾霾,通过少开车、不烧煤和寻找替换能源是可以做到的,北京和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这样做,而且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但是,土壤的侵蚀、消耗、毒化以及沙尘暴,是无法以这些较为简单、直接的方式解决的。我们必须依赖土壤生存,而且很可能会一直需要它,我们无法彻底转向水耕法或者其他形式的农业。城市人往往不能真正理解土壤的重要性,也不能真正理解沙尘暴的严重性。他们仅将沙尘暴看作另一种污染源,仅焦虑他们的家庭环境、所呼吸的空气和自己的健康。他们当然应当关心这些问题,但是不应将其食物的所来之处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侯深:您的个人经历以及生态学对大平原的认识都在发生着变化,您适才谈到,如果有机会重新修改《尘暴》,您会对风险有更细致的讨论。那么,您会去修改它吗?
唐纳德·沃斯特:我不会再修订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无瑕的。事实上它有很多问题,但我有新的书要撰写,有新的问题要思考。那部书对我而言属于过去,它是真实的,是过去的我,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让它继续以它曾经的模样存在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作者:侯深,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