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雅婷,编辑:木村拓周,题图来自:《新蝙蝠侠》
一、2022的切肤之痛
DC 恐怕要感谢这个糟糕的时代。
如果今天依然盛世太平,美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有条不紊,地球村的叙事没有被打破,经济全球化继续高歌猛进——2010年代漫威宇宙对超级英雄电影市场的绝对统治,恐怕还要再延长一些年头。
但接近20年代,世道往奇怪的方向走去,更擅长表现混沌和失序的DC终于等来了它的好时机,拖拖拉拉五六年的《新蝙蝠侠》项目也终于在 2022 年的3月全球上映。
在 IMBD 上,《新蝙蝠侠》得到了8.4分,同系列中仅次于《蝙蝠侠:黑暗骑士》,与《小丑》和《蝙蝠侠:黑暗骑士的崛起》持平。Variety、IGN、Vox 和 RogerEbert.com 等媒体上,专业影评人给出了具体而类似的佳评:“马特·里夫斯创造了多年代最佳的蝙蝠侠电影迭代,这就是我想看到的那种蝙蝠侠电影”,以及“影迷真的需要重启蝙蝠侠吗?——看完《新蝙蝠侠》后,答案是肯定的”。
挑战一个已经有了青史留名三部曲的超英IP,难度难以想象。但导演马特·里夫斯很好地完成了这一项工作。他创作出了电影史最独一无二的蝙蝠侠,这种独特,植根于创作者对美国或全球化心灵缺口的敏锐感知。
戴锦华在《电影大师课》中曾提到过,好莱坞征服大众的魅力不只在于大制片厂和团队靠技术与资本制造出的视觉奇观,更在于好莱坞对公众生活、社会及文化变化的洞悉。好莱坞佳片总能从公众有切肤之痛的议题切入,但却能靠着高超娴熟的叙事技巧,带观众从痛楚中走出,为公众创造理解之途。
在这个意义上,《新蝙蝠侠》完成了电影所能完成的最好任务。

影片想要谈论的“切肤之痛”,在影片开篇就被点明——
晦暗的哥谭市依旧耽溺在换脸的沉沼里,阴影里的愤怒以街头涂鸦、抢劫和恐怖袭击在街道里显形,蝙蝠侠信号灯在黑夜上空盘旋。地铁上有群热衷于暴力的青年,将一个亚裔逼到角落。蝙蝠侠从他用以掩匿的黑暗中现身,打斗前有人问他是谁,蝙蝠侠回答说“我是复仇者”。
熟悉蝙蝠侠身世的观众知道,“复仇者”的身份标签来源于蝙蝠侠真身韦恩父母的被害。作为开创了哥谭市的韦恩家族,韦恩的父母原本是哥谭市颇有威望,形象偏于正面的一代。但在大都市经济下行之时,韦恩却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在“犯罪巷”被射杀。这是韦恩成为孤儿的起因,也是他下决心化为蝙蝠侠铲除邪恶罪犯的开端。

紧接蝙蝠侠作为“复仇者”亮相的下一个场景,是蝙蝠侠徒手打跑暴力青年之后,地上的亚裔却面对他作出虚弱请求,“请不要伤害我”。这句对白简洁,但足以传递出多重信息,一个是《新蝙蝠侠》的故事发生背景是在蝙蝠侠出现初期,蝙蝠侠还未作为英雄符号被世人所知的阶段;一个则是表明了哥谭市本身的黑暗程度——考虑到常规被超级英雄救下的 NPC 说出首句话通常是“谢谢你!XX侠!”——这无疑是在说哥谭市市民对漫溢的暴力之无助和绝望。
将这两个场景结合,《新蝙蝠侠》尝试要打开的议题是,今天的公众要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与绝望?又或者说,(美国)观众要如何在一个绝望的世界里,应对“愤怒政治”?
二、回到“新好莱坞”
在这个命题下,马特·里夫斯试图从历史上类似的“纷乱世道”当中寻找商业电影的表达范式。
早在华纳公司首发《新蝙蝠侠》预告片时,马特·里夫斯对媒体说起过影响《新蝙蝠侠》创作的几个灵感来源,大部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新好莱坞”电影,例如《唐人街》、《法国贩毒网》和《出租车司机》等影片。

好莱坞的六七十年代,本身也是一个电影制作、题材及美学锐意变革的年代。变革前夕的好莱坞既要受电视机兴起并逐渐普及的“威胁”,也要面对套路化创作西部片制作模式的失效,正处于商业制作衰退的阶段。但从六十年代末起,一批作者性较强、“反”类型制作、受意大利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等欧洲电影影响的创作开始逐渐出现,也就是马特·里夫斯灵感来源的“新好莱坞”电影。
具体到电影特征,以《唐人街》、《法国贩毒网》和《出租车司机》为例——
故事背景上,这些电影都勇于讨论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社会危机,比如说城市化进程里的高犯罪谋杀案件、黑恶势力和政府势力勾结的贪污腐败、越南战争以及此起彼伏的民权运动。

人物角色设定上,主角通常是一个侦探或小人物,由于工作和计划被无意卷入到政商勾结等罪恶事件里去,然后不得不出于寻找真相的目的,表现小人物和整个时代系统的斗争。

拍摄手法上,这时期集大成的是犯罪探案电影,也被称为黑色电影。“黑色”既是说电影的拍摄场景通常集中在暗巷/夜晚/阴影的“低光照明”区域,也是说电影的题材和表达多集中在犯罪和探案的过程里。这种风格通常会加强电影的压抑感,也表明主角本身的心理变化,对明确的道德观念通常抱有质疑态度。

在这几个维度上,《新蝙蝠侠》都有着和“新好莱坞”电影明显的对应——
罗伯特·帕丁森所饰演的蝙蝠侠,比起超级英雄,某程度上更接近于“新好莱坞”电影里的侦探形象。相比于惯常超级英雄直接能代表正义,惩处邪恶的作用,这一版蝙蝠侠要做的,则是应反派谜语人之邀,先去找出真相。
在探查真相的过程里,蝙蝠侠被卷入到他守卫哥谭市的巨大政要丑闻里,亲眼见证自己维护的理想和价值崩塌,目击要守护的市民充满恶意与歧视,目击的父辈受利益的诱惑加害他人,遭受一场信念瓦解的危机。
与“英雄不那么英雄”所对应的,是“反派也不那么反派”了。尤其在影片前期,谜语人做的尽是惩奸除恶的事,恐怕连观众也会产生疑惑——“这到底是谜语人还是谜语侠?”

实际上,这是电影借蝙蝠侠的视角想要传达的核心困惑,那就是他难以在所谓正义和邪恶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下确认“立场”。“道德”和“正义”到底什么?蝙蝠侠需要和观众一同历经锤炼和价值观的摇摆,不惧面对真相,才能查明真相,理解“犯罪者”的处境,理解社会把一个人变成“犯罪者”的过程。
类似这样对真相和事实的探明,也正是“新好莱坞”电影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在美国政治丑闻频传的六十年代,公众对政治和一种声音所宣布的真相多持怀疑态度。电影主角常常只能凭自己薄弱的信念,以及保护挚爱的理由才有力气行动。超能的英雄色彩也非常少见,四面楚歌的境遇外,侦探们被抓到必定被暴揍。这类电影的结局也很少有圆满结局,总是以悲剧和压抑绝望的氛围结尾。
总之,马特·里夫斯成功从 6、70 年代寻找到范式和资源,把《新蝙蝠侠》以一种新好莱坞模式的侦探故事(而不是全球化时代一往无前的超英故事)呈现,成功把蝙蝠侠的困惑和当下公众的困惑呼应到了一起,共同进行了这场三小时的探索。
然而,坏结局对于“新好莱坞”阶段的电影观众来说是必要的,因为那个时期的人们迫切需要文化作品看见并承认自己所承受的痛苦,需要个人和社会文化对无望的事实达成一种共识,之后才有可能去谈“采取行动”和“改变现实”。

但是《新蝙蝠侠》毕竟出现在“新好莱坞”浪潮的50年后,而且电影也需要对诺兰三部曲时期的“蝙蝠侠”形象完成一次精神迭代。
于是,《新蝙蝠侠》并没有停留在悲剧和绝望中作为结局,而是又多走了一步,让蝙蝠侠在这个迷惘时代找到并确证了自己的存在的意义。
三、终点不是绝望,是希望
学者刘康在论文《超级英雄电影:由对立构筑起的当代神话》曾这样说过超级英雄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即把观众感受到的现实文化矛盾,转变成叙事矛盾,在叙事中将这样的矛盾解决,电影结束后,观众也会产生现实文化矛盾被解决的抚慰或是错觉。
通俗一点说就是,广受大众欢迎的超级英雄电影,通常都是能敏锐察觉到时代现实矛盾并加以解决的作品。如果有什么超级英雄电影口碑扑街了的话,那多半是它误判了公众感受到的现实矛盾。
这条超英和现实呼应的线索可以被清晰地梳理出来:《超人》系列为代表的超英在二战和战后走红,是为了给当时的美国民众的民族精神注射强心剂,同样也是为了提振战后民众重建经济的信心。
到超级英雄长篇电影出现80年代前后,则适逢苏联声势式微与好莱坞“饱和计划”的扩张,对未来有信心的年代,美国观众热衷于看人神合一,拯救世界的《超人》长篇电影。
而在被《时代》杂志称为“地狱十年”的 911 后十年,超级英雄的电影则多以纽约为背景,在彻底的毁灭到来前总有蜘蛛侠、蝙蝠侠和钢铁侠倾力相助。
到了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时代后,出于政府推行的“合作制衡”与多元化的政策,这个时期观众喜欢看超级英雄开始放下个人自大的倾向,讲究科技进步主义、合作与身份文化多元……

《新蝙蝠侠》的成功迭代则在于,它察觉到现实的文化/政治/社会矛盾之后,还用巧妙的叙事技巧把观众从怒火中救出,并且再和蝙蝠侠人物转折点进行了完美结合。
这一切完成电影中后段,阿尔弗雷德被炸伤后,在医院醒来的那场戏。
彼时,整个哥谭市和蝙蝠侠本人,都面临一场心灵危机。
哥谭的市民很绝望,因为这一届政府没能做到他们在竞选时承诺给民众的——“重振哥谭”。但哥谭的市民绝望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城市的机要机构都被黑暗和邪恶势力所把持,他们无法干预政策的执行和制定,既不能跻身于腐败阶层,光明阶层也没有他们的位置。
而蝙蝠侠本人,在此前,一直在规则之外当义警,力所能及地伸张正义。但也就是在一系列的行动和调查里,他意外发现支撑自己行动的“起点”——也就是他的父母韦恩夫妇,本身也不是什么完美之人,甚至手上间接沾染着鲜血。支撑蝙蝠侠行动的原始动力沾上了污点,瞬时令他动力全无,陷入自我怀疑。

实际上,这不仅是哥谭市民和蝙蝠侠的心灵危机,也是今天年轻人,尤其是西方持进步主义观念的年轻人普遍所面临的心灵危机。过去信仰的主义和体系被证明失效,过去赖以行动的精神动力被残酷现实接连瓦解,过去被视为照亮黑暗的灯塔光芒甚至变成了狙击手瞄准的工具。蝙蝠侠此刻感受到的无力和自我怀疑,和今天全球年轻观众高度同构。
而这场戏里戏外的精神危机,在电影中,被两代人之间的一场真诚沟通所拯救了。
电影里,蝙蝠侠从坏人处得知父母的不堪“真相”后找到阿尔弗雷德,质问阿尔弗雷德为什么要欺骗自己。阿尔弗雷德则告知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另一幅“真相”。到这里为止,两幅截然不同的“真相”听起来都合逻辑,但也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撑。蝙蝠侠仍然需要自己从中做出一个“相信”的决策。
而这个时候,阿尔弗雷德向蝙蝠侠表示抱歉——对不起,我没能做到我应该做的。

这句话的力量不仅可以放在《新蝙蝠侠》电影故事背景来看,更可以放在当下全球青年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以及我们对父辈/前辈/先辈们的复杂情感中看。
阿尔弗雷德理解布鲁斯·韦恩受到欺骗的心情,他也坦诚相告,他和布鲁斯的父辈们这一代人(造成哥谭今日窘境的上一代人)确实犯了错,他们也确实想改正,却也真的没有办法。“我也想教你怎么去继续战斗,但是我却只能做到现在这样了”。
这是整部电影和现实互文程度最强的一个时刻。它同时治愈了布鲁斯·韦恩,和银幕前经历着经济下行、房价高企、阶层固化、失业潮、气候恶化、资源短缺和疫情肆虐的全球青年。
就这样,怒火被熄灭后的韦恩,又回到了探明邪恶的战场上去。只是这一次,他不再被愤怒、不安、恐惧和困惑所支配。他拦下即将失去理智要以杀人熄灭怒火的猫女,又投入到市长大选的危机里,在断电的黑暗中高举火把,救下一个又一个曾称他是“怪物”的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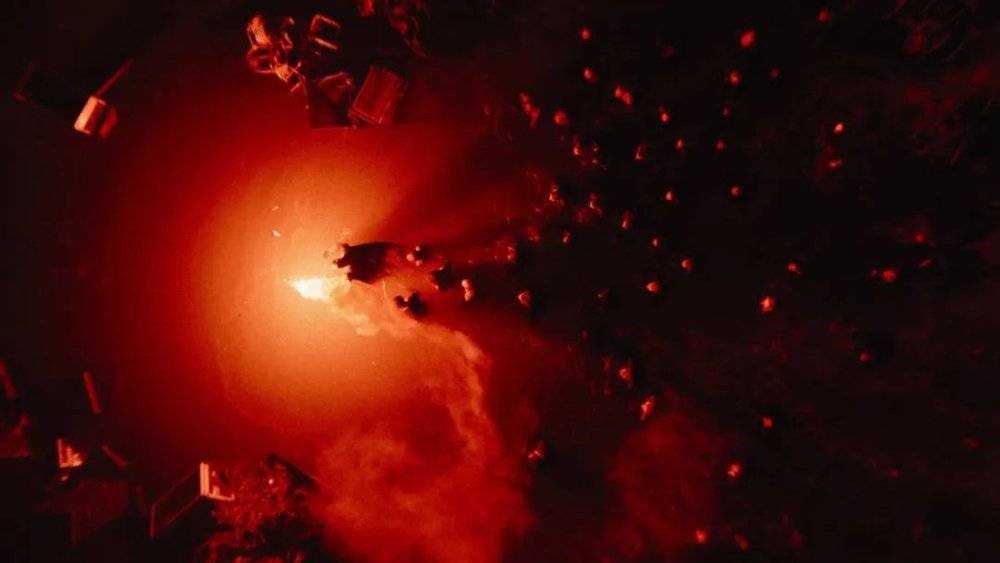
相比于此前的超级英雄们,新蝙蝠侠也许缺乏不容挑战的信念、阳光正面的人格又或者是炫酷战斗装备及能力。他所能做的,只是投身到具体的行动里,把道德和正义的意义,变成主动为他人谋求福祉的冲动,而非对他者要求上的暴力。
也正因为这样,相比于一个崩坏时代的全能拯救者,新蝙蝠侠更像一个“兜底”的人。他无法保证哥谭市下一个上任的市长能比前任更清廉、更出色;无法保证旧的恶势力网络崩塌后、取而代之的“新恶”会否更残酷;无法保证下一次潮水涌来时,哥谭市那个地势最高的、被用来举办选举大会的广场会不会被淹没。
他只能保证,下一次黑暗出现,他会继续点亮那束火光,既吸引了影片里的民众同行,也照亮电影院里观众的面庞。
参考文献:
1.崔辰:《美国超级英雄电影研究:神话、旅程和文化变迁》,上海:上海戏剧学院,201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雅婷,编辑:木村拓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