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我们曾报道2022年沃尔夫化学奖颁发给了细胞通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Bonnie Bassler。Bassler教授所研究的,是微生物之间沟通的独特语言系统。这套系统是怎么被发现、怎么被破解的?它对临床医药应用有什么现实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洪纬(科学技术史博士),审阅指导:耶鲁大学严兢教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知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
一个种族的所有个体因为遗传而得到的共同特征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族的灵魂。但是,当其中一定数量的个体聚集成群体,来进行某种行动,那么,观察显示,由于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心理特征,与种族的特征重叠在一起,有时候与种族特征会有深深的不同。
人类群体行为的产生是社会学家一直关注的话题。然而,群体行为并不是人类或是高等动物独有的行为。
近些年来,微生物学家发现细菌也有它们独有的群体行为。通过独特的化学语言系统,细菌之间能够互相交流,感知彼此,并集体投票做出决定。具体说来,细菌的生理和生化特性会随着群体的密度而变化,展现出少量菌体或单个菌体所不具备的特征和群体行为,以此应对环境的变化。这种现象就是微生物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
细菌小至肉眼无法观察,也不会发出声音。倘若不借助现代科技,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们的个体行为,更遑论监测它们的交流过程,解析它们的群体行为。对人类来讲,它们的一切行动在被发现之前,仿佛就是一场场密谋,而科学实验就是研究人员的一场场探秘行为。接下来,我们就将对群体感应的发现和微生物语言系统的破解过程做一个简要回顾。
一、发光细菌泄了密
1913年,自幼酷爱远足和收集生物标本的普林斯顿大学青年教师哈维(E. Newton Harvey)与水生生物学家迈耶(Alfred G. Mayer)结伴环游南太平洋,在澳大利亚的默里岛(Murray Island)一呆就是三个月。正是在这三个月里,哈维逐渐迷上了生物发光现象。
三年后,哈维与从事水生生物学研究的新婚妻子远赴日本蜜月旅行。在日本的西海岸,他被海面上的蓝光魅影吸引了。更令他着迷的是,光源海萤(Vargula hilgendorfii)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也是一种完美的研究材料。在干燥并储存多年后,只要经水湿润,它的发光系统就能重新焕发活力。没人知道哈维那次到底运送了多少干海萤回美国,但在这之后的四十年里,他一直在用这些材料做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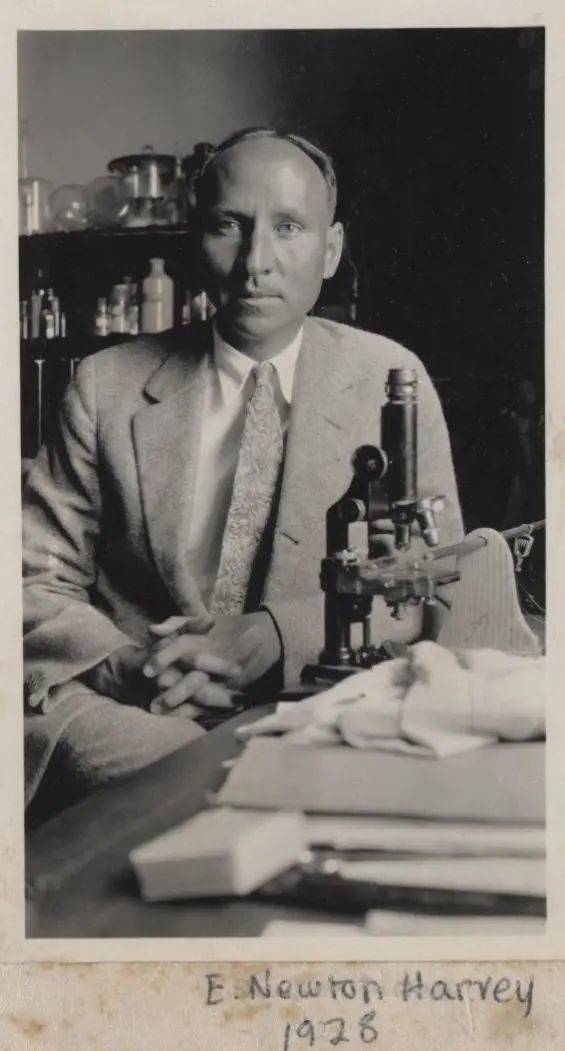
哈维涉猎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生物发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微生物居然也会发光。1953年,斯特雷勒(Bernard L. Strehler)首次从发光细菌(Achromobacter fischeri,又被称为Vibrio fischeri,费氏弧菌)中找到了影响发光的化学分子DPN(Disphosphopyridine nucleotide,二磷酸吡啶核苷酸),并完整地从细菌中提取了发光系统,实现了细胞外发光。
听闻喜讯,哈维发觉斯特雷勒的导师正是自己的得意门生麦克尔罗伊(William D. McElroy)时,他无不自豪地说道:“现在,我有一种自己就是生物发光领域研究祖父的感觉!”
有趣的是,在哈维的众多学生当中,黑斯廷斯(J. Woodland Hatstings)既是他的弟子,又是他弟子的弟子。1948年,黑斯廷斯随哈维攻读博士,1951年又追随麦克尔罗伊做博士后研究。在哈维实验室,黑斯廷斯开发了一种新技术,以测量不同物种的发光反应对氧气的定量要求。在麦克尔罗伊实验室,黑斯廷斯在萤火虫发光系统的传统领域奋斗一段时间之后,便转向了发光细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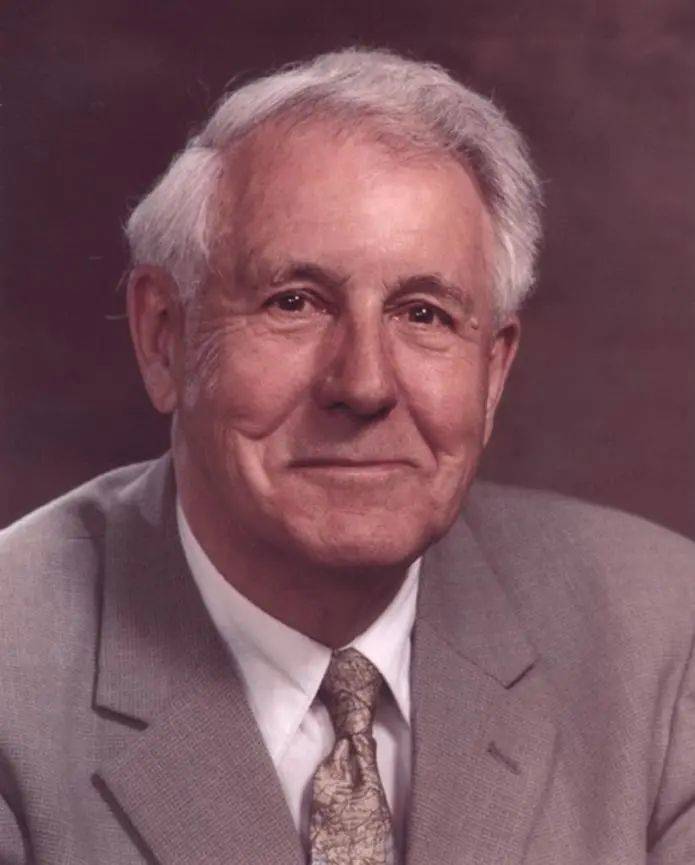
当时学界普遍认为细菌的行为是独立、不依赖于其他个体的。按照这条思路,如果菌体数量增加一倍,同时间里,光亮强度也应该增加一倍。可是在1970年,黑斯廷斯注意到费氏弧菌和哈维氏弧菌(Vibrio harveyi,1936年以哈维命名)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新接种的培养基里,菌体的数量每30分钟就能够增加一倍,但发光却需要2个小时以上才开始增强,继而亮度每5分钟增强一倍。
与此同时,细菌还不断地向培养基释放一种名为高丝氨酸内酯的分子( homoserine lactone,简称HSL),而且只有当HSL达到一定浓度时,被抑制的特定基因才启动转录程序,细菌才能绽放魅力四射的光芒。这是有记载以来科学家首次发现群体感应现象。
黑斯廷斯将信号分子HSL称为“自诱导物(autoinducer,简称AI)”,因为不同于外加的诱导物,HSL既能诱导基因的表达又由细菌自己产生。
对于新生事物或者新学说,大众总是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有时候甚至充满着抵触情绪。就像历史上许多做出重大发现的人一样,这一次,黑斯廷斯也处于类似的境地,学界非但不接受他的发现,反而冷眼嘲讽。
二、语言系统遭破解
阿格隆研究所(Agouron Institute)的西尔弗曼(Michael R. Silverman)是个例外。他认为黑斯廷斯的发现极其有趣,并于1980年代找到了群体感应的核心分子机制。在费氏弧菌中,西尔弗曼发现LuxI蛋白催化合成AI分子,作为受体的LuxR蛋白则结合AI,继而激活编码荧光素酶的基因的转录。
接下来,他又进行了大肠杆菌转化实验,经过改造后的大肠杆菌能够产生信号分子HSL,也能利用它感知菌体浓度。当菌体浓度达到阈值时,大肠杆菌就开始发光。陆续地,他找出了能够产生和检测细胞外信号分子的基因和蛋白质,并向学界全面诠释了这些组件如何激发群体感应。
西尔弗曼很少公开演讲,一直像“隐士”般地存在于科学界。一次机缘巧合,正值博士毕业之际的巴斯勒(Bonnie Bassler)听了一场他的讲座,演讲的内容便是细菌如何通过群体感应启动发光系统。巴斯勒感觉这太美妙了,细菌竟然能够投票表决何时开灯!更重要的是,她察觉到发光细菌作为遗传学研究材料的便利性,只要随手按下实验室的电灯开关,看看细菌有没有发光,就可以知晓实验结果。
讲座一结束,她就直奔讲台,向西尔弗曼表示要跟他做博士后。西尔弗曼被她的研究激情感染,当场给了工作允诺。这一富有戏剧性的开端,成为了巴斯勒出席各种公开演讲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一幕。收获一枚得力干将之后,慷慨的西尔弗曼便将群体感应的研究完全移交给了她,再次退居乡野。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找到了信号分子以及相关基因和蛋白质,也大致清楚细菌发光系统的运作流程,但都没有对细菌的这一群体现象进行正式命名。1978年,黑斯廷斯的一位博士后格林伯格(E. Peter Greenberg)在康奈尔大学开始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团队,同样利用费氏弧菌做着相似的工作。生物研究耗时耗力,道阻且长,直到1994年,发光细菌的这一群体行为终于在格林伯格研究团队的一次头脑风暴中拥有了一个正式名称:“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 。
这一领域当时相当前沿,想要获取学界的广泛关注,名字也必须稍有特色。果不其然,“群体感应”这个名称逐渐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接受,关注和研究它的科学家也越来越多,日渐形成了一个较有规模的群体。目前,全世界已经有几百家实验室在从事相关研究。
然而,于1990年抵达阿格隆研究所的巴斯勒并没有将费氏弧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而是转向了哈维氏弧菌。巴斯勒发现,哈维氏弧菌与它的同种细菌交流时,也是依赖一种HSL自诱导物。不同的是,哈维氏弧菌还会释放另外一种化学分子来激发种间的群体感应。也就是说,哈维氏弧菌具有两套不同的群体感应系统,第一种自诱导物用于种内交流,称为AI-1;第二种自诱导物用于种间交流,称为AI-2。原来,细菌不仅不自闭,反而更像是语言天才。
科学家这才意识到,细菌世界还可能像人类一样存在多种语言。后来的研究发现,细菌们甚至还有一种世界通用语。自诱导物不仅仅有HSL,即常见的酰基高丝氨酸内酯类(Acyl-homoserine lactones,AHLs),还有其它类型:譬如,革兰氏阳性菌一般利用寡肽类信号分子(Autoinducing Peptide, AIP),弧菌类特有霍乱自诱导物(Cholera autoinducer 1,CAI-1),以及种间交流信号分子为呋喃酰硼酸二酯(Autoinducer-2,AI-2)等等。
这些信号分子的发现凝结着众多研究者的心血,也是他们探索之路上的必然结果。必然性常常隐藏着偶然性,甚至有时候还有浪漫色彩从旁点缀,比如AI-2的晶体结构解析就稍带传奇性。当时,巴斯勒刚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独立领导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不久,她便和晶体学家休森(Fred Hughson)共同解析出了实验条件下生产出的AI-2的晶体结构。
分析结果惊呆了在场的所有研究人员,因为AI-2分子中竟然含有硼原子,而元素“硼”在自然界极其少见。更不可思议的是,硼来自玻璃试管 。玻璃公司为了提高玻璃性能往往会参杂一些硼元素,而这微量的硼元素完美地还原了弧形菌在自然界中的生活环境。
试想下,倘若当年他们用的是不含硼的塑料试管,也许AI-2分子结构的秘密就没有那么早被发现!有趣的是,不同细菌会对AI-2进行不同的化学加工,因此AI-2就成为了细菌世界里的通用语言。
更加有趣的是,有些细菌还能利用这种通用语言来欺骗其它种群。比如,巴斯勒发现在一个混合多个菌种的菌群里,大肠杆菌会消耗霍乱弧菌的AI-2,让它们以为群体数量没有达到群体感应所需阈值。霍乱弧菌致病关键就在于,它会启动群体感应来释放毒素,继而导致宿主腹泻。当霍乱弧菌发现自己未能达到群体感应所需的数量,则趁机溜出宿主体外,伺机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如此说来,肠道里的大肠杆菌或许可以通过干扰群体感应来阻止霍乱弧菌的感染和进一步的传播。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们现在知道,群体感应能在细菌中开启或者关闭数百个基因表达。也就是说,细菌的交流过程启动了一个巨大的遗传程序。这个过程类似于胚胎的发育,它使细菌能够快速完成从个体成员到群体成员的转变。群体感应还调控着细菌的许多其它行为,比如生物被膜的形成、致病因子的产生、抗生素的合成、质粒的接合转移以及细菌的迁移运动等等。
这些行为当中有一些均与细菌的致病机制相关。前文提到的格林伯格就是这方面的领衔人物。自独立领导研究团队以来,他除了研究费氏弧菌,还研究螺旋体,并在后一领域里颇有建树和富有一定的影响力。1988年,格林伯格回到母校爱荷华大学之后,开始专注于费氏弧菌中的LuxR蛋白的研究。

当时西尔弗曼已经研究清楚,LuxR蛋白是由自诱导物激活的转录因子,再反过来与自诱导物结合,参与细胞的群体感应。后来,格林伯格领导的团队发现LuxR蛋白的C端保守,N端可变。C端有30%序列保留了激活发光基因的能力,但不需要信号分子。距离N端最近的60%序列可以结合信号分子,但不能影响基因的转录。
也就是说,他们进一步弄清楚了LuxR蛋白参与群体感应的分子机制,这距离细菌语言系统的完全破解又更近了一步。格林伯格当机立断地停止了螺旋体的相关研究,全力以赴地进行群体感应的“信号”研究。
一次会议中,他偶然得知罗切斯特大学的伊格莱夫斯基(Barbara Iglewski)实验室找到了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又称绿脓杆菌)的致病因子的调控基因,其中有一段基因序列与LuxR基因高度同源,这说明群体感应可能与致病因子的产生密切相关。一阵交流后,他与伊格莱夫斯基两人一拍即合,立即决定开展合作,重点关注铜绿假单胞菌的群体感应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群体感应控制着许多与致病因子相关的重要基因。
值得一提的是,铜绿假单胞菌广泛存在,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呼吸道和肠道中都有踪迹。但是,它又是一种条件性致病菌,是医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同时,它还是囊性纤维化病(CF,cystic fibrosis)患者的致命杀手。
CF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疾病,高发于高加索人群,美国约有35,000人受之困扰。患者的粘液过于粘稠,肺部难以排出细菌,使得感染相对容易发生。如果铜绿假单胞菌在细胞浓度较低时就产生毒力蛋白,这无疑是在提醒宿主尽快启动免疫反应。但是,铜绿假单胞菌非常聪明,它们在自身细胞浓度相当高时才开启群体感应,产生毒性蛋白,破坏肺部组织,达到严重损害肺部功能的目的。
治疗过程中,CF患者需要不断地使用抗生素。然而,铜绿假单胞菌天生对大部分抗生素有抗药性,而且能快速地产生抗药性突变,这真是雪上加霜!多年下来,CF病患最终受困于无药可治的泥沼里,任由疾病折磨直至凋零。如果有一天能够开发出群体感应的抑制剂,CF患者或许就能得以解脱。
黑斯廷斯曾经在一个采访中说过:“相比癌症这样实践性非常强的研究领域,生物发光或者昼夜节律是非常基础的研究,研究人员对它的热爱必须发自肺腑才行。”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生物发光的研究,科学家们才逐步将他的“群体感应”发扬光大,如今又不知不觉地将基础研究引入了实践之中。
三、病毒在窃听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联手药物研发公司,尝试开发群体感应抑制剂,希冀为对抗疾病带来新技术,让患者不再被细菌的耐药性困扰,尽早进入“后抗生素时代”。
令人头痛的是,很多狡猾的细菌耐心十足。它们知道,凭借一己之力,单个细菌会被宿主轻易地清理消除。于是,它们静静地复制、分裂、变异,等候时机成熟,直到它们认为群体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才发起集体行动,协同作战,攻击宿主。可见,它们绝非“乌合之众”。正因如此,科学家群体和医药公司目前还没未开发出可行的药物来对付细菌的“群体感应”,攻破细菌堡垒。
就是这样一群“精锐之师”,亦有天敌。世界上早已经有其它物种比人类快一步破解了它们的秘密,那就是噬菌体——一种侵袭细菌的病毒。
一天,巴斯勒的一位研究生西尔佩(Justin Silpe)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认为病毒会窃听细菌的交流。巴斯勒虽然心存质疑,但是仍然让他自由探索。西尔佩用一种叫做VP882的噬菌体去感染沙门氏菌。他观察到,噬菌体会提取宿主的分子信号,但并不参与细菌的交流,而是利用它来决定攻击细菌的时间。当信号越来越强时,病毒就知道细菌的群体规模已足够大,是时候产生子代、裂解宿主了!释放出的新噬菌体再去感染其它的细菌,让细菌大军全军覆没。
就在西尔佩发表该项研究成果的前一年,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证实了病毒中也存在着交流系统。索雷克(Rotem Sorek)和他的团队本来想利用噬菌体感染细菌,再观察细菌对噬菌体的反攻是单打独斗还是群起而攻之,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细菌很安静,病毒在喧嚣,原来病毒正在用自己的语言传递信息。噬菌体知道在宿主细胞里什么时候该潜伏,什么时候该进攻。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索雷克发现噬菌体应用的信号分子是一种寡肽类,并将这种分子命名为“仲裁员(arbitrium)”。
通过对病毒的研究,科学家对微生物们的群体感应系统又多了一分了解,为对付微生物感染找了新的突破口。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微生物无处不在,并且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科学家们的愿景虽美,但路漫漫其修远兮!
主要参考资料
[1](法)古斯塔夫·勒庞著,董强译:《乌合之众:群体心理学》,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2] Frank H. Johnson, Edmund Newton Harvey (1887-1959),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67。
[3] L. Stephen Coles, Bernard Strehler(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ofessor of Biology), Journal of Anti-aging Medicine, Volume 4, Number3,2001,p:233-234。
[4] Tinsley H. Davis,Profile of J. Woodland Hasting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Jan 2007, 104 (3) 693-695。
[5] Farooq Ahmed,Profile of Bonnie L. Bassler,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pr 2008, 105 (13) 4969-4971。
[6] Tinsley H. Davis,Biography of E. P. Greenberg,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ov 2004, 101 (45) 15830-15832。
[7] 美国疾控中心网站关于囊性纤维化的介绍。https://www.cdc.gov/genomics/disease/cystic_fibrosis.htm#:~:text=Cystic%20fibrosis%20(CF)%20is%20a,makes%20infections%20more%20likely%3B%20and
[8] Bernard L. Strehler, Milton J. Cormier, Factors Affecting the Luminescence of Cell-Free Extracts of the Luminous Bacterium, Achromobacter fischeri, Archives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1953: p16-33。
[9] Susan Brink, A Virus Can Eavesdrop On Bacterial Communication, December 13, 2018. https://www.npr.org/sections/goatsandsoda/2018/12/13/676389858/a-virus-can-eavesdrop-on-bacterial-communication
[10] Elie Dolgin, The Secret Social Lives of Viruses, Nature, 18 June 201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1880-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洪纬,审阅指导:耶鲁大学严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