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68期,作者: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文标题:《古典中国与当代乡村——从建筑人类学的视角》,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标题(原题)就放下“建筑人类学”“古典中国”“当代乡村”三个“大词”,注定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吃力不讨好。
先说“建筑人类学”。应该说,在中国,这还不是一个广受认可的学科名称。尽管“建筑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开到了第五届,但它依然更像是一个建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年轻学者开展思想交流的平台。之所以叫“建筑人类学”,固然不乏尝试去开创、建设一个新学科分支的野心,但也可将之解读为“建筑学与文化人类学交叉学科研讨会”的简称。
在国际学术界,维克托 · 布克利(Victor Buchli)的专著《建筑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出版于2013年,在时间上相当晚近。该书的两位中文译者潘曦和李耕,正是“建筑人类学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发起人,潘曦更是在2020年推出了自己的建筑人类学专著——《建筑与文化人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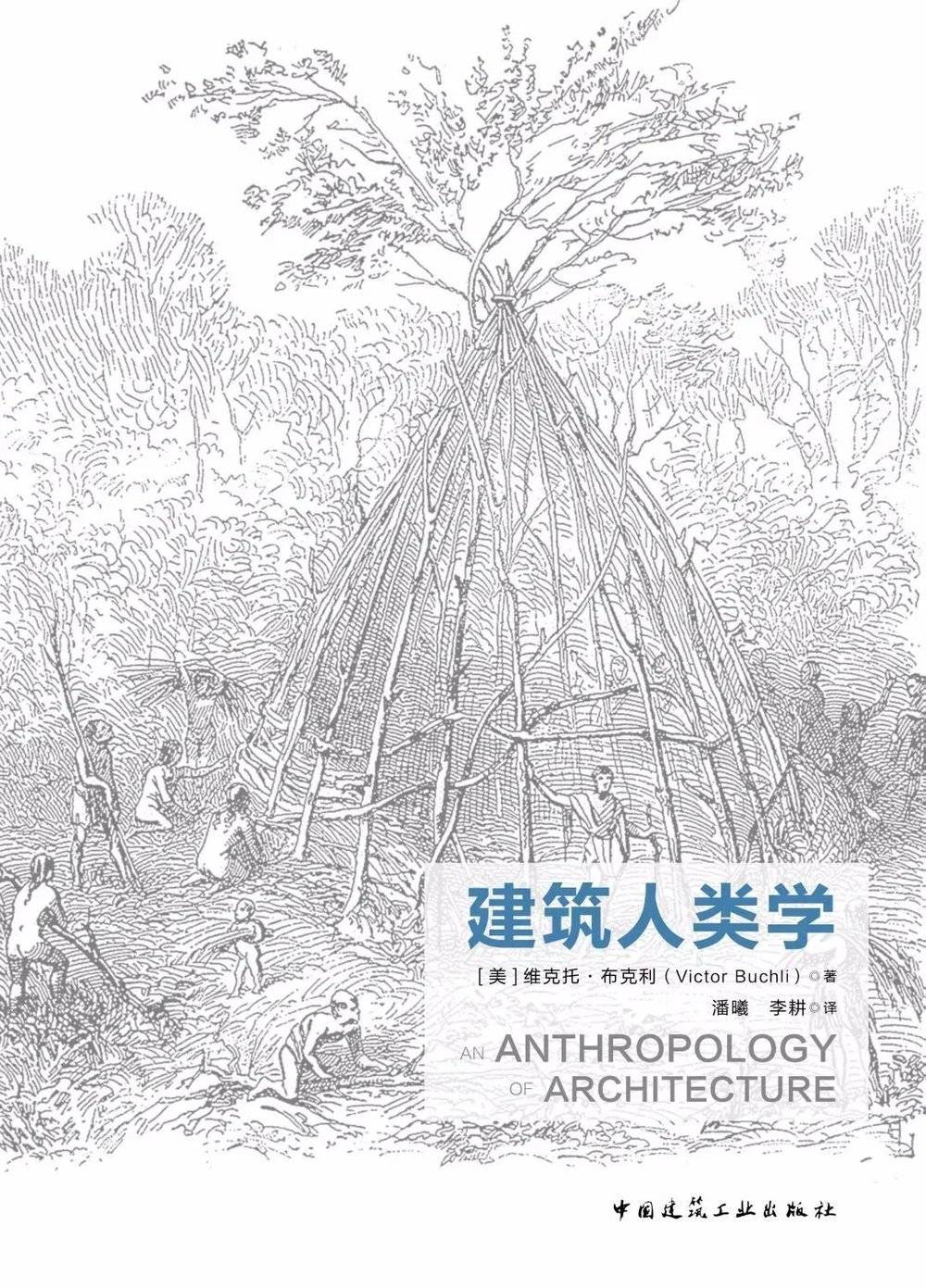
《建筑人类学》开篇基于18、19世纪时人类学对建筑的思考,提出了“人类心理一致性”的概念,之后分章讨论了建筑与考古学、家屋与社会关系、建筑与制度建构、消费与家庭、身体与建筑、建筑形式的破坏等议题。
对“建筑人类学”的默认的解释是“建筑的人类学”。换言之,如果要严格地遵守该命题,就要把人类学作为理论、方法和工具,应用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建筑之上。在此前提下,要拆解的对象是建筑,而不是人类学。《建筑人类学》勒口处的内容简介也说明,“全书讨论的范围覆盖到了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
在章节安排上,第三章讨论小型定居社会,第四章讨论城市(即大型定居社会)中的若干建筑类型,第五章讨论建筑在社会流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第七章讨论建筑形式被破坏之后的生产性效果,这几章确实暗含了将建筑作为分析和拆解对象的意图,甚至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纵观全书,各个议题之间的相关性仍不够显著,还不能形成很好的拼图或串联关系。这可能并不是作者的思考水平不到位,而是代表了“建筑的人类学”本身所遭遇的困难。

潘曦的《建筑与文化人类学》,从书名就能看出来,建筑与人类学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在架构上,全书以文化人类学的不同学科分支为线索,分别选择和分析作为研究对象的建筑,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章至第九章的议题分别为:建筑与文化进化论、建筑与文化多样性、建筑与社会功能学派、建筑与结构主义、空间与身体、建筑与社会建构、建筑与权力制度、建筑遗产与身份认同。
如此架构,坏处和好处都很明显。坏处是:由于各章议题相对独立,所以距离“建筑的人类学”似乎更远了,也就是暂时搁下了建设一门学科的野心。好处是:全书的内容更加清晰明了, 尤其是作为一本建筑系的教材,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学生了解文化人类学不同分支的学科特点,以及目前被认为适合作为研究对象的建筑类型或空间场景,从而在自己做研究、写论文的时候更容易选择合适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了解《建筑人类学》《建筑与文化人类学》这两本书的大致内容和特点之后,读者或许也就能理解,本文“从建筑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古典中国和当代乡村,并不是要用“建筑人类学”的学科理论来分析古典中国和当代乡村,而是要借助文化人类学中的某些方法和角度,来观察古典中国和当代乡村中的某些具有互动关系的建筑、空间现象。
“古典中国”似乎也不属于“正规”用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古典”一词的解释是:(1)名词,典故;(2)形容词,古代流传下来的在一定时期认为正宗或典范的。我们通常会说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园林,而不会把“古典” 加到“中国”的前面。用“古典”来形容某一类文化或物品是可以的,但用来形容一个国家似乎就会显得奇怪。
不过,这一用法大概也不算我的发明,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曾出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名著,把“乡土” 这个形容词放在了“中国”前面。如此,“乡土”这个原本带有土气的词汇似乎瞬间有了登堂入室的高级感。
既然有乡土的中国,就不妨有古典的中国。“古典中国”的“诞生”,源于松阳县政府在2014年委托给我们团队的一个任务。当时的松阳县在前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申报中成功上榜了50个村落,一跃成为华东第一、全国第四。由于前三名的县都在云贵两省,所以松阳县的这些传统村落俨然成为“捍卫”华中和华东地区,进而“代表”广大汉族文化地域的“排头兵”。

规模效应是暂时起来了,但接下来的问题仍棘手而迫切。保护是需要资金的,钱从哪里来?修缮维护、改造利用是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的,人才怎么培养?旅游业是不能没有的,但单个地看松阳县的众多古村,都远不如宏村、西递(甚至与附近的兰溪诸葛村也有明显差距),怎么能对外界产生吸引力?就算旅游业做起来了,又该如何避免旅游业经常会带来的文化异质化后果?这一系列问题, 每一个都很难应对,更别说将它们同时摆到桌上。我们似乎需要先做一个整体的资源梳理和价值判断。
我们的调研团队对松阳全县50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以及部分虽未入选但保存仍比较好或比较有特色的村落,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这几十上百个古村落做一个整体的、高度的概括,是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且反复讨论的话题。
其实,在此之前,松阳县已经有了“田园松阳”“最后的江南秘境” 的旅游宣传口号和文化名片。这两张“名片”并非不好,甚至可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松阳本身的特色,但是总感觉它们的文化高度还不够,我们是否能找到更有高度和概括性的文化定位呢?
首先给我们启发的,是陈志华先生对中国乡土建筑的价值判断。陈先生是1947年上的清华大学,当时就读的正是费孝通先生所任教的社会学系。陈先生在1989年开始乡土建筑研究时,曾提出用“乡土建筑”来取代“民居”作为正式的学术词汇,一度引发学术争论。这一主张,显然跟他早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上过两年学有着深厚渊源。从“乡土中国”到“乡土建筑”,也可以说是从人类学到建筑学的学术薪火传递。

2008年,陈先生在具有学术总结性质的文章——《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中提到,“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乡土建筑遗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可以凭借它的乡土建筑对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做出重大的贡献,原因在于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里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
他还写道:“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给中国乡土聚落带来了大量艺术水平很高的建筑,这些建筑无论在结构技术上、功能型制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是中国传统乡土建筑最典型、最高水平的代表作。这三大类辉煌的建筑又是中国所独有而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无的。”[1]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 · 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20世纪50 年代提出过“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影响很大。我在2005年前后读到雷氏的理论,觉得挺有启发,于是就在自己的乡土建筑研究报告里拿它来分析了当时的调研对象。没想到陈先生看过文稿后,在旁边写了这么一句批注:“这是美国人搞出来的理论,在中国使用要小心。”言下之意是,别被人家带跑了。说老实话,我当时多少有些不服气,想着就算雷氏是“美国的”学者,能有这么大影响,总不会一无是处吧。
几年之后,我有机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在一次研讨会中我以“Chines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中国乡土建筑》)为题,给研究伙伴们做了20分钟的分享。讲完之后,来自南美洲、中美洲、印度尼西亚、叙利亚等地的朋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你讲的这些建筑,都很grand(辉煌)啊,根本不像Vernacular Architecture!

国际伙伴们的这番话让我突然意识到,相比马来西亚的高脚屋、哥伦比亚的棚户这些欧美学者眼中“地道的”乡土建筑,中国的很多乡土建筑确实过于“辉煌”和“正统”,并不适合放进“乡土建筑”这个筐里。
由此,我也想起陈志华先生在《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中的观点。对啊,这不正是中国跟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吗?中国的乡土建筑不仅仅局限于小传统,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承接甚至参与塑造了作为上层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周礼最重要的实践场所也许就在农村社区。[2]在中国,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野并不那么清晰,而是在互动中形成了完整的中华文化。
我后来在读葛兆光先生的书时,也看到了类似观点。他在《宅兹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而在宋代之后逐渐凸现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唐宋以来一直由国家、中央精英和士绅三方面合力推动的儒家(理学)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使中国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3]

葛先生的这段话,针对的是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的“民族主义造就民族,而非民族造就民族主义”的论述。安德森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学者,但是毫无疑问,他的这部经典名著也相当有人类学色彩。可以说,《宅兹中国》和《想象的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学和国际人类学的一次对话。
陈志华先生对中国乡土建筑的价值判断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给予了中国乡土建筑一个极具文化高度又理由充分的“定位”。有了这个定位,我们就可以从具体的资金和技术问题中跳脱出来,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如何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高度,来思考到底为什么要研究和保护我们的乡土建筑。
这跟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1999年发布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的核心精神——乡土建筑遗产在人类的情感和自豪中占有重要地位——高度匹配,甚至可以说更有学术分量。
既然中国的乡土建筑可以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松阳县的传统村落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呢?
松阳县传统村落的优势是数量多、成规模。造成这种数量和规模效应的基础是“全县域”。那么,在全县域范围之内,除了传统村落,是不是还有其他文化遗产资源可以整合起来,让“县域” 的特点更为突出?
至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松阳的县城西屏镇,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只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是“乡村研究者”而在几十次来松阳的差旅中对它几乎视而不见; 我们又想到,只要来到松阳,每天都要喝上不知道多少回的端午茶,以及跟端午茶一样依然鲜活存在于松阳百姓生活中的种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跟松阳乡村和县城古镇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依存和互相成就的。

全县域的古村、保存完整的县城和丰富多样的非遗,构成了多层级、有机的文化空间。这样的空间让我们想到了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它仿佛把每个县都打造成了一个“微型中国”。在“县” 这个地理空间单元内,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大一统文化的几乎所有要素。所以,“古典中国”的最小地理单元就是县。
有了这个思路,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番比较,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松阳在“古典中国”的代表性上虽然比不上江南核心地区诸县,但其要素和空间是齐备的;假如时光倒流十几年,“古典中国”的桂冠一定轮不到松阳来戴,但当现在江南核心地区的传统村镇大多已消失时,松阳反倒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县。
再来看当代乡村。从上文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古代的乡村是兼具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换句话说,它们一方面是正统文化的承接者和塑造者,另一方面也是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地方性知识的制造者。地方性知识,又是近年在人类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议题。反对文化进化论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独特之处,相互之间没有优劣高低之分。
克利福德 ·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则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编织的“意义之网”,认为人类学家应该“尝试透过将社会现象安置于当地人的认知架构之中以寻求解释”。对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视,正是1964年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乡土建筑展并获得巨大影响力的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亚历山大 · 佐尼斯(Alexander Tzonis)提出并经肯尼斯 · 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发扬光大的“批判地域主义”,在建筑学领域也受到了广泛拥护。[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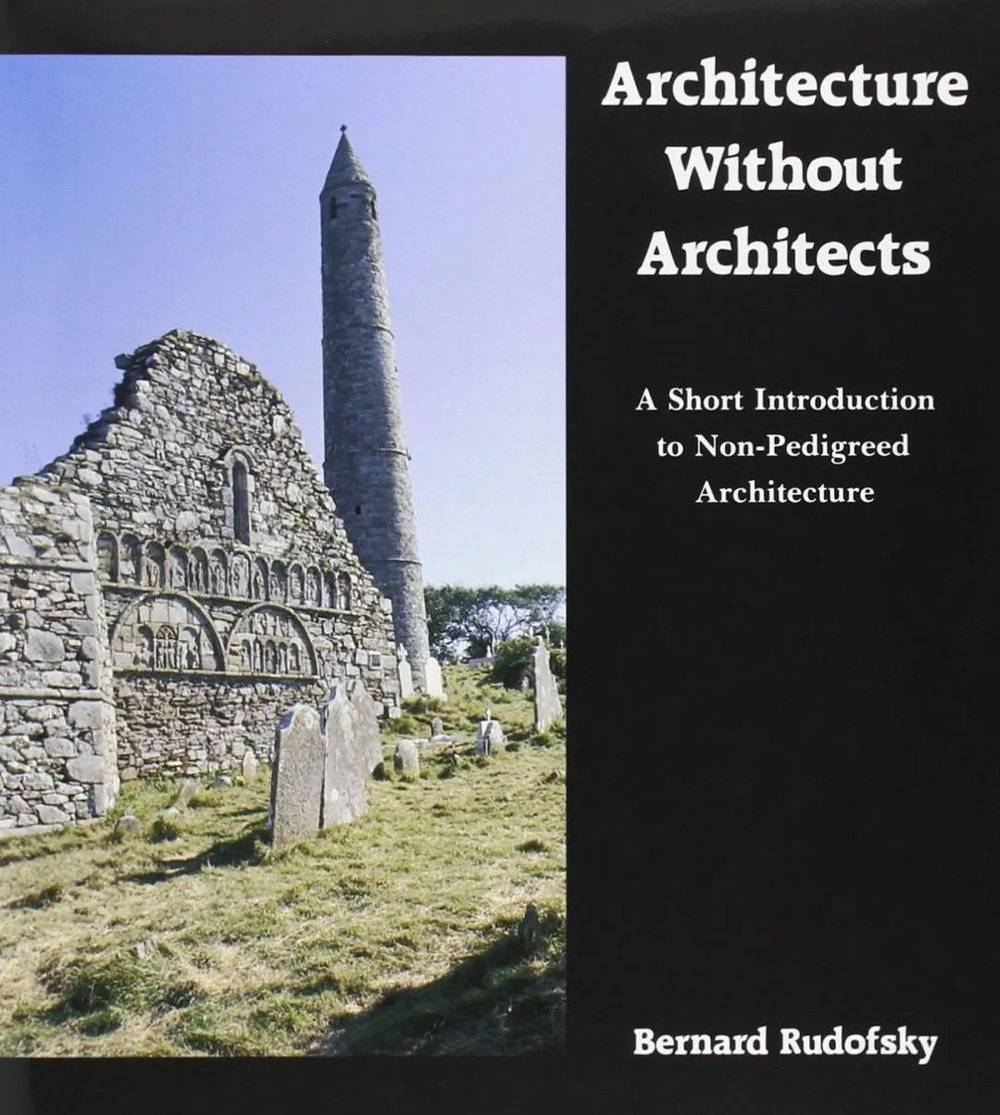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对于乡村的价值的判断,即乡村“在人类的情感和自豪中占有重要地位”,跟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所强调的“历史信息”很不一样。“历史信息”是个很有“科学范儿”的词汇,这是《威尼斯宪章》获得全球同行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遗产跻身“科学”阵营的基本理由。“情感”和“自豪”,则是充满了人文主义尤其是人类学味道的词汇。这是一个重要的范式转换。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的起草人很敏锐地意识到,乡土建筑遗产要想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留存,主要不能依靠旅游之类的实际功能和经济价值(虽然现实当中我们经常这么做),也不能靠历史信息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去获得政府部门和基金会的拨款(尽管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保护乡土建筑遗产经常还是离不开政府经费);它最能依赖的,是各个地方的人们在过去的生活中留下的集体记忆,和由此产生的情感性因素。
情感性因素,可以说是“地方性知识的意义”的另一种表达,也是联通古代乡村和当代乡村的一座桥梁,这一点是国际学术界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
在中国,又该如何实现呢?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应该算是一条路径,它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国人的荣誉感。然而,这条路实在太窄(基本上每年只有一个名额),而想走的人又太多(中国之大,每年光是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项目就有几十个),竞争实在太过激烈。可以说,松阳县这几年的乡村实践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也为这个国际学术问题交出了一份中国答卷。
我们在松阳做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最初是为了保留传统民居而不得不为它们寻找新的合适用途。空心化是当下中国农村的大趋势,对抗这一趋势的直接策略就是发展旅游业。
2014年,我们在承担平田村规划任务时,邀请了几位建筑师朋友一起来想办法提升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山村”的吸引力。建筑师朋友各自针对一两栋老房子进行了细心的改造设计,增设了包括民宿、青旅、餐厅、咖啡厅、农耕博物馆、艺术家工作室等功能,围绕村中心的一块小三角地,形成了一个服务于度假的小型综合体。
村里的老房子在外观上看起来都是相似的,双坡瓦顶、木结构、夯土墙,但是建筑师的个人风格又各不一样。改造之后,除了基础设施有所改善,路边景观有所提升,村落的整体风貌几乎保持原样,但是室内的风格却呈现出差异明显的多样性,这也成为平田村对外重要的吸引力所在。作为当时国内较早开展的古村落改造项目,平田村沾了一点“时代的红利”。在政府、业主和设计师的共同努力下,它一时间成为“网红村”,旅游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承担平田村农耕博物馆设计任务的徐甜甜和四合院餐厅设计任务的王维仁,此后在松阳县又承担了一系列设计任务。他们两位都践行了“建筑针灸”的设计理念,徐甜甜还将她的“针灸”主张进一步表述为“要扎在村民最自豪的地方”。这就跟《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的核心精神完全匹配了。
“建筑针灸”系列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是兴村的红糖工坊。当地村民有煮红糖的传统,在松阳县一直颇有名气。原本是由各家各户分散煮红糖,在红糖工坊建成之后,工人被集中起来,不仅高效地利用了土地,工作环境也因从室外转移至室内而得到了改善。
建筑师在现场考察中还发现,煮红糖时土灶上会升起很重的水雾,工人们在水雾里穿梭,就像是在舞台上表演舞蹈,于是顺势而为,在屋顶上设计、安装了一排排聚光灯,专门用来照亮这些“舞蹈演员”。工坊化身为剧场,村民化身为舞者,在这个场景拍出的照片发到网上后,取得了相当好的宣传效果。而宣传效果又产生了品牌效应,使得当年工坊生产的红糖的价格从每斤5元涨到了25元。

兴村的红糖工坊项目当然有其偶然性,它依赖于建筑师考察现场时的慧眼,也离不开设计过程的灵感,我们很难指望每个乡村项目都能有这么巧妙的发现和这么出彩的灵感。但是,它的原理是具有普遍性的,并可大致归纳为两点。
其一,要选择公共空间。兴村的红糖工坊是跟浙江省推行的乡村文化礼堂相结合的,所以它既是部分村民(即红糖手艺人)的共同空间,也是全体村民的公共空间。尽管平田村的改造项目的出发点是为了民宿度假,但也配备了乡村博物馆,而民宿大堂、咖啡馆、餐厅这样的商业项目其实也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
其二,要做到传统性、地方性和现代性的创造性结合。传统代表了历史的记忆,地方代表了文化的认同。作为置身于现代社会的人,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我们都无法拒绝现代化的生活。这两点体现了建筑学和人类学在乡村的结合与碰撞,也是乡土建筑遗产之所以能在人类情感和自豪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答卷。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 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M]//文物建筑保护文集.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8: 98-103.
[2] 苏力. 大国宪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01.
[3] 葛兆光.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26-27.
[4] 潘曦. 建筑与文化人类学[M]. 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20: 44-48, 5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68期,作者: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