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园自杀,来自中科院的最新统计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是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7.4%。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一的中小学生可能存在抑郁倾向。什么令他们抑郁,抑郁在学校如何被发现,发现之后他们会受到学校、老师、同学怎样的对待,他们会好起来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ID:zmconnect),作者:洪蔚琳,编辑:陈晓舒,顾问:魏玲,视觉:梁爽,插画:陈禹,出品人、监制:曾鸣,原文标题:《校园心理老师自述:成绩、霸凌、24.6%的抑郁检出率》,头图来自:《少年的你》剧照
在一个月内,“12岁男孩坠楼,疑因压力太大”,“上海长宁区‘自杀’问卷风波”等新闻再一次引发人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早在2012年,教育部就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心理健康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但我们了解到,许多地区的心理老师是在疫情后政策重申之下“一夜上岗”的,许多学校压根找不到有心理学习背景的老师,他们有的是主课老师兼任,也有体育老师转成心理老师。
而心理老师的日常工作却颇为专业:包括一两周一次心理课,在校心理辅导室接待学生的咨询。
我们找到了其中三位专业的心理老师。他们毕业于同一所重点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是研究生同学。近三年,他们去往北京、深圳、河南不同的三所学校,也看到了三地巨大的差异。
河南老师所在的高中模仿衡水中学,学生们的心理问题大多关于成绩;深圳初中生的困扰则很“深圳”——喜欢的女团解散了、打游戏被家长骂、想转国际学校但家长不同意;北京小学生的烦恼是一些微妙的人际变化:“a跟我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跟b玩?”也会困扰于“为什么不正直的同学反而混得很开?”
我们也能看到这三位老师得到的是学校完全不同程度的支持:北京、深圳的心理辅导老师都是专职的,而河南的老师却需要兼职做政教工作,事实上,后者才是全国更普遍的情况。
当河南的心理辅导老师预算只够买两个枕头,工作重要性在领导眼里“基本是0”时,北京的心理辅导老师却能“坐拥”两间会谈室、休息室和辅导室,工作设备包括音乐治疗椅和宣泄人。
但有一些困境是全局性的——即使在北京,儿童精神科医生也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况;另一些困境是更根本的,青少年不像成年人,他们没有选择,往往只能困在问题家庭、校园霸凌、成绩排名这些压力源里。
以下是心理老师们的讲述:
坐标:河南——“衡水模式”高中


喜欢的女团解散了,学生也会来咨询
我们学校是深圳的重点校,家长大多是高知中产,心理老师这个岗位在我们学校已经存在十多年了。并且,我是一个专职心理老师,不兼任何非专业的工作。去年,我接待了100多个学生,平均每天一个个案,时长超过区教育局对心理老师每年心理辅导时数要求的1/3。
深圳的初中生会有一些我们不太能想到的心理问题,比如追星、追动漫、打游戏。这些对他们很重要,但很难被家长理解,而且支出比较大。有的家长摔手办,引起孩子很大反应。
有女孩会因为喜欢的女团解散了,就来找我咨询。我把这理解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客体:丧失了,就像失去了一个朋友或伴侣,可能程度会轻一点,但本质上是一类事。
这些孩子往往学业压力大、人际交往不适应、亲子关系不好,把追星当作精神寄托。当他们压力很大时,偶像是真的能给到鼓励,但长期又耽误学习,然后压力更大,更沉迷,陷入恶性循环。
他们说“好想死”、“想跳楼”,但大多是想寻求情感支持
个案中,9/10都是学生主动找我的。其实并不容易——要对老师建立信任,还要克服说出自己不好一面的羞耻感。
心理课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机会。我们每个班两周一次课,我上课的目标不是纪律好,而是要建立关系。当他们很吵,我就说,我注意到现在你们有些兴奋,能不能安静一下,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我尽量不评价和批评他们。
这样熟了之后,经常是我走在路上,就会有学生对我说,啊心理老师,成绩出来了,我好想死——他们很爱在我面前说“好想死”、“想跳楼”,但大多是想寻求情感支持。这时我会拍拍他,说快跟我说说,怎么了?听他讲完,安慰完,我会邀请他来咨询室聊一聊。
慢慢就有学生主动来咨询室了。他们通常会说,老师,我有点“难受”——孩子们还不会描述具体的情绪或感受,只会说“难受”。要么就是A带着B来,说老师,B想跟你聊聊。
班主任送霸凌者来矫正,我更关心他为什么施暴
也有不到1/10是家长、班主任转介绍的。家长求助是因为孩子手机成瘾、厌学、在家发脾气不沟通。老师来求助,主要是学生实施了霸凌或有行为问题。但往往心理老师和班主任的视角不一样——我更关心他为什么选择施暴,而不是对他进行思想矫正。
出现校园霸凌后,我经常会连着接两方的咨询:前一个是受害者,下一个就是施暴者。这时我会尽量保持中立。因为这些施暴的孩子,自身也有很多痛苦和局限。他们的家庭,要么管教无力,要么就是也存在暴力。他在家里是受虐者,在学校就变成施虐者。
有一个施暴者,爱说他们班谁谁娘娘腔,谁谁公主病,班上一部分人还很认同他,会跟着他起哄。班主任把他带到咨询室,他很不配合,我俩面对面坐一节课,大部分时间在沉默。后来,他说:我觉得来这儿的都是很脆弱的人,说他们班谁谁,被他欺负了,来咨询室哭一下就得到了同情,回去的时候还拿着一个巧克力。
他爸妈对他比较严。他身上有股江湖气,认为男生就不该掉眼泪,不该露出脆弱的部分,所以他对其他人的这些表现非常鄙视,来咨询也会让他觉得有些羞耻。
我就对他说,其实来找我聊的人有好多,并不是像你说的都有问题。然后,我会跟他聊聊他感兴趣的事。
一次访谈,我几乎帮不到他什么,但可以建立下关系。之前,他会故意在我的心理课上写作业,也不听讲。但后来,他在课上会跟我互动了,也不再写作业。我想,未来他如果遇到什么事,也许会想到找我。
当女孩要自杀时,我感觉我学的专业知识都忘记了
在我的辅导案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危机干预事件。那天下午,一个初三女孩走进心理咨询室,很明确地跟我说,她想要自杀。
我认识这个女孩,她遭遇过校园霸凌,成绩不太好,亲子关系也很糟糕。从前,她找我做过几次咨询,后来就断了。这次时隔一年,她又来了,对我说她和最好的朋友绝交了,彻底失去生活的支点,再加上初三压力大、家里长期对她语言暴力……所有这些堆在一起,她就撑不住了。
我俩坐在咨询室,她反复说想死。我一直听着,帮助她平复情绪、做安全计划。中途,我让班主任联系家长,可是家长没有到学校。一段时间后,我看她情绪稳定了,就让她出了咨询室,先回教室。
结果放学后,女孩还是站到了附近一栋楼的楼顶。
她最终被救了下来。
但事后,我一直在反思,我为什么会放她走啊?我明明应该一下午啥也不干,耗着,就等家长来把她接走。我发现,每一方包括我自己,都会在应激状态下生成防御。我当时想的是:我已经通知了家长,家长应该会配合,会保护好她的。而家长的想法是,孩子在家经常喊死喊活,是在发泄情绪,不是真的要实施。
在此之前,我希望让危机干预流程化。但事情真的发生了,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制定的危机干预手册老师们是否认真读过?我们也没有实践过。在那一刻,我感觉我学的专业知识都忘记了。
家长不配合,心理筛查也没用
其实,这个女孩入学时就被我们筛查出是高风险。
区里有统一要求,各中学近5年都要做新生筛查。风险分两个等级。二级预警是指可能有焦虑障碍、强迫,或有些抑郁发作的症状,这些学生我们会请班主任帮忙观察,简单访谈,并强调要保密。一级预警是高自杀风险,有明显的精神病性的症状,比如幻觉、妄想。会由两位心理老师做访谈。
今年,我们筛出每个班(48人左右)平均5到10人有风险。特别严重、典型的抑郁症不多(全校确诊的在30人左右)。
目前,筛查结果不会跟着学生档案走。但今年,上级有新规定,要求各校把已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名单、联系方式、身份证号报上去。在我看来,这违反伦理。所以我们将这些信息进行了隐私保密处理才上报,也就应付过去了。
中等程度的个案,一般学校老师都装作没事人,不会对孩子区别对待。但对确诊了的孩子,老师们会在学业上对他们网开一面。我们很少建议孩子休学,强调“遵医嘱”。但现在精神科医生也很少做出明确判断,还是让家长自己做决定。
问题就在于,一些家长对就医不太配合,说“好好的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就是学业压力大,拿心理问题来当借口”。
那个走上楼顶的女孩,开学时我们就建议家长带孩子就医。我和她爸妈分别沟通过好几次,说不动,也没有办法。
危机事件后,家长终于带她去医院了。医生建议住院,他们不愿意,签了保证书说还想回学校试试,后来发现她上学真的不行,就休学了。
成年人不开心可以换单位、搬出去,但孩子没得选
虽然我们学校已经非常支持心理老师了,但我感受到的困难是,成年人工作不开心可以换单位,家里有问题可以搬出去,但孩子几乎只能生活在他们的压力源里。如果把我们的工作比作撬地球,成人的反思能力、认知能力、对情绪的觉察也会好一些,你找杠杆稍微一撬,他自己就能动,但跟青少年工作,你会发现你撬不动。
去年,我接过很多长程个案,有两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女孩,来咨询过20多次。她们面临的困难都非常实际:家庭争端、友谊问题、已经确诊的抑郁。我能做的太少,只能是共情。常常有种尽力在做,却发现力量很小的感觉,一个变量就能把你的成果打回原型,比如中考来了,或者家里的纷争。
赖在咨询室的“校霸”们,又回到了厕所
有段时间,咨询室里还聚集了一群“校霸”,五六个,男女都有,会抽电子烟,有时会打架。他们不上课,不是待咨询室就是待厕所。我让他们走,他们就耍赖,说再坐20分钟。
我挨个跟他们聊了厌学的原因,发现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有家庭问题。比如,有的孩子爸妈离异,忽视孩子,让他们自生自灭。
他们在我这儿待着,有时聊天,有时睡觉,有时就是嘻嘻哈哈打闹。他们聊最近新开的咖啡店、怎么炒鞋、他们群体里的一些八卦,还有吐槽爸妈和同学。
起初,班主任还来找我,说别让他们来了。但后来,班主任放弃干预了,跟我说辛苦你了,保证孩子们安全就行了。
他们讨厌学校,觉得很压抑。因为抽电子烟,他们都被通报批评过,也因此承担了一些本不该有的评价。比如有老师说一个女生,“一看就谈过很多次恋爱”、“一看就是那种抽烟打架的”。对这样的话,他们其实很敏感,于是就只能抱团取暖,越抱团情绪越扩大,更难回归。
几个月过去了,我想不能总这样。他们这个状态,就像个毒泡泡,被一团安全气体罩住了,没人去戳它,毒泡泡会一直存在下去。
于是有一天,我对他们说,以后不能在上课时间待在咨询室了。我还给他们拉了个微信群,在群里重申了一下。他们说,对不起。
之后渐渐不来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又回到了厕所。再后来,他们中有人转学、有人休学,小团体渐渐散了。
坐标:北京——九年一贯制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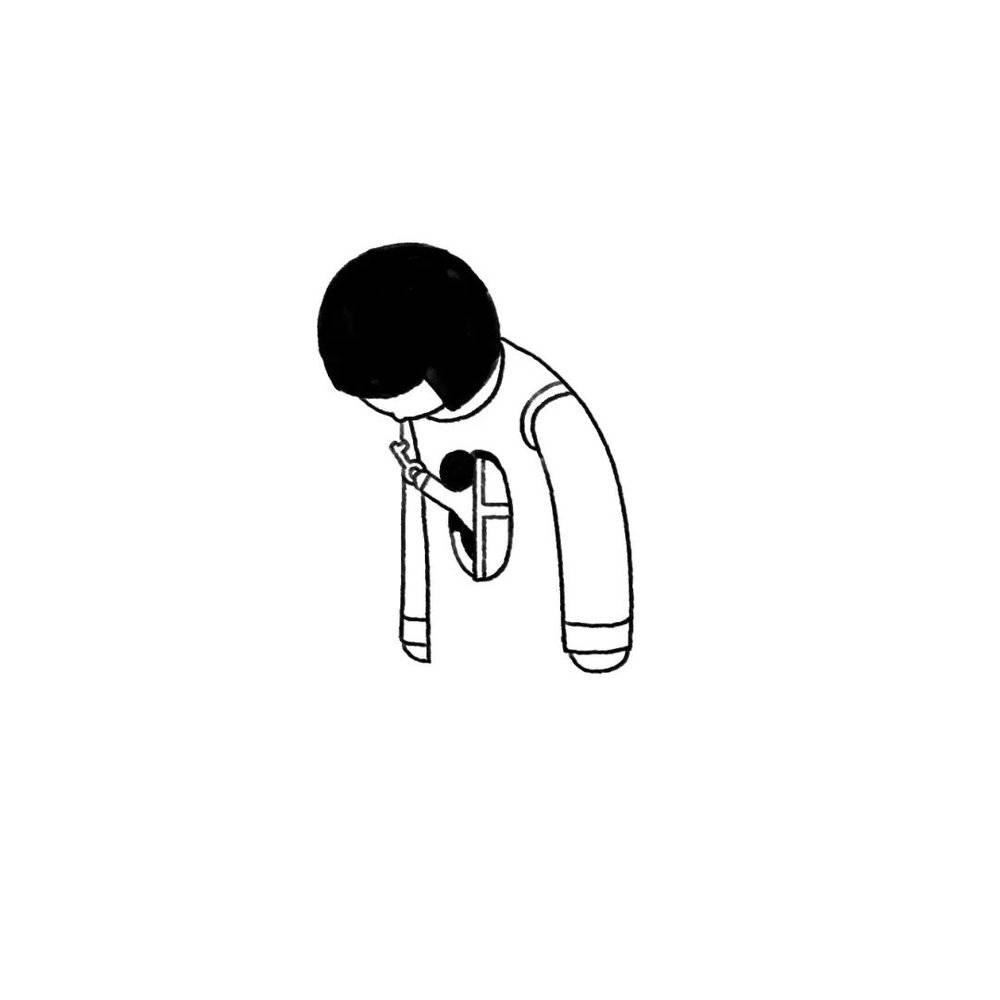
小学生的心理困扰:“a跟我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跟b玩?”
我接待的个案数也和那位深圳老师相近,不同的是,我的来访者很多是小学生。他们还没有太重的学业压力,主要都是人际交往问题。
一些孩子对人际关系微小的变化都很敏感,特别是四、五年级,他们的“朋友”关系很不稳定。曾有一个女生给我讲她对“朋友”的理解:朋友就是我有题不会,她能给我讲。这个描述看起来很轻易,可是一旦失去这样的朋友,她看得很重,要来交流。
另一个女生来过辅导室5次,都是讲自己的人际变化故事,剧情几乎都是“a跟我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跟b玩?而且和b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多”。她反复问为什么。我试着告诉她,选择玩伴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是一件非常自然、现实的事,也会反问她:那你对待不同的朋友是完全一样的吗?但她对我说,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待人接物应该有绝对的公平,为什么会有人对别人很好,却忽略自己呢?
“为什么不正直的同学反而混得很开呢?”
六七年级的学生还有一类心理问题是,班上一些孩子,在老师面前会表现很好,老师一走就马上对同学不友善。有孩子会对这类事很困扰,为什么这些人表面一套、背地一套,老师还很喜欢他们?
孩子们也很看重头衔,当那些“两面”的孩子当了大队干部,他们更会想,为什么不正直的同学反而混得很开呢?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不都是美好的,也有一些阴暗的地方,包括现在媒体很发达,他们自己会掌握很多信息,有时会产生非黑即白的极端想法。
我会共情他们的感受,也会如实地说,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是当前社会现状的一部分。但我不会直接给他们输出价值观,也不会一次就把这些问题讲明白。有时,我会把他们的想法像时空胶囊一样,封存一下,过几个月或者下学期,再跟他们探讨这些话题,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在变化。
我们有会谈室(两间)、休息室、辅导室、音乐治疗椅和宣泄人……
我的大多数日常工作就是面对孩子们这些微妙的心理。除此之外,我们还开展了针对老师和家长的心理工作。每周一次,通过音乐、舞蹈、心理剧这些艺术表达的方式,帮老师们放松身心。另一方面,我们邀请校外专家,来给老师们做心理健康讲座,提高他们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
也有家长课堂,每两周请一位专家线上开讲,比如如何识别儿童的情绪、学习的核心素养,通常都有上百个家长报名。
我所在的学校是北京一所市重点,学校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尤其体现在经费上,甚至比大学的还要多。我们的心理辅导室包括两间会谈室、一个预约等待的休息室、能组织15人活动的团体辅导室(用于心理社团和心理选修课),还放了音乐治疗椅(用于冥想放松的按摩椅)和宣泄人(被打的玩偶)。
想做一年级多动症的测查,但上级担心引起不好的舆论反应
感觉像是在体制内创业:有人给我场地,给我钱,我可以比其他大多数学校的心理老师开展更多工作。但随后我也体验到了,当我想再往前一步,受大环境影响,推进很困难。
我一直想做小学一年级多动症的测查。这些孩子很难遵守规则,容易冒犯别人,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但家长往往不知情,认为孩子是行为问题,还会骂孩子,而一旦错过关键期,三年级后再干预就很难了。
我做了市场调研,想买个针对多动症的测评软件。我想家长可以帮孩子一起填测评,出结果了,就可以跟班主任沟通,也建议家长带孩子去专业机构做排查,这样早发现早干预。
但最后没买,因为区里说,学校最好不要私自去测评。他们担心的是,现在大家普遍对多动症还缺乏认知和理解,做筛查家长会恐慌,引起不好的舆论反应。其实只是规避了麻烦,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上报了孩子的个人信息,却没有得到更实际的帮助
疫情后这两年,从上到下都高度关注心理问题。区里还建了线上危机干预管理系统,让各校把确诊了抑郁症的、有自杀、自伤等极端行为或意念的孩子,信息都填进系统,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心理健康状况、诊断和服药情况。要求30天更新一次。
我们跟家长说,区里建这个系统,能集中各种资源,给孩子一些支持。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些家长同意上报。我们也很期望区里汇总信息后,能有专家给指导,帮助到孩子。
可是,我们上报后没收到任何反馈。我很困惑,那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即使在北京,儿童精神科医生也不够,看病看不过来
严重的个案,需要就医,但儿童精神科挂号并不容易,因此需要有一条从学校到医院的绿色转诊通道,一是方便学生加号,二是心理老师可以和医生形成工作同盟,及时沟通孩子的情况,能更有效率地帮到孩子。
正好我认识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就去拜访他,讲现在学生自伤的问题。医生听了就说,以后像这种超出心理辅导范畴的情况,可以及时联系他,通过学校来加号。
其实,这种合作应该是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的,才更好落地,并且很多大学早就有这样的通道了。之前区里培训,我讲了当前类似的困难,期望区教委可以对接这件事,得到的回复是:老师们,儿童精神科医生太少了,很难满足所有学校的需求。
去年,我听一个北大六院精神科医生的讲座,她也说她真的看病看不过来,要建绿色通道,还是需要更多人力才好实行。所以我也理解,儿童精神科医生确实是稀缺资源。
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一小时收费800元以上,学校很难招到
很多的阻碍,似乎归根到底都是因为缺资源,包括心理老师这个岗位。我们学校早在2017年就开展心理工作了,但在去年我来之前,只有一位心理老师,是教政治的。我面试时,才知道招一个专职心理老师有多难。校长说,这几年他们面试过很多人,但都缺乏实践经验。
(作者注:一位桂林的心理老师告诉我们,当地小学不仅找不到有实践经验的,连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都很难找。疫情前,当地小学几乎没有心理老师。疫情后青少年心理问题加剧,市里要求配备,各校才紧急招聘。情急之下,有体育老师转做了心理老师;也有新入职的心理老师,应付完检查,就转做了数学老师或语文老师)
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都是个性化的、很复杂的,参照教科书上的诊断条目根本不足以准确判断一个孩子的状况。但真正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一小时收费能在800元以上,很难有动力到中小学做一名心理老师。
我是作为应届生被录用的,因为读研时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兼职,积累了300多小时的经验。目前我的想法是,把心理老师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
*数据来源:《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ID:zmconnect),作者:洪蔚琳,编辑:陈晓舒,顾问:魏玲,视觉:梁爽,插画:陈禹,出品人、监制:曾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