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理想国《运气的诱饵》,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娜塔莎·道·舒尔,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你拿起手机,一个接着一个地划着小视频停不下来;当你沉迷于抽卡游戏,一定要抽出SSR才甘心;当你不停买着盲盒,集齐一套才肯罢休……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你?是你玩了游戏,还是游戏把你玩了?
当你沉浸在不知道下一张牌带来的是欧皇还是非酋的命运时,你可能也已经被运气“诱捕”了。抽卡、盲盒、软件界面的设计,其实都暗藏玄机。沉迷于概率的游戏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赌徒。
《运气的诱饵》一书中,作者娜塔莎·道·舒尔对那些赌博成瘾者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和分析,他们沉沦在掌控、失控、受控的深渊中,无法摆脱和机器赌博的强迫性的关系。
在被运气诱捕时,你是怎样把对自我的控制权交出去的?为什么明明很想停下来,却还是不受控制地继续刷着手机,玩着游戏?阅读今天分享的文章,或许会让你有所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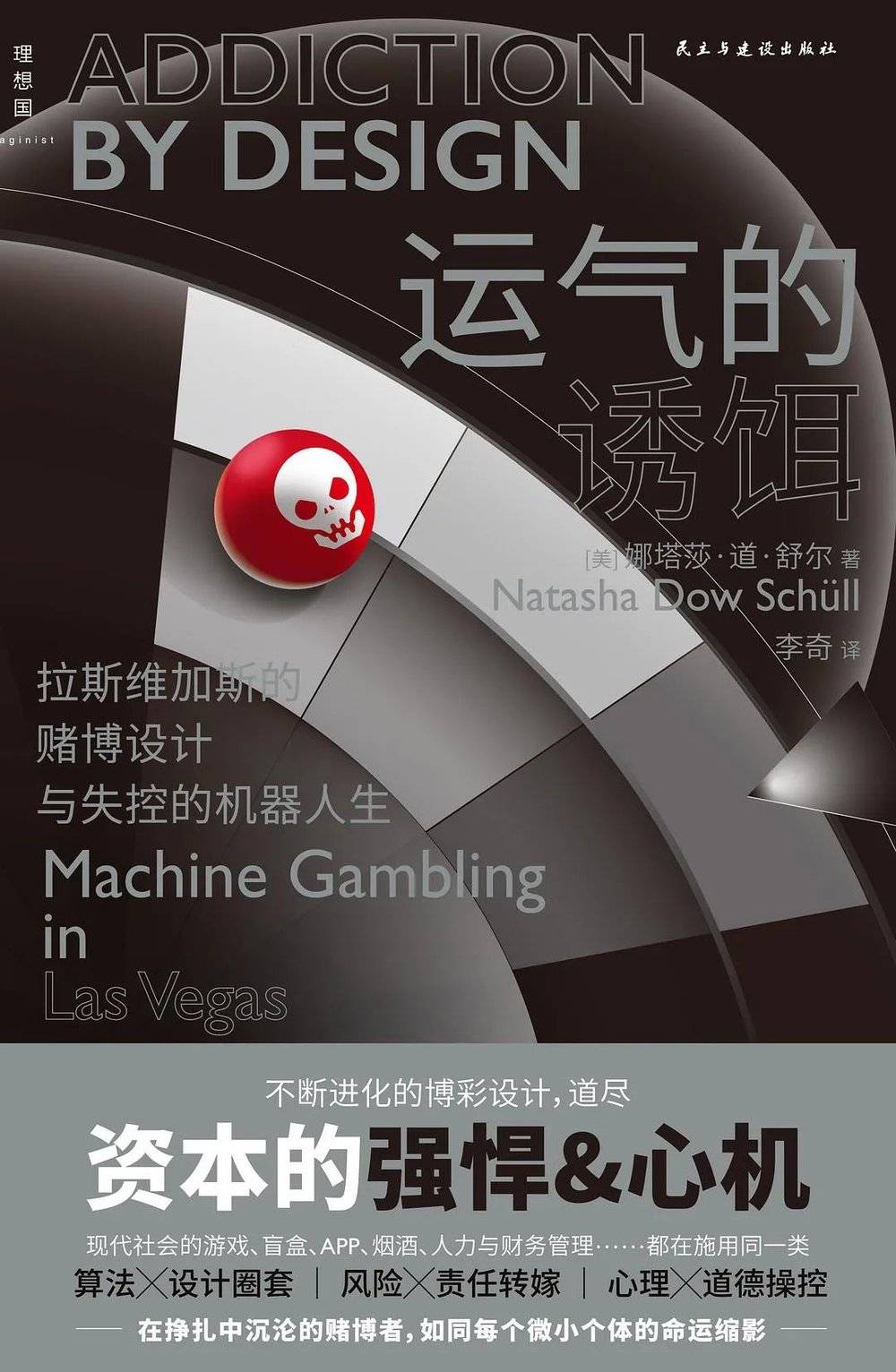
“拥有控制权的是我,是我在伤害自己。”
赌博者的行为看似矛盾,其中却有线索可寻,其中一条就是赌博者经常提到,意外事件带来的损失,与他们在机器赌博中自己制造的损失,是不同的;他们感到,对不可控事件(地理距离、疾病、暴力、遗弃、死亡等)带来的损失是无能为力的,而自己赌博中的损失则尽在掌握。他们认为,赌博可以把真实生活中不可控事件带来的被动困难转化为一种更主动、可控的东西。

言及人与生活中的偶发性有怎样的常见关系时,肯尼思·伯克写道:“如果一个人碰巧遇到了一些阻碍,那只是时运,不算是他的主动行为。”谈到赌博成瘾者想要掌握损失的主动权时,他继续写道:“然而,一个人可以把……这种纯粹的意外转化为主动的选择,就好像一个人在意外跌倒时,突然也想‘自愿’跌倒”。
赌瘾者经常会提到,机器赌博可以让他们把意外的、非自愿的损失转化为伯克所说的“自愿”损失,就像罗拉说的那样:“是我在伤害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在伤害我)。拥有控制权的是我。”
亚历山德拉的问题赌博发展历程,就印证了这种“自愿损失”的观点。在我们访谈的五年前,她业已成年的儿子突然患病去世了。她提到了这件事情对她的影响:
我儿子的病是我无法控制的,因为我对此无能为力。所谓“控制”,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摔断了腿,我能尽力帮他恢复——带他去医院,把骨头接好,这是我能控制的部分。但他的这个病我完全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如此没来由、没办法的事情。然后,还有赌博。
亚历山德拉对儿子的去世深感悲痛,她辞去了赌场荷官的工作,每晚都在她家附近的24 小时超市“阿尔伯森”(Albertson’s)赌博,直到天亮。
“我在那些机器中可说是找到了避难所。赌博时,我不想……任何事。”她承认,赌博就像她儿子的死一样,“我无法控制”,但同时她又感到机器赌博赋予了她一种自相矛盾的控制感:“奇怪的是,在赌博时我确实感到自己又获得了控制感。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自己不能控制这台机器,因为那是一台电脑,但我能控制我自己的……损失。”
在面对创伤的损失或其出现的环境时,人们有时会重演这种损失,或故意再把自己置于一个容易发生损失的情境之中。这一现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试图用他的“强迫性重复”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的灵感来自他蹒跚学步的孙子恩斯特。恩斯特发明了一个游戏:他不断把一个物体从自己这里扔开,然后宣布它“消失了”。在后来的版本中,恩斯特把一个拴着绳子的物体扔出去,再把它拉回来,然后宣布它“在这里”。
弗洛伊德发现,他的孙子在造成物体“消失”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满足感(游戏中“在这里”这部分对恩斯特来说似乎是次要的)。弗洛伊德猜测,这个游戏是孩子应对母亲频繁缺席的一种手段:当恩斯特宣布他的线轴“消失”时,他感到母亲的那些缺席和随之而来的被遗弃感,已经受他掌控。
赌博成瘾者玩赌博机,正是另一种“消失”游戏。生活中若有偶发事件让她们痛失所爱、处境恶化、剥夺了其确定性,这时,她们会试图借赌博机这一数字化的工具不断地下注再下注,以此来“重演”自己的损失。恩斯特的游戏不仅揭示了成瘾者行为的内部机制,也揭示了其外部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赌博机是如何抑制、取消或掌控赌博者真实生活中那些无能为力的损失的。

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恩斯特无法空手玩他的损失游戏,为了重演母亲的出现、消失过程,他需要儿童线轴这个人造道具,它可以被扔出去再拉回来。与这种简单的“儿童科技”相比,当代赌博机或可看作一种复杂的数字化线轴,其触感功能给了赌博者一丝控制感,控制他们珍视的、但又正在“消失”的东西。
“当我意识到我不能完全控制它时,我就彻底放弃了。”
在研究过程中,我遇到很多“自愿损失”案例,其中最引人注目、最深思熟虑的莫过于莎伦的例子了。
她是一位40 多岁的意大利裔美国女性,近20 岁时随家人一起搬到了拉斯维加斯。她的故事与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样,也是在损失中寻找控制感,但她陷入强迫性机器赌博的路径,与伊莎贝拉那样的赌博者截然不同。
莎伦并没有那种在生活的各种事件面前缺乏能动性的感觉,远非如此,她似乎因为有着过分的能动性而感到痛苦。她最终坠入赌瘾,是因为她的自我最大化动力及掌控生活中一切的欲望撞上了天花板。
“我要讲的不是自己总也得不到的东西”,她告诉我,“而是一个把所拥有的一切都挥霍掉的故事。”
在她的讲述中,她的人生就是一场对控制感的追逐,不论是获取还是挥霍,她都要自己掌控。“我的最初计划,”莎伦回忆道,“是去文理大学拿两个学位,再进一所顶尖的医学院,然后成为一个名满天下的成功医生。”当得知暑期课程中学生获得学分的最高纪录是19学分后,她给自己安排了24个学分,光申请就被驳回了六次:“这件事从来、从来没有人做成过,也没有人认为它可能。”她奋勇发起挑战,同时还在某赌场做全职荷官,只在业余时间学习。
莎伦对掌控的欲望从追求学业蔓延到了自己的身体上。她回忆说:“那时,我一门心思地想把自己改造完美。”她警惕地监控着自己的摄入和消耗,只喝有机果汁,只吃天然食品,从不让体重超过125磅。她每天跑6英里,每天早上喝啤酒酵母,知道如何排出体内的水分,知道如何增肌减脂。
“我对自己的控制不仅限于外表,在体内,我也可以操纵大分子来实现氨基酸的增殖。我不会让任何毒素进入我身体。”
然而有一天,她的这项事业也撞上了天花板:
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永远保持完美,无法总是强过自然规律时,我彻底放弃了。我知道我输了,因为再加码下去,我就需要去做整形手术了。我就得去特殊的健康农场一类的地方,每次住上几个月。很明显,我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单凭我的财力已经走不下去了。当我意识到我不能完全控制它时,我就彻底放弃了。
在莎伦的叙述中,她的人生轨迹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是在她意识到自己的竞赛是必败的时候,毕竟对手是自然,是无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于是她的人生急转直下,滑入了强迫性机器赌博的深渊。
莎伦在别州的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她最好的朋友自杀了, 她的哥哥也死于谋杀。这让她的必败之感更加彻底。在这些事件之后,她转向了新的计划:这次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毁灭。她精心策划着自己的损失,仿佛损失本身也是一场比赛,而她要赢得冠军。
一直以来追求高效控制的定制策略失败了,而莎伦对此的反应似乎是转而去追求高效的毁灭。这种自愿“摧毁”毫无保留,似乎只有这样才配得上她痛失兄长和挚友的磨难,才能中和、消除她的痛苦。说完自己的故事后,她问我:“在你的访谈中,我算不算最糟糕的赌瘾患者?在赌瘾这个事情上,我能得个A+吗?”当然只是半开玩笑的。
莎伦这种“自愿损失”的模式与前面提到的例子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她没有试图去管理损失的速率和时机,而是完全放弃了自己,把一切交给几率;对她来说,赌博并不是在面对人生中的痛失时为自己找回一点控制感,而是她在与“终有一死”的持续斗争中向生存的赢面屈服了。她考虑的是“超出控制”的东西,因为她最终想在赌博中预演的,并不是控制几率的可能性,而是不可能性。
我们已经知道,赌博机本身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媒介,不仅是赌博者实践自身驱动力的一个渠道。相反,机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交互力量,它执行程序使玩家“熄火”, 并在这一过程中限制赌博的可能结果。然而,机器中除了令玩家熄火的脚本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这种控制感的反转现象?或者,我们用亚历山德拉的话来提出这一问题:
刚开始,我可以按心意控制自己的去留,甚至可以赢钱离场,但后来事情就发展到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了。太阳就要出来时,我会问自己:“我想走的——但什么东西让我留下来了?我为什么坐在这里?”
有个东西,有个“它”,钻到了我里面, 让我一直玩一直玩……这个东西就像鬼魂附体,让人沉迷,把我拴在了那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我啊?
赌博机把人生的“悬置性回路”转变成一条导向迷境的路
尽管弗洛伊德在“死亡驱力”里提到“死亡”时,象征意义多过字面意义,但赌博成瘾者在讲述机器迷境的感受时,通常会提到字面意义上的死亡,特别是自己的死亡。表达方式有暗示(“确定无疑的自毁之旅”)、联想(“我宁可先被烟呛死”)、比喻(“我把自己玩死了”)、直接指涉(比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等。
在赌博者的叙述中,死亡这个主题如此广泛地存在,这意味着赌博者与真实的死亡,与死一般的迷境状态之间,都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下面我们会聚焦于这种联系特别明显的几个案例,不是要让这些案例自成一类,而是因为它们把对一种广泛地贯串在赌博行为之中的情形推到了台前:对“终有一死”的隐隐的全神贯注。
黛安40 多岁,高个子, 红头发,是个鸡尾酒女招待。她把自己的成瘾理解为一种宿命,这种宿命一直潜藏在她体内,赌博机只是从外部激活了它。“接触赌博机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有这个宿命,”她解释说,“所以我上瘾并不是因为机器。它们是我遇见过的最让人满足的东西,让我体内的那个东西成长起来,来接管我。”
当她详细阐述这个“内在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时,一个充斥着创伤和死亡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她父母生了三男三女,黛安是老四。
她的人生中总是不时出现兄弟的死亡:一个兄弟小时候就死了,另一个13 岁死于吸毒过量,还有一个兄弟总算成年了,却死于博尔德高速公路上一场诡异的车祸。黛安承认:“最后这位也去世时,我并不惊讶。”这还没完:她的父亲是自杀死的,而父亲的父亲和一些叔伯也是自杀。说到这里时,她带着嘲弄的口吻:“自杀是我们家的恶心传统。”
她有位表姐妹,“有五个孩子,赌博问题非常严重”,在我们访谈前不久,这位表亲刚从胡佛大坝上跳了下去。“奇怪的是,”她补充说,“她把车停在桥上,然后跳下大坝,但之后人们发现车里有2000 美元……也许她觉得,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才能不把这笔钱还给赌博机。”最后,黛安讲了自己17 岁时险险逃过死亡魔掌的经历,当时一个陌生人强奸并差点勒死了她。她对我说:“知道自己被人杀过,还被丢下等死,那是种奇怪的感觉。”
她认为自己总是担心十几岁的儿子,就是和这种“奇怪的感觉”有关。“我每晚检查他三四次,看他是否呼吸正常。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会让我很紧张。”后来黛安发现,只有玩赌博机时,她才能停止这种持续的担心。“这是一种麻木的解脱感。做任何别的事都没法让我忘了儿子。”等她把钱输光,玩不下去时,儿子总是在第一时间重回她的心头。
“万一他出了什么事,而我又没在,怎么办?这总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于是我必须马上回家看看。”黛安的妹妹也有同样的强迫性焦虑。“她觉得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知道人就是可能遭遇不幸。别家的人都以为每个人都能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好好活着。但我们知道,事情可不是这样的。”
在了解了她的生活经历之后,我们可以认为黛安之所以赌博,是为了重获对生活的控制权,逃避失去一半家人的痛苦,逃避自己的儿子可能同样被夺走的可怕预感。然而,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把赌博理解为她让自己更接近死亡那种“麻木的解脱感”的方式——在这种状态下,再无任何由头让人预期进一步的损失。这一点在她说到自己对悬疑小说的态度时可以窥见一些苗头。
“悬疑小说我都是倒着看的:先看结尾,再回去看剩下的部分。我想看看作者是怎么一步步写到结尾的。”她痴迷于情节设置的时间机制,痴迷于作者把故事推向终点的迂回路径;她每个时刻都在想着结果会怎样展开,好了解各角色的结局都是怎么来的。“我喜欢及时快进,然后回来,这样每一步我都心里有数。这方面,机器赌博比真人赌博强多了,它能让我更快地快进到结束。”
我们再次看到,她的表述同时流露了两种渴望:既想掌控人生,又想了结人生,让它“消失”。弗洛伊德也注意到,最终他的孙子恩斯特发现了一种让自己消失的方法:蹲下,低于镜子,让自己的镜中影像消失。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赌博者用赌博机所做的事。
让我们回到亚历山德拉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我?”看起来,这个“东西”既不完全在人的心里,也不完全是机器运行的脚本,而是一种双方都有贡献的混合力量。
在机器赌博中,赌博业的目标是清空玩家的资产(或说实现“玩家熄火”),这与玩家自己自我消解(或说“自我熄火”)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这个意义上,机器设计的功效不在于将一种外来的腐化力量注入人的心灵,而在于它能够将赌博者心中已经存在的倾向引导出来并加以利用。
我们可以说,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赌博机将死亡驱力的心灵机制加以凝结和利用,把人生的“悬置性回路”转变成了一条导向迷境的通途。
本文摘编自理想国《运气的诱饵》,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娜塔莎·道·舒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