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府最生活(ID:cdqqcom),作者:匡匡,本期讲述者:小石,曾经的养熊人、如今的巴西柔术“地板王”,原文标题:《在成都养熊18年后,我成了教人“打滚”的地板王》,题图来自:作者供图(成都巴西柔术学院内,教练小石和学员的对抗)
2002年8月1日,交织着兴奋和惶恐的一天。
兴奋的是,我终于有一份工作了。那天,我正式入职四川龙桥黑熊救护中心,成了一名保安、黑熊饲养员。
那是亚洲最大的黑熊救护中心,救助、治疗从养熊场救回来的取胆熊。

曾饱受活体取胆折磨的黑熊,在这里度过余生。
惶恐的是,我还没学会保护自己,就要去“保护”体型数倍于自己的庞然大物。
上班头几年,我经常做两个噩梦:一是熊舍的栅栏突然塌了,熊跑了出来;二是梦见被熊抓住了手,怎么拽都拽不掉。

当熊在熊舍时,如果越过中间的两道黄线,将可能置自己于危险境地。
因为年龄最小,同事们亲切地称我为“小石”。
之后,我在这里工作了18年,从一个少年,步入中年。“小石”成了我的固定称谓,一如我的性格:沉默、腼腆、不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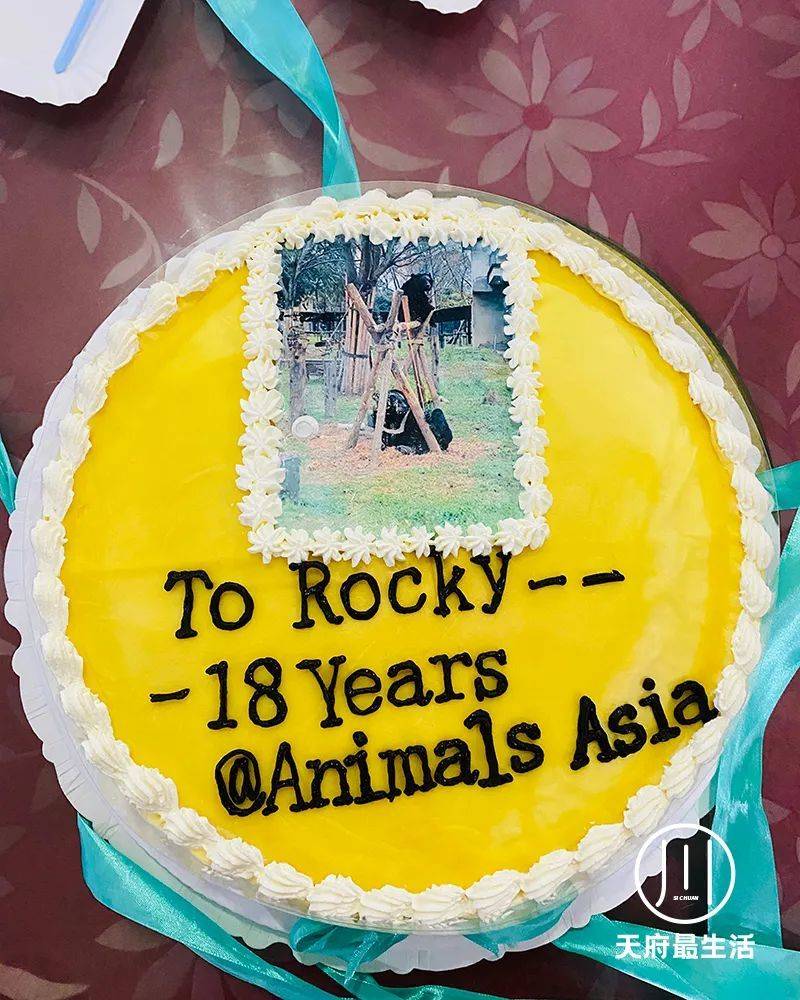
入职后,我给在厦门打工的姐姐打了一个电话。
在讲这个电话前,我可能需要介绍一下我的成长背景。
一、16岁,第一次出远门
我的老家,在安岳县的一个丘陵小村。
我的童年记忆,关于父亲的成分不多。早在我和姐姐年幼时,他就离家打工了,在成都拉三轮,每年也就春节回家一次。
我和姐姐算是母亲带大的。
在我们这个只有百十户人家,以种粮为生的贫困村庄,这样的家庭结构其实很常见。

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父亲的勤劳而改善。
我记得每到大雨天,我家房子就会漏水。它由石板、木板和竹篱笆围成,像我的家境一样弱不禁风。
家里很穷,一个月才能吃一次肉。初中毕业后,我主动辍学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同时上学。
那时姐姐在读高中,她成绩比我好,读书的前途比我远大。我相信,她会成为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

16岁那年,我跟搞装修的表哥去了自贡,母亲的老家,当了一名刷墙学徒。
刷一天墙能挣15元钱,工地上没活时,我就在姨妈的饭店打下手,吃住在她家里,我的工资也给她保管。
离开自贡时,姨妈把工资给了我,大约有两三千元。
我没想到,我居然存了这么多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姐姐交了学费。

回家前,姨妈带我买了件西服,花了100多元。
我很心疼,但姨妈说,穿撑抖一些,才算是衣锦返乡。
第一次出远门,让我懊悔的只有一件事,因为干活时的意外,我的一截手指留在了自贡。
二、“我养你啊”
回家后,我又没有收入了。
在成都的幺叔告诉我,龙桥要开一个黑熊基地,他推荐我去当保安,收入肯定比我打零工多。
听了幺叔的话,我来到了成都。
我岁数太小,面试比别人多了一些曲折。可能是幺叔面子够大,基地最后还是把我留了下来。

我给姐姐打电话时,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已寄到老家,但她准备放弃。
姐姐说,她想继续打工,不读了,不愿再拖累我。
我对她说,你去读嘛,我在成都找到工作了,工资高的很,我来供你。
其实,我这句话半真半假。
真的是找到了工作,但工资并不高,我白天当饲养员,晚上兼职保安,算上加班费,一个月就七八百元。

我中午在基地食堂,和同事搭伙吃饭,花销不大。
早晚饭在幺叔家蹭,不用花钱。每个月发工资,我留50元生活费,省下的给姐姐读书。
父亲很少在家,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认为,我有保护、照顾家里两个女人的责任。
但最终,我还是没能护住我的姐姐。

五年前,远嫁台湾的姐姐,因抑郁症离世。
她在离开前,曾向我倾述过她在那边的孤独和苦闷,但这些不寻常的对话,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我认为,更苦的生活,我们姐弟都过了,这算不了什么。我把原因归结为她刚生完孩子,情绪低落。我开导她,“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没想到,姐姐就这样走了,甚至没和我这个弟弟说一句再见。
得知姐姐噩耗那一刻,是我这辈子最孤独的时候。
三、我当上了熊经理
月熊基地远离城市,环境封闭,就像一个世外桃源。
每天除了同事,面对的只有黑熊和其它动物,生活单纯、安静,没有社交氛围,简直就是为我这样内向、不擅交际的人量身打造。
在这里,我开始自学药剂配置、兽医基础、动物救治……
当时我以为,动物保护可能是我下半辈子的事业,既然是事业,就要做好。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因为我曾经历过一无所有。

我的踏实、好学、少言、负责,得到了同事们认可。
饲养员们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总会说,“去找小石吧,小石能解决”。
当了两年饲养员后,大家推选我当了饲养组长,接下来又当了主管。
主管之上,就是“熊经理”这一职位了。如果我晋级成功,将成为黑熊基地唯一的中国籍熊经理。

黑熊基地的管理层、兽医、护士多是外国人,英语是工作语言。要当熊经理,怎么也该会说英语吧?
我只有初中学历,英语水平略等于零,我决定自学。
学英语比学配药、兽医难多了,好在基地老外多,我的方法是随身带个小抄本,记录不懂的单词和句子,一有空就找老外对话,向他们请教。
作为一个社恐症患者,当初能走出那一步,想想也不容易。

我最早学会、说得最溜的三句英文是:
“这样说对吗?”
“我该怎么说?”
“你能告诉我怎么说吗?”
自学多年,从只会“Yes”和“No”,到可以和老外对话,我终于成了一名能用全英文教学的动物保护专家。
我也如愿以偿,当上了“熊经理”。
不过,读写仍然是我的弱项——这和我妻子刚好相反,她经过系统学习,英语过了六级,读写很流畅,但口语不如我。
四、被“玩一把”改变的人生
原本我以为,我会在黑熊基地干一辈子。
但在和上司Boris的一次“交手”后,我的人生,却被牵引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是当时的我,万万没想到的。
Boris,中文名乔博理,香港著名影星乔宏的儿子。
老乔是巴西柔术(以下简称巴柔)爱好者。这项脱胎于日本柔道,在国外已很普及的运动,当时在国内还很没什么名气。

老乔邀我“玩一把”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摔跤。
说实话,我很怕伤到他。拳怕少壮,那时我20来岁,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养出一身蛮劲。
而老乔已年过半百,论体力远不如我。
抱着让他一把的心态,我上场了——短短十几秒后,我就被他“锁”在地上动弹不得,拍地求饶。
我不服,再来。连续几把被老乔完虐,只能认输投降。



带着胜利者的高姿态,老乔向我解释,巴柔不靠蛮力,讲究技巧,通过关节技、杠杆原理制服对手。
他说,“巴柔,是一项以小搏大、以柔克刚的运动”。
以小搏大这个词,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起了自己的出身,打工、求职、寄人篱下的经历,从一无所有,到生活稍微安定……

这一路的获得和失去,我不就是那一颗以小搏大的小石头吗?
于是,我诚心拜了老乔为师,开始学习巴柔。
五、愿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一开始,巴柔对我和老乔来说,都只是业余爱好。
对巴柔的推广,老乔比我要狂热,但他热情的顶峰,最多也只是在基地开个兴趣班,和同事们练练。
直到2011年,棕带Jerry(现已是黑带),这位美籍老挝人的加入,我们这个小团队,才算有了真正的教练。

顺路科普:巴柔的段位,从低到高依次为白、蓝、紫、棕、黑、红带。
对常人来说,黑带即是巅峰,只有对柔术发展有贡献的宗师,才会荣升红带,数量极其稀少。
Jerry的加入,彻底点燃了狂热分子老乔的激情。
2011年,在老乔主导下,我们成立了成都巴西柔术俱乐部(CDBJJ),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也不设会员。

除了养熊,我还要负责组织活动、登记人员、整理场馆、当翻译、指导新人。
由于是非盈利组织,缺少资金,直到2015年,我们才筹备了自己的道馆——它位于成都市中心,距黑熊基地26公里,并更名为成都巴西柔术学院。



有了道馆后,我的时间就更紧张了。
每周3次训练,从黑熊基地到市中心,单程26公里,骑行约2个小时,训练完再骑回去。
我常骑行在深夜空荡荡的路上,路过一个又一个路灯,我的影子忽长忽短。那时那刻,我心里夹杂着寂寞和充实两种情绪。
这种骑行生活,我持续了4年。在路上,我常想起李宗盛那句歌: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希望如此吧。

相比小石,孩子们更喜欢全英文教学的Jerry。
因为他们觉得Jerry很酷。
六、被巴西柔术改变的命运
是的,它确实算数了。
在悄然之间,我的命运被改变了。
练习巴柔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参加过比赛。对在黑熊基地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我来说,获奖只是收获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开阔了眼界。

我从一个自卑、内向、腼腆的人,变得勇敢、开朗,甚至有点健谈。
我有很多小学员,他们大多是我学员的孩子,通过练习巴柔,在他们身上,这种变化更加明显。
毕竟,他们的怯弱,只是因为年幼,而不像我,源自曾经自卑的人生。


我拿到了西南地区首根巴西柔术紫带,并在2018年升为棕带。
我们的道馆,开始接收学员,有了一定盈利,进入良性循环。
也是在道馆工作的过程中,我认识了Sue,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女孩,她原本只是想来道馆体验。
2015年,她成为了我的妻子和助手。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有了两个孩子。
随两个孩子一起到来的,还有一道艰难的人生选择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身兼“馆长”和“熊经理”两重身份。
成家后,我搬离了黑熊基地的宿舍,和家人在市区生活。早上6点,我起床,前往龙桥上班。下班后赶回市区,到位于陕西街106号的道馆工作。
结束道馆的工作,回到家往往已是凌晨。

出门时,我的孩子还没醒来,回来时,他们已经睡下。
我想起幼年时,父亲离家的日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有一个和我相似的童年。
另外,2019年底,疫情的暴发,也让道馆经营一夜之间陷入困境,风雨飘摇。
“馆长”和“熊经理”,这两个身份,我只能被迫二选一。
2020年,在黑熊基地工作18年后,我辞去了熊经理的职务,离开了那个我曾当成家,打算待一辈子的地方。
我从一个员工,变成了义工。当它有需要,我依然会回去帮忙。
我计划着,等我的两个孩子长大一点,我会手把手教他们巴柔。
我希望,他们能成长为两个小小男子汉,像爸爸现在一样勇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府最生活(ID:cdqqcom),作者:匡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