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ID:TheThinker_CITIC),作者:姜虹(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原载于《信睿周报》第58期,原题为“植物学的‘被女性化’和‘去女性化’——《花神的女儿》的另一种解读”,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安娜:哦!多有启发性的学问!多么难记的名字!……里面还有如此稀奇的真理。为什么,植物都成了男人和女人。
……
桑普尔:依我看,女士,您学的这门学问看起来真不赖;但我可不怎么想让我的妻子沾上一丁点这样的学问。
安娜:那您可能会发现,很难让谁对它视而不见;对植物学略有耳闻的女士都在学。[1]
以上对话来自剧作家詹姆斯·普伦普特里(James Plumptre)在18世纪末写的讽刺喜剧《湖畔来客》(The Lakers, 1798),谈论的主题是当时正流行的林奈植物学。
瑞典植物学家林奈被誉为“现代植物学之父”,他创立了“性分类体系”和“双名法”,让两人觉得怪异的植物学知识正是“性分类体系”的核心。林奈以植物繁殖器官为分类标准,并将人类的性作为隐喻。他根据雄蕊数目、形态、比例和位置等将植物分成了24“纲”,再根据雌蕊特征进一步分成65“目”,并用希腊语中的“丈夫/男人”“妻子/女人”作为纲和目的名称词根,如“单雌蕊纲”中的“双雄蕊目”,表示该类植物中有一位丈夫、两位妻子。
尽管性隐喻饱受争议,但林奈方法大大简化了植物分类,降低了学习门槛,使植物学在18世纪下半叶迅速流行起来。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也被称为“林奈时代”,这个时期植物学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女性的广泛参与,植物学也因此被贴上了各种女性标签,如女性化的植物学、女性植物学、女性气质的植物学等。
笔者曾在拙文中谈过,科学的女性化关乎“谁”在做科学,表明科学中女性比例的增加。就植物学而言,女性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其中,这使得植物学成为一门“女性科学”,甚至具有“女性气质”。[2]
加拿大女性主义学者安·希黛儿(Ann Shteir)的著作《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以下简写作《花神的女儿》,引用仅标注页码)探讨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100年间,在植物学“女性化”和“去女性化”的历史变迁中投身其中的众多女性,撰写了一部英国“植物学的女性志”。
作者曾指出,在这100年间,前70年(即林奈时代)植物学文化的性别化为女性打开了植物学大门;而在后30年里,同样的性别观念却阻碍了女性的参与。(232)既然是“同样的性别观念”,何以产生了如此不同的影响?这就需要了解这100年间植物学文化的变迁及其主导者——男性。
![花神的女儿, [加] 安·希黛儿 / 著,姜虹 /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https://i.aiapi.me/h/2021/09/18/Sep_18_2021_02_51_46_18932077298952320.jpeg)
在18世纪的英国,科学成为受到追捧的公共文化,科学出版物、公众讲座、大都市和地方性的协会大量涌现,标本收藏和展示、科学仪器、实验演示常常出现在精英阶级的社交活动中。中上阶级女性也积极活跃在科学文化活动中,而植物学被普遍认为是最适合女性参与的科学:优雅、简单,没有残忍的猎杀和解剖,没有抽象的原理和公式,也没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既培养心智又有益身体。
从植物学的种种特征来看,它符合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角色的规约,与女红、绘画、音乐、舞蹈一样,是提高女性文化素养的方式之一。林奈植物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性别观念下被译介到英国,并迅速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广泛传播。
从传统的淑女规范来看,林奈的性隐喻有伤风败俗之嫌,然而它的简单易行、高效实用轻而易举战胜了有关性的焦虑。如希黛儿所言,“林奈关于植物繁殖中的性功能假说反映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因为他以雄蕊(男性器官)为标准划分等级更高的‘纲’,而次一级的‘目’的划分则是基于雌蕊(女性器官),而且将植物繁殖过程中的男性器官当成主动一方,女性器官当成被动接受的一方”,“将当时的性和性别意识形态自然化”,成为“性差异的一种建构方式”,“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性和性别差异问题的痴迷”。(19~22)
因此,林奈性体系带来的文化焦虑更多停留在直言不讳的性语言描写,而这样的语言修辞很容易通过一些写作技巧变得“纯净”。不少传播林奈植物学的普及作家修改或删除了性描写的词句,将其改写成妇孺皆宜的读物,例如植物学家威廉·威瑟灵(William Withering)的《大不列颠本土植物大全》。这本书是当时植物学的标准教材,威瑟灵在最初的两版中将大量拉丁文术语改成英文,也回避了所有的性描写文本,使“穿着英国外衣”的林奈植物学更加适合女性阅读。
自此,以女性或儿童为目标读者的植物学普及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女作家参与到植物学传播的行列,她们的故事和作品正是希黛儿的主要研究对象。
![植物学通信,[法] 让-雅克·卢梭 / 著,熊姣 /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https://i.aiapi.me/h/2021/09/18/Sep_18_2021_02_51_51_18932081575504513.jpeg)
对植物学女性化有着重要影响的一部作品出自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之手,他在18世纪70年代写了《植物学通信》,指导一位年轻母亲学习植物学,好让她再去教年幼的女儿。英国植物学家、林奈的追随者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yn)在1785年将卢梭的书信翻译成英文,并模仿作者添加了24封“全面讲解林奈植物学”的书信。
“卢梭-马丁”版的《植物学通信》在英国出版后的30年里再版了8次,风靡一时,拥有大量的女性读者和模仿者。尽管希黛儿和卢梭植物学研究者曲爱丽(Alexandra Cook)都认为卢梭并非林奈的追随者,[3]但马丁搭乘这部书信集的顺风车,为林奈植物学的传播“推波助澜”,吸引了大批女性参与到植物学研究中。也难怪萨姆·乔治(Sam George)断言,英国植物学的女性化最初受到男性创作的文本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就是卢梭。[4]
而且,卢梭用书信讲授植物学的方式被大量女作家模仿,最成功的模仿者莫过于贵格会作家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Priscilla Wakefield),她出版了多部畅销的博物学读物,多以书信和对话写成。这种亲切的写作方式也成为女作家们传播植物学惯用的策略——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在看似随意的闲谈中普及科学,传播宗教思想和伦理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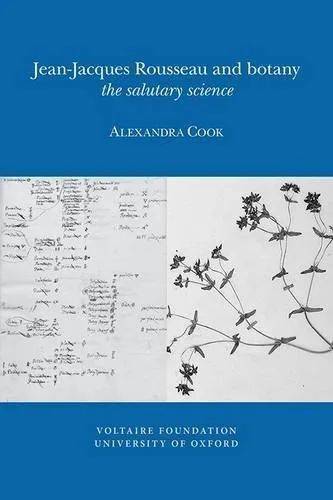
这个时期另一个对植物学女性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文本是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植物之爱》。达尔文信奉林奈方法,但与威瑟灵不同,他主张忠实于林奈的术语和描写,无须“纯化”——“植物之爱”这个标题淋漓尽致地传达了他对性体系的认可。《植物之爱》是一首长诗,其中提到了80多种植物,并在脚注中以林奈的方式对每种植物进行了详尽描述。
如希黛儿所言,达尔文毫不隐晦,将“植物王国的爱和性进行人格化”,“展示了性和繁殖是植物世界最重要的使命,激发着每朵花里‘男人’和‘女人’的行为”。(33)他在开篇诗句中就写道,“情郎和美人们簇拥在小树林的盛宴/相互追逐,赢得植物之爱”,植物们“深情地紧紧相拥”,享受着“甜蜜的吻”。
而具体到每种植物,它们都有独特的情爱,例如柏木“[丈夫]鄙弃黝黑的新娘/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分睡两床”。[5]同林奈一样,达尔文难免遭到批判,但他将诗歌文学与植物学融为一体的写作方式,却有效传播了林奈植物学,对植物学感兴趣的女作家也热衷于模仿这样的方式,如著名女诗人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弗朗西斯·罗登(Frances Rowden)则修改了《植物之爱》有伤风化的语言,以纯洁的诗句向小学生传授林奈植物学,出版了《诗意的植物学入门》。
1828年,林奈学会创始人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离世,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此同时,植物学在科学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开始分层,严谨的研究型植物学才被视为真正的植物学,大众植物学不过只是文雅休闲的女士娱乐。前者是“男性的科学植物学”,是专业、高级的研究,后者是“女性的休闲植物学”,是业余、肤浅的爱好,这样的二分法产生了与林奈时代截然不同的植物学文化。
植物学家开始摈弃林奈方法,转向自然分类体系——后者逐渐成为植物学的主流,尽管普及读物依然青睐前者。因此,让植物学摆脱女士娱乐和肤浅知识的污名成了植物学家的目标。伦敦大学第一位植物学教授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被希黛儿列为推动植物学“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典型代表。
林德利将林奈植物学视为过时的方法,认为其只关注命名,流于表面知识。在他看来,林奈植物学是专属女性的文雅知识和娱乐活动,破坏了植物学严谨、科学的形象。他的目标是培养新型的专家型植物学家,将植物学打造成“严谨的男性的职业”。(215~219)
在这样的势态下,植物学家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科学写作方式,林德利一边努力推进植物学的职业化,写了一系列替代林奈植物学的教材;一边迎合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采用女作家们喜欢的书信形式写了《女士植物学》,好让年轻母亲去教育小孩子学习植物学。
植物学文化的去女性化趋势也影响着新一代女性普及作家,她们紧跟植物学的发展潮流,更改自己的写作方式,例如19世纪中叶的简· 劳登(Jane Loudon)在《写给女士的植物学》再版时将书名改成了《现代植物学》,而且摒弃了她早期的写作风格,即女作家前辈们青睐的书信或对话体。维多利亚时期对两分领域的强调,更是将女性的植物学活动限制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在公共的植物学界难觅她们的踪影。
在希黛儿研究的这100年里,英国的性别观念并没有多大改变,例如开篇所引的《湖畔来客》,其作者普伦普特里就是一位传统观念的捍卫者。普伦普特里在戏剧的序言中承认,“对更优雅的性别来说,学习植物学这项娱乐活动可不怎么成体统;放纵时代的不良嗜好正在盛行,侵蚀着世间原本最可爱的一类人温柔优雅的行为举止,得竭尽全力阻止才行”。
而他塑造的恨嫁女角色,因为热衷于林奈植物学,被剧中男性讽刺道,“她一直在探究植物的体系,时至今日渴望了解男人的体系”;当她兴高采烈用拉丁文谈论一株植物时,同行的人觉得她不过是不懂装懂、卖弄学问,“对着一株小小的植物啰嗦那么多!可怜的女人!恐怕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6]。
跟普伦普特里同时代的诗人理查德·波尔威尔(Richard Polwhele)对女性学习林奈植物学的厌恶更不加掩饰,痛斥女性探究植物是假正经。而到了植物学职业化时,医生和医学作家约翰·福赛斯(John Forsyth)谴责女性的书信和对话体写作方式,讽刺她们是“喋喋不休的老妇人或者卖弄学问的老处女在虚构的通信里成了更权威的基础知识掌控者”。(35~36,224)
不仅是男性,不少女性也惧怕被冠上学究的名号;即使有人要支持女性学习科学,也要保持谦虚,忌讳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炫耀知识。
从林奈时代植物学文化的女性化,到之后的去女性化,男性知识精英主导着植物学文化的风向标。在同样的性别观念下,科学文化却发生了相反的性别化过程。在这背后,我们必须看到林奈时代的科学与艺术和文学、专家知识与大众知识、专业写作与普及读物常常融为一体,达尔文、普伦普特里、波尔威尔和卢梭等人的作品都是文学和科学相融的典型例子,希黛儿所列举的众多女作家和艺术家亦是如此。
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女性的植物学都没有在植物学史上享有一席之地,但她们的广泛参与在职业化前的科学文化中更容易显现,并得到认可。而随着科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隔阂和冲突越来越显著,科学家渴望与人文化、大众化的文雅科学划清界限,女性气质的植物学随之遭受排挤,女性的植物学活动隐退到以家庭为中心的私密空间[7]——“炉灶边的天使”依然是女性首要的社会角色。
注释
[1] 安·希黛儿. 花神的女儿[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25; COOK A.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Botany: The Salutary Science [M].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2: 319.
[2] PLUMPTRE J. The Lakers: A Comic Opera in Three Acts [M]. London: Printed for W. Clarke, 1798: 43-44.
[3] 姜虹. 从花神到植物学: 论科学的女性标签[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5(7).
[4] GEORGE S. Botany, Sexuality and Women’s Writing, 1760-1830: From Modest Shoot to Forward Plant[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 Press, 2007: 5.
[5] DARWIN E. Part II, The Loves of the Plants[M]//The Botanic Garden: A Poem, in Two Parts (3rd ed). London: Printed for J. Johnson, 1795: 2, 9.
[6] 同[1], xii, 2, 16.
[7] 见《花神的女儿》第七章“维多利亚时期早餐室里的女性与植物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ID:TheThinker_CITIC),作者:姜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