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多样性运动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它关切的只有高功能人群,而忽视了那些在重度孤独症中挣扎不得脱身的人。”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Moheb Costandi(神经生物学家兼作家),译者:M.W.,审校:Soda,编辑:Orange Soda,原文标题:《神化“雨人”,为孤独症群体带来了什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与托马斯·克莱门茨(Thomas Clements)见面之前,我不禁感到不安。放在过去,这个30岁的英国人会被视作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而他也将自己描述为“有轻微的孤独症”。直到我们在伦敦的会面前,我都不曾与孤独症人群有过近距离接触,所以我并不清楚应当如何表现,他又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会与我有眼神交流吗?我该与他握手吗?
*译者注: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s Syndrome)是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的一种,但患者没有明显的语言和智力障碍。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诊断标准被纳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中,但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DSM-5)中则被取消并归入孤独症谱系障碍。
尽管我很焦虑,我们的会面还是顺利进行了。克莱门茨会避免加入人群,因为在人群中他感到非常混乱;但一对一的交流对他来说没什么问题。我们在西区见了面,中午一起吃了咖喱鸡排饭,然后走进附近的唐人街——那是他在镇上最喜欢的地方。
很快我就发现克莱门茨天赋异禀。就像大多数高功能孤独症人群一样,他会为一些事物痴狂,常常忘我地陶醉其中。我了解到,他对中国和日本很是着迷,曾在这两个国家居住并且做过英语老师(他说比起英国,他在这两个国家更有舒适和被接受的感觉——借由外国人的身份,他可以掩盖行为上会被人谴责的奇怪之处)。我们在唐人街上散步的时候,他先是从街边商贩那里点了两个猪肉包子,又从超市里买了两小瓶中国的白酒,嘴里说的话听起来很像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
除了他出色的语言能力,克莱门茨还对艺术电影以及美国、英国、中国的嘻哈文化有广泛的了解。他杰出的能力无疑与阿斯伯格综合症有关,但他并不把孤独症视为馈赠。对他来说,孤独症使他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如果没有孤独症,有些事情分明是他可以处理的。
他说,“我并不知道社交暗示为何物,也不能理解人们的肢体语言。我看不上那些肤浅的谈天说地,也因此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形下冒犯了许多人。通常,别人和我的对话非常单调,因为我常常把话题直接引向我的兴趣所在,也由于我无法考虑到他们是否感兴趣,对方总是不得不承受过载的信息。但我已经在学着调整了。”
这个问题导致克莱门茨很难建立并维系人际关系,而找女朋友就更难了:他告诉我,对于像他一样的孤独症人群来说,“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机会渺茫,而找到长期的性伴侣则近乎不可能。”
克莱门茨独自住在剑桥旁边的一个合租房里,通过做德语-英语翻译谋生;但是对于他在孤独症“谱系”另一端的弟弟杰克来说,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杰克不像我们一样能够用语言交流。”克莱门茨在2018年个人出版的书《孤独症兄弟:两条通往成年的不寻常之路》(The Autistic Brothers:Two Unconventional Paths to Adulthood)中写道:
“(杰克)能说出单字和基本词组,但他不太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句子……(他)永远不可能像一个正常的成人一样生活。他这辈子都需要专门的护理,包括得有人给他擦屁股。他永远不会有工作、房子、车、或是像我们一样的家庭。我们都深爱着他,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咽下事实的苦果。这太让人难以接受。”
孤独症谱系障碍这种情况,或者说这一系列情况的特点是社会交往和交流上的困难、兴趣上的狭窄、重复性行为以及敏感的感官。正如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所说,这些都“有损于一个人在学校、工作、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正常表现”。美国精神医学学会2013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也就是DSM-5,基于个体的社交障碍、兴趣狭隘和重复性行为程度,列出了三种孤独症严重性水平。
一级孤独症的诊断标准包括了“启动社交互动存在困难”“对他人的社交示意有非典型或不成功的反应”“奇怪且显然不成功的交友尝试”,以及“能妨碍独立性的自我组织与计划上的困难”。二级孤独症的标准则包括了“语言及非语言社会交流技巧上存在显著缺陷”“启动社交互动的能力有限”“存在尤其奇怪的非语言交流”,以及“行为缺乏灵活性”“应对变化有困难”并且“转移注意力或行动有痛苦/困难”。
三级孤独症的标准包括“语言及非语言社会交流技巧上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导致了功能上的严重损害”“非常有限的启动社交能力,以及对于社交示意有极少答复”“应对改变有极大的困难”“有显著影响了各个方面的功能的狭隘/重复性行为”,并且“转移注意力或行动有极大的痛苦/困难”。
被确诊为三级孤独症的人在社交方面存在严重的困难,他们看起来像是失去了所有的社交技巧。例如,DSM-5中就描述道,他们“几乎没有词汇来产生清晰易懂的语言,很少开启社交,并且当他们真的开始社交时,只能另辟蹊径来满足社交最基本的水准,他们仅仅对非常直截了当的社交行为作出回应”,并补充道,这样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极大的支持”。相反,有一级孤独症的人能够在仅仅一些支持的帮助下正常生活。
*奥地利裔美国精神病学家利奥·坎纳(Leo Kanner)在他1943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中报告了11个案例,三级孤独症就与这些案例密切相关[1];而一级孤独症则对应了奥地利儿科医生汉斯·阿斯伯格(Hans Asperger)在1930年代描述的轻度孤独症[2]。

对孤独症患病率的估计不尽相同,但近20年来的估测总体呈现了急剧增加的趋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于2012年发布的一篇新闻稿称,在美国8周岁的儿童中,每88个就有1个患有孤独症,这意味着该数据比2004年的估算增长了78%;而CDC在2019年最新的估计更是达到了1/59。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范围内,每160个儿童中就有1个患有孤独症,并指出患病率的显著提高有着“多种可能的原因”,“包括人们意识的加强、诊断标准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好的诊断工具和更多的病例报告。”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也提醒,在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尤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孤独症的患病率仍是未知。
尽管我们对孤独症有大量研究,我还是找不到关于三种严重性水平中分别有多少确诊病例的数据,但通过CDC我们得知,大约40%的孤独症儿童完全不会说话,有至少1/4在12~18个月期间学会了基本的语言但之后又丧失了语言能力。
2016年发表的一项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纵向研究结果与这一估计是一致的[3]:总的来说,这一研究发现在246个孤独症儿童样本中,有26.3%在研究结束前都只会“自发使用不到五个功能性的词汇”,并且36.4%在项目结束前还没有学会“两个词的短语”;这些数字稍高于使用其他方法以及父母报告得到的结果,而那些结果指出在研究结束时,大约30%的孤独症儿童没有“命名至少三样物品”的持续能力,并且多于43%不能持续“使用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组成的短语”。
孤独症一般也伴随其他病症。一半以上的孤独症儿童同样也有智力障碍(其定义是智商低于70),并且多达一半的孤独症儿童表现出多动症的症状。孤独症儿童比其他儿童的就医比率更高:其他儿童仅有2%的就医经历是由于精神问题,但在孤独症儿童中,这一比例则高达13%。在孤独症成年人的一生中,焦虑和抑郁症的患病率分别为42%和37%。孤独症也通常伴随着癫痫,而这个症状在智商低于40的孤独症人群中最为高发。
可以说,孤独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话题。一部分是由于我们对它的发病原因缺乏了解,当下对这一话题的叙事充斥了不成熟、鱼龙混杂、考虑欠妥的想法,仅为在热点话题中占有一席之地。像是“冰箱母亲”*、微生物感染、疫苗**、以及环境污染和毒物这些荒诞的理论都还只是冰山一角。
*译者注:冰箱母亲理论(Refrigerator Mother Theory)是一个已经被摒弃的心理学理论,它将孤独症的发生归因于母爱的缺失或匮乏。1948年,《时代》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医学新知:被冰冻的儿童》(Medicine:Frosted Children)埋下了有关“冰箱母亲”这一观念的种子。
据其观点,有据可查的病例中,所有患儿的父母都几乎不理解孩子、冷漠且感情不外露,是他们将孩子“简单地塞入了永远不会解冻的冰箱之中”。后来,有关责任的讨论则绕过父亲、完全集中在了母亲身上,她们也就被贴上了“冰箱”这个隐喻的标签。
**“疫苗引发孤独症”的恐慌曾于21世纪初席卷美国和英国。1998年,胃肠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等人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称,麻腮风疫苗中的活性麻疹病毒可能会引发肠道炎症,而这种炎症可能会导致脑部炎症,从而形成孤独症。
同时,新千年伊始,英国和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率升高,而这两个国家的孤独症诊断率也剧增,不免引发了对于二者关联性的猜测。虽然起初韦克菲尔德全文的用词都表明这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假设,但随着他后续相关言论的发酵,这场关于疫苗的噩梦在英国和美国相继蔓延开来。
在这个舆论大漩涡中诞生了神经多样性运动(Neurodiversity movement),其支持者将孤独症歌颂为组成个体独特身份必不可少的一个“天赋”。在孤独症人士被边缘化、被欺辱长达数十年后,这一运动的支持者承诺,会通过让世界更加接受、包容孤独症人士来让他们的声音被倾听,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但是,近几年来,人们对这一运动生发了强烈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公然反对神经多样性运动,理由是它不仅没有代表这个群体,反而忽略了那些重度孤独症人士的窘境。
1990年代晚期,社会学家朱迪·辛格(Judy Singer)发明了“神经多样性”这一名词,她主张道,孤独症人士一直以来被压迫的方式同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经历十分相似,她还提出,他们的大脑不过是和“神经典型”(neurotypical)——或非孤独症——人群的大脑构造方式不同罢了。这一运动是民权运动以及人工耳蜗引入后的聋人骄傲运动*的延续。1998年的美国《大西洋》杂志中,调查记者哈维·布鲁姆(Harvey Blume)写道,“神经多样性之于人类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全体生物一样重要。”
*译者注:聋人骄傲运动的推崇者并不认为耳聋是一种残疾;相反,他们相信耳聋使他们通向了聋人独特的丰富历史、语言及价值体系。尤其在人工耳蜗面世、普及之后,越来越多的聋人认为这项人工耳蜗移植是非常“酷”的,并且会特意露出他们的接收器并向其他人解释这项用在自己身上的前沿科技。
在过去的十年里,神经多样性越发受到欢迎,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蒂夫·希尔伯曼(Steve Silberman)2015年出版的《自闭群像》(NeuroTribes)一书的造势。现如今,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上充斥着一些宣扬雇佣孤独症人群的好处的文章,声称孤独症人士的潜能将对品牌口碑与形象大有裨益——只要我们不再将他们视为残疾人。
这种思维方式现在则成为了主流:例如在美国,孤独症自我宣传网络(Autistic Self Advocacy Network)组织的代表能针对医疗和社区融合对孤独症人士会有着何种影响,向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提出意见;在英国,工党在2018年发起了孤独症神经多样性宣言(Autism Neurodiversity Manifesto),关于残疾的社会模型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则之一。
从表面上看,这一改变值得钦佩——神经多样性运动的确赋权了许多孤独症人士,也包括最近将孤独症描述为“超能力”的年轻气候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但是我们也能从多个角度证明这个运动是有害的。
首先,神经多样性的支持者浪漫化了孤独症。许多有着轻度孤独症的人能够在少许或零帮助下进行“正常的”生活;但相反,被孤独症严重影响的人则无法离开24小时照料。中心神经多样性(Pivot Neurodiversity)是一家位于旧金山的组织,旨在“让孤独症的走势向更能赋权孤独症人士及其家人、雇主的方案靠近”,其创立者、自我宣传家约翰·马布尔(John Marble)却在推特上说道,“根本没有重度孤独症这种东西,就像没有‘重度同性恋’或‘重度黑人’一样。”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浪漫化孤独症的趋势蔓延到了其他严重且能使健康日渐衰弱、威胁生命的情况。现在有许多自我宣传的组织赞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甚至,支持厌食症网站的壮大和最近出现的“毒瘾骄傲”也与这有关。
这种孤独症是“常态的一个变种”的思想与科学界对孤独症的理解大相径庭。神经科学家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孤独症有着神经发育上的源头,而最近的研究更显示,孤独症伴随着脑细胞数量和白质结构的异常以及突触修饰(即抹掉多余的突触连接的过程)上的缺陷[4~6]。
研究还指出,遗传学也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每一个患有孤独症的个体都携带着大量非常稀有或独特的基因变种以及多余的基因片段、基因删除以及其他染色体的问题。其中一些是遗传的,而其他的则是在受精过程和胚胎早期发育中新产生的。因此,似乎每个患有孤独症的个体都带有独特的基因变种的组合,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各自都有独特的一套行为上的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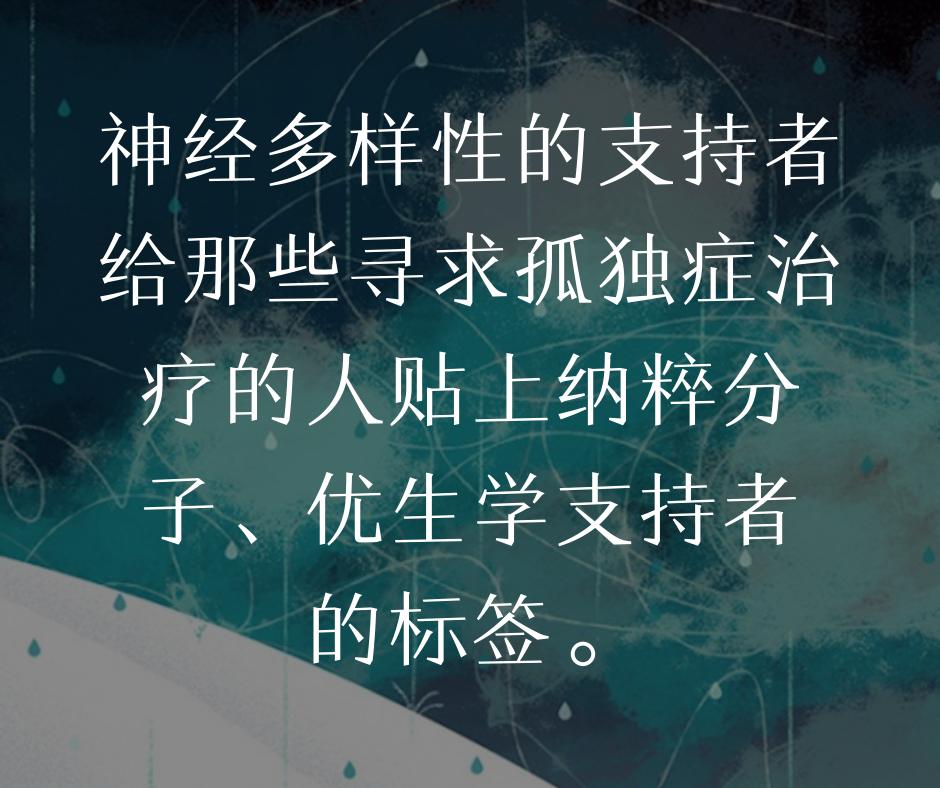
但是,神经多样性的支持者拒绝孤独症在医学上的模型,转而支持至今仍未经证实的社会模型,也就是将孤独症人士面临的问题视作系统性的“健全霸权主义的”(ableist)歧视。他们这样做确实是有一些道理的。一直以来,孤独症人士都处在社会边缘,并且被一些医疗-工业复合体所牺牲(他们致力于强制性消除孤独症及其他残疾群体)。汉斯·阿斯伯格就与纳粹政权的残疾儿童安乐死计划有过勾连。
自此之后,医学界对孤独症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不再想着如何根除孤独症,而是致力于理解孤独症,并为那些需要治疗的人研发新的疗法。
尽管医学上有许多重大突破,我们对孤独症的患病机制仍不得而知,这让许多孤独症儿童的父母感到绝望:只要看到一个能帮助孩子的方法,他们就愿意做任何尝试。这为无效或未经证实、甚至伪劣的治疗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从颅骶疗法和神经语言程序学*,到声称可以增强“上胸部‘情绪呼吸’来帮助我们学习经验中的情绪负荷”的疗法。甚至还有人鼓吹一种穿戴设备,该设备使用了所谓的双边交替触觉刺激技术(Bilateral Alternating Stimulation-Tactile)来传递“交替震动,并以此改善由于压力和焦虑而产生的战斗、逃跑以及僵硬的身体反应”,并声称该设备能通过恢复“神经系统功能的稳态,让您能够清晰地思考并平静下来”。
*译者注:颅骶疗法(craniosacral therapy)属于替代疗法(alternative therapy)的一种,声称通过柔和的按摩来触诊颅骨的不动关节(synarthrodial joints)。颅骶疗法是一种伪科学,被批判为“骗子行医”。
神经语言程序学(neurolinguistics programming,NLP)同样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其创始人理查德·班德勒(Richard Bandler)和约翰·格林德(John Grinder)相信神经过程、语言和通过经验习得的行为模式之间有着联系,并且人可以通过改变这三者来达到特定的人生目标。科学界认为NLP只是一种对大脑的工作方式粗劣且过时的比喻,且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
神经多样性的倡导者还给那些寄希望于治疗的人贴上了纳粹分子或优生学支持者的标签。自我宣传家杰克逊·康诺尔斯(Jackson Connors)在2019年六月的《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上写道,“我们为孤独症权益作斗争,实则是为我们长期的存在作斗争。我反对将我们非人化。我反对‘治疗’,那是对健全霸权主义优生学的招魂。我反对将我们推向贫穷和自杀边缘的体制。”
在对孤独症权益狂热的追求中,一些神经多样性支持者开始变得专制、激进,甚至开始骚扰、威胁那些胆敢对孤独症有任何负面形容、甚至渴望治疗的人。这种霸凌波及了学界的孤独症研究者、制药业、还有重度孤独症儿童的父母。
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ural Analysis)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疗法,它包含了高强度的一对一疗程,旨在帮助孤独症儿童习得社交技巧。然而,神经多样性的支持者认为这种疗法是残酷、不道德的,并进行公开运动敦促政府从该治疗中撤资。
此外,神经多样性支持者还希望合法化孤独症的自我诊断。索尔维格·斯坦达尔(Solveig Standal)于2019年4月在一个提供孤独症相关资源的网站“专家的孤独症指南”(Thinking Person’s Guide to Autism)中的博客上写道,“神经典型者一直以来都在与孤独症人士的对话中占上风,这当然会导致一种将孤独症视作病态的话语,并且还是基于一种我们无法为自己发声的错误观念。”她接着说:
是的,最终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会意识到自己不是真的有孤独症,但是这个探索的过程还是会帮助他们找到关于自己的答案,并且没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会被伤害。然而,当我们否定一个人的孤独症身份时,我们把他们关在了整个程序的门外,夺走了能让他们更好地获得医疗服务的媒介,也一并剥夺了他们得到专业诊断的可能性。
尽管许多孤独症的研究者意识到了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并且知晓形势的不利,却很少有人愿意就这一问题发声,因为他们害怕危及他们的研究资金、不小心冒犯到敏感的患者及其家人,或成为被骚扰的对象。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父母和看护者开始公开反对神经多样性运动,因为这一运动的支持者对孤独症的描绘并不符合他们自己照护孤独症儿童的经历。
65岁布鲁斯·霍尔(Brucce Hall)就是这样的反对者之一,他是加州一对18岁的双胞胎兄弟杰克(Jack)和詹姆斯(James)的父亲。霍尔告诉我,“这两个孩子都有严重的孤独症和智力障碍,一直以来,他们的行为对于看护者来说都充满挑战性。詹姆斯会乱发脾气、尖叫长达数小时,直到九岁。他现在能说一点话,尽管你不会太理解他在说什么。杰克则完全不会说话。”
霍尔和妻子瓦莱丽(Valerie)于2016年出版了《沉浸:我们关于孤独症的体验》(Immersed:Our Experience with Autism)一书,其中详细描绘了他们与两个孩子们的日常:
在公共场所,孩子们无时无刻都有可能大发脾气,而我们无法预测,也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可能是因为灯光或声音,或者周围的人群。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舒服或只是累了。有可能是几个原因的组合,也有可能无关于上述任何原因。
甚至那些适用于其他孩子的玩耍方式都无法让他们面露喜悦。他们对于各种场景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的忍耐力也同样有限……让正常的孩子觉得有趣的事物对有孤独症的儿童来说,可能是混乱不堪、甚至可怕的。
由于神经多样性叙事和重度孤独症经验之间的隔阂,另一群孤独症宣传者于2019年上半年在加州圣何塞组建了美国国家重度孤独症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Severe Autism)。
该组织的创始人主席吉尔·埃舍尔(Jill Escher)说道,“我有两个孩子都患有孤独症并且没有语言表达能力。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因为他们不能说话、阅读或写作,不能计算1+1,也没有任何抽象思维的能力。(神经多样性的倡导者)淡化了这一点,并且精心挑选了那些令人感觉良好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只有对孤独症虚伪的刻画,却没有直面现实。”
她补充道,“(神经多样性运动)提出的一些观点非常有利于所有孤独症宣传者,毕竟我们都想把孩子描绘成更容易被接受的样子。如果我的孩子在超市里突然崩溃,或是脱掉他的衣服,又或者开始尖叫,我当然希望人们能理解他的行为源自大脑构造上的不同。但你要是问我会把这种不同当成自然、正常的吗?我的答案是:当然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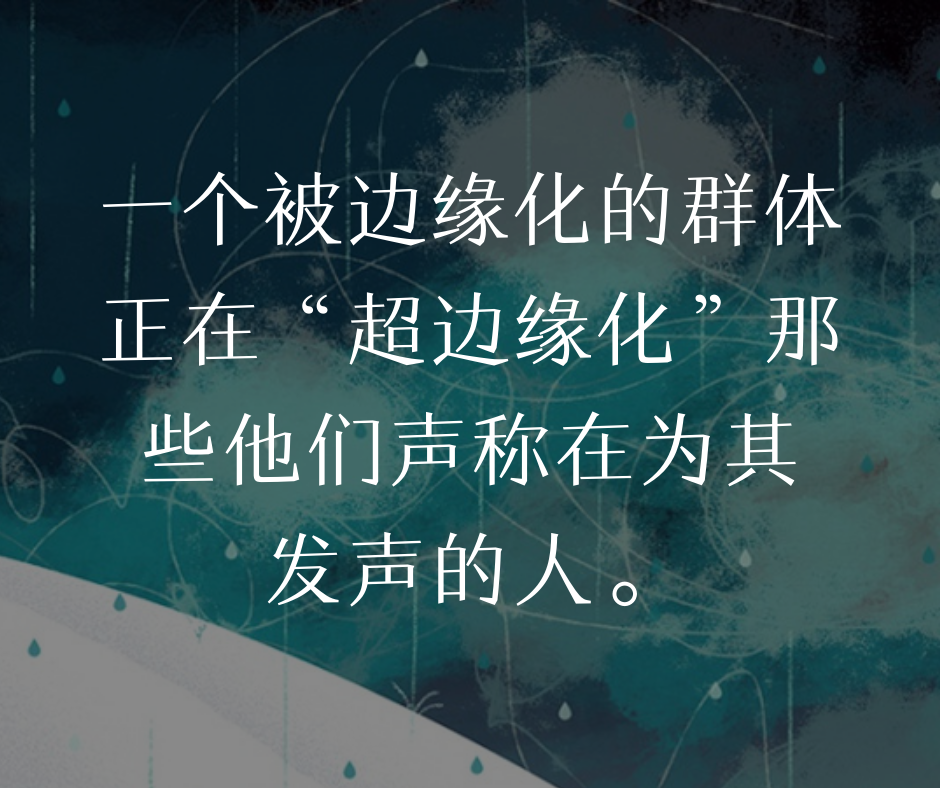
神经多样性运动正在分化孤独症社区及孤独症研究者们。其宣传者们区分了孤独症人群和“神经典型人群”,或者说是非孤独症人群。这催生了一种“我们vs他们”的心态,其中非孤独症人群被认为是压迫他们的敌人。这也导致他们不能包容其他关于孤独症的观点,也致使他们对科学及医学界产生了根深蒂固而病态的不信任。
讽刺的是,一个旨在强调孤独症人士如何不被社会善待的社会正义运动,现在对于孤独症群体中最弱势的群体(那些因为孤独症的严重影响而无法为他们自己发声的人)所遭到的不公平对待是有责任的。
在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过程中,他们作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同时也在“超边缘化”他们声称要维护其权益的那些人。他们垄断了关于孤独症的公共话语,并且继续竭尽所能消灭不同的声音;这种拒绝辩论、执著于寻求他人妥协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在孤独症社群中,同样存在于更广阔的社会中。
这也涉及孤独症研究者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在抽调样本时,整个领域的研究都针对有智力障碍的孤独症群体存在选择性偏差;尽管近半数的孤独症人士都有智力障碍,大部分研究只集中于那些有完整语言和认知能力的人群。因此,被认为是“低功能”孤独症的那些人都被整个研究领域忽略了。
埃舍尔说,“这个运动是有害的,因为该运动的支持者试图通过胁迫人们来让他们沉默,而我们只是他们霸凌和抹黑运动的众多受害者之一。这也严重影响了科学研究,毕竟那些神经多样性平台显然不觉得研究孤独症的形成原因是件多么重要的事。”
正因如此,现在是时候对神经多样性改变看法了,并且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关于孤独症的公共话语中,自由言论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如果神经多样性意味着所有可能,那它也应该意味着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持有不同的思想,并且不是所有人都该为有孤独症而骄傲。
霍尔说道,“如果你为有孤独症而快乐且把它视作你身份的一部分,那很棒,而我不想令你难过或者伤害你,只是不要阻止我设法缓解我孩子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说,孤独症是一个影响终身且残酷的神经障碍,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他们能感觉好一些并且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他补充道,“神经多样性的宣传者无视了重度孤独症患者所面对的冰冷的现实,还试图抹掉像我儿子一样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劫持孤独症患者所要传递的信息、垄断着舆论,并且正在严格控制关于孤独症的话语,这导致像我儿子一样的人在这世上没有了生存空间。”
托马斯·克莱门茨对这种情感表示十分理解——他于2019年8月在《卫报》上写道,神经多样性宣传者将孤独症平凡化的代价就是牺牲在整个谱系最底端的那些人,包括他的弟弟杰克。
参考文献
1.Kanner, Leo. "Autistic disturbances of affective contact." Nervous child 2.3 (1943): 217-250.
2.Barahona-Corrêa, J. B., and Carlos N. Filipe. "A concise history of Asperger syndrome: the short reign of a troublesome diagnosi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2016): 2024.
3.Rose V, Trembath D, Keen D, Paynter J. The proportion of minimally verbal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a community-base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me. J Intellect Disabil Res. 2016 May;60(5):464-77. doi: 10.1111/jir.12284. PMID: 27120989.
4.Avino, Thomas A., et al. "Neuron numbers increase in the human amygdala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but not in autis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14 (2018): 3710-3715.
5.Aoki, Yuta, et al. "Association of white matter structure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JAMA psychiatry 74.11 (2017): 1120-1128.
6.Tang, Guomei, et al. "Loss of mTOR-dependent macroautophagy causes autistic-like synaptic pruning deficits." Neuron 83.5 (2014): 1131-1143.
原文:https://aeon.co/essays/why-the-neurodiversity-movement-has-become-harmful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Moheb Costandi,译者:M.W.,审校:Soda,编辑:Orange So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