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采访:Lisa,编辑:Lydia,剪辑:小黎,设计:Sam,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本期嘉宾:
安超: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教师教育。著有《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
如果说都市里鸡娃父母们的教育焦虑,来源于对阶层跌落的恐惧,那对于数字更为庞大的底层家庭来说,他们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晋升的愿望更为强烈、面对的现实选择更有限,却在“教育焦虑”的讨论中近乎失语。
在近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社会心理背后,是人们不再相信底层通过教育逆天改命,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让差距越拉越大,通过文化资本的传承,精英实现自我复制,阶层逐渐固化,布迪厄的解释鞭辟入里,却也令人绝望。
层层困境以外,我们能否看见出路和希望?
本期问题青年,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安超。在安超的研究中,她从个体家族100多年的教育叙事和100余人的生命经验出发,探寻底层子女如何长大成人、如何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同时可以找回真我。民间教育如何依靠有限的资源将孩子“拉扯大”?透过传统的民间养育文化,我们对如今的教育有何反思?……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安超的研究,看见“教育焦虑”中的另一种真实,这之中既有匮乏,亦有希望与启发的力量。
教育社会学:兼具冷峻与热血气质的学科
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子学科,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既有教育学的希望和热血气质,同时它也兼具社会学冷静的、结构的、批判的气质。所以它是极具矛盾冲突,也极具挑战、极其有魅力的学科方向。
教育社会学的三大经典论题
第一个,研究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对教育的影响。比如现代化转型对教育的影响。
第二个,研究社会分层和流动。这也是我们今天学界和媒体炒的最热的话题,随即而来的问题是阶层和教育和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我认为是教育社会学的母题,是儿童的社会化问题:儿童怎么样成长和发展才能适应社会,同时促进社会发展?这才是教育社会学本源性的,也是终极性的问题。
尽管前面两个论题的批判性比较强,更为吸引眼球,但是第三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如何教育孩子、儿童如何发展这样的细节上来。
我们为什么焦虑?如何看待教育焦虑?
焦虑是一种现代性的宿命
我们今天谈焦虑,无论是阶层焦虑还是教育焦虑,或者“内卷”、“鸡娃”,这些词汇早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现代学科诞生之初就开始讨论了,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很多热度很高的讨论并没有超出一些古典社会学家的见解、洞察与想象力。我们应该超越这些碎片化的、转瞬即逝的热词,去寻找一些更具有理论洞察力的东西。
其实从人类进入到现代化、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就已经在跟焦虑相生相伴了,焦虑是现代人的宿命。

在传统社会中,我们不焦虑,但是我们也不自由。现代社会是高度流动的、高度理性化的,也是蕴含无限可能的一种社会形态。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新的人和事物,到处都是不确定的风险,所以我们焦虑。但焦虑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高度的自由,我们没有人想退回到一个不自由的时候。
古典社会学家们很早就开始探讨焦虑的问题了。涂尔干最早研究社会失范,讲到社会失范会带来自杀率的提高,而且自杀的情绪会传染。后来吉登斯提出“本体性的焦虑”,它是关乎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的,人在本体安全受到威胁时的焦虑,比如面对疫情,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能结束,会不会突然爆发。还有马尔库塞,讲现代人是“单向度的人”,人的本能是被高度压抑的。以及马克思舍勒,说现代人是“没有家园的孤魂野鬼”,一直在漂泊,现代人是异乡人、无根之人,会产生一种“怨恨”的情绪。
所以,焦虑并没有原罪,如果它是一种宿命的话,每个人都逃避不了。即使你没有育儿焦虑,可能还会有身份焦虑、职业发展焦虑,因为这就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与不可知的风险并存。如果去对抗焦虑,可能会更加焦虑,所以不如看清楚它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内观它。承认自己不完美,并不代表我们无能,焦虑也不可耻。
焦虑也是一种特权。对于大多底层和中产边缘层来说,还没有焦虑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
回到阶层焦虑。今天很多人在讲自己焦虑,但大家要去分辨,哪些人是真正焦虑,哪些人只是说说而已。根据我的研究和观察,很多人在说焦虑的时候是一边焦虑、一边享受。
焦虑有时候是一种社交方式、一种身份认同,跟以前见面说“你今天吃饭了吗”是一样的。现在见面是“你报班了吗”“你焦虑了吗?”
我接触了很多中产妈妈,她可能并不是真的焦虑,而是带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的“炫耀”,她在焦虑“该选哪一支股票、做什么投资”“在西城报班,还是去海淀报班”“选学区房,还是选一个郊区的小别墅”“要不要让小孩上国际学校”……这样的焦虑和真正基于匮乏与不安的焦虑是不同的。焦虑有时是中产的身份象征,在为这些事情焦虑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生活优渥的表现了。

焦虑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表达,那些真正焦虑的人,可能不是外显的。没有表达权力的底层在中国数量非常庞大,很多人可能还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也没有权利焦虑。
我认识一对夫妇,在北京打工,他们的孩子就在老家,相当于是留守儿童。今年母亲节我看到她的朋友圈特别感动。那天她的小孩给她发来了成绩单,成绩遥遥领先,她觉得这是母亲节最好的礼物。我当时就泪目了,我很少见她表达焦虑,同时她也没有权利焦虑。因为她没办法,小孩不能上北京的小学,即使上了也要回到原户籍去高考,所以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状况。其实孩子和母亲分离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这种分离的焦虑,和那些优渥中产的焦虑又是不一样的。
在中产阶层中,还有73%都是不稳定的中产边缘层
除了底层,中产阶层里面还有非常不稳定的一种,叫中产边缘层。相对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较高的、有稳定中产地位的精英来说,边缘中产的阶层身份和文化认同都不稳定。比如疫情一来,很多中小企业倒闭,财产一夜之间蒸发,他可能马上就变成了穷光蛋,他们就是在中产的边缘,焦虑密集的人群。
社会学家李强教授,2010年的时候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里的大样本,做了统计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大概占样本量的20%,但是这个20%里有73%都是中产边缘层,相当于3/4的比例,所以大部分中产其实都是中产边缘层。
《2019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把中国人的收入分成五等份后,月薪6000以上就是高收入群体了,才占到20%。月薪3000~6000元就是中间偏上阶层,占20%,剩下的都是中下阶层和底层,也就是说60%的人月薪在3000左右以下。
所以回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教育焦虑,我们看虎妈猫爸、小舍得这种电视剧的时候,它实际上讲的还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大部分中产边缘层甚至底层来说,连焦虑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
对“布迪厄神”的迷恋与反思
教育社会学界有大量的人用布迪厄的理论去解释阶层固化、文化再生产。现在关于教育最热门的一些书,比如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格雷格·卢金夫诺的《娇惯的心灵》,还有三浦展的《阶层是会遗传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跌入下流社会》等等,其实都是布迪厄的粉丝。
我一开始也非常喜欢布迪厄的,我叫他阶层教育学派,因为他最早洞察到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会通过培养和获取文化资本,再通过学校教育以及文凭社会里文凭的再生产机制,把自己的孩子筛选出来,实现阶层经济和文化的再生产。
可是读布迪厄的书越读越绝望,怎么办呢?我论文写到这儿就卡壳了。你就会想理论出路在哪里?布迪厄是大神,但是我们个人的、或者说底层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我痛苦了很久,理论出路也是从对布迪的反思开始的。
文化互嵌的中国,离明显的阶层固化还有很大距离
第一个反思是布迪厄理论产生的背景。布迪厄所在的法国本来就有悠久的贵族文化传统,并且和底层文化是壁垒分明的。但中国是“官民文化”,官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分别。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还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革命性、阶层翻身的意识本身就是非常强的。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太快了、人员流动太快了。今天成为精英的很多人,三代以内很可能就有一个农民亲戚,所以文化的分化并不像欧洲源远流长的贵族文化那么明显。我会用文化互嵌来形容现在的时代,我们还远没有到到达阶层和文化分化得特别明晰的一个时代,还早着呢。所以布迪厄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境。
底层的翻身,靠的往往不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而是一种文化性情
第二个反思是什么呢?布迪厄确实是很厉害的社会学家,他的视角非常犀利,但也是冷冰冰的,所以我只能回归到教育学热血、希望的气质,从教育学的角度重新看待阶层和阶层再生产。
很多出身底层的80后,也包括中产阶层的一些子女,原生家庭能够给予的教育支持是非常少的。早期中产阶层非常忙,大家都是双职工、早八晚五,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孩子。但80、90年代很多孩子也确实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像我就是上大学、然后留在北京工作,实现了阶层的跃升。
我并没有布迪厄所说的优渥的家庭,没有学过礼仪学艺术,我缺少那种高级的文化资本。可是很多人也通过教育实现了文化再生产。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黑箱,这才是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那些真正通过教育实现翻身的人,教育对他们做对了什么?

我最近几年接触到很多清北学霸,跟他们聊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能够成功实现阶层跃升,很大一部分并不因为文化资本,而是一种文化性情。比如说他们有高度的内驱力、自制力,不需要师长或权威施压,而是自己内心生发出来的强大动力。再比如说,他们对人、对物存有无限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真诚而勇敢…… 这些都是普遍人性,是跨越阶层的,它并非独属于某个阶层的文化资本,而是所有儿童成长的基本教养。
底层子女,如何“大器晚成”?
长大成人其实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最开始我的博士论文叫《庶民教育学:长大成人的家族记忆(1918-2018)》,我想知道每一代人,或者经历过很多历史苦难的人,他们怎样经历这些挫折、危险和陷阱依然“成人”。我回到我的家族,观察了100多年来——从晚清时期到民国时期,再到建国后,再到集体时代,然后再到现代社会,其中五代人的成长,从一百岁的老人,到两三岁的婴儿都有。我去看哪些人在这个家族中,最后过得成功且幸福,哪些人变成了败家子儿,他们又到底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
做家族史的研究,是受到了台湾省的夏林清老师启发,她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提出了实践中反思的研究路径。她当时找了一批劳工家庭子女做自我生命叙事与反思,发现这些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也曾有过堕落迷失。他们跟原生家庭有非常多的血泪冲突,跟自己的父母有很多仇恨和对立。怎么和解?她就创造了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回看我们的家庭,回看我们的父母,探究到底他们当年是怎么把我们拉扯大的,然后我们又是怎么样长大成人的。
好的民间教育,是在细微处见“性情”,是“人穷志不短”的教育
在对百年历史里不同家庭类型的研究中,我发现有些“文化性情”像家谱一样代代传承,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在每一代孩子身上留下印记。他们支撑了中产阶层和劳工家庭的子女,即使没能成功,也不至于很失败,或者变成一个坏人。
这种“文化性情”包含了一些底线性的教养。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庭,富有或贫穷,只要有这些教养,这个孩子至少不会走弯路,或者走向堕落与毁灭。
比如“不许偷盗”。很多民间家庭物质是很匮乏的,甚至要经常饿肚子,有时候经不住诱惑就去偷了。所以民间教育学很重要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许偷盗。我的研究发现在一百多年的传承中,“不许偷盗”这种要求几乎是在每一代人身上都有的。

“不许偷盗”的品质,其实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家庭教育道理。那就是要经得住诱惑、不眼馋别人的东西、尊重自己和他人。看似是“不许偷盗”,但它实际在要求你要有意志,“人穷志不短”。这是非常深刻的,也是民间教育学很重要的文化性情。
还有一个文化性情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底层家庭实际上有很多规矩,比如我小时候吃饭不能把筷子伸得很远、吃饭的时候不能到处扒拉。这种规矩也是很重要的品性,它背后是不能急功近利,要克制,要尊重别人,不能没有礼貌,要有教养和礼仪。还有很多规矩,比如去别人家做客不能乱翻东西、不能随便接受别人贵重的礼物……
所以以前的贫困家庭,是非常有骨气的。这些小的教养本质上是要“立志”,绝对不能因为人穷而志短。
但我们看到现在社会对于穷人、穷人对于自己、以及我们对穷人的看法都有一些改变。比如衡水中学的张同学所说的“土猪拱白菜”。我看了其实是非常遗憾的,首先孩子挺无辜的,17岁就要经受这样大的批判,希望他能挺住。他可能有很强大的原始驱动力,就是“我要翻身”、“我要改变命运”。这个很多底层家庭也有,还有刻苦努力这种重要的学习品质。
但他恰恰缺少了原有的民间教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人穷我志不短,我要靠自己的魅力、自己的能力,获得一个值得尊重的爱。我不需要去拱任何家的”白菜“,我也不是一个”土猪“。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莫欺少年穷”,我虽然穷,但不是一辈子穷,总有一天我可以有尊严地获得我自己应得的东西。
底层有着强大的、内生性的驱动力。其中一种基于匮乏与仇恨,一种基于远大理想和对幸福的向往
同时,在“土猪拱白菜”的思维模式中,存在着一个对立面,有一个仇恨对象。在帮助底层成功的文化性情中,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内生性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有两个源头,一种是基于仇恨和匮乏,一种是基于远大理想、和对幸福的向往。
尼采曾经专门论述过民间道德的问题,他说民间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基于怨恨产生的强大动力。他要经常通过仇恨、通过树立一个对立面、创造一个异己,来完成阶层的翻身。这种仇恨的动力极其强大,它会到处扎根,有强大的生长和创造性,但它同时也是行动和幸福对立的一种文化。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仇富的心理。他基于这种动力去学习,可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了,虽然他很强,他的人生支柱却坍塌了,这个发展动力不可持续。于是要找其他东西填补,然后可能造成一些悲剧,比如前几年的北大弑母案。
民间教育学,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学,保留了对于读书学习的纯粹目光
其实在我们的民间教育学中,是有基于幸福生活向往的驱动力的,但是现在少了。因为我们已经把读书学习工具化了,我们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是我们要仔细去思考,读书是改变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老一辈人很多时候爱读书,是因为读书可以明理、“知书达理”。所以他读书不是为了要马上成功,他们鼓励孩子读书,是说要有出息。像我的父母,以前会告诉我,读书就是要有出息,但我也不知道“有出息”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也没说你读完书就一定要赚大钱、毕业之后年薪多少,没有这些很量化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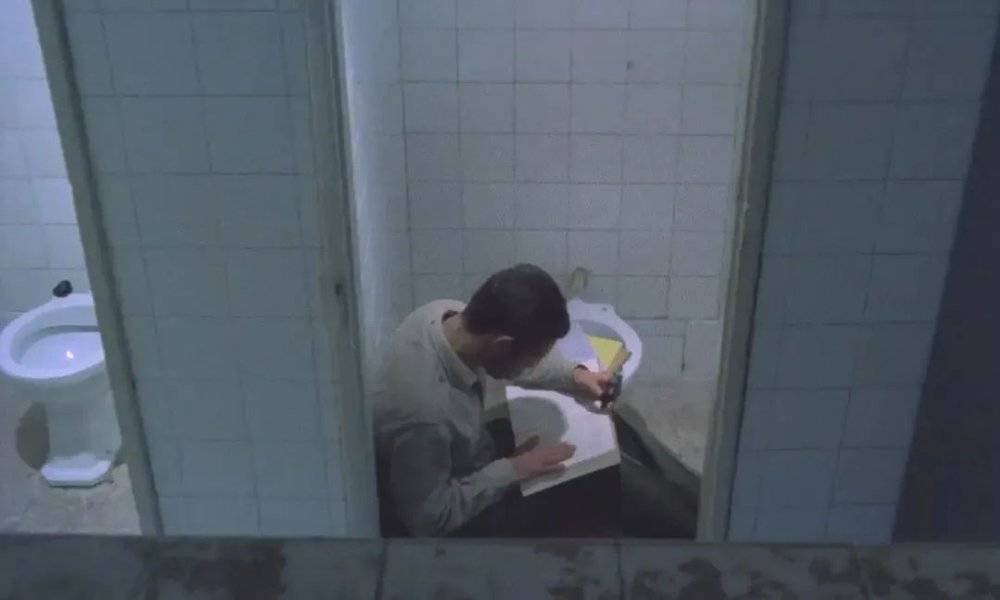
老一代人有句话叫做“大器晚成”,后来我把这句话概括为整个劳动阶层子女,或者整个民间文化中,最筋道的一面。劳工家庭的小孩没有什么家产可以继承,但他要成“大器”。就是说你不仅要完成功利化目标、要赚钱,最终你是要做事业,做一件有功德的事情,成为栋梁之材。
然后就是“晚成”,家里穷,但是要慢慢来,不急功近利,所以很对于很多底层家庭来说,一时的失败不会放在心上,因为知道会“晚成”,所以不会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大器晚成”这个词在我研究的这100年教育历史当中,一直是贯通的。
老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一辈人,有对读书的纯粹目光。就是享受读书和学习本身的乐趣,对于读书学习这些事情,有非常旺盛的探索和好奇心,不是为了分数和成绩这种短暂的目标和动力。这样反而能专注于学习本身,不受杂七杂八的东西困扰。比如说像我当时家里没有多少书,但是我爱学习,所以自己会去找村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早早地把他们的教材借来看,或者跟亲戚、朋友们借书。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闺蜜家境很好,她的父母也很接纳我,我就经常去她家蹭吃蹭住蹭书。
现代社会更需要“养育共同体”
博士论文写到最后,就发现公共支持特别重要。滋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一个社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如今的城市社会中,如何重建一个养育共同体。
如今的三人核心家庭是市场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它比较适合现代的生产方式,因为摆脱了大家族中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人情关系。但现代的核心家庭想要生活得好,实际上还极其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生活支持。可我们恰恰发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市场化走得很远,但公共生活、或者说公共领域,都在不断缩小。
乡土社会的养育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郑新蓉老师曾经跟我说,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具有公共性,就看你是不是“可托付”。比如说育儿这件事,我能不能在小区里找人帮我带一天孩子,把孩子托付给他。如果能的话,说明这个小区的公共性比较好。但如果我不能,要交钱给托儿所帮我做这件事,这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公共性,不是民间自发完成的。
其实以前的乡土社会,作为一个养育共同体,其公共性非常强。每家一生就是五六个孩子,怎么带大的呢,都是托付给乡亲照看。像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妈以前摆摊卖衣服,经常出去进货,一去好几天。我父亲的工作离家又非常远,一两周都回不来一次,我们在城里租的房子很小,我的养育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我妈把我托付给了房东太太。房东的太太非常好,有时候她就会照顾我。我也经常去好朋友家,她的父母也会接纳我。

我们需要有公共性的教育与生活,把不同身份、家庭、阶层的孩子们聚到一起,帮助他们相互了解、共情、看见彼此,从孩子开始,打破区隔与对立。
所以在以前的传统社会当中,身份之间的对立并没有那么严重。我一个富人家的家庭,也可以接纳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在家里住,还可以吃我的、跟我孩子一起玩,不像今天,有一种人为的对立。我们把好学校和差学校、好小区和差小区分隔得太明显了,富有的小区通过栏杆进行物理区隔,进而完成文化意义上的区隔。
很多富人以为,把穷人家的小孩、穷人文化给隔绝了,自己的孩子就能成功长大。但恰恰相反,一个中产家庭或一个富人家庭的小孩,他想成长得更好的话,是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的,他要通过他人、通过穷人家小孩的成长经验,来间接体验苦难,并且生成同理心。这样即使这些小孩长大后,相互之间可能仍然有经济意义上的差距,但他们依然可以做好朋友,依然可以是一个和谐社会。
而且很多富人家庭、中产家庭子弟,能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真正的尊严,然后反而能生出更强大的改造世界的愿望,和更长远的人生目标,就不再只是维持我家财富这种很小的动力了。
所以我们需要公共教育,要让孩子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在养育共同体中,把不同身份、不同家庭、不同阶层的孩子们在公共区域中聚到一起,帮助他们互相了解、看见彼此,认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参考资料:
【安超的相关论文和书】
[1]《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 ——“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安超,2015
[2]《经验回溯与文化反思:劳动阶层研究生的群体叙事》,安超,王成龙,2016
[3]《“文化区隔”与底层教育的污名化》,安超,康永久,2019
[4]《半规制化养育与儿童的文化反叛:三个中产家庭的童年民族志》,安超,李强,2020
[5]《大器晚成:“教育改变命运”的家族代际变迁及其双重面向》,安超,康永久2020
[6]《科学浪潮与养育焦虑:家庭教育的母职中心化和儿童的命运》,安超,2020
[7]《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安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文中提到的论文和书目】
[1]《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江苏社会科学》, 李强,2017
[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9
[3]《不平等的童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安妮特·拉鲁,2018
[4]《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罗伯特·帕特南,2017
[5]《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格致出版社,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2019
[6]《娇惯的心灵》,三联书店,格雷格·卢金夫诺,2020
[7]《阶层是会遗传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跌入下流社会》,现代出版社,三浦展,2008
[8]《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夏林清,201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采访:Lisa,编辑:Lydia,剪辑:小黎,设计:Sam。「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相信,提出问题,是一切改变的开端。我们将邀请来自青年文化、学界、媒体等不同领域的朋友,来聊聊我们的爱与怕。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