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作者:罗山,原文标题:《同样一个土豆:为什么中国人做成炒土豆丝,西方人却是炸薯条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马铃薯在今天是一种世界性食物。无论世界哪个角落,都有马铃薯制作的特色美食。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欧洲人点亮的是炸薯条——而中国人解锁的是炒土豆丝呢?
这就要从马铃薯在旧大陆引入与发展的历程说起了。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发现了野生马铃薯,并逐渐培育出茄碱含量较低的栽培品种,经过艰苦的选育,成为一种适应山地环境的高产作物。
1492年,哥伦布船队来到美洲后,欧洲殖民者发现了这种农作物。但当时他们还看不上这种原住民食物。在当时,欧洲人的食谱里没有这类圆形块根食物,觉得这东西看着就不吉利,并把马铃薯与结核病、梅毒等出海水手的流行病联系到一起,觉得吃马铃薯就会得病,甚至会引发战争。而且这些安第斯山低地的马铃薯栽培种只能适应阴凉的环境,不耐寒,在欧洲动辄大雪满地的气候中根本养不活。
1551年,西班牙人将马铃薯带给国王,王公贵族看着这种远方稀有植物,大手一挥,送去当成观赏植物培育。将近二十年后,马铃薯才在温暖的南部和加纳利群岛推广。1588年前后,马铃薯被引入英格兰,随后在北大西洋沿岸推广,在这些地方的沙质土壤中大获成功。同等面积土地,马铃薯的产量转换成热量,是小麦、黑麦的2~4倍。

马铃薯的优点自不必说,但它初到欧洲时完全被当成观赏植物,农民又迷信,害怕吃这个会得梅毒。欧洲在传统上,除了萝卜之外,只有欧防风(parsnip)等为数不多的块根类蔬菜。欧防风长得像白色的胡萝卜,是马铃薯传入之前,欧洲人吃的最多的蔬菜。
18世纪的英国保守分子说,我们老英格兰人每天起来,就好一口欧防风,那叫一个地道。吃什么马铃薯啊?马铃薯是天主教徒吃的,甭吃了。
吃马铃薯在英国一度要遭遇社会性死亡。吃这种天主教徒吃的东西,是否意味着里通外国,出卖大英情报?马铃薯是《圣经》只字未提的邪物,来路不正,埋在贫瘠冰冷的烂地里都能膨胀发育。吃马铃薯,是否等同于参加巫术,把灵魂卖给魔鬼? 吃这种外观光滑、曲线饱满的东西,是否容易想入非非,要行淫乱?看看,欧洲人讨厌马铃薯,连它的外形也讨厌。
直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马铃薯迎来了它在欧洲推广的最关键契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德意志地区,反复拉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农业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这一时期,亚欧大陆也进入小冰河期,英法多次发生饥荒。长得快、产量高、对土壤肥力要求低,还不需要磨坊和牛拉犁的马铃薯成为最理想的救荒粮草。
对于马铃薯的偏见终于一扫而空。
18世纪末,马铃薯终于成为欧洲平民最广泛的食物来源。
这一时期,欧洲人如何吃马铃薯呢?答案出人意料,最广泛的做法是熬粥或做汤。面包乃是宗教仪式中都要用到的天神赐粮,尽管马铃薯无论在产量还是烹调难度、甚至口感,都要远远胜过当年欧洲人常吃的一个月前烤的干硬面包,但就是很难取代它。马铃薯在欧洲那些有吃粥习惯的地区较早地被人接受也就不奇怪了。
前文讲了,欧洲人讨厌马铃薯,连它的外形也讨厌,熬成粥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原先吃燕麦粥,现在吃马铃薯粥,做法没变,而且马铃薯煮化之后也看不出形状,足以让人们暂时忘记它那可疑的外来背景,心安理得享受着一碗热气腾腾又不明所以的糊糊。
这些地方缺乏木柴,烤面包成本很高,当地的面包甚至不是小麦做的,主要是耐寒的荞麦,而熬粥只需要一些灌木枝牛粪之类的燃料,比较省事。如在比利牛斯山区,当地人把马铃薯煮熟,加到卷心菜汤里,或者加牛奶搅拌。
经济因素在此时的马铃薯食物版图中尤其明显。同样在比利牛斯山区,有一地区盛产铁矿,当地的主食就是面包。因为当地矿工的经济状况更好些,节假日甚至吃得上白面包。但周边地区只好吃马铃薯。
除了没有矿产导致经济状况不佳之外,还因为相邻地区的铁矿带动了冶铁业,消耗了周边地区的海量木材,导致周边的人连柴火烤面包都吃不上了,所以只能用灌木枝条煮土豆汤喝。惨遭马铃薯瘟疫的爱尔兰,传统吃法也多与水煮土豆有关,如champ是加了葱和黄油调味的土豆泥,colcannon是白菜丝土豆泥,还有牛肉汤炖土豆等。这种水煮马铃薯的做法,传承至今的典型菜式是土豆泥。
今天的炸薯条,有一条更为曲折的演变路径。炸鱼薯条在今天看来乃是“大英国粹”,但这种套餐19世纪才出现在英国。据美国学者任韶堂(Dan Jurafsky)的研究,配醋汁的英式炸鱼薯条是19世纪中期被犹太人传入英国,此前的英国烹饪书中,只有炸鱼没有薯条,如这类“犹太人储存三文鱼的烹饪做法”:鱼类去头洗净、切片,裹粉,浸入蛋液,下油锅炸至金黄,隔壁小孩都馋哭了。最关键的是,配炸鱼的是酸黄瓜和油醋汁。
而这种醋汁配炸鱼的犹太美食在当时西班牙称之为ceviche,在阿拉伯语餐谱中则叫做sikbaj,是一道极其古老的菜,词源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开始是用醋炖肉,在阿拉伯出现了醋炖鱼,中世纪的埃及人把鱼裹面油炸后再配醋炖煮,传播到阿拉伯人占领的西班牙,随后传入南欧。
当地天主教徒有数不胜数的斋戒,每年超过一百天,斋戒期间一整天不能吃肉蛋奶,但可以吃鱼,因此醋炖炸鱼迅速流行。而南欧天主教徒西班牙、葡萄牙人为了远航,醋炖鱼变成了冷盘,最终变成了炸鱼蘸醋汁,并以外国风味菜的身份进入英国,新的日不落帝国同样有大量海员水手,这种可以极大延长鱼类保质期的做法流行开来。
到19世纪中期,英国北部苏格兰、爱尔兰的马铃薯饮食也传入英格兰,马铃薯切成块,和当地流行的炸鱼一同下锅油炸,最终形成了炸鱼薯条的组合。
在英语里,薯条至今仍被称为法国油炸品(French fries),可见其原本就是外来食物。也有人翻阅菜谱,在比利时、西班牙等地发现了更古老的油炸马铃薯的做法,地中海地区的油炸食物传统也的确助长了炸土豆的流行。
在工业时代,起一个油锅,用高温油炸食物,实际上效率很高,很快就能把几百人份的食物炸好。炸薯条也适应了这种快节奏的工业生活,进一步流行开来。炸薯条、薯片、薯角、薯饼等,也由此走入千家万户,给大众带来便利的美味,当然也带来了摄入高热量食物的健康问题。

马铃薯到了中国,则是另一番场景。和欧洲不同,中国人的餐桌上从来不缺乏块根类蔬菜,如芋头和山药,所以对马铃薯的接受并无心理障碍。马铃薯的薯字,古代就指山药,《广雅》记载:“藷藇,署预也。”
王念孙注释:“今之山药也。根大,故谓之藷藇”。藷藇又写作薯蓣,是山药的古称,唐朝时为了避唐代宗李豫的名讳,改名“薯药”,到宋朝时又为了避宋英宗赵曙的名讳,只得再把“薯”字换掉,变成“山药”。而芋头也是先秦时期就有的蔬菜。

所以,较之缺乏块根蔬菜的欧洲,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隔阂更小一些。正因为有长棍状的山药,马铃薯在西北一些地方被称之为山药蛋。明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已经记载马铃薯为“土芋,释名土卵、黄独、土豆。土芋蔓生,叶如豆叶”。又云“土卵蔓生,如芋,人以灰汁煮食之,肉白皮黄,可蒸食之”,徐光启《农政全书》也有类似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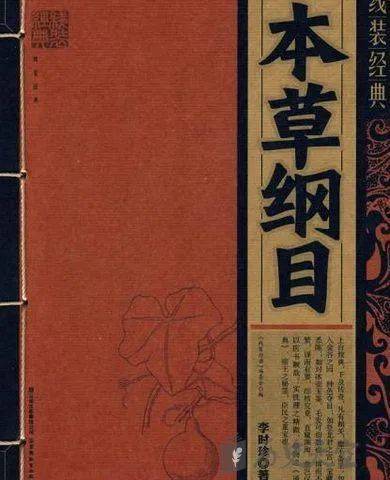
可见,在明末土豆传入中国时,土豆有两种做法:灰汁煮着吃、或是蒸着吃的。前者做法较为黑暗,用灰水煮马铃薯,或许可以减轻马铃薯中的茄碱,这种做法随着品种选育、淘汰,以及储存条件的进步,逐步不流行了。
到了清初,蒸马铃薯一度成为主流吃法。随着清代人口的爆炸,大量此前不适合开垦的山区也迎来了垦荒者,在这些贫瘠寒冷的山区田地,相比其他美洲作物,马铃薯比红薯更加耐寒、耐盐碱,比玉米更耐旱。因此,马铃薯成为最好的备荒粮,一些地方将洋芋切片晒干堪以久贮。
磨粉和麦荞可作饼、馍,但马铃薯终究不如红薯香甜,也不如玉米顶饱,所以产量不如前二者,而且马铃薯是适于在高寒地带生长的作物,用块根繁殖会逐步退化,在海拔较低、气候温和的地方种上1~2年,薯块就会变小。在做法上,最常见的仍然是整个蒸或烤,要用手掰着吃。

1958年,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整天研究土豆。他见识到了开花有香味的麻土豆;一个可以当一顿饭的大马铃薯“男爵”;有“味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的”品种;还有“外皮乌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入口更为细腻”的紫土豆,这是汪曾祺最为喜欢的,曾扛了一袋带回北京,全家过年吃了好几天。
在农业科学研究所,汪曾祺读苏联小说,“每每写战士在艰苦恶劣的前线战壕中思念家乡的烤土豆,马铃薯和祖国几乎成了同义词。”他自己给农业研究所画马铃薯的图,“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当地的“大笼屉蒸新山药,是待客的美餐”。
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北地区吃马铃薯仍然是以传统的整个蒸、烤为主。清代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称马铃薯为阳芋,认为其“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臑煨灼,无不宜之。”
羹臑煨灼,即煮羹、煮成泥、埋入炭灰烤、火烤,没有超出汪曾祺的食谱范围。另外,土豆叶子也可以吃,还“清滑隽永”,恐怕今天很少有人会这样吃了。道光年间,陕西巡抚杨名飏推广马铃薯种植,并告诫民众:“食用不尽,并可磨粉,磨法:洗净切碎,浸泡盆中,带水置磨内碾烂,用水搅稀,竹筛隔去粗渣,再用罗布滤出细粉,澄去清水,切片晒干,其渣仍可饲猪。”
马铃薯的高淀粉性质已经为人所知,切碎,泡水,淀粉溶解在水中,而其余的土豆渣滓拿去喂猪,这是在清中期就已经普及了的。
而土豆丝的普及,则既拜传统所赐,又与新中国的工业化息息相关。南北朝时期,炒菜就已经出现,明清大为流行。土豆丝要想炒得根根分明,需要用水将土豆丝的淀粉洗掉。此前,马铃薯制切碎泡水以获取淀粉的技术已经推广,因此用泡过水的土豆丝下锅猛火快炒,也就是临门一脚的事,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当然有这个创造力。
随着新中国煤矿的开发,城乡居民生火做饭的燃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猛火快炒也不再只是城里饭馆的专利,渐渐地,大家在家也可以试试炒菜了。再随着钢铁产量的不断提高,轻薄、导热快的铁制炒锅也进入寻常百姓家,土豆又是很便宜的蔬菜,炒土豆丝也就成为最常见的一道家常菜。
同一颗土豆,却在地理大发现后,在东西方形成了不同路径的菜式。一道道佳肴背后,是沉甸甸的历史。

参考资料:
(美)拉里·祖克曼《马铃薯 改变世界的平民美馔》
(美)任韶堂:《食物语言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作者:罗山,编辑:詹茜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