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王小笨,编辑:木村拓周,头图来自:《老友记》剧照
在被疫情拖延了整整一年之后,上周四,《老友记》重聚特辑正式上线了。
尽管经历了“二次删减”,但至少国内观众还是享受了一次和海外观众同步观看的体验。一时之间,从微博到朋友圈,无数人为重聚特辑奔走相告,有人在主题曲刚响起时就已经止不住眼泪,有人为“瑞秋”和“罗斯”在戏外也曾真情流露的“八卦”而兴奋不已。
在2004年《老友记》完结后的15年间,编剧 Marta Kauffman 开玩笑说自己被问到过“大概147000次”有关剧集重启或者续集的问题,但直到2019年《老友记》开播25周年,盛况空前的各类庆祝活动让主创们第一次认真考虑,“为粉丝做点什么”。
从全球观众的热烈反应看来,这次重聚特辑还是相当成功的,尤其在过去一年多疫情的大背景下。重聚特辑导演 Ben Winston 说到,“人们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就像他们在这一年中一直等待其他事情一样。我希望它所做的是提供一些真正的快乐和欢笑,也许还有一两滴眼泪。”

重聚特辑的成功固然有怀旧、情怀和疫情大背景下人们对陪伴抚慰需求等诸多现实加成。但《老友记》的长青作为一个现象,则需要一个比“怀旧”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5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老友记》是如何帮助世界各地的人学习英语的”,文章中采访了在美国的英语教学网站创始人以及韩国和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并且提到说虽然已经跨越了不同代际,《老友记》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英语学习材料。
如果说学英语听上去像是带着上个时代的烙印,那么《老友记》和 Z 世代产生强烈的连接就是一个新的文化现象了,得益于 Netflix 和 HBO MAX 这样的流媒体平台,Z 世代的年轻人可以随时随地打开这部剧集,甚至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称,瑞秋在剧集中的服装造型都成为了 Z 世代的心头好,根据 Pinterest 的报告显示,“Rachel Green 美学”在2021年初的搜索量是2017年同期的8倍。
二十多年过去了,在21世纪20年代,人们为什么还在看《老友记》?今天中国的观众又可以从《老友记》中,获得什么和过去观看时不一样的东西?
一、《老友记》的历史局限性
要回答《老友记》为什么在今天仍然广受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没有缺陷的“神作”。
事实上,作为一部1994年开播的情景喜剧,它不可避免地有着诸多“历史局限性”。
一个关于《老友记》不那么冷的冷知识:在《老友记》开播前的一年,FOX 电视台开播了一部名为“Living Single”的情景喜剧。这部连正式中文译名都没有的美剧,从人物设置(六个朋友)、故事发展(在大都市的生活和喜怒哀乐)甚至海报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它们也有一个彻底的不同——“Living Single”是一部全黑人班底的剧集。

2016年“Living Single”主演之一的 Queen Latifah 在接受 James Corden(也就是《老友记》重聚特辑主持人)的采访时说到,“Living Single”开播不久后,刚刚开始担任 NBC 总裁 Warren Littlefield 在被问到有没有让他印象深刻的新剧时,就回答了“Living Single”;而就在一年之后,《老友记》在 NBC 正式开播。
我们很难因此武断地认为《老友记》就是对“Living Single”的“抄袭”。但一方面,全白人主角班底的《老友记》大红大紫,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比它更早出现,剧作结构高度类似,但全黑人班底的“Living Single”无人知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就是那个时代美国流行文化的一大“局限性”。美国白人掌握着影视行业和文化输出的绝对话语权,由此以白人为主角的内容占据了绝对的主流,也收获到了最多的关注。美国黑人的内容即便同样出色,也走不出自己的圈层。
去年年初,“罗斯”David Schwimmer 还因为“Living Single”的事被挑战了。在接受《卫报》采访时他说,“也许应该有一部全黑人的《老友记》或者全亚裔版的《老友记》”,而“Living Single”的主演 Erika Alexander 在 Instagram 上质问他,“你真的是认真说你从来没听过‘Living Single’吗?”
David Schwimmer 的回复道,“我不是要暗示‘Living Single’没有存在过,或者说它不是在《老友记》之前开播的,我知道它是。我是一个‘Living Single’的粉丝,我也不会暗示说《老友记》是这个品类的第一部。很可能华纳兄弟和 NBC 就是被‘Living Single’的成功所鼓励,所以才给《老友记》开了绿灯。”

“罗斯”的态度诚恳,但这番话听上去比是否借鉴更让人唏嘘。在一些品类上,黑人创作者当了开拓者急先锋,却很少被人真正记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成为娱乐行业主导群体的注脚。
多年以来,全白人阵容这个争议也一直围绕着《老友记》。David Schwimmer 曾经在《滚石》杂志的采访中谈到种族问题,他用一种倾向于巧合的态度来解释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加多元化,但这件事并没有困扰我,你不能做一件事来取悦所有人,我知道在选角时,他们会看各色各样的人,这只是他们最终选择的组合。”
人们并不是站在上帝视角去苛责《老友记》的选择,但当你是一部在十年时间里都是排名第一的喜剧(最终可能还成为了排名第一的剧集)时,如果还能有哪部剧有能力去打破这个藩篱,那一定是《老友记》,但一切并没有发生。
当然《老友记》主创们的态度也一直在变化之中,“菲比”Lisa Kudrow 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就说,“如果《老友记》今天开播,情况会完全不同,肯定不会是全白演员。但现在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时光胶囊。”
就在重聚特辑开播前后,我在 Quora 上看到了一条回答,它或许应该是我们所应该保有的态度,“享受这部剧集,尊重它的高质量,但不要对那些完全合法的批评感到冒犯。承认它们,思考它们,然后继续前行。”
二、中国观众的成长和超越
基于种族的视角和好莱坞权力结构的问题,更多是这些年美国观众讨论焦点。对于中国年轻观众而言,《老友记》一直是一本“教科书”,教导21世纪初的中国人如何过好城市生活。
最近我看了很多分享对《老友记》的记忆和感受的内容,也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把美国《老友记》这一代对照我们中国的时代,最接近的就是现在。
《老友记》最初传入国内的时候,它所描绘的青年都市生活图景,是中国年轻人还没有过的。当时的它,满足的是我们对于都市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脱离原生家庭、探索以友情为基础重新构建生活的渴望。项飚在《十三邀》中提到过一个说法,外部的事物能带来一种超越现实,我们觉得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世界,于是自己身边的世界变成一个要抛弃,要离开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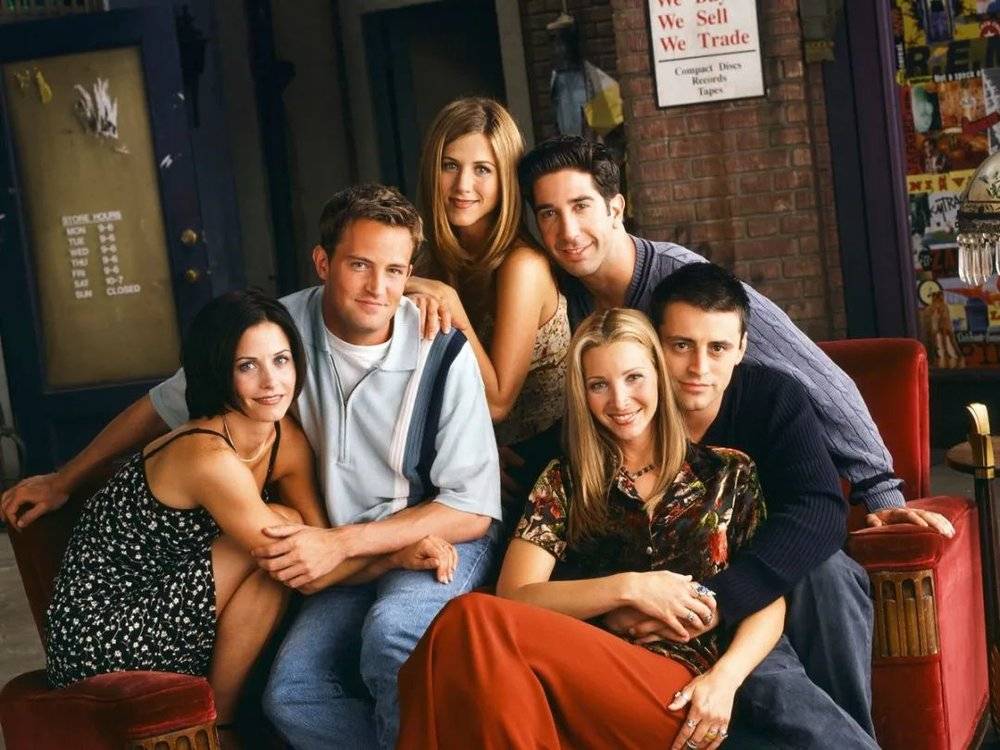
我记得郭敬明的《小时代》原著里,有一段关于几位女主角非常有仪式感地观看《老友记》的大结局,即便事实上《大结局》已经播出了很多年。虽然以《小时代》举例子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毕竟那是对城市生活不切实际的想象,但从心理上,我们能够看出《老友记》对那一代人真切的影响。
对于中国入世和北京奥运会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年轻人,脱离原生家庭是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而《老友记》几乎提供了一个关于独立生活的绝佳范本,即和一群朋友一起面对成年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事件,我们希望朋友成为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我们能够在友情构建的社群和支持系统里获得慰藉。
这也正是《老友记》开播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年轻人所经历的,对于他们来说,观看《老友记》更像是在一片价值感和意义感的真空中,重新构建自我,并且尊重他者的存在的过程,这也许也能解释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老友记》迎来了观剧人数的又一次爆发,剧集能够帮助所有人找寻自我。
但今天,对于当下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这些超越性的部分,我们事实上大抵完成了。都市生活不必多说,在原生家庭的层面,我们甚至已经出现了回潮,即从过去的一味追求脱离,到如今尝试主动重新融入和修复。
城市中心的咖啡馆,脱离父母的独立生活,合租的朋友......《老友记》中描绘的生活,我们似乎也够到了。在描绘城市生活和消费图景的各个维度,都有比《老友记》钻更得深,切得更广的作品。
为什么我们仍然喜爱《老友记》,而没有把它扔进应该摒弃的历史垃圾堆里?
三、在《老友记》中反思个人主义
事实上,可能直到我们抛开“城市生活教科书”这个叙事,《老友记》真正的价值才浮出水面。
同样是在那期《十三邀》节目中,项飚和许知远提到了在当今的时代,个人的层次被简化成了纯粹自我的个人,和作为一个很大的集体的载体的个人,中间的那一部分是断裂的。
其实不只项飙,学界、知识分子近年来针对泛滥的“个人主义”的反思愈演愈烈。许纪霖在他的《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里简介过,“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个人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出现”,但今天“占主流的似乎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具有道德自主性的、权利与责任平衡的 individualism ,而是一种中国传统意义上杨朱式的唯我主义(Egoism)。这种唯我式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欲为目标,放弃公共责任,是一种自利性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
包括最近两年声势颇高的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著作《爱欲之死》里解释爱情的终结,也归结于一种畸形的个人主义盛行。他提到,在当今时代所有的生活领域,伴随着个体的“自恋”情结的加深,“他者”开始消亡,一切变成了“自我”的参照物,消费社会力求消灭异质化的他者世界的差异性,这使得我们从根本上失去了爱的体验,因为“爱欲的对象实际上是他者,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
这可能也是《老友记》中相对中国观众被忽视的部分:放下自我,体验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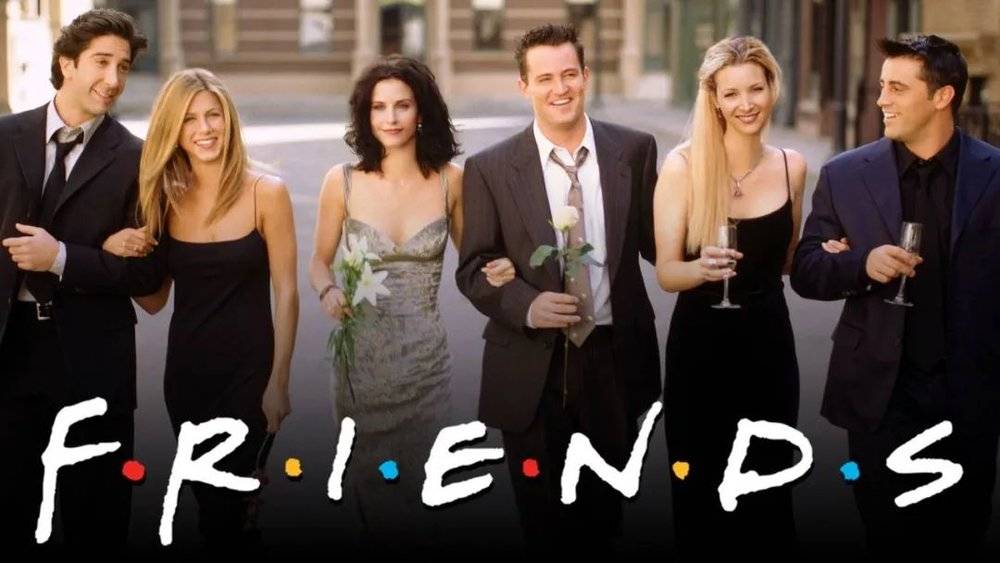
二十年前我们看《老友记》时,看到的大多是象征着脱离原生家庭、集体观念限制的独立生活、象征着友情和爱情交织浪漫的群租生活、象征阶层的符号性消费场景如咖啡馆、夜生活、约会等。我们看到的是被个人主义解放的、开始拥有无穷尽选择自由的城市青年。
但事实上,老友记还有另一个解读维度,即6个性格、背景、能力各不相同的人,如何共同构建一段积极和谐的生活体验。某种程度上,这种集体参与的构建,是需要让渡一定程度的自我的。角色们如何分配生活中公共的资源,如何处理朋友间的摩擦,如何界定并执行亲密关系和友达情感,如何放下利己的自我成就更好的集体。这些部分也许比一句“青年人的都市生活图景”更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品味。
因为《奇葩说》被观众熟知的学者刘擎2014年做过题为《救孤独的自我——克服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危机》的演讲,也提到过克服“原子化个人主义”危机,他给出解法可能是尝试构建一种“关系型个人主义”。“关系型个人主义不同于一切以社会为法则的社群主义,更不是万众一心的集体主义,而是主张自我选择,从社会限定中抽身出来,借由一部分社会资源区反思另一部分。”
换句话说,二十年前的中国观众借《老友记》追求个人主义;今天中国观众,则可以借《老友记》反思一种稍微“走偏了”的个人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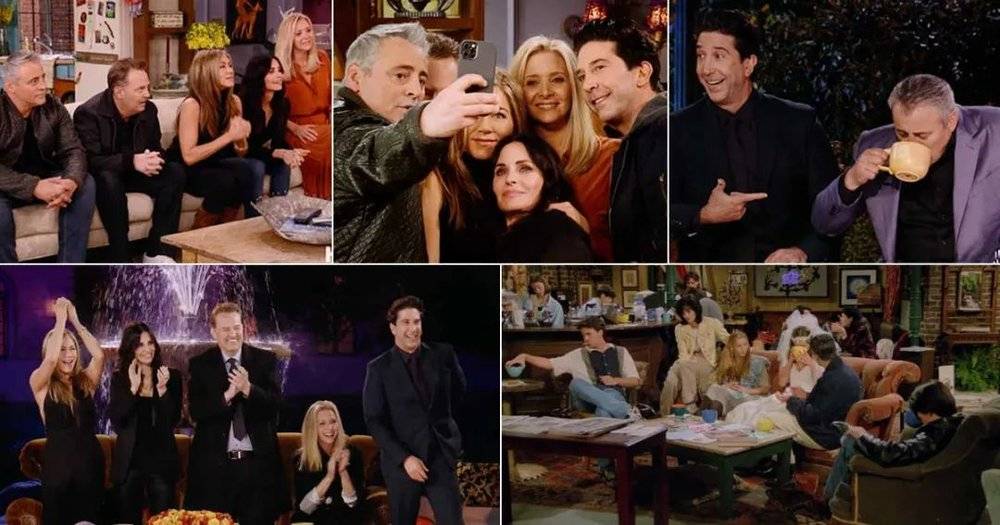
巧合的是,在《老友记》重聚特辑上映的正好一周之前,今年的“思想之夜”论坛上海站刚刚举办,主题是“家庭:近乎,远乎”。上面引用过的、今年以来观众很熟悉的项飙和刘擎都有出席。
8个中法学者们探讨了“家庭”这个概念在过去几十年的深刻变化。每个学者都有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观察面向,对家庭的思考着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大致共同的整体基础。界面的记者在报道中将这种共性其总结为:“在个人主义将个人从各类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时,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和稳定性亦受到冲击,一个‘后家庭时代’似乎正在降临。”
再联系上5月31日“三孩”政策落地的新闻,离婚冷静期还没搞明白,老龄化带来的生育压力又毫无防备地落到了这届青年人肩头上,对于组建传统婚姻家庭关系兴趣寥寥甚至心生恐惧的年轻人,到底还能怎么办?如果不知道,还是先点开一集老友群居的《老友记》缓一缓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王小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