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三三,原文标题:《所以,我们该如何时髦地谈论幸福这件事》,头图来自:《幸福像花儿一样》截图
在语言学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
如果一个词语被过分使用,久而久之,这个词语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便会在口口相传中被逐渐消解。每个互联网热词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比如PUA、内卷、共情、政治正确、道德绑架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表达我们基本生活需求与精神状态的词语,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遭受语意的架空和表达能力的磨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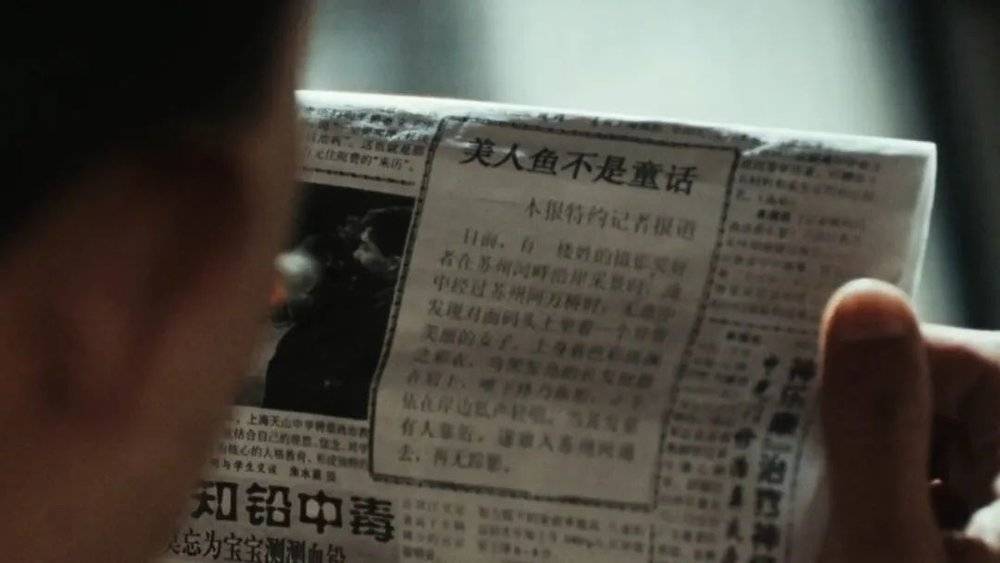
拿“幸福”来说,我们越来越少地讨论这两个字了,但相关的衍生词语和话题却不绝于耳。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迷思之中:一方面,买个东西吃个饭看本书都可以被跟“提升幸福感”挂钩,但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会真的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尽管这确实是一个被认为是一个人人都有权追求幸福的时代。
幸福是什么,或者说不是什么
在讨论“幸福”这个概念出了什么问题之前,我们先谈谈幸福可能是什么,或者说,它曾经被定义成什么。
关于幸福的讨论古已有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建立国家是为了全体公民的幸福”。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尝试定义幸福。在他眼里,幸福与其说是一种状态,倒不如说是一种美德,因为它需要三种类型的“善”作支撑。第一种是灵魂的善;第二种是肉体方面的善;第三种是外在的善,有钱、有名、有地位等。亚里士多德眼里的幸福,俨然是一种终生的“考验”:“以高贵的、坦然的姿态对待人生的起伏,尽其所能且随遇而安,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以充分的战略指挥着自己有限的兵力一样”——一言以蔽之,就是为幸福确立了某种门槛,你想拥有它,可以,但需要有资格。
相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素不光讨论幸福,还在1930年出版的《幸福之路》中给出了实用(但也相当悲观)的建议。比如他认为人们过度强调竞争,成功只是幸福的一分子,倘若牺牲其余去赢得这一分子就是得不偿失,进而提倡一种“有节制的”、不要兴奋过度的生活。
相比之下,当代学者们给出的视角就显得不能再务实了:著名心理学教授、文化评论家 Jordan Peterson 在一次演讲里就直接说,我们就不该把开心幸福当作人生目标,快乐本就可遇不可求,“追求快乐”更是一种错误的概念。
到了当下,幸福公开课更强调个人感知,所以有越来越多的高等学府开设幸福公开课,概念也大同小异。比如哈佛大学幸福课的讲师泰勒本·沙哈尔认为,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快乐代表现在的美好时光,属于当下的利益;意义则来自于目标,属于未来的利益。
而在耶鲁大学开设这门课程的心理学教授劳里·桑托斯看来,学生们经常将人生的满足与成绩、大公司的实习机会与工作薪资挂钩,而这些其实并不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她甚至提倡期末成绩只分及格和不及格两档——但不管是以上哪一种,似乎都和 Jordan Peterson 一样是在劝我们:过得“省”一点就会幸福很多,痛苦大多来自于预期过高。
举个例子,如果看电影这件事能让你得到瞬时的快乐,又能让你体会到一些形而上的价值,那么看电影这件事便是幸福的。从瞬时的碎片信息中获取到的只能是当下的快乐,从而无法上升到幸福的层面,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快乐和幸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悖的,如果要获得那种“我过得有价值”的幸福感,需要有节制瞬时快乐的能力。
幸福怎么就成了另一种玄学?
一方面,人们把幸福放到了终极目标的位置,另一方面,却苦于没有追寻的万能公式。这让幸福这个概念蒙上了玄学的色彩。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关于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的故事。列侬五岁的时候,老师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他说想做个快乐的人。老师说他不懂问题。他说老师不懂人生。没有证据表明这句“名言”出自列侬,人们之所以买账,多少有一点试图把问题简化的、一厢情愿的浪漫。
以上所说为理论上的幸福之说,而当下实践中的“幸福”却背离了这种深层次的内涵。它更多地成为了一种与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挂钩的量化标准,如衡量城市和国家的幸福指数、xx个让你提升幸福感的小物。我们偶尔也探讨幸福与单身/丁克、财富、工作等的关联程度,但当我们在讨论这些的时候,我们其实讨论的并不是有关幸福的自我感受,而只是一种庸俗的、缺乏现代精神的群体经验,它基本上可以等同于“肉体上的舒服+心理上的安全”,甚至不比买买买那一刻的快感高明多少。
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很幸福的时候,往往有两个动机,一是显露自己当下生活的优越性,二是破除外界对自己“不幸福”的猜想。多数时候,总是女性在证明自我的幸福,男性很少把幸福挂在嘴边,可见,在传统的、也是当代流行的语境中,幸福具备着浓厚的性别色彩。女性谈论幸福,男性探讨成功。
若是追根溯源,幸福是比成功更高级、更健全的目标。但是当下的幸福之说往往立足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比如富足的生活、有良人相伴、清闲的工作等世俗或传统的评判标准。


我们习惯性将幸福误读为某种被动和沉溺,像一个安全舒适的被窝,削弱了人们(尤其是女性)的动力和意志。但更可怕的,其实是关于幸福的另一套说辞——“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种观念把“个体的幸福”团团包裹,形成一个外人不可多说的围墙。如果说幸福是孤立的、自由心证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能说围墙内的这种幸福是可以自欺欺人的?我们无视了这个词语本身的内涵,但同时也致力于借助外物来获取所谓的“幸福感”和提升所谓的“幸福指数”,这时,我们对幸福这件事便产生了一种错位的关注和求索,因此难免陷入“不幸福”的漩涡。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体验》里写道:“忧郁指向最高世界,它伴随的是这个世界的虚无、空虚、易朽的感觉。忧郁指向先验的东西,同时它又意味着与先验的东西不相融性,是我和先验的东西之间的无底深渊。”或许这正是“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自然也称不上幸福)”的另一个版本。
如何以一种时髦的方式谈论幸福
很多时候,幸福演变成了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等家长里短的体面表达,然而,“我有钱有闲有伴但我不幸福”的言辞比比皆是;北欧和日本式的“小确幸”“Hygge”在流行了这么多年之后,似乎也终于可以被大家以平常心相待了;结婚、生孩子、生活无忧无虑可以是幸福,离婚、不生孩子、能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和焦虑似乎也是一种幸福——很多曾经的“反幸福”场景,现在反而成了新的“另类幸福”。
所以在当下,我们还能找到时髦的方式谈论幸福吗?

一种可能的思路是,放弃幸福有确定唯一、长期有效答案、甚至是“幸福有答案”这件事:没有对象是孤独的,那么有了对象就会好吗——如果把某个孤立的答案作为获得幸福的唯一转机,就很容易掉进所谓的幸福方法论当中去——“你觉得不幸福吗?谈个恋爱/结个婚/生个孩子/养个猫/断舍离/健个身/算个星盘就好了”——而兜售这些方法论的人,往往并不真的在意你到底在想什么。
另一个更是,只以行动本身(而不是结果)来探索,但放弃获得答案的可能,乃至不再需要以它为人生坐标。毕竟毕竟行动才是构成一个人之为人的基础,在这个高呼自由意志的时代,实现自由意志所需要做的努力与牺牲却被无视了,人们焦虑的同时又要安抚自己万物皆可自由,甚至连焦虑也是一种自由。这种自欺欺人就是当代人的割裂所在,在看似自由如风的时代飘来飘去乱作一团。
在这股自由狂风里,还有什么是值得扎根的?我们需要的,就只是重建“去做”的勇气。相信当下的行动胜过自由的焦虑,也许是一种更值得现代人追求的时髦的“幸福”——如果我们真的还有必要再去讨论它的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