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文章摘自《每个人的经济学》,作者:张夏准,头图来自:《平凡的荣耀》
在人头攒动的地铁上,你会不会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为什么薪水和你的待机时间不成正比?为什么加班到凌晨,仍然只是公司里的一枚小螺丝钉?为什么勤勤恳恳多年,还是无法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为什么必须努力、奋斗,否则就不能获得幸福?

这些个体化的困惑和焦虑背后,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分裂的个人:个人有“多个自我”
个人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个人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社会单位。在肉体意义上,显然是这样。但是否个体能够被视为一个无法再细分的实体,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
个体即使没有多相情感障碍,自身也会具有互相冲突的偏好。多重自我问题普遍存在。这虽然是个比较陌生的术语,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
我们经常看到,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完全不同。一个男人可能在和老婆分摊家务上非常自私,但一到战场上,却愿意为战友牺牲自己的性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在生活中扮演多个角色——在这个例子中,这个男人既是丈夫也是士兵。人在不同的角色下行为不同,不仅合情合理,也屡见不鲜。
有时候是因为意志薄弱。本来下决心未来要做某事,但真到那时候却泄气了。远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了。他们甚至还为它发明了一个词——“akrasia”(不能自制或意志薄弱)。比如,我们决定过更健康的生活,但在诱人的甜点面前我们的意志力立马崩溃。你有自知之明,于是你预先使用一些手段,防止后面我们的“其他自我”贯彻其意志。

这就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一样,为了不让海妖塞壬的歌声诱惑而使航船触礁沉没,事先要求手下用绳索把自己绑在船只的桅杆上。你去参加晚宴,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正在减肥,不能吃甜食,这样一来,因为怕食言丢脸,你就不会点甜点了(当然,作为补偿,你可以在回家后多吃几块巧克力饼干)。
只有不完美的个人才能做出真选择
将个人定义为高度不完美——理性有限、动机复杂又彼此冲突、容易轻信、受社会制约甚至内部矛盾,其结果反而让个人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
正是由于承认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我们才更能欣赏那些做出跟社会习俗、主流意识形态或其阶级背景相抵触的选择的人的自由意志。当我们接受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就更能欣赏企业家做的那些人人不看好的“非理性”冒险(而当这些冒险成功后,大家又称之为创新了)。换句话说,只有在承认人的不完美之后,我们才能谈论“真正的”(real)选择。而在一个充满完美个人的世界,人们总是知道什么是最优行动,因此所做选择是注定的,这样的选择也就空洞无意义了。
强调“真”选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做出任何我们想要的选择。励志书可能会告诉你,任何事情,只要你选择去做,你就能做成。但事实上每个人能做的选择(选择集)非常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少了。马克思曾经非常形象地写道:在资本主义时期早期,摆在工人面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在恶劣的环境下每周工作80个小时,要么就等着活活饿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养活自己的独立手段。选择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社会化过程和对我们偏好的刻意操控,缩小了我们想要的事物的集合以及可行(可以实现的)事物的集合。

像所有经典小说或电影一样,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复杂又有缺陷的角色,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的确,构建关于他们(或任何事物)的理论,不可避免要对他们进行做某种程度的一般化和简化。只不过主流经济理论简化得太过了。
只有考虑到个人的多面性和有限理性,并意识到拥有复杂结构和内部决策机制的大组织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才能建立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选择的复杂性的理论。
收入差距过大有害经济:不稳定和阶层流动性变弱
几乎没有人会提倡极端平等。不过,许多人也认为,收入差距过大(高度不平等)也是坏事,理由不仅有道德上的,还有经济上的。有些经济学家强调,高度的不平等必将弱化社会凝聚力,造成政局不稳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投资。政局不稳增加了大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包括投资人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感。投资减少,增长肯定也就放缓。
收入差距过大也会造成经济动荡,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额在赚最多钱的人手里会增加投资占比,但就像凯恩斯指出的,投资占比增加意味着经济会更加不确定,从而更不稳定。许多经济学家还指出,收入差距扩大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大因素。美国尤其典型,美国顶层收入飙升,而大多数人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停滞不前。人们如果想要跟上顶层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借钱。家庭债务(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使得经济更加不堪一击。

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加剧会给社会流动制造障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富人家的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贵族学校),毕业后从事高薪工作,但这种学校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上。另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没法打入特权群体的小圈子,套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术语,就是无法积累“社会资本”。最后,甚至精英阶层的“次文化”也是阶层流动的障碍,而这种文化大多也是在贵族学校养成的,比如口音、姿态等。
阶层流动性变差,出生平民阶层的人才就没法从事高端工作,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这都是才能的浪费。同时,一些占据高层职位的人,也不一定是社会上最优秀的那批人。如果这些障碍持续数代,没特权背景的年轻人会对获得高薪工作没信心,甚至连试都不试了。这导致精英在文化和知识上的“近亲繁殖”。如果你相信大变革需要有新的观念和突破传统的见解,那么一个精英近亲繁殖的社会就不利于创新,最后经济就会失去活力。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不平等导致健康和其他人类福利指标上的糟糕结果。的确,收入不平等加剧,穷人数量会增多,而穷人的健康等各项指标本来就比较差。但排除穷人增多这个因素,不平等本身也会有害身心健康和其他指标。
这种论述近些年因为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的《公平之怒》一书而被大众所熟知。书中分析了20多个富裕国家的数据(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大多高于葡萄牙,也就是两万美元以上),并得出结论:国家越不平等,婴儿死亡率越高,青少年生育率越高,教育表现越差,凶杀案和坐牢人数也越多,甚至国民在平均寿命、心理疾病和肥胖上的表现也越差。
在很多情况下,越平等增长越快
除了有很多证据证明收入差距越悬殊,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实例说明,越平等的社会增长越快。
这几个实例分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三个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拿它们跟几个类似的经济体相比,比如拿日本跟美国比,韩国、中国台湾跟非洲或拉美国家比,它们的收入差距较小,但增长更快。
芬兰是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比苏联时期的成员国家还要小。而美国,则是富裕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但芬兰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过美国。1960~2010年间,芬兰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7%,同期的美国只有2.0%。这意味着,在这段期间,美国的收入增加1.7倍,而芬兰增加2.8倍。
以上例子并没有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低增长。事实上,跟类似国家相比收入差距较小但增长更慢的例子也是有的。但是,上述例子至少已经足以反驳“收入差距大有利于增长”这种简单绝对的说法了。此外,大多数采用大量国家数据的统计分析都表明,一国的收入差距大小与其增长率逆相关(但相关不一定是因果)。
对某个社会长期发展的分析,也支持“不平等不利经济增长”的观点。过去三十年,尽管在大多数国家,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比变大,但这些国家中大多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都放缓了。
“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劳动标准 vs.自由选择
既然工作极大影响了健康和幸福,那么我们制定的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安全、就业保障机制等的劳动标准,对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类标准,尤其是以政府法规强制的那些。他们认为制定标准最好通过雇主制定的“员工行为守则”或通过跟工会签订的自愿协议。他们认为,不管工时多长,危险程度多高,只要心智正常的工作者自愿接受,我们就不应该说什么。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一份“恶劣的”工作,那就说明他赚取的工资足以弥补“恶劣的”工作条件带来的痛苦。这背后还真有判例支撑。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案》的判决认定,纽约州政府制定的烘焙业10小时工时上限违宪,因为这“剥夺了烘焙师傅在工作时间选择上的自由”。

这种说法本身合理。如果一个人自由做了某个选择,根据定义,这必定意味着这个人喜欢这个选择超过其他选择。但事实上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个选择是在哪一种条件下做出的?这种条件合理吗?有没有可能改变?大部分工人愿意接受“恶劣的”工作,是因为另一个选项就是饿死。也许当时失业率非常高,他们没法找到其他工作。也许他们由于童年贫穷,身体发育不良或不识字,没法吸引到其他雇主。也有可能他们家乡遭遇洪水,失去一切,特别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做什么都行。那么,这还算是“自由”选择吗?这些人难道不是被迫(为了有饭吃)做出选择吗?
天主教“解放神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拉美盛行。其代表人物巴西主教多姆·赫尔德·卡马拉有一句名言:“当我给穷人食物,他们说我是圣徒,当我问穷人为何没食物, 他们说我是共产党。”也许我们偶尔应该像一名“共产党员”,质问穷人自愿从事“恶劣”工作背后的条件是否合理。
穷国工时比富国长
在大多数富国,人们每周工作35小时左右(东亚富国则要长一些,日本是42小时,韩国44小时,新加坡46小时),是他们的曾祖父母或高祖父母(70~80小时)的一半。
今日穷国工时确实没有处于同等收入时(18、19世纪)的富国长,却比今日富国的工时长很多。有些穷国的平均工时多达每周55小时,比如埃及(55~56小时)和秘鲁(53~54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5~50小时也算长的,比如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巴拉圭、斯里兰卡、泰国和土耳其。
这些工作时间数据低估了我们被工作占有的时间(而不是真正“在”工作的时间)。在那些公共交通差、居住区与上班地点距离远的国家,通勤时间大大增加,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在南非,大部分城市住的都是白人,贫穷的黑人都住在偏远城镇,黑人每天去城市工作,来回可能就要花掉6个小时!另一方面,如今互联网已在商业应用上普及,许多白领下班后也要继续工作。
干旱或洪涝:工时分配的不平等
在看工作时间数据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数据都是平均值。在许多国家,有些人工作时间过长(ILO的定义是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有健康风险。其他人则处于与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即使他们想要全职,也只有兼职可做。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的工作处境。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也就是他们有工作,但对产出没啥贡献,主要是为了获得微薄收入而已。比如说在农村,一家人耕种一小块地;或者说在城市,有很多穷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做点未登记的小生意(比如路边摊),而且多半是一个人。他们给自己“创造”工作,往往只是把乞讨变得不像是乞讨。这些人不算失业,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失业。
工时过长的劳动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51%)和韩国(50%),泰国、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也都超过40%。占比最低的是俄罗斯(3%)、摩尔多瓦(5%)、挪威(5%)和荷兰(7%)。
实际工作时间有多长:带薪休假和年工作时间
每周工时看不出人们工作量的全貌。有些国家的人们每周都工作,而另外一些国家的人们则享有几周带薪假期。在法国和德国,带薪假期可以长达五周(25个工作日)。因此,要对不同国家的人均工作量有全面的了解,必须看年工作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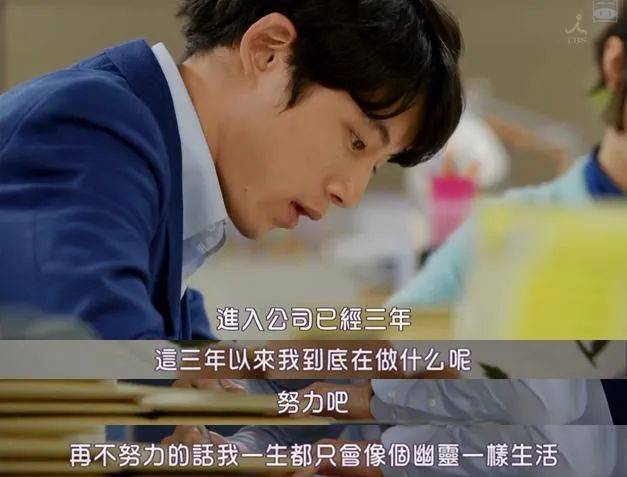
只有OECD成员国才有年工作时间的数据。在这些国家中,2011年,年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是荷兰(1382小时)、德国(1406)、挪威(1421)和法国(1482);年工作时间较长的有韩国(2090)、希腊(2039)、美国(1787)和意大利(1772)。OECD成员国中也有一些不是富国。在这些国家中,墨西哥(2250)的年工作时间超过了韩国;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智利的年工作时间则为2047小时,介于韩国和希腊之间。
哪个国家的人最“懒”:工作时间的迷思与真相
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一些国家是勤奋还是懒惰的文化刻板印象是完全错误的。
墨西哥人在美国人眼里是“懒惰的拉丁美洲人”的典型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每年的工作时间却超过了“工蚁”韩国人。而在OECD成员国中年工作时间最长的12个国家,有5个就是拉美国家。因此,说拉丁美洲人懒散,工作不努力,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刻板印象。
欧债危机期间,希腊人饱受其他欧美国家媒体诋毁,说他们是勤劳的北方人(即南欧以北国家)身上懒惰的“寄生虫”,但希腊人的年工作时间实际上比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富国都长。希腊人的工作时间是德国人的1.4倍,荷兰人的1.5倍,而德国人和荷兰人一直被认为是工作狂。意大利人也被认为是“懒惰的地中海人”,然而意大利人的工作时间却跟美国人一样长,是他们的德国人邻居的1.25倍。
为什么工作越努力越穷?
一种解释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些误解,是因为信息严重过时。就以荷兰人为例。
在很多人眼里,荷兰人至今还是勤劳节俭的清教徒形象。然而,这种刻板印象背后依靠的信息至少是50年前的,甚至是80年前的,非常过时。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荷兰的确是今日富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几个之一。然而,这种状况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以后则变得更快。如今,荷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懒”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年工作时间最短。
对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的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往往误以为贫穷是懒惰的结果,因此自动假定穷国的人民比较懒。这些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率低下,这很少是他们的错。一国生产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资本设备、技术、基础设施、制度,这些都是穷人没法提供的。
因此,如果真要怪谁,也要怪希腊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富人和权贵。他们控制着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却没有为这些决定因素提供足够和优质的投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张夏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