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雅婷,编辑:木村拓周,头图来自:《司藤》剧照
“真·大女主”来了?
在《山河令》播出的尾声里,是《司藤》走向了“BG(异性恋 CP) 之光”。彼时,双强男主的兄弟情设定还没有完全下头,言情剧不需要女主角的观念,正在“耽改101”的蓝图里逐步攀升成另一种喜闻乐见的主旋律形式。
因此多数人并未料到,这部剧在首集放出的明确信号,有多让人为之一振——“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主人,你凡事都要听我的,记住了,我叫司藤”。
女主角司藤的这段台词,和紫霞仙子在《大话西游》开头里喊出的那句“现在我郑重宣布,这座山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还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的这种“所属关系”,是寄希望于至尊宝个人对爱情的投入和承诺,主要任务是为了帮他完成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
而在《司藤》里,男主角秦放的性命直接受制于女主角司藤的前途,这种所属关系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帮司藤完成梦想。
在“大女主”类型式微、男男CP统治小荧幕的今天,这样的初始设定不可谓不惊人。

《司藤》这部剧改编自网文作者尾鱼的同名小说,原著从2014年年底开始在晋江文学城连载,原名《半妖司藤》。女主角司藤的设定,按电视剧里的介绍,是“性狠辣”“善绞杀”“同类切齿”和“战无败绩”。主要剧情是说死于 1946 年的司藤在 2020 年时复活了,有超强战斗力的她拉着她的“仆人”秦放,开始了寻找来自真相的旅程。
尾鱼自己曾在《司藤》小说的后记里写,在所有她写过的角色里,最爱的还是司藤。主要原因是“她不依赖任何人,把自己从人生的欲海里救赎出来……走上过歧路,自己扳回来;爱过错的人,仰天一笑,安守寂寞,却也最终接受陪伴。自问做不到,也没有见谁做得到。”
这段话,联系上司藤的人物设定,我乐于把其解读成一种颇具女权色彩的宣言。尾鱼想创作出的女性角色,是一个不必依附于他人,不惧“犯错”和“犯错”所必须要支付的成本,不必非要有爱情做结尾、靠爱情升华个人价值的人。这在现实里稀罕,但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想象层面的应许之地。
只是 2015 年晋江文学城的言情小说区,尚难以为司藤要走的路点出明确指向。作品连载初期,读者因为难以接受男女主角纯粹的主仆关系、秦放有过两个前任女友的过去,以及看起来无法被跨过的“祖孙关系”,而频频给作者留言建议。
尾鱼多次在小说后记、连载区和读者回复里解释说,“我依然在晋江的文章属性里找不到合适的分类……不是单纯的言情,但总得言点情吧……情之一字,你看它有就有,你看它没有就没有……”

局中人司藤能靠“定义”关系掌握主动性,原著创作者却甚至无法在平台上“定义”自己的作品类型。
但几年过去了,性别议题的水温早已大不相同。
如果说,对六年前的类型文学或影视剧作品而言,在创作里建构必须要拥有爱情、用婚姻来确立个人认同和身份价值的女主角,是一种无可被避免的惯性;那六年后的今天,在“伪大女主”被轮番剖析病因、女性意识在赛博空间有空前进步的当下,难道不正是新“大女主”诞生的绝佳时机?
从女性世界中来,到女性任务中去
客观来说,《司藤》确实为电视剧里能展现出的异性恋关系模式,添加进了一些新的元素。
首先,司藤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多数身着古装的大女主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事实上,无论是仙侠、架空历史或是穿越,无论原文有多么强调女主个人的能力拔群,她还是要先闯入到一个“男性”的世界里去。
要么是完成男性视角历史里为她划定的任务,常见为争嫡打小的宫斗或宅斗,靠猎杀男性价值取向里的不同女性来完成自己的升级。要么是完成男性本来要完成的任务,常见的是扶植自己代表的师门成为名门正派,在一个广不看好女性能力的虚构世界里,靠着“玛丽苏”的超能力来证明极个别女性可以做到和男性一样的事情。多数女性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眼花缭乱的服装设计,人物弧光也主要集中在从筚路蓝缕到穿金戴银的演化中去。
当然了,这些全都可以解释成是,旧时代封建礼教下女性命运的悲鸣。只是在这样的故事模式里,难以出现或者孵化出真正的女性主义,创造出能完全挣脱父权,真正从女性视角诠释女性价值的人物和故事。即便印象深刻如甄嬛,她亲手杀死父权制最大的代表皇帝,也还是要坐上太后的位置,成为亲手稳固父权制社会的关键人物。

而司藤是没有旧时代身份包袱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是苅族,本来就不受人类秩序的规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从民国穿越到当代,只为寻找自己异变出来的那部分恶,接纳和成为完整的自己。
男主角秦放在书中和剧中都向司藤问出的那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司藤始终坚持的回答是,“重新变回妖,再见到司藤”。即便在电视剧里秦放对她多次表白,以不复相见为理由多次劝阻司藤放弃。司藤也能板起脸告诫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该管的别管,她想做什么从来都是她个人的事情。
这样的情节天然形成了一个只属于司藤自己的视角,是秦放闯入到了司藤的生活里去。女主角不必再围绕着总裁、皇帝和将军等种种权力名词代表来书写自己的故事,男主角因为可能存在的孙子身份会总是处于司藤之下的权力层。

另外,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司藤要完成的事情也很感人,找到被父权传统观念侵蚀扭曲的那部分自己。再次面对那个女孩曾受爱情哄骗,坠入红尘,甚至想靠生个孩子的方式来挽回男性注视的过去。司藤要找到她,然后要么和她和解,要么被她杀死,要么把她杀死,从思维和观念的桎梏中,再开出一条更广的未知前途。
以上种种都让人无法忽视《司藤》内里那条明显女性主义叙事线索,而这或许是解释《司藤》前期受到意料之外关注的最好原因之一。相比“女强男弱”、“女攻男受”、“女A男狗”或者粗略一句有新意等种种关系设定,最重要的是,国产剧终于有了一个还比较完整的女性主义解放视角的叙事结构。
直到秦放在电视剧里变成了一棵树。
言情的价值
秦放是棵树的剧情是在电视剧的第 24 集才讲明的,对于一直用女性主义视角看剧的观众例如我来说,这几乎是一种背叛。
先不说藤和树之间是否有依附共生关系,最直接的,电视剧之所以要加入原著没有的设定,最终还是为了要让观众用一个更符合伦理的视角来理解司藤和秦放的爱情,并为两个人最终能走到一起增加可能性。
这大大消解掉了尾鱼描写司藤“无风亦能招展”的魅力,一个看起来已经能在社会秩序里有诸多越轨行为的电视剧女主角,“被爱”依旧是衡量她人生价值的重要指标,她的“美好”结局还是要传递一种被爱的重要性,且这种被爱如果不能社会伦理秩序所承认,终究是显得不够圆满。
我对这样的叙事耿耿于怀,甚至开始反思自己怎么就忍得下《司藤》粗糙的镜头设计和度假村式场景编排,会这样一直看到快要邻近结局。
能接受这个设定变化的观众有一个经典逻辑:大女主电视剧就非得是女性专心搞事业,全然抛弃甜甜的恋爱吗?现实生活已经够累了,安安心心嗑个 CP 不好吗?
并非如此,言情当然有其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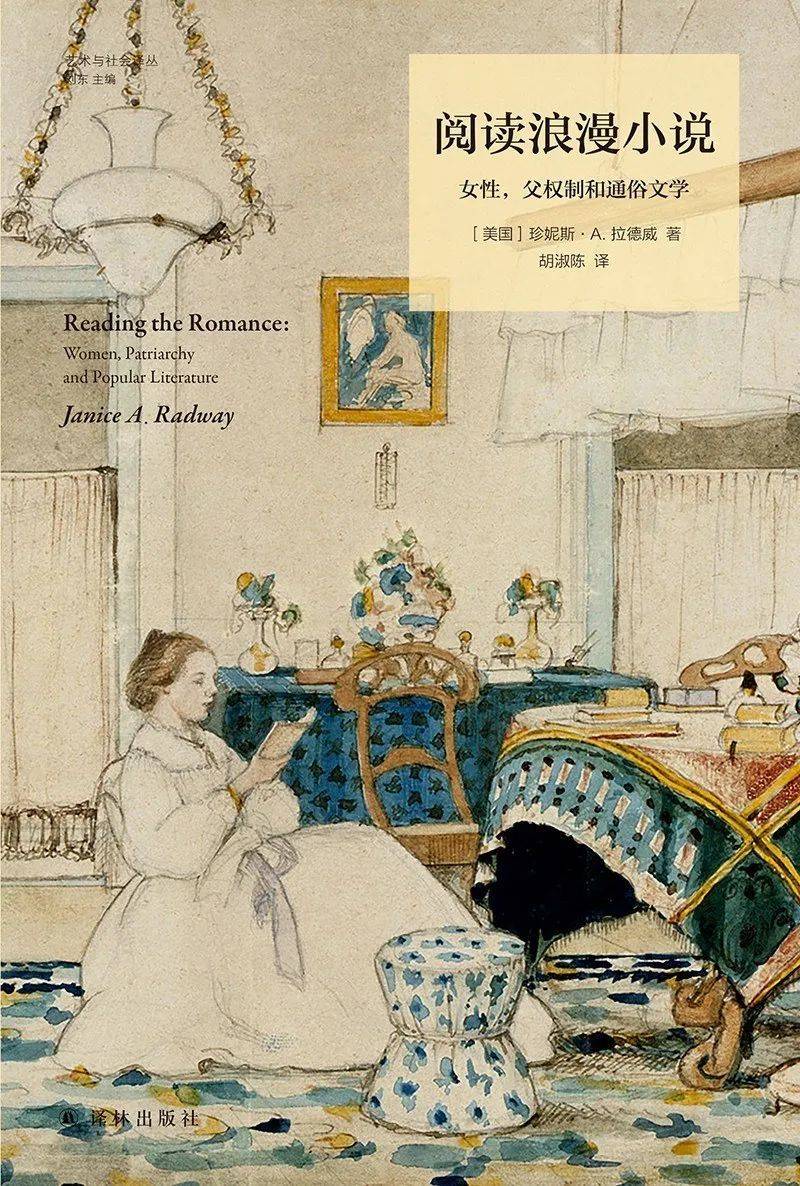
美国文学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Janice A.Radway)曾在著作《阅读浪漫小说 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一书中解释女性为什么喜欢看浪漫(言情)小说。其中有一个观点是,“阅读浪漫小说让女性在传统的方式之外又多了一条可获得情感满足的途径,间接地提供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充分获得的关注和呵护”。
由这个观点展开来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充分获得关注和呵护,是因为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往往会比男性有服务于他人,哺育后代,因母职身份而不得不牺牲自我的“工具色彩”,对于全职主妇这样的“工具色彩”则会更为加重。
言情存在的正当性正在于此:女性不得不靠进入阅读场景的方式,通过代入浪漫小说女主角的身份,来重温那种她被视若珍宝,得到一个人全然投入的温柔注视的感觉,是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提供给他人这样的感受,他人却难以反馈给她相同的感受。而在这个过程里,为了提供足够好的代入体验,浪漫小说也会对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情感暴力(渣男行径)作出合理化解释,因此冷暴力控制欲和闪躲在言情剧情里,一般都会被象征成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超级爱你。
但也正因为此,女性热衷消费言情,有时候是一种“逃避”:通过消费一个美好的幻想,逃避对现实做出积极回应的责任。
并不是说这种“逃避”值得被谴责,相反,“逃避的出现”本身说明了很多。珍妮斯·A.拉德威认为言情文化产品作为女性“逃避”空间批量出现,本身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结构里时时在出现着裂隙,那些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人会在这样的裂隙里发出抗议。
因此,相比否定逃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承认自己无法创造出一个不靠阅读来产生替代愉悦体验的世界”,研究并分析那些常常被自己忽视掉的“逃避”,或许才能更好的认识甚至是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
脱轨的电视剧容不下积极的现实
回到《司藤》中。在大女主剧整体走下坡路的阶段中,它是其中表现还算亮眼的作品。一个相当重要的推力在于,对于电视剧《司藤》的绝大多数受众来说,很多女性已经能在现实生活里识别出,以“爱”之名包装出的牺牲和妥协。
明明有那么多人已经抛下了结婚生子就是人生唯一选择的路径,但我们还是要看一个情感复原着力在女性意识尚未苏醒的东西。相比较几十年前女性只能靠婚姻爱情实现自我价值的现实,当下的我们所向往但还未达到的世界,应该是女性全面解放的号角,而这也是女性还需要虚构的重要原因。
而如果有人因为秦放最后被一股天外之力拉平了他和女主之间原本不对等的权力天平,从此两人可以展开一段甜甜的恋爱而感到轻松和宽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愿意忽视的是,这种宽慰和轻松的代价是《司藤》把本应该发生的女性解放,最终以一场爱情幻想的兜售所替换掉。
基于观众对关系中男女权力关系结构深入骨髓的“习惯”和默认,电视剧《司藤》最终决定不在今天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表面上看来,消费这样的故事似乎意味着电视剧观众的某种权力升级,即自己不再受现实爱情蛊惑,能靠嗑工业糖精达到多巴胺自由,默认言情剧不能捕捉到这个时代社会结构里的裂隙,是生产爱情代餐的职业工具,最终喊出口号“我可以单身,我嗑的CP必须结婚”。
可实际上这也是在说,我们默认国产剧,以及更多大众娱乐产品,失去了情感复原功能的合理性。它可以不再主动洞察现实中时时变化着的情感创伤,为某一个群体发声,制造共鸣去暴露一个整体的创伤和抗议,而这被我们认为是合理且实用的。
长久以往,我们也会更习惯于按照某个固定情感公式产出发出一种标准化的声音。这样的文化娱乐产品是是能赚钱的,是可以尽最大程度规避掉风险的,是保守的,也是无害的。
所以即便《司藤》的原著里有一些已经被 2015 年读者群成功验证过的能被接受的“不同”,有能被近两年女性理论完整解释的“进步”性叙事。可当它转变成电视剧这一媒介后就还是要被修剪得足够整齐。当作品面向的是窄众的青年群体时,它在表达上的先锋性是被允许的;而当其被改编为电视剧这个更“大众媒介”的形态时,它的表达就必须龟缩回到那个更大、更普遍的工业规则之下。
这让国产剧以及我们的大众娱乐,看起来实在相当消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雅婷,编辑:木村拓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