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Nikita,主播:@寇爱哲,文字整理:雨露,头图由受访者提供。
回家
我叫 Nikita,今年 43 岁,现在生活在美国洛杉矶。
我的家乡是陕西武功的一个小地方,从小父母支援三线,工作比较忙,没有余力照顾家庭,所以我哥跟着父母,我则被放在老家寄养。
小时候我一直跟着外婆外公在乡下生活。农村养孩子就像养小猫小狗一样,没有人教我识字数数儿这些,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识字;我就像一只小猫小狗一样野蛮生长。

直到快上小学的时候,父母才来接我。
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我正在村里的麦垛堆上玩,爬到了最上面,像个好动的小男孩,玩得正开心;突然看到远处有个白白净净的小男孩,穿着干净的湖蓝色衣服,紧接着就看见我爸。
我爸脸很长,看上去挺凶的,他来叫我回家吃饭。我那会儿还不认识他们,但看他们是从外婆家里走出来的,就下了麦垛堆跟他们回去了。
回家才看到我妈,她烫着卷发,穿得干干净净,很好看,跟当时村里人的穿着打扮都不一样。我之前吃的一般是玉米茬子粥,但是那天吃的是面条,菜里还有肉,我就挺开心,光顾着吃,也不问这些“客人”是谁。
第二天,我外婆说镇上有集市,让我跟他们去赶集,我就跟着他们出来了。一路上我都很高兴,小孩子嘛,感觉很新鲜;而且他们还给我买肉夹馍吃,我说要买两个,给外婆带一个。
到了集上,我爸问我坐没坐过小汽车,我说没有,他就带我们坐汽车进了县城。到了县城,我们就往火车站方向走。我爸接着问我想不想坐火车,我们带你坐火车。我才觉出不对劲,意识到离家有点太远了,于是我说,不行,我要回家找外婆。
但是我爸妈还是把我抱上了火车,我一上车就哇哇大哭,特别害怕,哭到乘务员来检查证件,查问孩子为什么哭,大概是担心是贩卖儿童这种事。
那时候的火车开得很慢,我几乎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有时候半夜睡醒,懵懵懂懂地睁开眼,看见车窗外的夜色和远处房屋的剪影,感觉既陌生又有点好奇。
经历了几天漫长的行程,等下了火车,我发现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兄妹之间
我们生活在一个山沟里的工厂,周围什么都没有,但工厂里设施很齐全,有自己的电影院、车队、游泳池、学校等等,就像一个自成体系的小宇宙。
这个地方在广西。八十年代初,在北方农村长大的小 Nikita 来到了这个设施完备的工厂大院。她发现,这里的人说的都是普通话,而自己那时候操着一口陕西话,经常被其他孩子嘲笑。所以她变得不爱说话,总是心里纠正自己的口音,慢慢地,她成功地把陕西话忘光了。
除了语言上的融入,还有行为举止上的。
Nikita 在农村的时候可以像男孩子一样到处野,但在这个大院里,她得表现得像个女孩子,否则,可能连哥哥都会嫌弃自己。

我长相比较糙,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好看;但是我哥和他同学的弟弟妹妹都很好看,特别是妹妹,都很漂亮。所以记忆中,我哥不太愿意带我去玩,他的同学也不太愿意带我玩。
我就像个小跟屁虫,在他出去玩的时候默默跟着他。他同学就挺烦我的,甚至把我按在墙上打我,当时我哥就站在旁边,但没有帮我。其实我现在长大了,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毕竟年纪比较小还不成熟;但那个时候,我心里很委屈,觉得他是我哥,应该保护我的。
对小孩子来说,不开心的事儿其实很容易忘掉。小孩子也最容易适应环境,没过几年,Nikita 就完全融入了这个大院的生活。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兄妹俩也都越来越懂事。很多年后,哥哥还为自己小时候总欺负妹妹道过歉。这些,Nikita 现在都是笑着说出来。
但是一些让她笑不出来的事情,从她 12 岁起陆续发生。
公交车上的手
我小时候发育早,长得很高。12 岁那年我们全家一起去北京旅游,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去逛商场,北京的公共汽车特别挤,我跟爸妈被挤得隔开了。
我当时穿的是短裤,突然就感觉到有一只手,不知道从哪来,开始从我的短裤外往里面摸。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性骚扰,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是性骚扰,甚至没有性的概念,因为那个年代是没有性教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身体,也很难描述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感到害怕,很不舒服,于是就不停地转身想躲开。我还感觉到大概有两只手,但我不知道手来自何方,也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
当时车上挤到人们可以把脚悬空的那种程度,我根本转不动身,没有办法去挣脱。我就开始喊我妈,妈!我要到你那去!
我妈说,你别动,挤来挤去的,还有两站就下了,在那待着吧。
我就只能使劲转身,很害怕也很无助,就这样熬了两站路。
下了车之后,我蹲在地上就开始哭,感觉整个天都是黑的,但其实那天是北京的一个下午,天气非常好。
我妈很不理解,觉得我在闹脾气。“一家人高高兴兴逛商场,你在这哭什么?”
我是想说些什么的,但我真的无法描述,不知道是巨大的恐惧感还是耻辱感,很莫名其妙,我就是无法说出刚才发生的事。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隐隐约约开始有了性别意识,知道了我是个女孩。

所谓的“叔叔们”
14 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邻居有一个叔叔来敲门,我就给他开了门。
我很诚实地说,我爸妈不在家,哥哥也不在,您找谁?
他反问,那就你吗?
然后就进来了。
我以为他可能有什么事情想等我爸妈回来说,于是就打算回自己房间做作业。但是他叫住我说,看你现在长挺高的,叔叔给你量一下身高。
我们家门框上有那种身高标记表,我当时也完全没有危险意识,就站到那里,同意他给我量身高。
但接下来他就把我挤在门框上,开始动手动脚地摸我。我反应过来后就开始疯狂地反抗和挣扎。
我使劲把他推到房间之外,想关上门,但他很健壮,直接就把我推到了书桌上。
我随手抓起书桌上的一把学习用的钢尺,胡乱地挥舞着试图反抗,结果慌乱中一不小心划伤了自己的脸,左眼旁边,今天还有痕迹。
他大概没想到我反抗得这么激烈,担心无法收场,就停下来走了。
这个叔叔是我爸同一个厂里的同事,平时和我们家关系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的邻居跟现在的邻居非常不一样,现在邻居都见不着面,但那会儿,谁家包了饺子、做了好吃的都会给邻居端过去,关系特别亲密。
所以这个叔叔做出这种事,我觉得不可思议,很荒诞。
过了两天他又来到我家,找我爸谈工作的事。正常来说,我应该礼貌地问候他叔叔好,给他倒水之类的,但我没叫——我根本叫不出来。
而他竟然还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过来拍拍我的头和肩膀,我马上闪开了,紧张地回到我的房间,关上了门。
这个行为惹怒了我爸妈,他们觉得我这样很没家教。等叔叔走了,他们就把我叫出来,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做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心情。
他们就一直骂我,最后我实在被逼急了,大声说,我不喜欢他!
我爸妈感到很奇怪,追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他对我动手动脚的,老摸我!
我爸还以为是他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拍拍脑袋、肩膀的动作,于是说,这是人家待见你的意思。
我简直百口莫辩,又很难说出他那天具体的性骚扰行为;但我当时听说过强奸这个词,并且知道它是很严重的后果。于是我边哭边说,不行!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把我强奸了!
我爸妈听后非常生气,他们觉得这个词是不能出现的,这个词怎么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太脏了。
他们甚至根本不相信我说的,“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在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你认个错不就完了,编这些事干什么?”
我那时就很崩溃,一瞬间觉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我自己了。
其实不只是他,我们厂里还有很多叔叔,他们的行为也没有多光彩。
比如我同学的父亲。有一次我同学发烧,在家里休假,老师让我给他带笔记。我带过去在他床前给他读笔记,他爸爸就会在背后对我动手动脚。
比如去另一个同学家里玩,一碰上停电,我就赶紧把自己蜷起来,抱在一块,用膝盖把自己身体关键的部位全挡住。因为我知道不出几秒,就会有只手伸过来。果然就是这样,等到我同学点了蜡烛,这只手才会离开——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像是家常便饭一般。
可能是我们工厂的环境比较闭塞,再加上那个时代大家都处于很压抑的状态吧。
现在我长大了,前两年春节回家的时候,要和我爸的这些同事、这些当年的叔叔们一起吃个团圆饭。
当我得知当年性骚扰过我的那个叔叔也在,就跟我妈说不去了。但我妈指责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好不容易大家聚一下,怎么不给面子啊?
我说我真的不想去,我妈就硬要逼我去;终于我急了,我说,我不想去的原因你难道不知道吗?
结果我妈说,那还能怎样?难道跟别人撕破脸吗?这么点小事!
我都已经 40 岁了,听到这句话还是忍不住哭了。
我后来听到过一个笑话,讲一个农妇拎了一筐鸡蛋进城,打算去卖鸡蛋。路过小树林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的来打劫,这个农妇就很害怕,结果这个男的只是劫了色。于是她拍了拍身上的土,站起来说,多大个事,我还以为你要抢我的鸡蛋呢!
我当时听完就哭了,一点也没觉得好笑。
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价值观的问题:在我妈的眼里,同事关系比我的感受和经历更重要。其实我现在并不恨他们,甚至能“理解”他们,但能“理解”不代表我能接受,不代表我能忘记那些对我造成过伤害的事情。
就因为这些经历,我后来读高中的时候都是剪短头发,Tom Boy 的那种打扮,爱穿大格子衬衫,牛仔裤,回力鞋,没有任何曲线,跟男生一样。经常在去上洗手间的时候,被阿姨拦住,以为我走错了。每当这时我就把衣服稍微撩一下,挺挺胸,证明我是女的。

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男性化到这个程度,对我自己是一种保护。
军队记忆
打扮的像男生一样的 Nikita,在上高二那一年放弃了参加高考,选择了去广东参军。在军队里,她如鱼得水。
我是 1996 年底入的伍,在部队我很能吃苦,身体素质也还不错,各种训练、任务我都能应付得很好。后来其他女兵都分到机关去了,干一些文职工作。我就找了领导谈,要求在基层,继续站岗,男兵能做的我也能做,所以他们都把我当男兵一样看待。
有一次,排长的婚礼之后,大家转场到酒吧去喝酒。我的同事都了解我男孩似的个性,有的就来给我灌酒。这时一个其他单位的男同事看到了就说,你们怎么能对女孩这样?
于是他帮我挡酒,在旁边一直照顾我。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当做女性对待,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后来我和这个男同事关系比较好,他也成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真的要结婚吗?
认识这个男朋友的时候,Nikita 已经服役了将近五年,她很快就退伍了。退伍之后,她短暂地回老家开了一个内衣店,因为那时候 Nikita 逐渐有了女性意识,开始对时尚产生兴趣。但是为了这个还在部队的男朋友,Nikita 很快就回到了当兵的城市,在那里开店。这样两个人就能经常见面。
他是广东人,个子不高,挺壮实的,有点大男子主义。所以他会经常跟我讲他妈妈是如何贤惠,如何早上 4 点就起床烧水、烫碗筷等等。
这跟我受的教育和价值观很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我为人又很讲义气,当时他家盖房子没钱,我就把自己的店卖了,把钱给他盖房子,他因此很感动,觉得我好像是那个可以跟他一起过日子的人。
他想要跟我结婚也有他的原因。有一天他下班来公司接我,我正好在加班开会。他就站在玻璃门外看见了我开会的样子。当天晚上他就跟我说,要和我结婚。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工作的时候看上去跟和我在一起时很不一样,特别有光芒。
我想,可能他从那个角度看到了我的价值,担心我如果不和他结婚,可能就会跟别人走了,他会遗憾。
但那时我还不想结婚,因为我还很年轻,想继续发展事业;但他也很坚定,表示不结婚就分手。
于是我妥协了,答应了和他结婚。
结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花好月圆的日子,民政局排满了人。我们是上午去排的队,下午才能领证。中午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饭,我就有点闷闷不乐。
他跟朋友很开心地吃着饭,我就出来给我妈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我就哭了。我说,妈,我结婚了,可是我觉得我好像犯了个错误,好像这婚不该结。
我妈在电话那头,很冷静地说,自己酿的苦果,自己吃。
那一刻我心里更加觉得,我可能真的犯了个错误。
温水煮青蛙
我跟他结婚之后才越来越发现,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不让我跟我的朋友接触,因为看不惯他们有的人大龄未婚或者离异。又比如我那时候喜欢玩户外,纯粹把这项运动当爱好。但他觉得一堆大龄青年待在一起,有男有女的,很不好。
他经常会打电话到我公司,看我是否在上班;然后打电话到家里,判断我花了多长时间回家,所以我只好掐着点儿到家,怕他多想。
这样的日子就像温水煮青蛙,从一开始没有察觉,到后来我也慢慢习惯了。
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联系我说,我们很久都没见着你了,正好刚结束一场徒步,大家正在你家楼下的餐厅吃饭,你能不能和我们见个面?
于是我就跟丈夫建议一起下楼散步,然后特意路过餐厅。我提前给他们发过短信,然后隔着人行道,我看见朋友们在餐厅里使劲儿跟我招手,但我不敢进去;我们就这么看着彼此,其中有个朋友就哭了,我在这边也哭了。我很心酸:我怎么是这样见朋友的,我是被软禁了吗?
这之后我才隐约觉得这样的婚姻状态不正常,但偶尔还会劝自己:可能是他太在乎我,很怕失去我吧。
反抗?无效!
有一天晚上,他喝完酒回家,已经凌晨 4 点了,硬要我给他煮粥喝。但第二天一早我还得上班,给他煮粥的话,压根就没空睡觉了。于是我说,想喝粥的话,咱们明早点个外卖。
结果他很不乐意,“要老婆干什么的!不就是回家有口热饭吃,能说说话,能搂搂抱抱。”老婆就是干这个用的。
我只好忍着困意,不情愿地起来给他煮粥。
谁知道他那天突然挺有兴致的,非要抱我,想和我发生关系;但我凌晨起来煮粥已经够疲惫了,根本不想回应他。
但他不理会我的意思,强制着我往下进行,我只好不停地抵抗。
我小时候被性骚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成年男人很强壮,我打不过很正常;但现在我 20 多岁,身高 1 米 7,已经人高马大的,我还坚持锻炼身体,而对方是一个比我矮的男性,还不怎么运动......我以为我能挣扎,但我不行。
我那时才知道,男性就是比女性要强壮,他就是可以压制住你,为所欲为,做他想做的事。即便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很强大了,但我还是保护不了自己。
到后来我渐渐放弃了挣扎,躺在地板上无奈地歪着头,看着平时从没注意过的家具。甚至看到厨房的橱柜有个踢脚线松了,事后我站起来,很平静地把它敲回去了。
那几年我还不太有婚内强奸的概念,只是觉得他违反我的意志去做这件事,对我很不尊重。而更让我伤心的是,我之前跟他讲过我小时候那些被骚扰的经历,结果他还是拿这种事情来伤害我;就像我跟他说,这是我的伤口,但他还继续戳那里。这个事情我很难接受。
所以虽然之后他和我道歉了,但我已经产生了想离开他的念头。
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离婚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家里人会觉得,你一个女人离婚很不光彩,“离异妇女”是个很难听的称谓。所以我也很犹豫,尽管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不想过这种日子,想过自己向往的生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终于离开
有一天上班,我听到许巍的一首歌叫《九月》,歌里唱着:我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我决定去海边看一看落日......
那时正好是 8 月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立刻写了一封请假信,请了一个月的假——9 月份去西藏。
现在听起来,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些烂俗,但当下的我真的一刻也坐不住了。
很意外,不知道是为了表现对我的理解和支持,还是出于某种愧疚和弥补的心理,我先生也同意了。
我借了冲锋衣,买了个背包,从广州坐火车到成都,然后进藏。他派了个司机送我到广州火车站,那个司机一直看着我上了车才走。
后来我才知道,我先生以为我是跟别的男人一起去旅行。因为他骨子里不相信女性可以一个人去远处旅行,他觉得女人应该在男人的陪伴之下,或者跟别人一起才能出门,单凭一个女人自身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事情的——但我真的是一个人上路的。
到了成都,一路旅行让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跟事。
旅行路上认识的这些人,很多都成了 Nikita 至今的好朋友。在拉萨,一伙朋友要去阿里无人区,就劝 Nikita 一起去。听说能看到藏羚羊,Nikita 很心动。
所以她临时改变了计划,又跟公司多请了一个月假。但这也让丈夫更加怀疑 Nikita。

其实我想的是,就这一次,痛快地玩一次,从此把自己的这份自由和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全部埋葬掉;然后回家安安分分地去过那种日子,没准我真的能做一个每周煲汤、煮糖水的广东型家庭主妇。
结果他就天天和我打电话吵架,问我,你这样是要干嘛,是要离婚吗?!不然就给我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跟别人跑了。我心想,这日子算是过不下去了,那就离婚好了。
结果等我旅行完一回到家,一开门发现,他竟然把我爸找来了。
我一下子很生气,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你把我爸找来了,这就是在拿父权那一套来压我:我是你的男人,你要听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把你爸请出来,他是你的父亲,你的权威,你总得听他的吧!
我当下就很坚定地要离婚。我已经不在乎那张纸了,也不在乎我出了钱的房子,我只想尽早离开这个家,于是我就搬出去了。
一碗馄饨
分居的半年里,他还会打电话骂我,指责我毁了他的人生,各种 PUA 我。再加上那半年我状态很差,甚至爆发了夜食症和抑郁症。
Nikita 在青少年时代尝试过两次自杀,但幸好两次都被人撞到,她也编了个借口糊弄过去了。
但这回的抑郁症爆发,让 Nikita 又一次想到了自杀。
这件事情很奇妙。
有一天下午,我处在抑郁的状态中,不吃不喝也睡不着,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我打开厨房和洗手间的煤气,关上窗户,静静等待着死亡。
但这时突然有个人敲门,一直喊我的名字。因为怕吵到邻居,我只好挣扎着起来了,给她开了门。
——原来是以前的一个同事,她说,我刚好路过这儿,给你带了一份你之前带我去吃过的馄饨。
就很神奇,因为我们两个平时没有什么交集,而她也只是碰巧路过。
接着她就进来了,闻出气味不对劲之后,她默默地关掉煤气罐,打开窗户,看着我吃馄饨。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那碗馄饨冒着热气,我吃着吃着就哭了。
她说,你之后想吃的话再跟我说,我给你带。
然后她就先走了,临走时说,她明天还来。
可能是这碗热乎乎的馄饨,吃完之后我觉得好像有点元气了,就起来洗了个澡,下楼去转悠。当时正好是晚饭时间,我闻到邻居们做饭的香味,看着路上的行人三三两两地散着步,一股人间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我就给那个朋友发短信,告诉她明天不用来了。我说,我会好好吃饭的,我没事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自杀了。
和先生分居了两年后,有天我收到了他的短信,他终于提出要办离婚手续,虽然我中间也没有催过他。
于是我们约了个日子,和和气气地去了民政局。
对面照相馆的东北大姐看见我打扮得很漂亮,以及我们俩客客气气的样子,很惊讶地问我们,真的是离婚吗?
我笑了,又想起结婚那天,民政局里乌泱泱地排着队;现在我们离婚了,倒是不用排队了,很快就办好了手续——竟然有点戏谑的意味。
孩子
分手后的这些年,Nikita 陆续去过澳门、成都发展,最后她在成都安稳下来,开了餐厅,事业发展不错,也交到了很多朋友。这些都让她抑郁症的问题缓解了不少。
在成都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小几年的美国男孩,并且怀孕了,但我怀孕的时候他已经回加州了。
我想我已经 35 岁了,自己也有能力养一个孩子 ,于是很自信地打算生下这个孩子。
那时我身体非常好,怀孕期间还能去健身房游泳,游得比别人还快。我自己拿个本子记录着时间,定期做检查,临近生产的日子就去了医院。
生产那天也很顺利,是顺产,半个小时就生出来了。
孩子出生的前两天,医生们都觉得很正常,但我觉得有点不对。因为我好像在哪见过她的样貌,想了半天,想起来有个美剧叫《Glee》,里面有一个患唐氏综合症的女孩——我觉得我孩子的样貌和她有一丝相像。
但孩子当时已经做了唐筛,并没有显示出症状;在她一个月的时候也做了儿保,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依旧觉得不对劲,因为孩子过于安静了,很少哭,哭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表情,不像正常孩子那么鲜活,像是蒙着一层什么东西。
我就要求再做检查,医生又进行了抽血和检查。等待结果的半个月里,每一天都非常煎熬,我觉得有可能是病,但又很希望奇迹出现。
去医院拿通知的那天,我一大早就起来化妆,穿的很漂亮,想着就算是很崩溃的结果,我也得撑起来。
——结果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
这个病只有百分之几的患病率,但它落在我和孩子的头上,那就是百分之百。
辗转
因为孩子的病情,再加上有些产后抑郁,我的抑郁症又复发了,严重的时候我甚至想过抱着女儿从楼上跳下去。但我知道再绝望也不能这样。因为对于抑郁症情况下的我来说,我可以不在乎我的命;但眼前这个孩子,她是无辜的,我没有权利决定她的生命。
女儿发育得不好,气管很窄很小,平躺着容易窒息。于是我就整整抱了她 8 个月,每天都是抱着的。
我查找着这种病的相关资料和治疗机构,但国内的机构都要求一岁以上才能开始康复或者干预。根据我搜到的资料,这个病越早进行治疗越好,对孩子的恢复和开发越好。
所以我就先根据国外的网站视频,开始给她做康复,每天做操、按摩;后来经过考虑,告诉了她的父亲,幸而他很爱孩子,不觉得孩子是唐氏综合征有什么不好,也希望试着带孩子去美国生活,于是我们就结婚了,在孩子 9 个月大的时候,我带着她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Nikita 和那个美国男生短暂地一起生活过,但是因为各种不合适,再加上 Nikita 抑郁症复发,两个人还是分手了。
更糟糕的是,很多唐氏综合症的孩子都有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Nikita 的孩子也不例外,也有先心的问题。而且孩子在美国做了一次手术,不太成功。
国外做手术可能没有国内的医生那么有经验,后来我了解到北京的阜外医院在先心这方面比较领先,所以在女儿需要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带她回了北京。
两个月里我天天带着孩子跑医院,咨询哪个医生最合适,怎么才能挂上号。后来是在一位专家去急诊室的路上拦下了他,请人家边走路边看病历,给他描述情况,才挂上了号,安排了手术。
在医院照看女儿时,等她晚上睡着了,我就会在走廊里用弹力带健身,保持运动量,或者画画、写东西和看书;每天早上我会化妆,换衣服,因为在医院,大部分人都穿睡衣,但我每天都会换上日常的衣服,因为我想让孩子感受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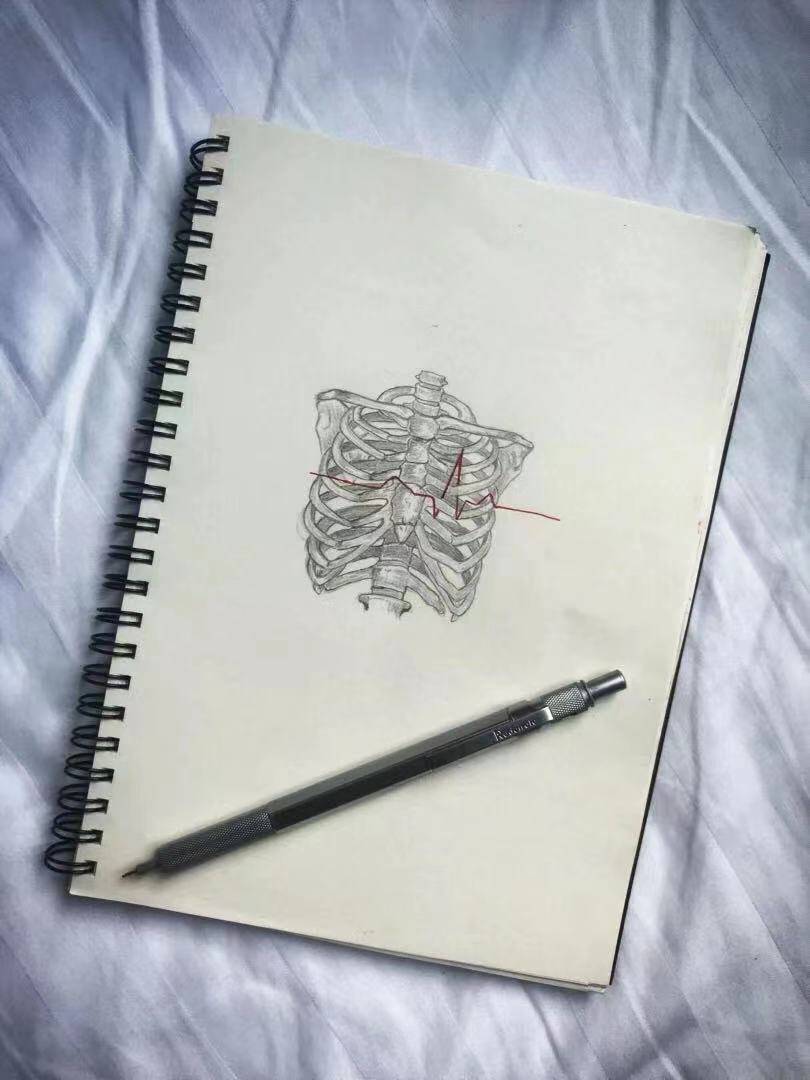
有些人会觉得我这样很没必要,大家都住在这个医院里,你化妆给谁看?——有时候女人对女人的伤害之大可能是男人想象不到的。但也有一些妈妈会觉得我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坚持去做这些事情,是一种精神和鼓励,她们就会在我运动的时候过来跟我聊天。
做手术的前一天,我被医生找去谈话,说了各种手术风险。那时候我身边根本没人商量,也不想跟父母说,他们更承受不了;只好给战友打电话哭,最后是他们鼓励我,签吧,没问题,你要相信我们的医生。我才签了字。
手术的那天,孩子进了手术室,医生说大概要进行 5 个小时。
这时候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在外面等着,但我没有。我回到短租的房子,洗完澡换了身衣服,去逛商场、看电影,用这种事情打发时间。因为我无法想象我坐在门口等 5 个小时的那种煎熬。
其他家长还觉得我心理素质好,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心理素质才好,竟然可以在这里硬生生等着,忍受煎熬。
很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功,回到美国之后,美国的医生都赞不绝口。所以孩子现在长得很健康,壮实活泼,在唐氏孩子里还属于聪明的,个子高的。
她现在没有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但我知道将来有一天她可能会察觉出来的,但我依旧希望她能够健康快乐、自信地生活。
成为一个“人”
分手之后孩子爸爸拿到了抚养权,因为他觉得 Nikita 抑郁症的情况不适合带孩子。Nikita 也觉得,虽然他们两个人不合适,但她认同孩子爸爸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是一个爱女儿的爸爸。所以她同意了这个安排。而且因为现在疫情期间的一些特殊安排,Nikita 大部分时间都能陪女儿一起度过。
Nikita 很高兴,今年开始,女儿已经会逐渐表达了,就比较容易带了。她开始有了精力想做一些创业的事情。对未来,Nikita 还是充满了干劲儿。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能感受到父母、同性的偏见,他们会觉得作为女性,我是不成功的。比如我父母已经对我失望透顶了,觉得我没有走那条他们认为该走的路,这是非常离经叛道的,很不正确的。
但我常常在想,我一点也不害怕老去,我甚至期待 60 岁的来临。因为我觉得当人变成老人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老男人”、“老女人”了,性资源、生育资源这些都消失之后,我们才会变成一个单纯的“人”;那个“女”字的前缀去掉之后,好像才会有一种绝对的自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Nikita,主播:@寇爱哲,文字整理: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