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采访:小曾、姮慧、沐雪、芙蓉,撰文:Sharon、青豆、Lydia,编辑:孟常,排版:小七,设计:Sam,头图来自:《我,到点下班》剧照截图
我们对远离北上广的工作状态,和一线之外的生活有着一些“乌托邦”式想象:家里买车和买房、挖小蒜、摘槐花,上班骑着小电驴,下班不愁要加班。“通勤时间短,业余生活就能多一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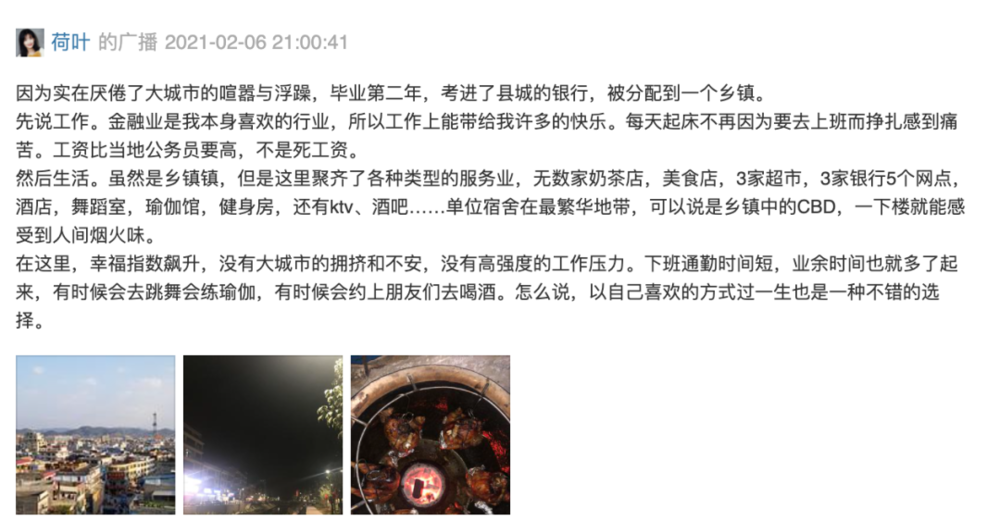
996只是一线和互联网大厂的“特权”吗?离开一线,是“逃离”还是“选择”,它是一种奢侈吗?“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之外,真实的非一线工作是怎样的? 没有了车房的顾虑,会呈现一种怎样的生命状态?对于工作的焦虑,会有不同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和在重庆、成都、南宁、兰州的朋友们聊了聊他们的工作选择和对工作意义的探索。
红苕是成都一家电子公司的产品专员,早早就实现了“25岁前找到一份月薪六千以上”好工作的目标,但仍然想探索不按部就班、一眼望得到头的工作。
小黄在重庆一家研究所工作,他和所有北上广996的人们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加班文化”,只是情况有些不近相似。
楠楠是一位月薪过万的资深银行人,即使在广西首府南宁,也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实际上,她却形容自己做着一份“服务员”一样的工作,只是“底层人民”。
小梁是一位准备申请博士的准爸爸,日常“8117”的学术科研工作比“996”更加没日没夜,压力和难度不容小觑。但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内心与精神得到充实满足,让小梁足以应对压力与质疑。
阿兰和竑桥是目前生活在成都的自由职业者,阿兰是自由插画师,竑桥是诗人。他们都承认自己不是“社会的主流”,但也算得上是在过着“理想生活”了。
一
“我也不喜欢按部就班,一眼望得到头的工作。”
红苕 成都
在我们的想象中,非一线城市的工作状况对比高速紧张的一线城市来说,总是安逸、悠闲的,在成都一家电子公司从事产品专员的红苕似乎很符合这一想象。
每天一到五点半的下班时间,红苕会和同事一起准时冲向楼下。离开了公司,她便自动切断了与工作的所有联系,“同事如果来找我问事,我就回复他们明天再说”。玩手机,打游戏,看视频,做饭,撸猫…有大把的时间可供她自由支配,这些简单的事物构成了红苕下班后闲散的日常。

之前,红苕结束深圳的实习回到了家乡成都,虽然仅在深圳短暂的居住了一段时间,但这座繁华的城市却在她心中生成了强烈的隔离感:推开出租屋的窗户,眼前映入的高楼大厦更像是一堵围墙,而自己生活的地方却像个“菜市场”一样脏乱,甚至连阳光都鲜少照射进来。压抑感在她心中日渐膨胀,最终她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回到了家乡,也回到了一种“看似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对于红苕来说,回到家乡就意味着有父母帮忙提供车和首付,自己只需要平平淡淡的生活就够了。此前她还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希望在25岁前找到一份月薪六千以上的好工作。然而,这个目标却轻轻松松就实现了,甚至在去面试“好工作”之前,她也没有特意多做准备,而是在思考今天中午吃什么的问题。谁想面试过程非常顺利,让她提前进入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如今的工作对于红苕来说是轻松且安逸的,任务并不复杂,只需按时交付。但她也会有不安于现状的时候,“我想做一份更偏技术的工作。现在的工作感觉谁上手培训一下都可以来做。我也不喜欢按部就班一眼望得到头的工作,但是没动的原因是我太懒了!”就如“温水煮青蛙”一般,红苕对于安稳的未来也存在隐隐担忧,但似乎,还远没到需要“奋力一跳”的地步。
二
“我们有固定的加班时长要求,每人每月要累计达50小时左右。”
小黄 重庆
然而,在非一线城市工作,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如此安逸悠闲。在重庆某研究所工作的小黄也和所有在北上广996的年轻人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加班文化”,只是情况有些不近相似。
所里的部分部门,对于加班时长有着固定的要求,每人每月加班总时长需累计达50小时左右,检验的方式就是通过打卡的形式来计算。在小黄看来,大家的工作量并没有那么“庞大”,需要靠大量额外的时间去满足,很多人的加班仅是呆在公司无所事事而已。
如果遇到项目,小黄形容自己会“忙得像狗一样”。有时候他需要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还是按照平常的时间去公司上班,甚至又要连着熬通宵。

但对于小黄来说,无论是固定的加班时长,还是因项目导致的必要性加班,他都并不排斥甚至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人在社会上都是要不断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加一点班都没什么,只是不要让加班太影响到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活”,加班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社会经验的习得,也与自己换取的回报成正比。
三
“干银行这么久,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底层人民。”
楠楠 南宁
在南宁某大银行工作的楠楠,已经入行5年了。但对于他来说,这份外资银行的工作也算不上“体面”,认为自己依然是“底层人民”。
关于“底层”的判断,他认为简单来说就是:劳动力投入大、社会地位不高。“我假如在一群随机的人群当中介绍自己在银行工作,别人的反应都很平淡,不会一听就感到特别牛逼。”
像逢年过节搞活动、拉新促活这些销售常见动作,在楠楠的职责范围内竟是常见的。所以银行除了卖理财产品,也会去批发一些小商品用来做活动,作为福利派送吸引客户成为会员或让老会员感受到 VIP 的好处。由于这项工作在银行内部并未构成明确的体系,每个支行的经理需要自己去找供应商、谈价钱,申请费用将产品买回来,设计活动流程,再以一个优惠的价格组合卖给客户。
楠楠类比这样的工作状态为“服务员”,“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未得到任何的利润收益,只是做了一个活动的设计与执行而已。活动的设计者是我,卖米、卖油的销售也是我,这好像和服务员、收银员没什么区别。”

“像个服务员一样”的感受也体现在最平常的上下班时刻。平日里,银行对职员的着装要求正装上下班。即使在下班后,楠楠也需要准备着去应对随时会产生的正式会面。为了避免换装麻烦,以及可以快速展开行动、进入状态,他经常会在下班后穿着工服去超市逛街、餐厅吃饭,但总会被当成是店员或服务员,招呼着:“服务员,你过来一下。”虽然只是他人的无意之举,但出现频次太高,令楠楠很难不去介意。
“从事第三产业的,哪一个不是服务员。”楠楠一边自嘲,一边描述着他听到的心目中的理想工作范本:“我妈一个朋友的女儿在一个强势的事业单位当干部,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班喝咖啡,也不需要伺候谁,上下班还有专车接送。”
四
“即使读了博士,我的工作可能比996还要没日没夜,职业选择可能会更少。”
小梁 兰州
在兰州读文学硕士的小梁还未进入工作体系之中,下一步是准备申请博士。这一步帮助小梁略去了身份地位的顾虑。在兰州,读博即代表着社会地位的上升。无论他是否会因为仍然是“在读”状态在经济方面有些许窘迫,但“博士”的身份意味着能得到更多尊重。“在这边,不管是哪个学校的博士,只要能读到博士,人家会很尊重你。社会地位上去了,我对自己也会更加有信心。”
在知识沉淀和学历的铺垫下,小梁认为自己职业选择的平台起步就会比较高,在某些职业当中晋升得也会更快。读博至少能保证旱涝保收、收入稳定。比起做生意,当它的实用性被身边人反复质疑的时候,这也成为了他回应的底气。

但读博这条路并不会让他面对更少的工作焦虑,首先,得过了学术这道门槛。比起一线大厂“996”的工作常态,小梁日常“8117”的学术科研工作更加没日没夜,压力和难度不容小觑。如果说在大厂打工会有明确的 KPI 和目标指导工作的方向和完成时间,那么做学问就仿佛在挖一个未知的矿,并不知道这个在挖的矿是不是对的,还需要冒着快到底才知错的风险。
在不以结果导向或效率导向做一件事的情景下,知识焦虑就像滚雪球,只能踏下心来做。但有些时候,小梁仍然会怀疑自己做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他的书架前,陈列着三四百本书籍,其中有一半是还没看完的。由于文科是一个发散性的学科,小梁常常焦灼于书要先看哪一部分,文本要用到哪个学科的知识,这个词或文本对学术研究到底有没有用。
即使读了博士,小梁坦言,在兰州他的职业选择可能会变得更少。“文学类的硕士一般有三个走向,公务员、教师或者编辑。要么是在高校谋求发展,要么是去政府机构。但是读博之后,可能我对自己的心里预期也有所提升,所以不太会考虑做中小学教师、文员这样的工作。”
但除却这一实际因素的影响,读博带给小梁更重要的意义是在内心充实和精神富足层面发生的变化。小梁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将学术经历当成了一场修行。“陈晓明说过‘文学是弱者的伟业’。我相信只要用了功夫,自我内部会产生一种质变。当然,这个变化可能不会特别明显地体现出来,但实际上是一种充实的工作、生活状态。”
五
“我对于灵光一现的渴望和需求,大于了按部就班的生活。”
阿兰&竑桥 成都
阿兰和竑桥是目前生活在成都的自由职业者。阿兰是自由插画师,竑桥是诗人。
可能在外人眼里看来,插画师和诗人都不是所谓的“正经”职业,不稳定的收入更是一种风险。但在阿兰和竑桥看来,自己对所从事的工作有热情,活得也还算自在。
阿兰的生活节奏可以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形容,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接画稿,反正稿子就在那里,懒的话就少画一点,需要钱就每天多画几张,自然也挣得更多。有时候阿兰也去夜市摆摊给游客画画,国庆在成都画一周的收入能负担她一个月的开销。集中一段时间赚够钱之后,就可以随性画,完全不接稿子,潜心思考自己的创作。阿兰觉得,这就算得上是“理想生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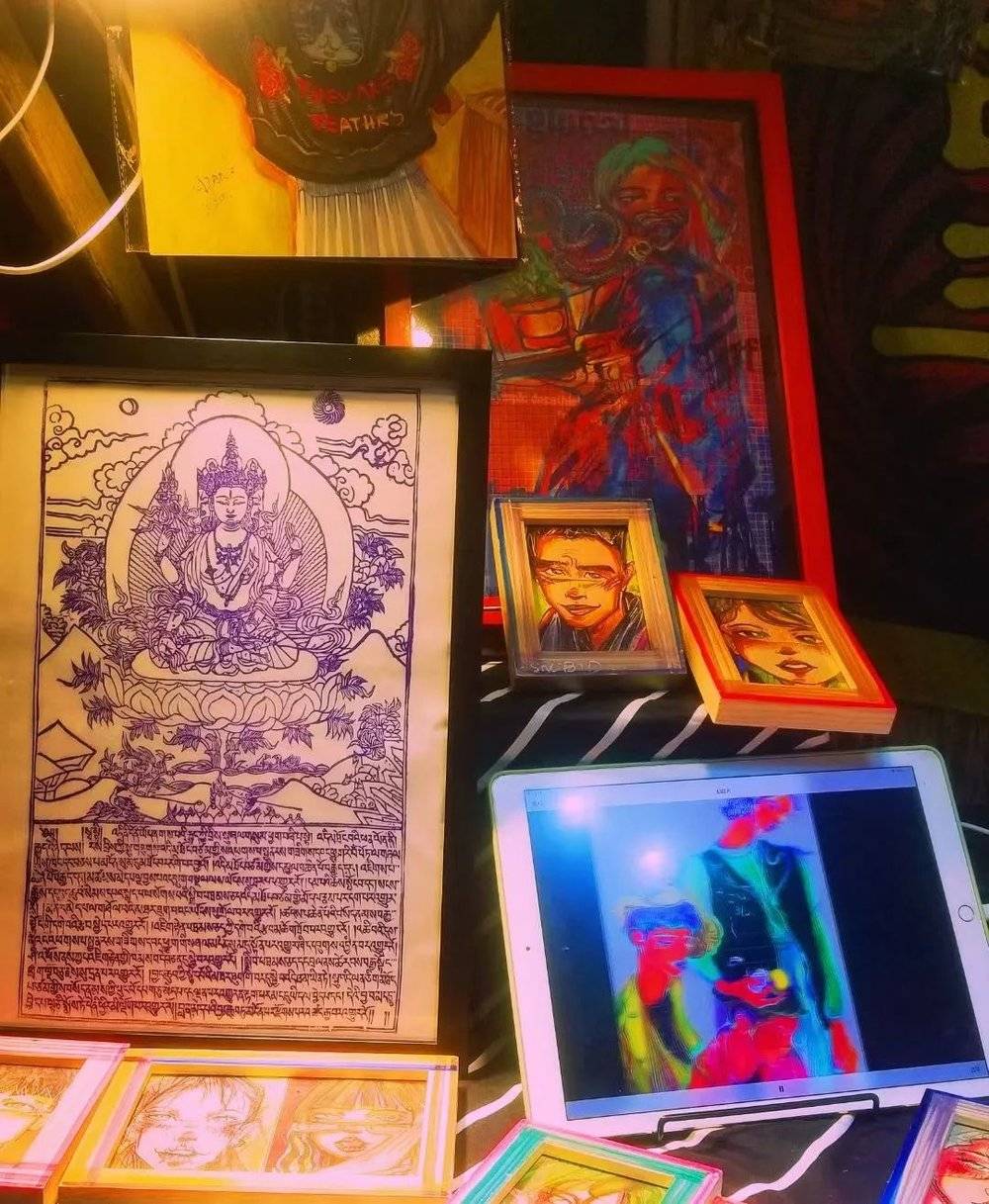
竑桥毕业于名校中文系,曾经出版过书,平时一直写诗,获了不少文学奖项,在圈子里小有名气。他目前的收入主要是稿费和奖金,虽然非常不稳定,但好的时候也相对可观,据他所说,去年光是奖金就拿了小十万块。
他们都承认自己不是“社会的主流”,没那么恐惧“不稳定”所带来“意外”,甚至甘之如饴。而对于主流的大多数人来说,或许也都曾在循规蹈矩的工作之中,片刻羡慕过阿兰和竑桥这样自由的、创造的工作。
这样“非主流”的生活,竑桥也不是没有过自我怀疑。看着本科同学纷纷进入北上广知名的互联网公司,起薪就四十多万,竑桥也说,自己根本没法和他们比,“商品和经济的逻辑已经如此深入人心,社会好像不允许你保留一些不一样的活法,这些声音太大了,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怀疑,可能错的是我”。可就算进了大厂,拿了相对高的年薪又如何?竑桥觉得生活的本质并不会因此改变,多了那么一点钱也不会变成富豪。可是诗,一旦领略过它的妙处,就再也无法忘记。
在竑桥看来,按部就班的人或许都曾有过想逃离的片刻,“只是对于按部就班的渴望和需求,大于了这种灵光一现的生活”。

阿兰说起自己的弟弟就是这样,曾经一直很想做摄影师,但了解到国内环境不好,做这行活不下去,就选择了按部就班的生活,以前阿兰会傲慢地认为,“为什么不去追寻理想,只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不可能活不下去的”,但现在,她觉得这样的选择也很了不起,“他能为了眼前的生活,或者他有更多要照顾的东西,把自己心中的远方放下,就着眼于当下的现实,这个选择对于他来说也是很伟大的”。
在这样一条“追寻艺术”的道路上,阿兰和竑桥也经历过心态上的转变。
阿兰说小时候会觉得“我不一样,我可以做一些事情”,但现在发现人想要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是毕加索,你也没法确定自己是不是毕加索。如果终其一生追求这个,可能会很痛苦,因为不一定有那样的结果。所以她不再想这些,而只想做一个快乐的人,“让周围的人因为你的存在感到开心,这就足够了”。就比如给别人画头像,收到了正面的反馈,对方很喜欢,阿兰觉得这样就很满足。
竑桥也有着相同的感受,他打了一个比方:“人类文明像荒野中一座透明、脆弱、美丽的玻璃房子,你能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加很小一块砖在上面。后来你发现,可能这也是虚妄的,你也做不了。”这时候,竑桥就选择退回到局部学科的意义,追求一个自己的小世界,给周围的人带来意义,仍然能试着做一些事情,把诗歌当作一个建筑去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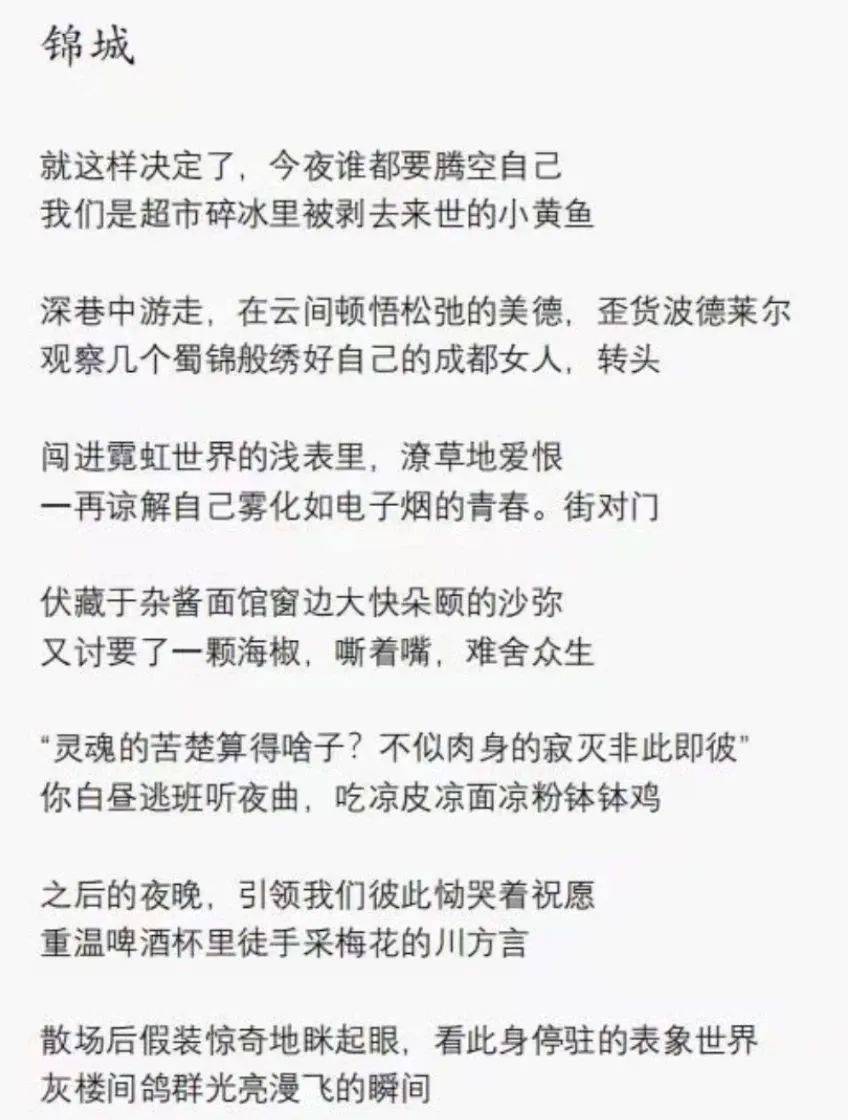
最后
采访提纲的最后一行,躺着这么一个问题:你认为体面的、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在他们的描述中,有的伙伴认为一份“更好的”工作,是隐约带着权利与特权向往的,比如无需担心利润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有专车接送;但我们也看到了那些顺从内心的工作选择,不指望稳定、一眼望得到底的工作。
非一线的工作状态并不完全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安逸、按部就班,也需要面对内外部评价标准失衡的结果:对内,会因为成为了系统中的某个环节而感到无意义;对外,则会顾虑社会对一份职业的评价而寻找尊重感、敬畏感。
我们感知到了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不易,有很多不想做、不喜欢、不擅长,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这样的无可奈何,不论在哪,都是再一次被印证的。
理论和现实的碰撞总是充满了错位,我们需要反复观察现实、深入对话,才可能填补空缺。一线内,一线外,我们也许是殊途同归的。归到最后,也许是李诞写在《候场》里的那句:“老子已经打卡了,还要我怎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采访:小曾、姮慧、沐雪、芙蓉,撰文:Sharon、青豆、Ly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