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詹姆斯·道斯,翻译:梁永安 ,原文标题:《我们伤害别人的能力如此巨大,恰恰是因为有能力把别人想象得非常小》,头图来自:《熔炉》
《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一书,讲述了好些凶残故事,浓度高——这也是读书朋友反馈的不敢看或看了不适的原因所在。
作者詹姆斯·道斯的书写方式颇有争议:割裂拆散访谈,时而紧扣历史背景,时而抽离,不断变换叙事语气和学科角度。对此,詹姆斯·道斯说:“我想尽自己所能让读者感到不安全,感到痛。”
一位书友留言:“虽然内容非常沉重,结构也比较散,但我真的喜欢这本书所探讨的颇有深意的人性之恶。去年十二月还在朋友圈写了一千多字推荐了这本书。”
今天推荐的文章,涉及同理心同情心这一话题。
“也许,对着这些虚构之事好好哭过一场以后,我们在感情上就会消耗殆尽,会努力避免在真实世界再付出同情。
齐泽克指出,我们只需要慵懒和蠢蠢地盯着电视屏幕看,便足以尽好‘我们的慈悲’和‘达成我们的哀恸责任’。
即便悲剧所唤起的恻隐之情真的可以影响我们,让我们决定在现实世界采取行动,但我们会采取的行动通常寥寥无几。”
同理心会像钱一样,花完就没有了吗?
1. 为什么同理心是文学研究热爱探问的主题?
如果我们把过程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并把视角稍稍转移,就会发现,阅读他人所遭受的痛苦这种休闲行为更像是出于幸灾乐祸而非同情心。读者在拿起一本小说以前便已经知道里头充满痛苦、心碎和放逐,但仍然甘之如饴。

小说家的情况也相当类似。她创造出一些角色,用层层描写让他们栩栩如生,她与这些角色长时间为伴,为他们注入深沉的人格,往往只是要用别出心裁的方法折磨他们,甚至是把他们杀死。即使作者没有加诸角色一些无缘无故的苦难,书写行为也必然是狠心的。例如,小说中一定会有主要角色与次要角色之分,而次要角色之设只是为了陪衬。一些人事关紧要,而其他人则无足轻重。
我们阅读关于痛苦的小说部分是为了满足我们对看见别人痛苦的“需要”,不论是作为向下进行社会比较的一种温和版本,还是不顾后果地进行解构的一种极端版本。这种思辨会让人想起一个有关喜剧的历史之悠久主张:笑是我们优越感的一种表现,它是对我们在那一瞬间解放出来的残忍的体验和否决。不用担心,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乐在其中。如果我们不难看出笑可以是无情的,那么哭不也是如此?会不会,哭也是一种用于拉大距离的防卫机制,可有助于加强主体的孤立和优越性?

但这一类犬儒立场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我们似乎会从中得到一种深深的满足感——一种苦中之乐,它来自从痛苦之中所体会到的团结,来自分享他人的悲痛并感到他人存在之重。有时我会觉得那是一种人类的基本需求:对被连结(connectedness)的需要,对超越贫乏人类互动(大多数人类互动皆贫乏)的需要。要我们去诋毁这种感情极其困难。
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同理心和同情心长久以来都是文学研究热烈探问的主题的原因:它们对我们生活在群体中的能力和想要活得有尊严来说是根本的,对我们追求改变世界和这种努力为自己的人生所赋予的意义来说是根本的。它们对于想要被人听见声音的学者们来说之所以是一个诱人的讨论对象,正因为它们位居我们存有的核心,以至于它们每受到一次解构,我们都会心惊肉颤。
2. “虚构的痛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不过,在某一个层次,我刚才所梳理的关于同理心的阅读行为的解释是否可信并不重要。在一个深刻意义下,人类的动机不仅是不可知的,而且极有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故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有带来改变吗?它们可促进帮助别人的行为吗?大多数从事人权工作的人都认为它们做到了这些,才会不倦于一遍又一遍地讲故事。
但也许它们什么都无法改变。伊莱恩·斯卡里警告我们,依赖于“慷慨的想象力”来促进社会改变是危险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或《印度之旅》都是稀有的例子,同时大概也是关于世界主义想象力所具有的力量的误导性案例。
她写道:“人类伤害别人的能力之所以非常巨大,恰恰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把别人想象得非常小。”而且不管怎么样,同理心大概更像一笔钱那样,花完了就没有,而不像肌肉那样能通过训练变得更强壮。我们把同理心耗费在战争照片上,耗费在虚构的人物身上,结果对现实生活中可以切实接触到的人毫无怜悯。
伊莱恩·斯卡里在别处又警告说:“总有这么一种危险,那就是虚构的角色所遭受的痛苦(不管身体还是心灵的痛苦)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活生生的姐妹或叔伯身上引开,而他们才是我们的同理心可帮助的对象。另一个危险是,因为艺术家极其擅长表达痛苦,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把他们这个集体当成真正的受苦者,从而无心地忽略了给予其他亟须帮助的人足够的关怀。”

也许,对着这些虚构之事好好哭过一场以后,我们在感情上就会消耗殆尽,会努力避免在真实世界再付出同情。也许,这样流过泪之后,我们会觉得已经奉献出了足够多的自我。也许,借由这种虚构的痛苦,我们会觉得自己充分印证了自我概念,验证了我们自身的善,并因此觉得无须再做些什么来达成人格的均衡。当我们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关心之后,还需要什么来践行有意义的行为吗?卢梭在1758年道出这些忧虑:
当我们把眼泪献给虚构作品时,我们就满足了人道的要求,用不着付出更多。但是现实生活中受苦的人却要求我们给予关注,要求我们的关心、支持、宽慰和善行,如果满足这些要求,就会令我们卷入他们的痛苦之中,或者要求我们至少牺牲掉自己的懒散与倦怠,而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豁免的。可以这样说,因为害怕受到触动时自己会付出代价,我们紧闭自己的心门。
说到底,既然一个人已为假想的善行唱过赞歌和为想象的不幸流过泪,你还能要求他什么呢?他对自己不是满意了吗?难道他没有理由为自己的心灵之美鼓掌吗?当他对美德给予充分尊重时,难道他不就完全清偿了他的亏欠吗?你还想要求他些什么?要求他亲自实践吗?但须知戏中并没有他的角色,须知他根本不是演员。
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指出,感伤政治(sentimental politics)乃是用“感情上的变化”取代“实质的社会改变”。这个论证在检视美国的种族主义时变得尤为尖锐。例如,约迪·梅尔米特(Jodi Melamed)指出,美国大学的多元文化教育让白人大学生“因为自己的反种族主义情绪”而认为自己是反种族主义者,哪怕他们实际上参与并受益于“贫与富的新种族隔离”。

菲利普·费雪(Philip Fisher)在讨论《汤姆叔叔的小屋》时也指出,这部引发人们同理心的小说所激起的“是眼泪而非革命”,他断言,这种富有同理心的阅读体验为人们提供的是“为疾苦而难过的心情,而非对抗疾苦的行动”。
而当我们情绪上被这些故事攫住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甚至可能不是痛苦的感觉。它甚至不是感觉,不是一种从我们内在、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感觉”。它可能要更浮于表面,更外在。在《理性的要求》(Claim of Reason)一书中,卡维尔把想象(imagination)区别于“富于想象”(imaginativeness)。
想象可以创造联结,看见联系;而“富于想象”则只是创造鲜明的意象。他指出,狄更斯两种能力皆擅长,但狄更斯同时深知,即便他有能力“让全世界的伪君子为他所描写的贫穷景象与夭折的孩子们落泪”,仍然无法让他们看出自己与这些苦难的关联。
齐泽克(Slavoj Žižek)把这个论证推至极端,论证了一种类似于自我的外在化(exteriorization of the self)的观点:
这一点对我们理解“精神分析不是心理学”这个拉康派(Lacanian)基本命题攸关紧要:最切身的信念,甚至最切身的情感(如慈悲、哀哭、忧愁、欢笑等)都不可能不在转移或托付予他人之后仍不丧失它们的真诚性。在其讨论课“精神分析的伦理”中,拉康谈到了合唱队(Chorus)在古典悲剧中的作用。
身为观众,我们带着各种日常生活的烦恼忧虑走进剧院,所以无法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戏剧要求于我们的感情,即恐惧和慈悲—但不打紧,因为合唱队可以代替我们感受忧伤与慈悲,或更精确地说,我们可以透过合唱队的中介感受到我们被要求感受的各种情绪:“所以,即便你什么都感受不到,一样不用担心,合唱队自会代劳。”
以罐头笑声当作“外在化感觉”的典型例子,齐泽克指出,我们只需要慵懒和蠢蠢地盯着电视屏幕看,便足以尽好“我们的慈悲”和“达成我们的哀恸责任”。
3. 悲剧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
说到底,那些可怕故事到底让我们有过什么实际作为呢?且再次听听卢梭是怎么说的:
据说悲剧是透过恐惧引起怜悯。假若这是真的,那怜悯又是什么呢?是一种瞬息即逝和空洞的感情波动,存续时间不超过引起它的那种幻觉;它是刚被激情压倒的自然感情的一点残余;它是无用的,只满足于流几滴眼泪的怜悯,从不曾产生过一个半个帮助别人的行为。
由此,嗜血的苏拉(Sulla)到别人干过什么残忍暴行时也会流泪。由此,暴君亚历山大看戏时会尽量躲起来,生怕被人看到他跟着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和普利阿摩斯(Priam)起哀哭,但对每日被他处死的许多不幸被害者的哭泣无动于衷。
即便悲剧所唤起的恻隐之情真的可以影响我们,让我们决定在现实世界采取行动,但我们会采取的行动通常寥寥无几。伍尔夫写道:“在联署书上签个名很容易,参加那些用华丽修辞向人们反复宣扬他们早已接受的和平观点的集会,这也不难。开张支票支持那些你模糊接受的主张虽不那么容易,仍不失为安抚你内在那个被权称为良知的东西的简单方法。”

有人会主张卢梭和伍尔夫是错的,或者说,他们是用对了量尺却量错了对象。由于孤立的行动会在时间里冻结,所以上述的行动(在剧院里流泪、为请愿联署、参加集会、开支票)无一可以改变些什么。但这些行动其实并不孤立,也没有在时间里冻结,因为大量类似的行动加在一起便可以改变些什么。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一段时间弧上的一个点,假以时日,说不定会开出一条道德进化和承诺升级的道路。
对此,卢梭和伍尔夫也许会这样回答:也许是你说的那样,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怜悯激发的行动在个别来看无足轻重,而是作为在时间中重复上演的相似行动的一部分,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们都是叙事的产物,而这种激发人怜悯之情的受害者叙事——特别是那些试图引发人强烈情感的叙事,以及用这种叙事来描述种族化的他者时——引发的忧虑着实非常多。
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也许会固化这种观念:即把受害者当成一个单独的“人”的类别。受害者可能会感到被迫要让他们的故事乃至自我认知去贴合整体的叙事期望。“受害者作为一种身份”会损害那些需要追求自主性甚至权利的人的努力。

而这种无处不在的印象会让我们难以把受害者当作人而非一种模式,而聚焦在极端的身体暴力也会让我们忽视那些不那么戏剧化的结构性暴力(通过系统性的否决基本需求而造成的伤害),从而削弱我们去为社会正义与经济正义构想一个更全方位的行动纲领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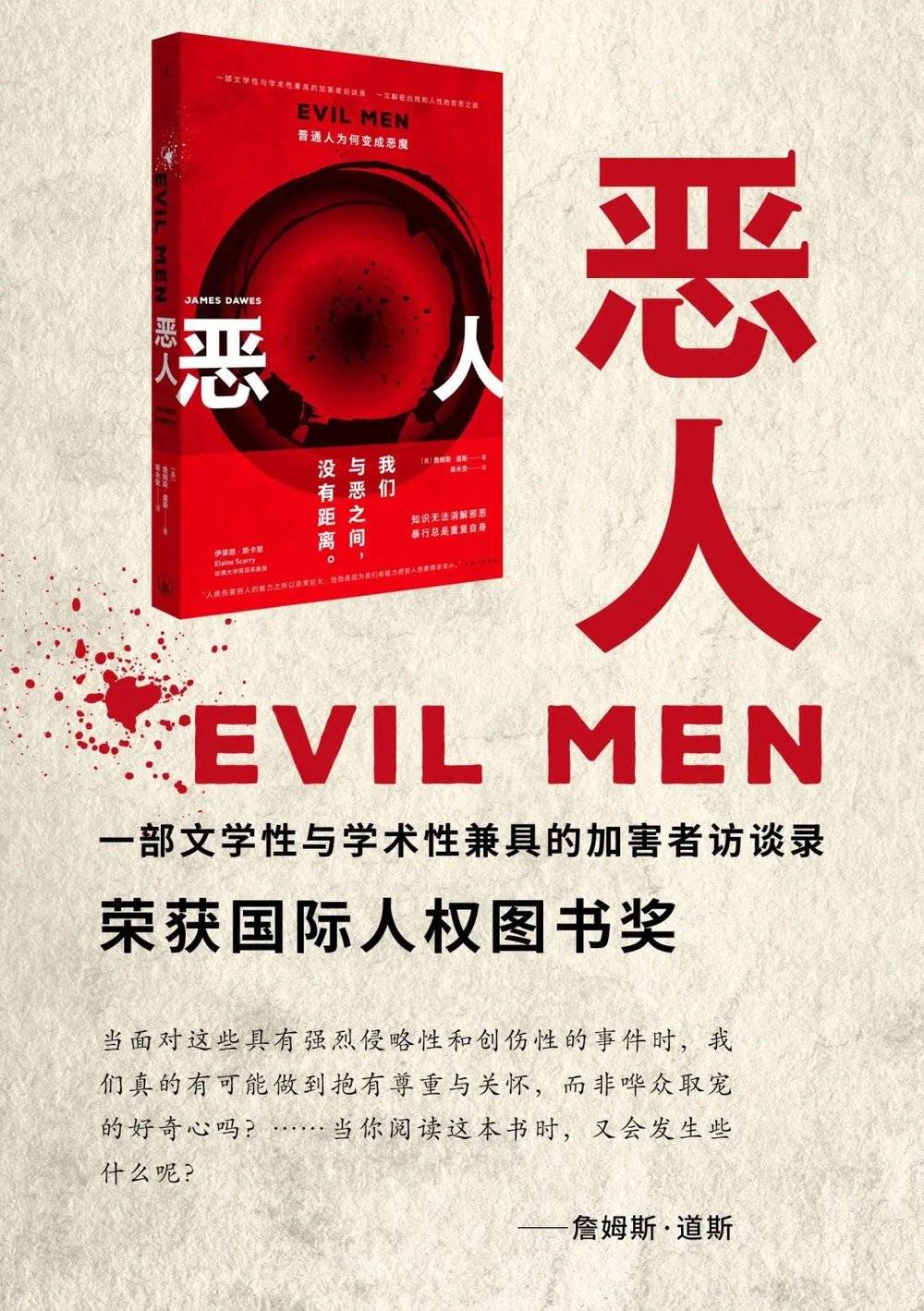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詹姆斯·道斯,翻译:梁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