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周末,瞎聊聊。
作为一名安利主义者(Anli-ism)我有种“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心理,即凡是看见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就非常想分享给身边人的习惯。
分享的物体包括但不限于:影视作品、书籍、餐馆以及衣服。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推荐的难度正在逐渐降低。
在过去,假如要向亲朋推荐一部电影或者书,你得完整地讲一条故事线,突出它的背景、桥段甚至是自己刹那间真挚的感受;推荐件衣服,还得讲讲背后的历史故事;要是推荐一部游戏,你还得着重描述一下操作的感受和快感。
如果你的描述足够打动他,朋友或许还会饶有兴趣地追问,你还得进一步阐述其中奥妙;总之,早年先的安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极力展现作品的复杂与深度,才能完成推荐闭环。
然后,一切都变了,变简单了。

现在,推荐文艺作品,你不需要讲述任何故事,只需要将某部作品的评分告诉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推荐;安利衣服,也不需要包装它的故事,只需要告诉他们:“它很火,你穿上就是最IN的人”就能让人们轻松买单。
至少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又不止一位朋友拒绝《爆裂无声》的理由是:
“xx上评分低于8.5分的电影我不看,那都是垃圾。”
描述这种体验并非是要旧调重弹,行活儿式的去批判评分体系:一者批判本身就显油腻,二者问题不在于这个评分体系,评分自有其参考价值,但人们把一根思想拐棍,上升至区分好坏的唯一神圣标准,才显怪诞。

评分系统出现伊始,是人们试图通过这套模式,直观地感受一部作品科学、公正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基地,碰撞出更有价值的思考。
但时至今日,暂且不论一些售票平台,所有电影都高达可怕的评分是否可信;在经历了《流浪地球》《最后的生还者》《辛德勒的名单》《热辣滚烫》等等一系列差评大战之后,你会发现评分系统存在的意义正在褪色,沦为党同伐异的另一个战场。
一出接一出的闹剧,总会让温存的人呐喊“就让电影的归电影,凯撒的归凯撒罢”,但这不过是梦中的一厢情愿,毕竟两者分开的缘由,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除非凯撒自愿出走。
或许在这时评分平台的创始人们才会惊讶地感受到,自己理想中思辨和对话空间,正在成为身份政治的舞台,这里没有妥协,只有共鸣和抱团。
你瞧,尽管评测仅供参考,结论也值得推敲,但“评分引导人民”仍然成了时代显学,以至于一旦自己的体验跟“权威评论”相差甚远,人们就会不自觉地产生耻感,进而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出了问题。
马丁·斯科塞斯在五年前就抱怨过自己对评分系统的不满,但被评分系统影响的又岂止是电影,在生活里我们见识过太多被评测劝退的故事了:
拿最近上的一个游戏《浪人崛起》来说吧,我一位朋友对幕末历史巨感兴趣,从早年先汤姆克鲁斯演的《最后的武士》到《西乡殿》他都快背下来了,但就因为游戏发售后他听评测说不咋地,逐放弃,直到在我游戏机上体验了一下,才决定重新尝试。
这次遭遇便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当干什么都先看评价成为人类新天性——人们为什么评价仅凭数量就能取代你感知到的事实和真相?是什么让人们不再看重自己体验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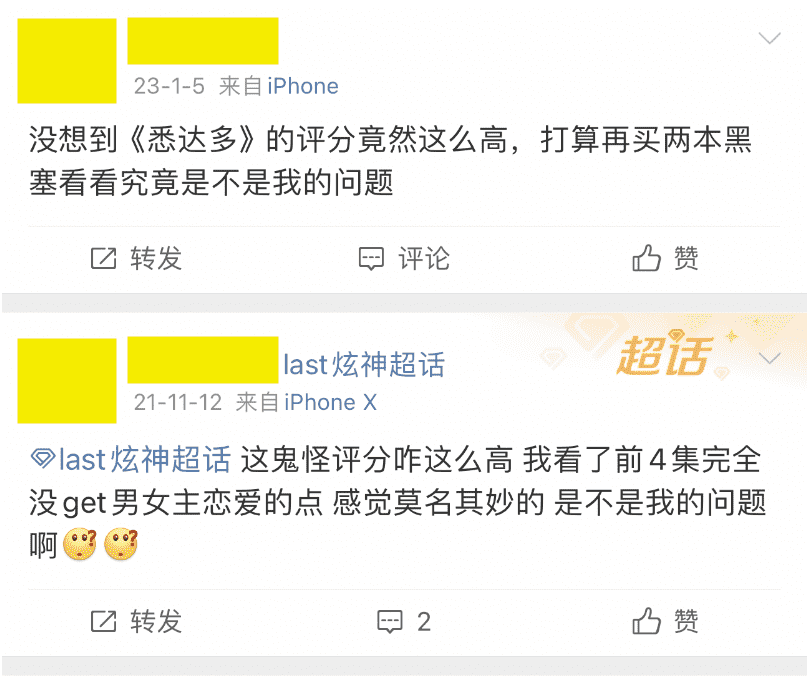
这样的感受在生活中和网络上比比皆是
总有人说之所以人们需要这些简化的辅助,是因为大脑总爱偷懒,所以直观的好坏二元评测和打分,会在这个信息流爆炸的时刻,成为决定人们对作品好恶的第一印象。
但在懒的背后,更深层的缘由是人们害怕出错。错的概念可能是怕浪费钱,也有可能是怕浪费时间,但它映射出的是人类更大价值观的变迁。
按照加拿大作家F·S迈克尔斯在《难逃单调》里的说法来解释,人们接受了单一文化,即绩效主义、经济故事的框架,放弃了对多样性的认可,这种状况沁入了各个角落:
...
当创意艺术的故事以经济效益为准绳之后,任何给予艺术创作时间、不顾市场需求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天真。
当人际关系成为绩效与成就必须超越他人的故事后,人和人之间的人性将遭到否定,而我们也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因为我们的价值与归属完全取决于绩效。
...
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下,理解当下人们不再重视文化作品之旅的理由,便显而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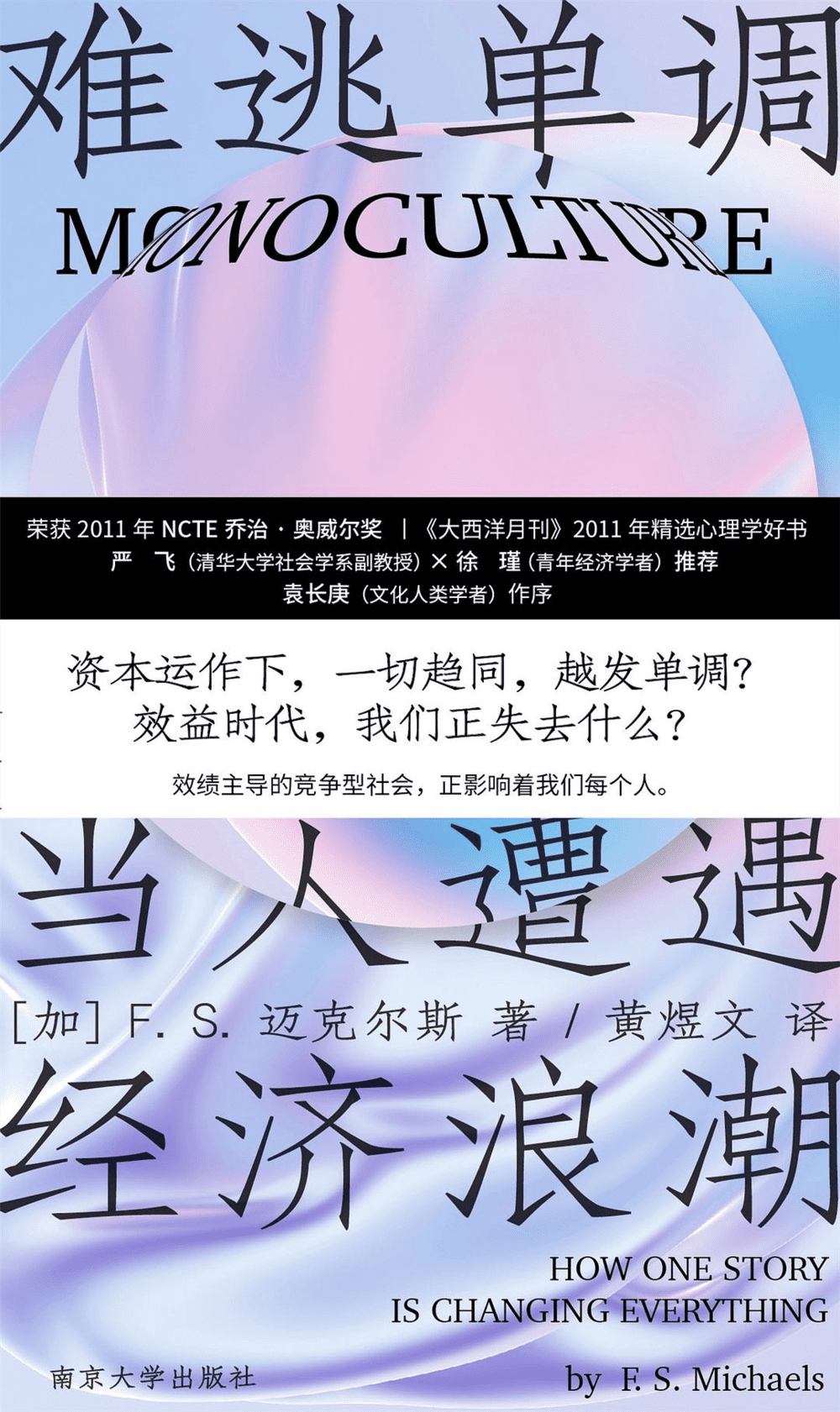
为什么要谈评分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文艺作品评分对人选择的影响,本身就是当下量化一切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符号。
如果你厌烦了这种单一价值的生活,希望重拾复杂性,不如从现在开始,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开始,尝试放弃外部的影响,重拾体验未知的勇气。
这或许就像爱斯戴斯说的那句话一样:
“如果你不走到森林深处,你绝对看不到任何新鲜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