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拍摄已久的电视剧《繁花》终于上线。
这部作品改编自作家金宇澄的同名小说,原作曾获得茅盾文学奖,讲尽了上海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属于世俗男女们的细碎生活。王家卫买下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后,众人对《繁花》的期待更上一层,终于,它在2023年年底,出现在观众面前。
《繁花》是王家卫所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剧集汇聚了游本昌、胡歌、马伊琍等一众演员,分为沪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镜头华丽,台词紧凑。然而,播出之后,《繁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人们认为,它并没有拍出原作的精华——普通男女命运的“不响”与难测。
那么,作为小说的《繁花》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有观众说王家卫所拍摄的不是“繁花”?学者许子东将从内容到形式,为我们讲述《繁花》为什么是近2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小说之一。
一、上海话写的最细密的世情小说
《繁花》出版后引起了各方好评,不仅上海评论家程德培撰长文作序,台北《印刻》的主编初安民,热情关怀小说中写的1949年以后的上海。就连北方学者,比如北大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等,也认为《繁花》用普通话阅读照样有魅力。
但是在我们近二十年中国小说的语境里,《繁花》并不完全是孤军独创。联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王安忆的《天香》等等同时期的长篇,21世纪初,中国小说界其实出现了“寻根文学”的第二次发展,从文体、语言及世情、生态方面,都有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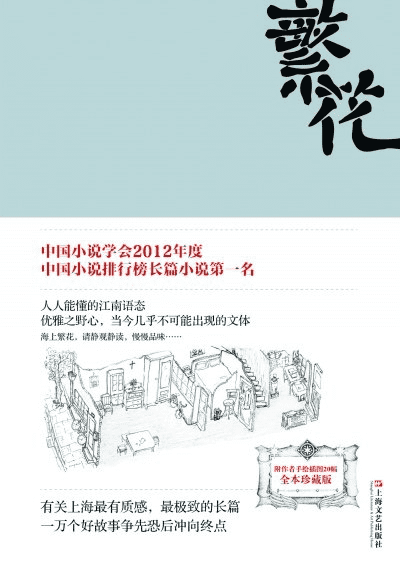
尤其是《繁花》跟《一句顶一万句》南北呼应,更是《清明上河图》的写法,细碎繁琐,百姓日常生活细节展览,构成了至少1949年以来最丰富、最琐碎的世情小说潮流。在文学史上能否体现新世纪小说潮流,当然还很难说,但《繁花》肯定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借用鲁迅对晚清“青楼小说”的经典评语,同样是近年长篇小说的这种细密的写实主义,王安忆《天香》是对古代女性生态的某种乌托邦“溢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是对北方乡民生态的某种“溢恶”,也就是直面麻木灰暗的人生。
而金宇澄的《繁花》是上海男女世情的近真写实。《繁花》写了两个时代,上世纪六十年代与改革开放以后,始终贯穿着各种男女之间的苦中作乐或者乐中见苦的生活形态。
《繁花》最主要的特点:一是沪语入文,方言叙事,二是细密写实,世俗男女。
我们先讨论第一点。金宇澄是《上海文学》杂志的主编,看了多年各种各样的小说文本。《繁花》最初是网络专栏,实验沪语入文,开始就受到一些同样有兴趣尝试沪语阅读的文学爱好者的支持。
《繁花》也是是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传统延续,后者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重要源头。胡适、张爱玲都非常推崇《海上花列传》,张爱玲晚年更是努力要把《海上花列传》从吴语译成国语。
金宇澄从一开始就考虑沪语和国语的关系,他说《繁花》“采用了上海话本方式,也避免了外地读者难懂的上海话拟音字,显现江南语态的叙事气质和味道,脚踏实地的语气氛围。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
“……但是文本的方言色彩,却是轻度,非上海语言读者群完全可以接受,可用普通话阅读任何一个章节,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
《繁花》的开篇讲了一些非常世俗的、琐碎的、莫名其妙的事情。两个主人公,沪生讲陶陶的老婆漂亮,陶陶就抱怨晚上床上吃不消,说要离婚,还嘲笑沪生的老婆出了国。
这一段体现了整篇小说的基调,基调就是世俗男女、生活细节,它绝不是那种看上去“高大上”的、英雄豪杰的或者极惨的故事情节。当然书的后面也有“高大上”和悲惨的情节,但表面上,是琐碎的人生。
二、形形色色的世俗男女
金宇澄原来打算以“上海阿宝”为书名,显然阿宝是作者心目中的男主角,最接近于作家的叙事观点。但因为小说采用话本文体,有大量对白,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抒情的机会并不多,所以阿宝的性格并不算突出。
比如阿宝和沪生的个性差异很难分清,只知道这两个上海人比较正经,谈恋爱也比较文艺腔,不大开隐形或明显的黄色玩笑。碰到桌上周围众人的黄腔谈笑,他们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响”——“不响”是他们一贯的姿态。
所以幸好小说名改成《繁花》,这个书名又接上《海上花列传》的“花”的传统,也突出了小说中的女性群像。这些女人的形象尽管不如阿宝、沪生那么正经,但各有独特的生命姿态。
小说里有着细密的写实手法与世俗男女主题。《繁花》里繁茂的“女人花”,在小说中,以男人的“树枝”为线索展开。小说以阿宝、沪生、小毛三个男人的青少年成长以及后来中年生态为主线,分成两个时段——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条线索,一三五、二四六交叉展开。
《繁花》里的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往事,近乎几个主角的成长小说,细节非常生动,比方说怎么集邮,去国泰电影院买票等等。但到了九十年代,它主要写饭局,延续的是“青楼文学”的文化传统,吃吃喝喝当中写男女,写生意,其实也有政治。人物众多,你方唱罢他登场;线索纷乱,情色生意捣江湖。
仔细读完《繁花》,就等于你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会看到上海的各个阶层,以及几十年前火红的上海。
小说里有着各色的女性,说不清楚谁是真正的主角。大胆热情的、革命的海员妻银凤,苦命贤妻、做不成良母的春香,以及商界蝴蝶、浑身事迹的汪小姐,这些只是《繁花》女性群像之一角。《繁花》中的女人并不一定要与情色有关。阿宝少年时喜欢邻居蓓蒂,是一个虚幻、纯真的洋娃娃般的形象,后来和阿婆一起消失了。沪生少年恋人姝华,是个知识女性,后来下乡以后生了几个小孩,神志不太正常,浪漫变成了凄美。
另外有一个女主角叫李李。李李对阿宝一直有意思,她的身世更是传奇。在九十年代开了饭店,招呼各路客人,有商贾,有富豪,颇能交际。
某天李李带阿宝到她上海南昌路的家,阿宝开了灯,发现卧室里摆满陈旧残破的洋娃娃,阿宝一看脑子就乱了,因为这些“架子上的玩具,材料,面目,形状,陈旧暗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塑料,棉布洋囡囡,眼睛可以上下翻动,卷头发,光头,穿热裤,或者比基尼外国小美女,芭比,赤膊妓女,傀儡,夜叉,人鱼,牛仔,天使,所谓圣婴,连体婴,小把戏,包裹陈旧发黄的衣裳,裙衩,部分完全赤裸,断手断脚,独眼,头已经压扁,只余上身,种种残缺,恐怖歌剧主角,人头兽身,怪胎,摆得密密层层”。
这种物件的堆砌是《繁花》的一个重要写作特点。在这样的诡异气氛之下,浴后穿睡衣的李李走出来,对阿宝讲了她的身世。
原来李李的父亲是工程师,又信佛,李李曾经在某省当模特,不肯内空,因为内空了以后下面是镜子。后来又被好朋友骗到澳门,要跳脱衣舞,不肯服从就被人打针,最后小腹被刺了图案,刺上肮脏的文字,形成了一辈子的伤害。
后来李李虽然也遇到好心人相救,经济自立,重新做人,但身上的伤痕,一直刺痛着她。李李和阿宝的关系,后来无疾而终。李李在小说结尾出家做尼姑了。
《繁花》从引子开始写世情男女,是当代世情小说的代表作。世俗里的男女关系有少年浪漫,有善良贤惠,也有大胆出轨或者心机,还有种种冒险,各色伤痕。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男女故事,都只是世情的一个侧面。从另一个角度看世情,我们会看到上海的不同地段、不同区域、不同阶级,还有不同的斗争历史。
三、不同的地段,不同的阶级
《繁花》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很多上海具体的路名、街道,一方面可能因为那是作者实在的青少年记忆,记忆常常是具体的、细碎的,而不是抽象、宏观的。另一方面却也隐含着作者对上海市民生态的阶级分析框架。
程德培说:“阿宝、沪生和小毛是同龄人,恰好同学少年,他们之间的友谊、情感和交往牵引《繁花》那长长的叙事。但他们的家庭背景又各自不同,资本家、军人干部和工人延伸出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生存环境。当然也暗藏着作者的意图。洋房、新老弄堂、周边棚户、郊区工人新村都是他们各自生存的场所,我们只要留意一下作者手绘的四幅地图,就可想而知小说所涉足的区域。经历了十多年不停顿的取消阶级差别的革命和运动,但差异残余依然存在,或者另一种新的差异正在产生。”
金宇澄的小说不仅好像客观地呈现了前后两种社会和阶级差异,更重要的是,无形当中令人思索这两种阶级差异之间的逻辑关系。
引文之后,小说第一章第一节,先写阿宝少年生活环境。小说写:“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
我们要说明一下,这两个小孩看的风景、路名都是真实的,香山路、皋兰路、复兴公园,以及阿宝祖父的洋房所在的思南路,都在前法租界内,是高档住宅区。
阿宝的祖父是资本家。整体上,阿宝一家在小说里代表资产阶级背景。后来全家被迫迁到近郊的曹杨新村,生活、物质条件上反差巨大。
阿宝的世界里,除了南昌路国泰影院、思南路洋房等等,还有小女孩蓓蒂和保姆阿婆。这个蓓蒂和阿婆是一对符号,分别代表纯真和忠诚。在小说中间部分,她们就失踪了。
有评论家庆幸蓓蒂最后再没有出现,说这个冰雪聪明的小姑娘没有老,没有胖,没有变俗气,更没有嫁人,作者将她留在了过去,永远穿着她的裙子和那些失去主人的钢琴相伴。所以在《繁花》里,蓓蒂就像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里的红衣小女孩一样。
沪生与阿宝在同一区,都住在茂名路洋房,却是因为不同的原因。阿宝的祖父是资本家,沪生的父母是空军干部,这两类居民是上只角的基本成分。但小毛住在大自鸣钟,那里是工人区,通常叫下只角。
沪生和阿宝及小毛怎么认识呢?是因为他们在国泰电影院排队买票。“排队”在那个时候是打破阶级隔膜的最普通方式。
上海作家常常特别关注不同地段、不同房子之间的微妙的阶级差异。王安忆写过《墙基》《流逝》,程乃珊写过《穷街》。在上海,房子在哪里,房子什么结构,影响、关系重大。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正是要改变上只角、下只角的这种穷富差异局面,或者说上、下只角应该颠倒过来。
相比之下,《繁花》的九十年代叙事大多在展览阿宝、沪生、汪小姐、李李等人参与的各种各样的饭局,展览像《海上花列传》那样的当代“叫局”风光。人物都简称为徐总、康总、丁总、吴总,这个很像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里边的老杨、老高、老李、老马等等。他们故意地要淡化名字、个性,突出他们共性的身份。
有些饭局场面作家调动自如,颇有技巧,但是如果在饭桌上也能涉及这些商家与官场、市民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我们都可以想象),如果能够把小说第一叙事线索里的阶级差异、社会差异和阶级斗争,在九十年代的饭桌上延续下去,继续变形……当然也许这是苛求,但小说里也有。
四、“不响”
《繁花》是近2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人物众多,线索纷繁,层次复杂。
金宇澄在《繁花》后面的“跋”里,透露了自己的写作原则,他说“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这个“心理层面的幽冥”就是要舍弃叙事者对人物的大段心理描写,这种欧化格式曾经是“五四”文学的一大突破;“口语铺陈,意气渐平”,“意气渐平”就是说叙事者不在行文中显示自己的情感倾向,只让读者在人物与人物间的对话中自己体会。
金宇澄继续说:“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在张爱玲以后,《繁花》是最详细展览人物穿戴的小说。
“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标点简单”在于它废除了问号。在这些细碎行文标准后面,金宇澄暴露了他的文化野心——“《繁花》感兴趣的是,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会是什么。”
一眼看去或者逐段读来,我们不难发现,对话占全部篇幅的比重《繁花》可能超过当代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中无数的故事,绝大部分都出自某一个人物的口述,但听者却也不会缺席,各有反应,当然,《繁花》最突出的一个标志就是“不响”。在别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别扭的说法,但在上海话里,“不响”很常用,指的是“沉默了”,它有很多的意思和功能。
“不响”的第一个功能是不同意;第二个功能是不想妄议;第三个功能是无可奈何,表示忍让;第四个功能是装聋作哑,有以上多种可能,既不同意,又不敢妄议,然后无可奈何,只好装聋作哑。
今天人们会把装聋作哑说成是“装睡”,这某种程度上它又发展出“不响”的第五个功能——麻木不仁。不仅是看客,有时候还是帮凶。当然有时候“不响”也可以是一种抗议。
简单而论,《繁花》是以对话为主,描写部分很少长句,但有些文言四字句。事实上,小说但凡写到文句典雅,风景如诗的段落,通常不是好戏将至,而是隐蔽“战场”。九十年代徐总跟汪小姐有一次在下午茶的时间“炒饭”,后来引出了很多风波,但是事发之时,小说却在描写众人在天井听苏白弹词。
春风春鸟,秋风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女角娇咽一声,吴音婉转,呖呖如莺簧……天井毕静,西阳暖目,传过粉墙外面,秋风秋叶之声,雀噪声,远方依稀的鸡啼,狗吠,全部是因为,此地,实在是静。
当然大家要想象这个“静”的后面是什么。
同样是有意用繁琐的文字复制世俗生态,刘震云和金宇澄是南北唱和。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怎么也讲不清楚人跟人之间如何能说上话;金宇澄的《繁花》则将上海的心态、生态,由一万句变成一句——“不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从先锋到守望者:21世纪中国小说》第30、31、32、33集,有大量删减编辑,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作者:许子东,微信文字编辑:汁儿,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