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自然》(Nature)年度十大人物盘点中,女科学家斯维特拉娜·莫伊索夫(Svetlana Mojsov)位列其中,她的上榜理由是“一位生物化学家终于因她在开发数十亿美元减重药物中所起的作用而获得了认可”。
目前,司美格鲁肽等药物已风靡全球,颇受减肥人士的喜爱。从最早应用到糖尿病领域,到如今广受认可的减肥灵药,GLP-1药物已然成为大热门,不少学者认为,GLP-1药物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诺奖风向标。《纽约客》也专门记录了GLP-1药物开发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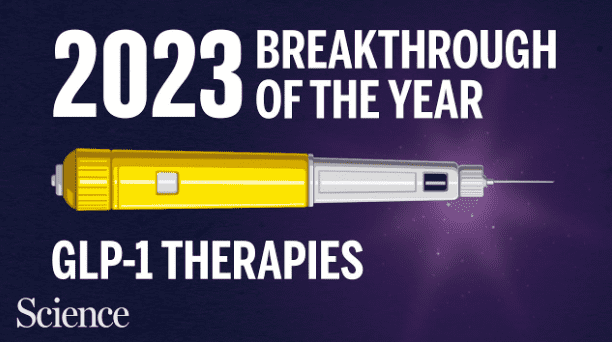
然后,GLP-1药物真的有这么神吗?不少人认为,GLP-1的减肥疗效似乎没有预期那么出众,另外副作用、对老年人的反应以及成本问题都给大热的GLP-1药物泼了一盆冷水。对于后GLP-1药物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一、从胰岛素到GLP-1药物
上个世纪20年代,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丹麦学者奥古斯特·克罗格(August Krogh)与妻子开启了讲学之旅。在多伦多的时候,他们有了意外的收获。

August Krogh
克罗格是一位生理学家,1920年凭借发现了骨骼肌里面的微血管调控机制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但获奖后,他的关注领域逐渐转向了另一个方向——糖尿病,原因是他的妻子、同样身为医生的玛丽·克罗格(Marie Krogh)也患上了这种疾病。
玛丽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并且从事糖尿病相关研究。
在多伦多,玛丽了解到一位外科医生和医学生正在探索“胰腺提取物”,这种物质能够把血液中的糖分转移到肌肉和其他器官中。
得知此消息的玛丽与克罗格协商在多伦多额外待了几天,并在之后将这种物质带回了丹麦。回到丹麦后,克罗格和几位同事共同创立了北欧胰岛素实验室。
1923年春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向第一批患者注射了一种早期的神奇药物:胰岛素。
到了第二年,实验室的两名员工,托瓦尔德·佩德森(Thorvald Pedersen)和哈拉尔德·佩德森(Harald Pedersen)兄弟打算离开团队。克罗格对兄弟二人的动向很困惑,于是问哈拉尔德,“你们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Pedersen兄弟
哈拉尔德如实相告,“我们想要生产胰岛素”。
克罗格听后,十分不以为然:“哦,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克罗格错了。佩德森兄弟成立了诺和诺德公司(Novo Terapeutisk Laboratorium),在后续的几十年里与北欧胰岛素实验室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胰岛素。
最开始的时候,诺和诺德公司主要为患有1型糖尿病的患者提供胰岛素。1型糖尿病是一种先天性免疫疾病,患者往往缺乏生产胰岛素的功能。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肥胖、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等因素的叠加让2型糖尿病患者的比重也开始增加,诺和诺德公司的市场规模也由此逐步扩大。
1989年,诺和和北欧胰岛素实验室合并,开始探索其他潜在的糖尿病疗法,其中包括了一种天然存在的激素——GLP-1,这种激素对血糖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二、GLP-1药物的成熟
最初,GLP-1并不被看好,因为它会在体内被迅速溶解。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内分泌学家皮埃尔·罗夫曼(Jean-Pierre Raufman)发现了基拉蜥蜴(一种北美原生动物)的毒液中含有类似于GLP-1的肽,可以持续作用数小时。他将这个发现授权给其他研究人员,于是开发出了一种每日两次注射的仿制蜥蜴肽的药物。
与此同时,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斯维特拉娜·莫伊索夫(Svetlana Mojsov)等科学家同样在进行开创性的GLP-1药物研究工作,即理解GLP-1在生物体内的功能和生物活性。
莫伊索夫仔细研究了构成哺乳动物GLP-1序列的37个氨基酸,并假设在较大的GLP-1肽内的第7至第37位之间的31个氨基酸可能是一种肠促素。
之后,莫伊索夫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她首先需要制造抗体来检测片段。这项任务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生产GLP-1,并用它给兔子注射,让它们的血液中产生特定的抗体。这个过程对于莫伊索夫来说非常艰难,尤其是从动物身上取血液的经历让她觉得头皮发麻。
之后,莫伊索夫陆续与同事乔尔·哈本纳(Joel Habener)、多伦多大学的丹尼尔·德鲁克(Daniel Drucker)陆续找到她,要和她一起合作。在实验中,他们使用了莫伊索夫的检测方法追踪GLP-1在大鼠组织中不同片段的活性,最终发现了肠道中的GLP-1的7-37段可能是活性片段。
1986年,莫伊索夫和哈本纳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在肠道中发现7-37肽段的有效性。这篇论文被认为是GLP-1药物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在论文中,莫伊索夫被列为第一作者,哈本纳排在最后。
然而,有关这项研究的后续插曲也十分有意思。2021年,盖尔德纳奖颁给了GLP-1药物研发中起到突出作用的三位科学家,其中出现了哈本纳的身影,可却忽略了在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莫伊索夫。这让莫伊索夫颇为疑惑和愤怒,也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研究贡献被忽略了。

于是,莫约夫选择了法律诉讼,获得了部分第一代GLP-1药物销售的专利收入。不仅如此,她还敦促《细胞》和《自然》等期刊修订了关于GLP-1发现的叙述,肯定她在GLP-1药物中的贡献。
12月14日,《自然》公布了2023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榜单(Nature’s 10),这一榜单旨在选出10位在本年度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的学者,上榜理由“一位生物化学家终于因她在开发数十亿美元减重药物中所起的作用而获得了认可”。
除此之外,北欧胰岛素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也研发出了他们自己的GLP-1类似物,2010年,他们推出了一种每日一次的注射药物,名为Liraglutide或Victoza,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
随着GLP-1药物研发的深入,科学家发现治疗糖尿病的药物还有一个额外的效果:减重。
三、GLP-1药物应用到减重领域
在美国,肥胖问题似乎长期存在。在食物匮乏的年代,肥胖可能代表着财富和健康。但随着时间推移,肥胖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出来。
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收到一封来自妹妹的信,在信中她忧心忡忡地写道:“我们亲爱的汉密尔顿工作太多,不运动,变得太胖了。”
在担任总统之前,威廉·霍华德·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或许是第一个因其体重而被定义的美国政治家。塔夫特曾寻求了一位英国减重医生的帮助,写道“没有真正的绅士,体重超过300磅。”
他的体重在一生中起伏不定,曾遭到漫画家们无情的嘲讽。
一项研究发现,在1922年到1999年期间,随着美国人体重增加,选美比赛获胜者的平均体重下降了12%,这表明一个不切实际、有时甚至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审美标准正在主导我们的认知,但静态工作、定向广告和过度加工的食品让这种理想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多年来,由于肥胖与糖尿病、高血压、胃灼热、关节炎、中风、心脏病、肝硬化、睡眠呼吸暂停、肾功能衰竭、抑郁、不孕和癌症的相关性,肥胖已经被医学化。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超重人口的比例几乎每年都在增加。
199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对肥胖宣战”后,短短几年内,美国的严重肥胖率翻了一番,与肥胖相关的心脏病死亡率增加了两倍。如今,近3/4的美国人口被认为是超重,超过4成被认为是肥胖人士。
目前,全球范围内,超重的人口是一个世纪前地球上人口的两倍。
而如今,新药物的到来可能是转折点。司美格鲁肽有效模拟了GLP-1的作用,能够降低血糖,抑制食欲,并产生更快的饱腹感。在临床试验中,服用这些药物的人平均减重35%。
另外,一种更新的药物Mounjaro也模拟第二种激素,产生更好的减重效果;
在同时模拟三种激素的retatrutide的II期临床试验中,服用最高剂量的人体重减少了接近1/4,这一下降幅度接近于更为侵入性的干预手术——胃旁路手术。这些药物往往使食物变得不那么吸引人,带来根本且持久的健康益处。
在过去的一年中,外界对司美格鲁肽和Mounjaro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供应量,导致需要这些药物的患者面临持续短缺。
有学者坚信,减重药能够重塑美国社会,产生更好的健康、更高的情绪状态、更多的性生活以及更深层次的创造力,甚至重塑了制造我们肥胖流行病的资本主义驱动力。最近几个月,啤酒、零食和快餐公司的股价下跌,预示着数千万美国人消费习惯的变化。
肥胖是我们高科技社会发明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探索,“技术”是否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
四、GLP-1药物并非万能
尽管现在GLP-1药物正风靡全球,但是GLP-1药物似乎仍然会带给我们失望。
首先,GLP-1药物并非对每个人都有效。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肥胖医学专家法蒂玛·科迪·斯坦福(Fatima Cody Stanford)提到,“每个人都想成为他们在TikTok或Instagram上看到的那个减掉五十磅的人……现实是,有高反应者和低反应者,人们需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他们可能位于任何一个极端”。
另外,司美格鲁肽等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便秘、腹泻和其他消化道症状。一位50多岁的男子提到,服用Ozempic司美格鲁肽以来,他正在持续经历这些副作用。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选择服用这种药物,主要原因在于他做出了权衡——相较于极有危害的老年肥胖,他更愿意接受副作用。
尽管大多数人在临床试验中能够耐受这些药物,但约2/3的患者会在一年内停止使用。停药之后,药物还会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体重往往会反弹。对于老年人来说,体重减轻本身也存在风险。人们在服用这些药物时可能会减少脂肪,但也可能降低骨密度和肌肉质量,这反过来增加了老年人跌倒和其他问题的风险。
最后,药物的成本也是一大挑战。尤其是在美国,司美格鲁肽的30天供应价格接近1000美元,而目前,美国医保无法用来支付减重药物的费用。与此同时,肥胖率最高的贫困人口由于医疗补助的预算紧张,可能无法从新药物中获益。
举个例子,一种名为Sovaldi的抗病毒药物可以帮助治愈丙型肝炎,在2013年推出时的成本接近90000美元;尽管最新版本的该药物的价格不到之前的一半,但只有1/3符合条件的美国成年人接受了治疗。美国患有丙型肝炎的患者大约300万,而却有1亿的人患有肥胖,可想而知,药物的支出成本会有多大。
当我们回顾这些药物时,或许会将其视为慢性疾病史上一些最重大的进步。尽管目前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GLP-1药物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们并非肥胖的治愈神药,一些人可能会面临药物副作用的困扰,药物的费用可能过于高昂……
但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后司美格鲁肽时代的世界可能会比以前更好。希望司美格鲁肽类药物在未来,能够拥有一个更美好的结局。
参考资料:
[1] The Year of Ozempic.New Yorker.
[2] Her work paved the way for blockbuster obesity drugs. Now, she’s fighting for recognition.Scienc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究科学 (ID:deepscience),作者: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