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曹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成为我除了家和工作单位以外最熟悉的地方,在心里,我悄悄地把它叫作“临终医院”,因为,能活着出院的病人是“稀有物种”。
每个周末,我都要开着我的车,从四十公里外的杨浦区新江湾城出发,以每小时八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开往浦东的曹镇。这一段路程,大多是在中环高架上行驶,途经张江高科技园区,总要经过那对雕塑 ——“谈恋爱的年轻人”,他们坐在屋顶边缘,红裙女孩的脑袋依旧靠在男青年肩头,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正在进行中。我手握方向盘,快速瞥他们一眼,他们让我在去往“临终医院”的途中多了一点点文艺和青春的亮色。
半个多小时后,汽车开进卫生院大门,并不十分阔大的院落,停车场紧邻住院部大楼。下车,偶尔可见穿豆绿色制服的护工推着轮椅在便道上走动,轮椅里,是某位失去智能的老人。这里的所有护工都认识我,看见我从车里下来,她们一定会大声招呼:外女儿,来啦!
我的外公已经在这所医院里住了两年,他的护工小张一直叫我“外女儿”,小张对我的称呼,成了所有护工对我的称谓。过去两年,我常来探望外公,却从未想过要找丁小丁,她每天坐镇门诊部五官科诊室,住院部不在同一栋大楼,我甚至从未偶遇过她,直到我的父亲也住进这所医院。
曹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共有五名护工,没有人确切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她们不分长幼,一律被称为:小张、小兰、小丁、小魏、小彭。五人的籍贯、姓氏、年龄、口音各不相同,但有两点她们几近统一,一是壮实的身材,二是壮阔的嗓门。从相貌判断,小张应该最年轻,圆盘脸上还带着些许胶原蛋白。小张的嗓门也是最大的,她若用她那带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外女儿,来啦!”调门拔得太高以至于破碎的嗓子里瞬间就能冒出一朵响亮的喇叭花,于是,整个住院部的病人、家属,乃至医生、护士都知道,23床的外孙女驾到。
23床就是我的外公,两年前,外公突发脑出血,开颅、插管,抢救过来,却也成了半个植物人。病情稳定后,外公住进了卫生院。第一次见到小张就是在病房里,当时她正给外公擦身换尿垫。在没有任何心理预设的前提下,我鲁莽地推门跨入病房,只见挨着门的23号床上,外公赤裸裸地瘫躺着,像一截剥了皮的枯白树干。病床边,身穿豆绿色护工制服的白胖矮个女人正弯着腰,用一块湿巾使劲擦着糊满病人臀部的粪便。见我进来,女人大喝一声:出去。
我快步退出病房,鼻子酸得几近冒出眼泪。从未想到会遇见这样的场面,外公赤裸的躯体暴露在所有进入病房的人眼前,很瘦很小的一段,这使他看起来像一株被太阳经久曝晒后严重缩水的朽木,又像一只被自己的屎尿淹溺到垂死的动物,大摊不明色泽的排泄物在他身下散发出恶臭,他却只能袒露着自己,任人摆布。我很想忘掉那个场面,可不知道为什么,越是想忘掉,刚才那一幕越发频繁而又顽固地在我脑中一次次闪回播放。
我的学龄前生涯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从记事起,我看到的就是外公那张不苟言笑的脸,高个子,肤色白皙,单眼皮细长眼,长相当属英俊,像老电影《红日》里的张灵普。外公很少开怀大笑,他帅气而又严肃,脸上时刻保持着某种庄重感。他也不太和我们小孩子说话,下班回家就躲在楼上的房间里看书,一向以来,他是个有些清高的人。也许,我脑中的“外公”始终停留在童年记忆的阶段,他没有随着真实的外公一天天变老。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外公袒露着污秽满身的躯体,连为自己感到羞耻的资格都失去了,这让我不禁想象,那个帅气而又严肃的男人从四十年前穿越而来,看见八十多岁的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会有多么不堪和悲伤?
身侧豆绿色一闪,白胖矮个护工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垃圾袋,裹挟着一股气味浓烈的熏风从病房里冲出来,把垃圾袋扔进医疗专用垃圾筐,而后迈着两条矮壮敦实的粗腿快速折向开水房,不一会儿,端着一盆热水出来,一股肥烟般让自己飞进了病房。十分钟后,里面传出喊声:进来吧。
外公的身躯已经被一条白被子盖住,只露出脖子以上部位,因为做过开颅手术,脑袋被剃光了,喉咙口还开着一个洞,洞口插着一根拇指粗的胶皮管子,管子通向不知所终的身体内部,也许是肺,或者胃?管子与皮囊的接口处用纱布封着,不知道外公有没有感觉到痛,我很想伸手去摸一摸,但我不敢。
我轻轻喊了两声“外公”,没有任何反应,白胖矮个女人在我身后说:没用,昨天小哥来过,叫他,不应,早上二姐来过,叫他也不应。
护工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我猜测,她说的小哥和二姐,是我的小舅和二姨。我扭过头,尽量保持礼貌的微笑:阿姨,你是我外公的护工吧,谢谢你。
女人拉大嗓门说:我知道,你是外女儿,不兴叫阿姨,都叫我小张。
所谓的小张,看起来要比我大十来岁,说话的时候,白胖的圆脸上充盈着来历不明的欢乐。
病房门口探进一张黑胖大脸,也是个大嗓门:小张,拿饭去啦。
小张一脸欢欣地冲我说:小丁喊我去拿饭了。
叫小丁的女人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也穿着豆绿色护工制服,与小张如出一辙的是,她那张黑胖大脸上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欢乐。
小张拖一张折叠椅给我:外女儿你别客气,来来,坐一哈,我马上回来。
小张和小丁去食堂了,我在这一间三人病房里扫视了一圈。另外两张床上的病人也都是老人,与外公一样,他们都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鼻子里一律插着管子,双颊凹陷、两眼紧闭,大张着嘴,竭尽全力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仿佛正与死神争夺稀薄的氧气。人老了、病了,就长成了一个样,曾经英俊而又不苟言笑的那张脸,与躺在这里的任何一张脸无甚区别。倘若不知道病床号,也许一进来我就会不知所措,这个代号“23床”的老人,只是一具躺在病床上的、与我毫不相干的躯体,他怎么能是我的外公呢?可他的确就是我的外公,床头插着的病例卡上写得清清楚楚:张明奎,87岁,脑出血……
那段日子,每隔一周我就开车带母亲去医院探望外公。小张似乎很明白我母亲的重要性,一看见她出现在病房门口,立马放下手里的活,伸出那双刚给病人擦过屁股的热情洋溢的手,搀住母亲的小臂或者扶住她的肩,几乎是喊着说:大姐来咧!尤其是发工资的日子,小张笑得如同怒放的向日葵一样的白胖脸上就会展示出非同一般的喜悦。她搬来折叠椅,展开在外公床边:大姐坐,别客气!而后,她开始向我母亲汇报外公的状况:老爸可好呢,中午吃了一碗饭加两块肉。老爸早上拉了屎,老大一坨,可香呢……
她一口一个老爸,好像躺在床上的外公是她和母亲共同的父亲。还有,她说外公吃了一碗饭加两块肉,其实就是把饭和肉混在一起打成糊,用大针筒注入外公的喉咙。她总说外公拉屎“可香呢”,这让我难以理解。
后来有一次外公腹泻,她终于说,“今天老爸拉屎可臭了”,我才确信她并不真的认为屎是香的。我猜测,她所谓的“香”,就是臭得很纯正,没有肠胃疾病引起的粪便异味。有时候她说着说着,突然跑到外公床边,伸出被消毒水泡得发白的胖手,一把拉开外公的被子,横陈在病床上的躯体顿时展示在我们面前。她伸手捏捏外公的肚皮,或者腰部的赘肉:瞧瞧,是不是胖了?比刚进医院那会儿胖多啦……她说话的语调总是显得喜悦而又骄傲,好像外公能安然活到现在都是她的功劳。这种时候,我只能瞬间放大瞳孔,模糊聚焦,忽略掉病人裸露的下半身,并且迅速抓起被子盖住外公:好了好了,知道了。
我很反感小张这么干,作为护工,这显得很不专业。我说:小张,不要总掀开外公的被子,会着凉的。我不想说“不雅”之类的话,说了她也听不懂,她每天都要对那些丑陋的躯体做无数次近距离观察、零距离擦洗,那些裸露的下半身,只是她的工作对象,又何来“不雅”之说?可是“着凉”这样的理由,却也无法撼动小张强烈的自豪感。她一次次在我们面前掀开外公的被子展示她的劳动成果,趟次多了,我也变得熟视无睹,甚至,我开始习惯她身上某种原始的职业荣誉感。很明显,她不怕脏,不嫌弃一具老病人行将就木、布满病菌的躯体,她抚摸外公的肚皮和捏他腰部赘肉的时候,就像在摆弄自己的孩子一样随意自然。这让我们在质疑她不够专业的同时,又觉得由她照顾外公挺放心。
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给小张发工资时的情形。母亲拿出账本算给小张听:这个月一共三十一天,每天68元护理费,扣除月初请假一天,共2040元。
我在心里替小张算账,她总共护理五个病人,一个月就有10200元,扣除劳务公司提成,大约能得六七千,遇到节假日,劳务费翻倍,就更多,护工全天候吃住在医院,没有别的消费,这就是纯收入,很不少了。
母亲从包里拿出一叠纸币,连着账单和收据一起交到小张手里:二十张一百元,四张十元,你数一下,在收据上签字。
小张接过纸币、账单和收据:签啥字啊!我还能不相信大姐?
母亲塞给她一支水笔:这是规矩,收钱必须签字。
小张犹豫了一下,把收据铺在外公的床沿上,屈身往床边一趴,举起水笔,扭头问:写哪儿?
母亲指着“收款人”后面的空白处说:这里。小张重新埋下头,提起笔,在母亲所指的地方,极其缓慢地、认认真真地画了三个浓墨重彩的、并不规则的圆圈。画完站起身,把收据交给母亲,“嘿嘿”着说:画得不圆。
我在心里暗笑,她让我想起《阿Q正传》。母亲看了一眼账单,也笑了: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我不会写字,只好画圈,我名字三个字,画三个圈。小张好像并不羞于自己不识字,母亲问她: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俺叫张J萍”,小张大嗓门一喊,谁都听见了,可谁都没听懂她那河南口音说出来的到底是张菊萍、张娟苹,还是张建平。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小张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无法想象,一个不识字的人,是如何通过护工入职培训考核的?她每天要给外公喂药,溶血栓药、降血脂药、消炎药,一天几顿,一顿几粒,竟从未搞错。她还让我帮她把我们家里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都存在她手机里,她怎么辨认那些由11个数字组成的手机号码归属于哪个名字之下?她还常常凑在小魏身边,一起看小魏的儿媳妇淘汰下来的iPad里存的电视剧。还有,她去邮局寄钱、去银行存钱,至少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吧?这个目不识丁的小张,实在是让我无法想通,她是怎么在大上海活下来的。
每次在账单上画过圆圈后,小张就会对母亲这个给她发工资的“老板”很是感恩戴德,恨不得要投桃报李地给母亲一些什么好处,于是和母亲聊天时,就多了一些“内容”。
“大哥已经两个月没来了,老爸偏疼小儿子,大哥不会是有意见吧?”
“小嫂昨天送来粽子,老爸不能吃糯米,不好消化,我说过,她不听。”
“二姐每个礼拜都来看老爸,小姐只来过一回,小姐夫一回都没来过。”
小张大概不懂,这种类似于打小报告的聊天,是要把嗓门压低一些的,可她几乎是光明正大在母亲面前揭发我的舅舅、姨妈们,她的高声喧哗使那些微妙的家庭矛盾公之于众,这让我有种无地自容而又无以躲避的尴尬。
对于小张传播的八卦,母亲的态度始终讳莫如深,她不动声色地听,不否定、不阻止,每次都把小张说得兴致勃勃、唾沫飞溅。直到某张病床上飘来新鲜的粪便气味,或者哪个病人忽然大声咳嗽,嗓子眼里有浓痰呼之欲出,她才闭嘴,迈开两条粗壮的短腿,飞也似的冲向那个病人……
外公住进曹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两年后,我的父亲也将住进这家医院。现在,他们翁婿俩天天在同一屋檐下生存着,一个躺在走廊顶头的第一间病房里,另一个躺在走廊尽头的第二间病房。然而,作为病友和邻居,他们却从未相互拜见,他们没有能力彼此串个门、聊个天,通报一下最近关心的国内外大事,谈一谈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聊一聊股票行情和房价趋势……
哪怕只是在五年前,这两个相差二十多岁的男人,也常常会坐在一张八仙桌的两侧,一聊就是半天,把一杯浓茶喝到寡淡无味。可是现在,他们住在一栋楼里的同一个层面,吃着一口锅里同样的饭菜,却再也没有促膝交谈的机会,甚至,他们都不能相互看上沉默的一眼。很有可能,他们会成为一对“老死不相往来”的老朋友,这句古老的俗语,大多时候是用于“绝交”的宣言,可他们从未绝交过,在他们还记得彼此的岁月里,他们一直维系着和谐、融洽和彼此尊重的翁婿关系。
现在,我和我的所有家人,都会在探望一位亲人的同时,顺便探望另一位亲人,这让我们省去了不少花在路途上的时间,虽然,“顺便”这个词似有缺乏诚意之嫌,但我还是愿意这么说,因为,这是真实的。我们一趟趟跑去医院探望亲人,与此同时,我们认识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每一位护工,并且成为她们日常八卦的对象,或者,倾诉对象。我们已然接受她们的风格,她们壮阔的嗓门,她们劳作的身影,她们热火朝天地生活在这里,她们使一家“临终医院”常年充满莫名其妙的欢愉气息,甚而过于喧嚣嘈杂,没有人确切感觉到,这里是死神频繁光顾的地方。
医院虽然不大,但也有两栋楼,门诊楼大多时候冷清寂静,住院部却是例外,它像大家族的旁门一系,护工是这一系支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做着为病人服务的工作,却更像是这里的主人,因为,“流水的病人,铁打的护工”。或者说,她们是大家族的管家、保姆,她们没有主人的身份,却操控着主人的衣食起居。她们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待在病房里,白天在病房里工作,晚上在病房里安睡。她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行军床,白天折叠起来塞在某一张病床底下,入夜就把行军床拖出来,在病床间铺开。她们在病人的鼾声中入睡,连接在病人身上的监测仪整夜发出“滴滴滴”的噪音,她们却从未因此而失眠。她们很容易入睡,也总能在病人发出异动或声响时及时醒来,她们有着随时入睡以及随时醒来的本领。她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这里,二十六个病人的家属亲友她们全都认识,谁家的孩子孝顺,谁家的媳妇刻薄,她们全都知道,这也成为她们在闲暇时候八卦的主题。
每次去医院,我都会有种走亲戚的错觉,心里总想着要给外公的护工小张或者父亲的护工小彭带点什么礼物。三八妇女节,送她们一块毛巾和一瓶花露水;端午节,给她们一人带一包五芳斋粽子……这几乎成了我的压力,多了一件操心的事,可不知道为什么,在送给她们小礼物的同时,我的内心总会生出一些安然与愉悦。也许这只是我的聊以自慰,我希望以赠送礼物的方式换取她们额外的重视,我希望她们能更加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的亲人,虽然,大多时候,我无法看见她们究竟是如何照顾我的亲人的。这让我在每次踏入住院部走廊时总是心生担忧,我怕看见某些“真相”,我不知道要如何应对。
那是一条随时都能听见各种声音的走廊,护工的呵斥声,病人的哭闹声,此起彼伏,从不停歇。外公病房的对面,小兰总是操着一口川味普通话训斥坐在轮椅上的汪老太:再吵,再吵把你扔到大该(街)上去,没得人管你!汪老太并不领受小兰的恐吓,照旧发出毫无章法的哭喊,小兰就亮出一把给病人喂饭的没有针头的大针筒,在汪老太眼前扬一扬:再哭,再哭给你打针……这种时候,母亲总会叹口气:唉!作孽,去吓唬人家干啥,儿女不在跟前,不作兴的。
走过第三间病房,就能见到胖大的黑皮肤小丁,或者听见她那淮北口音的大嗓门发出的喊叫声:拉屎会不会喊?会不会?不长记性要不要打?然后是两记“啪、啪”脆响。起初我很是怀疑,她是否真的在打病人?有一次,终于不敌好奇,我折身进了三号病房。我看见一个不会说话的老病人光着屁股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着矗立着的庞大的小丁,呆滞的目光里没有悲伤,也没有喜悦。小丁见我进病房,张嘴招呼:外女儿来啦?找小张还是小彭?不在这里……她宽阔的笑脸上写满了坦然,她不介意被我看见她打病人屁股,大概,她从不以为这已经成为她伤害病人的证据。
我问母亲:外公拉了屎,小张会不会打他屁股?还有老爸,小彭会不会打他屁股?
母亲怔了怔,说:你小时候尿床,我也打你屁股的。
我脱口而出:可他们是老人,不是小孩。
母亲看我一眼:那小张要是打外公屁股,小彭要是打你爸爸屁股,你要不要去投诉?投诉完了呢?打算换医院还是换护工?
我被母亲问住了。换医院是不可能的,外婆厚着脸皮找丁小丁,好不容易得来这一张床位,我们又能去哪儿再找别的合适的医院?至于换护工,那就更没有意义了,把小张或小彭换掉,换来小兰、小丁、小魏,又有哪个护工不吓唬病人、不隔三差五地打两下病人的屁股?
有一次,进住院部走廊,看见小张、小彭、小魏她们几个正凑着脑袋划拳,一来一往,最后是小张赢了,只听见她浪涛般的笑声阵阵翻滚:哈哈哈,我先挑,我挑13床和17床。
我问:你们在玩划拳?
小张说:我们在分病人。中秋节小丁要休假回老家,她负责的病人要我们分摊,我们就划拳,谁赢谁先挑病人。
我很好奇:病人还要挑?
小张并不掩饰作为护工的“心机”:那可不是?外女儿你不知道,病人和病人不一样,全身瘫痪和半身瘫痪的,能喊拉屎的和不会喊的,会吐痰和不会吐痰的,都不一样。
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同样拿一份加班费,分摊到什么样的病人很重要,就像以前农村杀了猪抓阄分猪肉,抓到猪腿还是猪头,要靠运气。
我说小张你运气不错。小张再次爆笑:哈哈哈,我故意出得慢,她们要出拳,我就赶紧张开巴掌,她们要一出巴掌,我就赶紧伸出两手指头……
小张不识字,身上却满是精明狡黠。我说:过节工资翻倍的,多两个病人,你能多赚不少,不回老家也值了。
小张笑得自豪而又满足:可不是吗!我不爱回老家,来上海五年,我一次都没回过。
母亲打断她:小张,我们结了这个月的工资吧。一听说结工资,小张立即忘了前面的话题,一如既往,兴高采烈地在收据上画了浓墨重彩的三个圆圈,然后开始在母亲面前八卦我的舅舅和姨妈们。
“小哥每个礼拜天都来,给老爸带来肉包子。”
“二姐每个礼拜三来,老爸的水果她包了。”
“大哥有日子没来了,大嫂倒常来。小姐也来过一次,拎来一箱牛奶……要不说孩子养得多好啊!”
我问小张:你养了几个?
小张的胖圆脸上顿时笑开了花:两个,大的儿,说对象了,小的闺女,在老家念书,五年级啦。
“两个?当时是要罚款的吧?”
小张的脸上泛起一团红晕:我罚不起,闺女是白捡的,人家扔了,我就抱来养了,不是自个儿生的,不罚款,划算。
她还伸手指着我说:外女儿,你一定要多养几个,等老了,儿女都来看你,多热闹,多好啊!说着扭头看向病床上的外公:老爸有福,正好养了七个,一天一个轮着来,一个礼拜齐了,哈哈哈……
小张巨浪般的欢笑声在住院部到处流窜,我几乎听见那笑声在走廊里迂回撞击,发出一波波朗朗的回声。这让我再次产生错觉,好像,这里的二十六张病床上躺着的,不是患了医不好的病等待寿限的老人,这里也不是被我暗暗称为“临终医院”的地方,而是一所婴儿医院,躺在床上的,是一个个巨型婴儿,小张、小丁、小彭、小兰、小魏她们,就是这些巨型婴儿的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保育员。
一个周末的午后,到达曹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停车,进住院部走廊,不知哪间病房里传来歌唱般的哭喊声,细细分辨,还能听出有唱词,好像是儿女们在哭“爹爹”,典型的浦东地方特色哭丧调。大概是哪个老病人作古了,很奇怪,那种尾音悠长,且有一定的叙事性的哭调,听起来悲恸万分,却又无限美好。我在越来越接近的哭声中朝走廊尽头走去,远远地看见父亲的病房门口围着一圈人,哭丧调正是从那扇门内传出。我知道,不可能是父亲,因为小彭没给我打电话。可我还是有些紧张,便放慢脚步,走到门口,站定在看热闹的人群后面,一时不敢挤进去。
父亲病房里有四个病人,6号床已经九十岁,心梗、脑梗、痴呆;7号床就是我的父亲老薛,阿尔茨海默病,正亦步亦趋地走在丧失所有功能的路上;8号床年龄最小,七十二岁,脑溢血抢救过来,成了一个整天打呼噜的人,睡着时打,醒着时也打;9号床八十五岁,中风,除了不能下地,恢复得不错,能简单对话。说实在的,这么几个老病人,哪天宣布谁突然离世,都不在意料之外,我只是担心,这么嘈杂喧闹的环境会不会影响到父亲。
围观人群忽然散开,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从病房里鱼贯而出,紧接着,两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推着一张停尸床出来,床上白被单覆盖着的长条隆起想必是死者。跟随在停尸床后面的,是一些唱着悲恸而又美好的哭丧调的男男女女,他们在人群的注视下呼啸而过,朝走廊另一头的大门热热闹闹地移去。看热闹的人有的跟着哭丧的家属送出门去,有的回了自家亲人的病房,一番喧嚣过后,病区安静下来。
我进病房的时候,小彭正在收拾空了的9号床。五名护工中,小彭当属护理经验最丰富的一个,之前她在肺科医院做过六年护工,转到这里也已经三年。小彭是安徽阜阳人,长着一张方脸,刚满五十岁,念过两年初中。后来我才知道,小张每次去街上给老家寄东西或寄钱,都会拉上小彭一起去,但凡需要签字,就由小彭代劳。
见我进门,小彭拔高调门喊道:外女儿,来啦!小彭的嗓门不比小张差,语速比小张稍慢,有种掷地有声的权威感。神奇的是,她这铿锵有力的大嗓门,近乎有着驱邪的功能,一开口,这间刚死过人的病房就不再令我感到恐怖了。打完招呼,小彭放下正卷到一半的床垫,走到7号床边,从我父亲耳朵里掏出两团棉花:他们哭那么大声,我们不听,现在他们走了,可以听了。说完又跑到6号床和8号床,把他们耳朵里的棉花掏出来。
我问小彭:不能让他们听见吗?小彭说:最好别听见,有人升天了,你不能不让家里人哭吧?可不能给老人听见,老人都怕死,我给他们耳朵里塞棉花,听不见,就不怕了。
小彭指着床上的病人:外女儿,你还年轻,有些事你不懂,他们都是一只脚跨进阎王殿里的人,有人要升天,就会拉上一伙结伴走,路上才不冷清,我见过好几回,今天一个,过一天,又一个……
小彭一番玄乎的言论令我疑惑不已,还有些瘆人,四顾周遭,却一如以往:6号床正用他那双被看护带捆绑住的手无意识地敲击着床栏,床架子发出没有规律的“哐、哐”声;我的父亲正瞪着眼睛看窗外,嘴里偶尔发出三个字的感慨:哎哟噻 —;8号床睁着一双三角小眼东张西望,半开的嘴里吹出一股股响亮的鼾声,他没有睡着,他只是鼻咽喉部气道狭窄,也许患有鼻窦炎,或者长了鼻息肉,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打鼾的人……三位老病人不明就里而又按部就班地活着,他们不知道,就在刚才,他们的一位病友“升天”了,小彭在他们的耳朵里塞了棉花,他们没有听见哭声。
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一脸平和的样子,我不由地对小彭生出了几许感激。抬头间,发现病房门口,一张尖瘦的小黑脸卡着门框探进来,是个小女孩,十二三岁的样子。小彭指着我冲门口笑道:来,喊姨。
女孩闪进病房,走到小彭身边,很自然地,和小彭一起收拾起床上的被褥和床底下的塑料盆,还有床头柜里的各种药品和生活用品。我问这是谁?小彭说:小张的闺女,放假,来上海找她妈,白天没啥事,在病房里到处玩儿。
这就是小张捡来的女儿?我问小彭:那晚上呢,她睡哪里?
小彭说:就睡病房里,和她妈挤一张床。孩子挺懂事儿,谁忙不过来就来搭把手,刚才9号床咽气,就是小张闺女发现的。
小彭看出了我脸上的惊愕表情,四方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神色,压低几分嗓门,颇为神秘地说:告诉你外女儿,9号床,是被红烧肉噎死的……她顿了顿,继续说:昨天9号床对他儿子说,想吃红烧肉,今天他儿子就做了红烧肉带来,谁知道他儿子喂他时,没把红烧肉打成糊,这事要是我做的,我就得丢工作。
我说:红烧肉打成糊不好吃。
可不是吗?9号床的儿子也是这么说的,他就想让他爸吃一口囫囵的红烧肉,一定要自己喂,要是我喂,不就打成糊了吗?老头真爱吃红烧肉,一口气吃了四块。他儿子还说:我爸胃口这么好,病也会好得快。谁想到,刚吃完,就在他儿子去洗饭盒的功夫,十分钟还不到,小张的闺女指着9号床喊我:大姨你看,你看。我回头一看,哎呀不好,脸是铁灰铁灰的,嘴角淌着白沫,我赶紧跑到跟前伸手摸他鼻子,我的个天,没气儿了。
说到这里,小彭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唉!吃着红烧肉“升天”,真是个有福的人。
与临终医院打了一段时间交道,我已基本了解护工们的说话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升天”——这是所有护工对死亡的正式叫法,似是约定俗成。虽然她们惯常于用最粗俗的字眼描绘生活,譬如她们会把呼吸道原因引起的猝死叫“噎死”,她们还把心血管病人的猝死叫“憋死”,要是哪个病人走着走着倒地而死,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她们都叫“摔死”。
但当她们需要正式告知家属,或者需要总结性描述,就会回避直接用“死”这个字,她们也没有如大多数人那样,把“死”叫作“没了”“走了”,这些词汇显得不痛不痒,偶尔还会产生歧义,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死亡并不温情,死亡是尖锐而疼痛的。她们生活在最迫近死亡的地方,有时候是白天,看着病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直至停止呼吸;有时候,是在午夜时分,死神来临的最佳时刻,病人静静地停止心跳,无声无息,而她们,也正睡得安然成熟,她们与那个不再呼吸的躯体在同一间屋子里安眠到清晨……她们无时无刻不在遭遇死亡,便需要泼辣的性格和热烈的情绪来应对,这样才不至于被随时降临的死神吸纳了精神。她们拒绝使用那些文雅而又词不达意的语言,她们愿意落入最为动人的庸俗,说话一律大声,做事一律大刀阔斧,连睡觉都要大张旗鼓地打鼾,她们必须夸张地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死亡,她们若非藐视,便是升华为神话,于是,她们把“死”叫作“升天”——她们的选择令我心生敬意,我喜欢这个词,它让“死”变得不再那么疼痛,而死亡的惨烈性质,也因为“升天”这个词,变得神圣和浪漫起来。
可我依然惊异于小张居然让她女儿住在“临终医院”,还让她在病房之间到处流窜。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正在叠被子的女孩,细胳膊细腿,除了黑瘦,五官长得不丑,是那种尖下巴小脸蛋,与小张的圆胖脸完全不一样,果然不是亲生的。女孩跟着小彭不紧不慢地干活,动作却娴熟,可见她对家务活不陌生。可是,这张床上的被褥以及各种用具,属于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而这个人从生到死的那一刻,被她亲眼所见,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果真不害怕吗?
我从父亲的水果篮里拿出一根香蕉递给女孩:给你,拿去吃。女孩扭捏了一下,接过香蕉,放在床头柜上,继续整理床铺。
门外传来小张的呼喊声:妮儿 ——女孩撒腿就往外跑,跑到门口突然折返,回到病床边,伸手捡起床头柜上的香蕉,再回身,飞也似的向门外奔去。
她终究还是个孩子,可她又不像孩子,“临终医院”不是游乐场,不惧怕死亡的人,莫非成熟理性之极,就是麻木愚钝,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属于哪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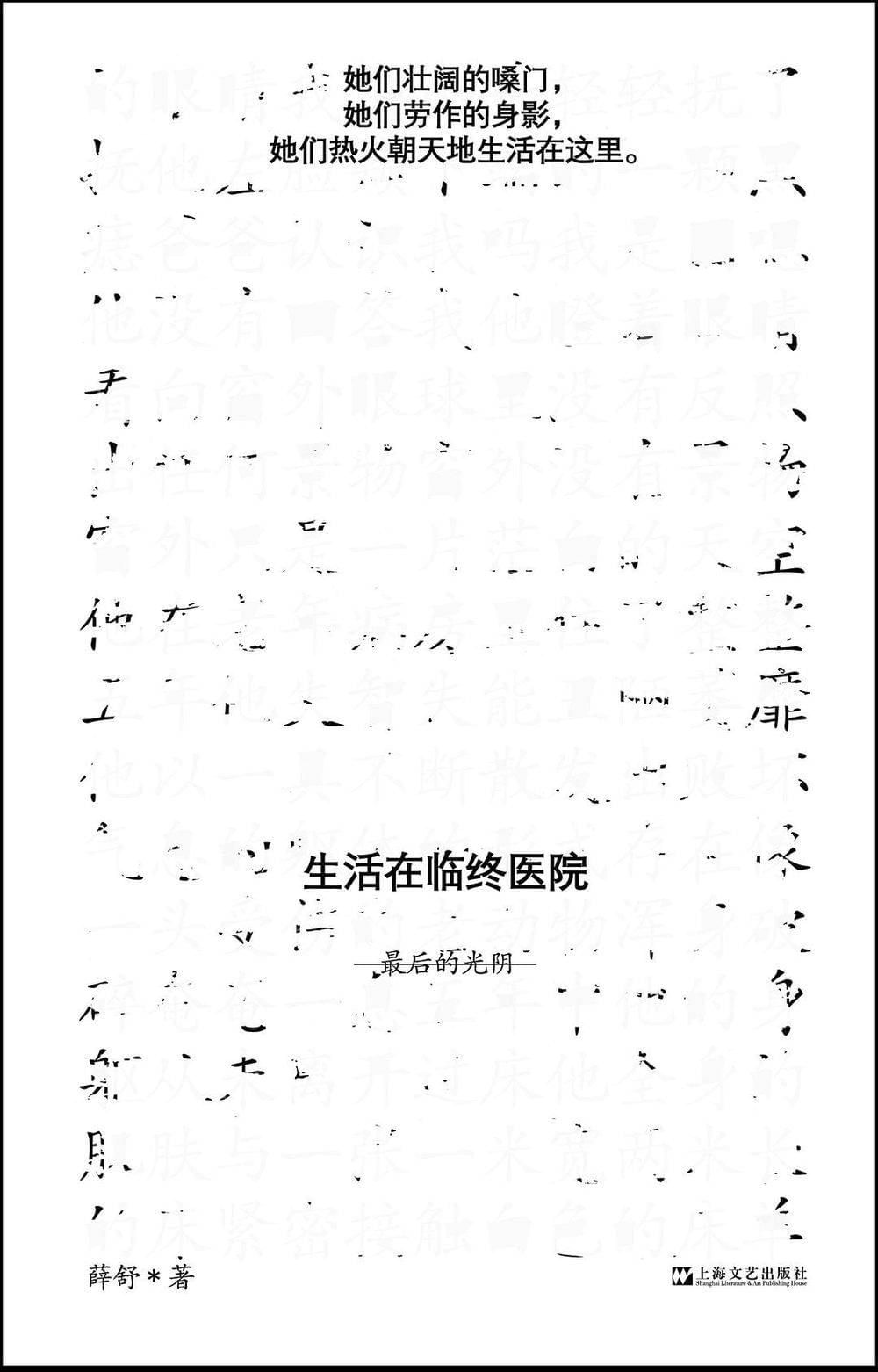
作者: 薛舒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单读
副标题: 最后的光阴
出版年: 2024-1
本文摘编自:《生活在临终医院》,作者:薛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