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年龄是指什么?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时点,用数学上精确的表达方式来说,在这个点的前后,他发现他只是他自己。他认识到,世界突然不再允许他透支未来,世界不愿再被牵扯进来,不愿再将他看作一个他可能是的人。
他自己仍旧相信为他保存的可能性,社会却不再将这些可能性融入它为他塑造的图像中去。他发现自己成了没有潜能的造物,不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而是他人目光的镜像,他人的目光很快会被他自己消化。
没有人会再问他“你打算做什么?”,一切都定好了,清醒且不可动摇:“这个你已经做过了。”他必然体验到,旁人做了张他人生的资产负债表,呈给他一个结余,他就是那个结余。他是邮局职员,如果勤奋并且走运,还可以成为部门领导。
他是个画家,要么更失败,要么更成功:如果成功在生命和阴暗事件的加总中累积,那么成功会对他继续保持忠诚,即便艺术品市场上存在动荡,即便今天他的画作报价不像昨天那么高;但成功(Erfolg),也就是随之发生的(erfolgt)事情,即他的艺术效应失效了,那么失败作为对其艺术生存的否定就成了他的标识。
无论A是谁,如果他还不是,那么他就既不会变成勇猛的猎人、政治家、演员,也不会变成惯犯或任何其他职业的从业者。他称之为“生活”的东西,抱负与放弃的总和,确定了他昨天也一样视为自己生命的东西,就是生命留给他的年数。这些年月他如今可以当作被挥霍的时间的千篇一律和单调的重复而不再顾忌。
真的啊,死亡才确定终点,生命的结束才给予开始和一切阶段以真理。理论上,游戏在终局以前,一次也没有玩耍过。断裂、启动、转折、爆发,以至于最终一个体验了惊呆和僵滞的阶段可以将自己揭示为单纯的过渡。高更,一位银行雇员拒绝了社会展示给他的自我的结余:他在多米尼克的死亡道出了银行雇员生存的真相,并使之消亡。可以传唤多少高更来作证?
未来,在一个通过互动和互相依存社会化的世界里,出格者会越来越少。自我的结余,社会编制的资产负债表的结算额被接受、被消化,最终被迫切要求。人是他通过社会表达出来的东西。变老的人表达过的东西已经被清点、被称量、被判决。即便他赢了,或者说,即便完全构成和耗费了他的意识的社会存在被标上高昂的市场价值,他也失去了它。
断裂与转折不再处于他的视野之中,他将死去,就如他活过,一个战士,而且是勇敢的战士。
……
肯尼迪四十三岁时成为美国总统,人们感觉他还年轻;一位四十三岁的高校教师助理却不年轻。或者相反:四十岁时获得议员荣誉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议员正是借助他的荣誉和他父辈的影响而成了一个非常成熟、德高望重的男子。他邋遢的兄弟克里斯蒂安带着腿上不知何处的疼痛和对香槟早餐的偏爱,就算临终躺在病床上时也还是个少年。
社会年龄由一连串因果的缠绕确定,太过复杂,在此无法解开。我们曾经的社会抱负也构成了大量线索中的一条。比如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四十五岁的下级官员是一个老人——当且仅当他曾经追求过一个更高的职位时。但只要他从未努力追求社会等级的攀升,既未对他的家人,也未对他的朋友,也没有对他的上级说过自己对于晋升的希望,他的社会年龄就不确定也不可确定。
在他的下级职位上他是三十岁还是四十岁都与社会无关。他无历史地活在他的部门里,一个没人记载的男人——只有记忆的重量或者成了负担的身体有一天会让他意识到,他老了。当他还很年轻时,在对他那小小野心的认可中社会就已经对他做出了判决。从社会的角度看不出年龄或者未老先衰,现在都无所谓了,他会被一直推到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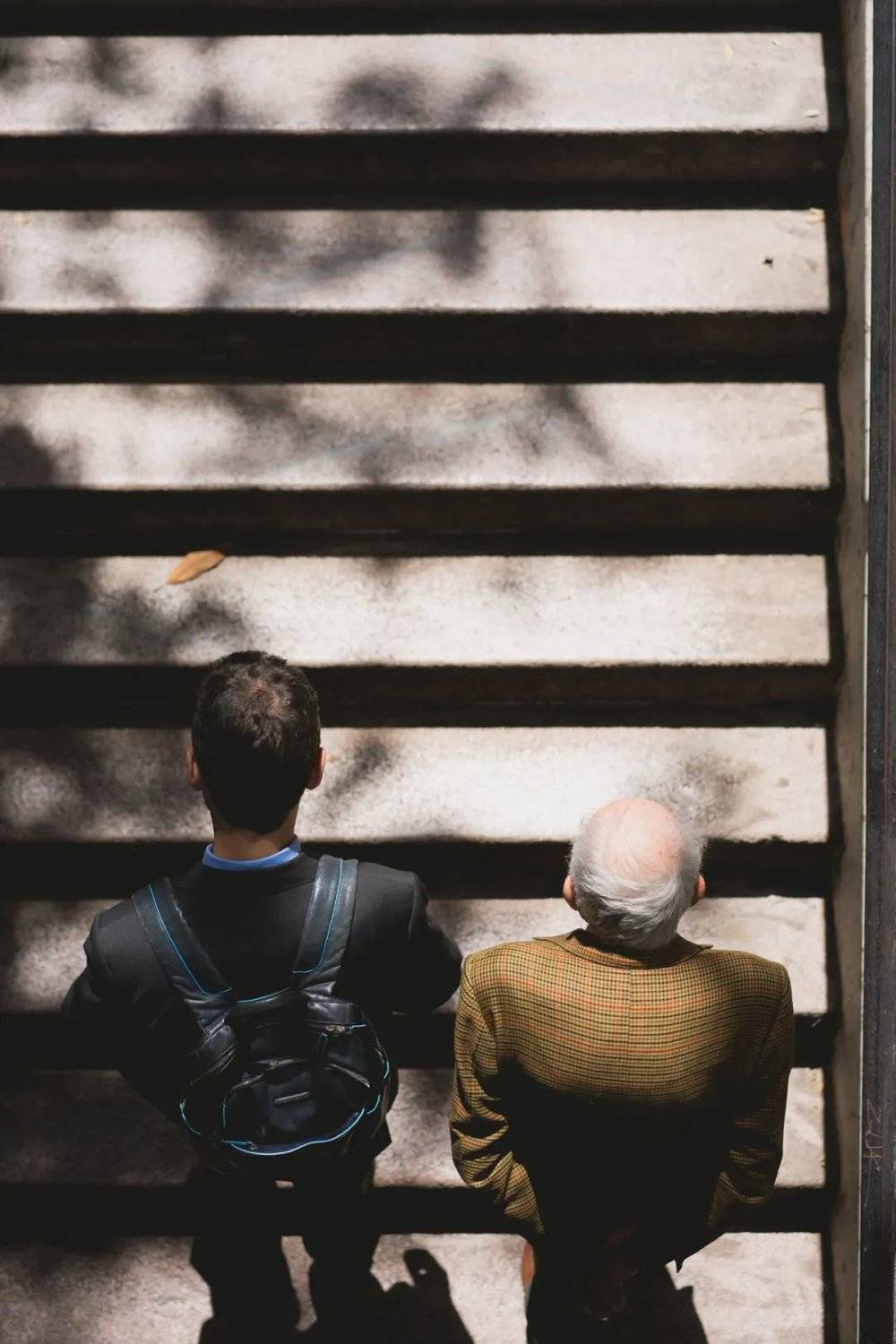
Photo by John Moeses Bauan on Unsplash
只要在我们的时代有超越所有结构、民族和个体差异的社会年龄标准,只要我们能确定那一时间段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社会判决获得完全的有效性,世界不再允许我们向自己所估量的可能之物自我超越,我们就在所有物的领域找到指向,我们大多数时候表现出的市场价值也属于这个领域。因为我们的故乡不是存在(Sein)的世界,而是拥有(Haben)的世界,准确地说,一种通过拥有才被给予的存在的世界。一个人是什么,一个人想象什么,通过他所拥有的被确定。
普遍的秩序希望这样,人们被要求,他要拥有可以被标价的财产或者表明以及担保财产的市场价值——一旦他拥有,他就进入社会年龄阶段。倘若他没有,他也许就省略了社会年龄,然而之后他必然体验到,无论是社会的实质还是人的生存都不再授予他了。
生之愚蠢,没有学到任何东西;生之贫穷,一无所获。他既无地位亦无恒产,是想象中的塔列朗或者曼萨德恩格尼。以拥有为基础的社会使自主的个体中性化,个体在拥有的要求压力下不再能用自我意愿、朝向未来的人格与他人的目光相对。
人们想要照着拥有的路标找到方向——然而要确定显年纪的时点则颇有难度,因为拥有的事实或者对拥有的要求是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与我们相关。
这个人拥有的命运很早就已开始,在摇篮里,当他作为继承人生下来,在意识到自我之前很久,父亲的工厂或者律师事务所就期待着他。
对于另一个人而言这个过程在高年级学校才开始,那时他的数学天赋促使他走上物理学家或者工程师的人生轨道,这些职业拥有确定的市场价值,在第三个人那里开始于大学或者职业培训的第一年。
但每种情况下一样的是,构建起意识结构的存在由拥有规定,而拥有对于人而言从两个方面看都是灾难:一方面剥夺了他自己的可塑性,剥夺了他每时每刻从零点重新开始、用自己的意志筹划生活,不需要社会甚至反对社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拥有抽离或者停止收集时,便判决他——作为对经济资源或者对一种被社会要求、可兑现为市场价值的确定能力,即“know-how”的占有——继续做一个社会的空缺,一个空腔,但已不再拥有零点的可塑性,因为社会已经判定,他不再能支配任何东西。
拥有的世界日复一日越来越容不得筹划未来的局外人。
拥有的整合力量格外强大。个人的财产和市场价值让这个人越来越顺从,仿佛它是戴起来就像首饰一样舒服的锁链。
A是一名四十岁的记者,适量完成些文章。他的技巧,一支如飞的健笔,就像他的客户们称赞的,保证了他写出的产品有确定的交易价值。
他活着,既不奢华也不安稳,但也不困窘,不害怕黑色的苦难。他写出并贩卖他的文章,住的地方几乎不引人注目,有一辆车,假期会出去旅游,有时候睡前会被回忆打扰:他坐在一间阁楼里,是一个零。他不相信他写出的东西每次都能找到买家,所以他勾画出他想要什么,想要怎么样。
在生命中获得他的,是宽广的视域:既然他什么都不是,他便是一切。他的潜力是整个世界,整个空间。他在潜能的领域里是世界革命者和城市流浪者,皮条客和哲学家。他年轻。他的年龄和身体都年轻,他在眼前拥有空间时,就是这样,因为尚没有太多时间在他心里累积。在他的社会存在中他也年轻,比刚刚目睹第一个死亡的病人的同龄医学博士年轻,也比把自己的第一份批评收藏进相册的演员年轻。
现在他不再是那样的了。现在他在他拥有些什么的地方,尽管拥有得如此之少。在社会第一次让他理解到,它只会在疯人院里忍受永远的年轻人之后,就分配给他一个社会年龄。他拥有了社会年龄,有时候深深诧异于自己对此的认同。是纳税人和公民,他的问候在楼梯间得到了邻居的回应!
可耻屈服的总次数附带着愚蠢无聊的骄傲暂时充斥着他。他感到羞耻,自己走到这一步,一种被拥有注定的存在偷走了他没有拥有的存在,偷走了他永远变化的存在。
然后他问,是否可以设想一种社会秩序,在那种秩序里,可笑的胜利,同时也是悲惨的失利,能够为他保留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存在不是拥有,也不是知识的拥有(因为也许知识的拥有不可转化为一个所有的范畴),而是保持为变化的存在:与他人一起的存在与变化,他人的目光不会压制他,反而帮助他一再地成为一个零点,并从零点重新构建自己。
A问自己,找不到任何答案,他知道,这一无所获很可能已经包含在他连续的屈从行为和完全为他所有的东西里。他已经融入事物中,无论这些东西多么微小,因为他拥有它们,便不再能不愿意拥有它们。就和无数其他相同的命运一样,他不得不失去戴起来容易且舒适的锁链,被摧毁的生存的装饰,这生存在以社会的方式构建起来后就摧毁了人性。
他老去了。社会负有责任。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负有责任,就看他如何屈从于社会的法则,而不是变成一个愚人或者一个流血而亡的切·格瓦拉。
格瓦拉、高更、疯人院里的妄想狂和穹顶咖啡厅里他的远房亲戚,他们不受他人目光的干扰,这目光代表了拥有的世界,就像此外也有富豪们,他们的财产如此庞大,以至于财产对于他们不再有意义,也不再能定义他们。阿里·汉从青年走向死亡。温莎公爵将像克里斯蒂安·布登勃洛克——一个未老先衰的青年——一样死去。
其他人或早或晚都会到达一个社会年龄,大多数是在那样一个时间点,在那时他们向社会表现出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生产者—消费者。
无论何时他们都有一份财产要去守护,要去提供一份知识财富,去照顾伴侣或者孩子。在被他们想要增加或者保存——二者都将耗尽人的心力——的拥有所规定后,他们辛苦操劳,终有一天意识到那生命的转折,那时他们的拥有—存在已不可挽回:那时他们在变老。门不会再打开。
谁向社会提出一个问题,就得到这个答案:努力做你昨天和前天努力做过的事,做能让你的过去证明你的事——或者什么也不做。招聘:有经验的银行业专家,管理我们的分店,最高年龄四十岁;精通纺织业的商人,懂英语,负责企业重组,不能超过四十五岁;年轻、有活力、有进取心、热爱工作、亲切友好、精力充沛的男士,旅游代理,实验室主任,工程师,编辑,广告策划。
人事经理所有的就是他人的目光:他不仅要求一个符合投资逻辑的社会年龄,而且明确的是,要一个特定领域的经验。他不招收四十岁的起步者。同辈X,从二十三岁到四十岁一直在研究汇率,计算计件工作的工作时间,设计广告草图,或者适量地写写文章。
有时候从工作中抬起头来问自己:“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吗?”于是感到恐惧。会这样继续下去,不是刚好永恒,而是还有一个他的人生那么长的永恒:如此之长,只要他健忘的大脑、沉重的躯体和有效的社会法则允许。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称为理所当然的退休,退休对一些人意味着国家养老金,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可怜的退休金,而对于两者都意味着从社会的、自我塑造的实际中被驱逐出去,还有这两个非常阴沉的问题:我究竟什么时候活过?我什么时候不再将我的身体当作一个持续更新的程序和持久的矛盾?幸运的是这样的提问时刻很少见。
无论他已经开始领养老金还是激动得手舞足蹈,还是“处于人生中途”,还是在增加或者守护自己的所有,这位同辈已经接受了社会加诸他的判断——他的社会年龄。他碰上了一个不再逾矩,却尚未满意地保持平静的自我,因为被社会的弃绝所包含的生存的死亡就像生理的死亡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每个人都对自己说还有很多日子,并且想像个男人一样行动。但在夜晚到来前,夜幕就已降临,而他只能按照社会要求、允许和禁止的发挥些作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 (ID:sanhuibooks),作者:让·埃默里(出生、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并在这座城市学习了文学和哲学。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军队进驻波兰后,他先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1945年才被释放。战后,埃默里在瑞士多家德语报社做记者以谋生。1966年,他出版了书写自己奥斯维辛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并因此广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