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 (ID:sanhuibooks),作者:黄宗洁,编辑:艾珊珊,原文标题:《在野性与驯养之间的猫》,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我喜欢他们的不必理我,不必讨好人,不必狎昵人,或相反的不需怕人,不需因莫名恐惧而保命逃开……他们只是如此恰巧地在生存环境中有人族存在,仅仅如此而已,人猫各行其是,两不相犯,你不吃我我也无需对你悲悯,有闲的时候,偷偷欣赏一眼便可。”
——朱天心
猫驯服了人类?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曾言:“人类驯服了狗,而猫驯服了人类。”若观诸人与猫狗在漫长历史上的复杂互动,这样的二分法自然略显武断,也是对于“驯化”概念的挑战,但它确实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同是人类最常选择的动物同伴,猫在人类心中的意义,和狗的确有着微妙的差别。若与第三章所述“忠犬护主”的人狗故事模型以及狗在文学中相对常见的“忠实”形象相较,猫在文学艺术中的形象不只复杂得多,更有趣的是,许多猫故事里往往还会显露出一种在人狗故事中罕见的近似爱情的迷恋。
许多创作者都爱猫,写出恐怖文学中最知名与令人难忘的猫咪形象《黑猫》的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爱猫人。猫不只扮演着缪斯女神般的角色,它们有时让人津津乐道之处甚至在于如何“以阻止/妨碍人类工作的方式,‘协助’人类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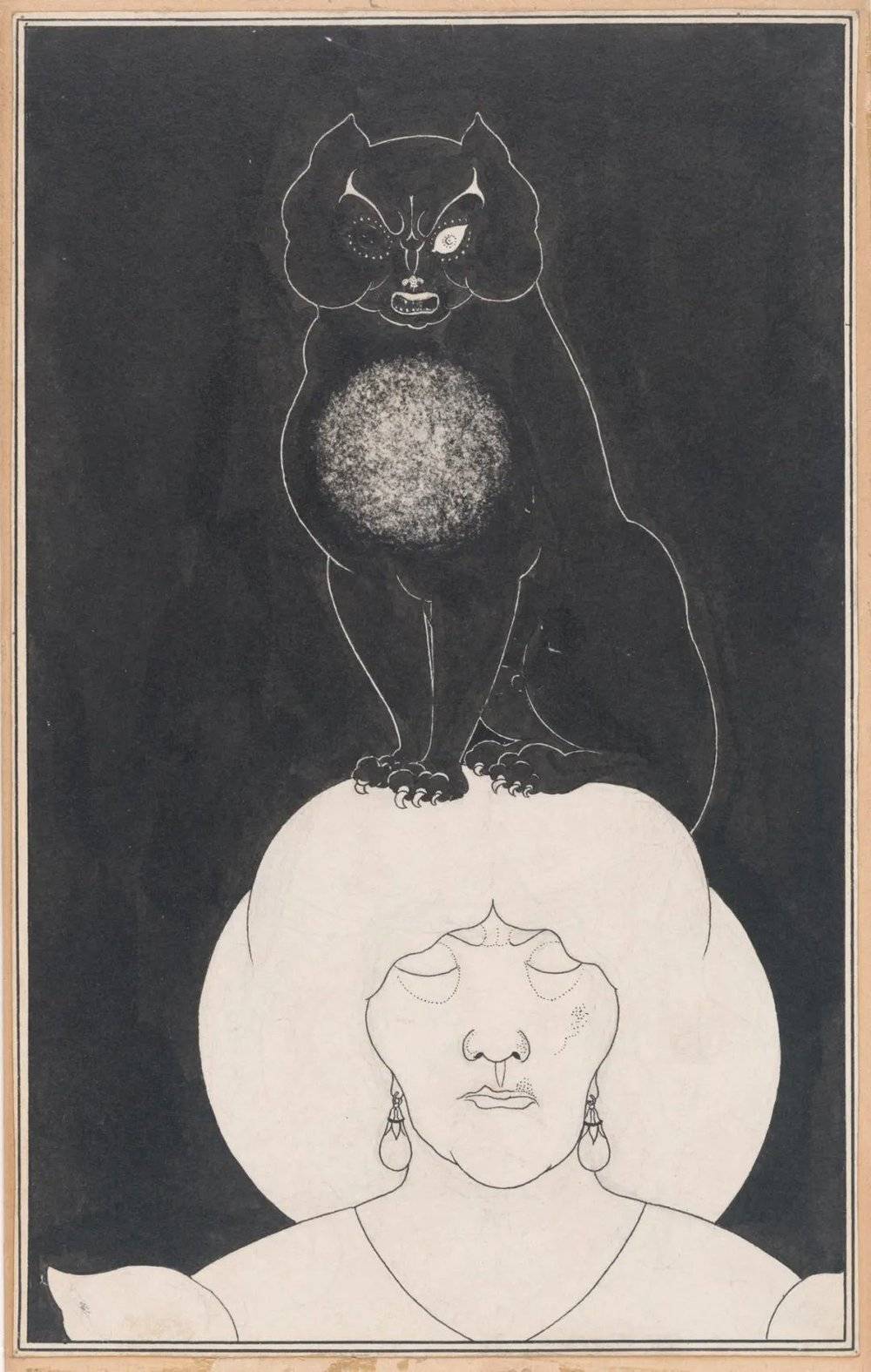
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就在信中描述他的猫是自己的“秘书”,这位秘书的角色如下:“通常不是坐在我刚用过的纸上,就是坐在我想修改的草稿上;有时它倚着打字机,有时也踞在桌子一角,静静看向窗外,好像想说:‘亲爱的,你在那里忙东忙西根本只是浪费时间。’”

无独有偶,其他作家对于爱猫的举动也有类似的描述与诠释,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表示:“我有时只要一坐近书桌,它就来我膝上坐。跟着笔杆来回摇晃,甚至出其不意,一掌劈下,划掉它不赞同的那几行。”另一位作家汉斯·本德(Hans Bender)则对于猫咪“小疯”把打字机旁的草稿扯碎的举动,充满爱怜地说:“我知道它专挑布满修改笔迹的初稿二稿,独独不撕完稿清样。真是善体人意的猫。”
在此种“猫咪永远是对的”的逻辑下,人仿佛放弃了他们要求狗所具备的那些忠实护主、牺牲奉献的特质,宁可牺牲自己的便利、时间与舒适,也不愿剥夺爱猫一丝一毫的生活乐趣或是惊扰它们的睡眠——如同传说中因为猫咪压在衣袖上,宁愿把衣袖割断以免打扰猫的穆罕默德一般。
观诸当代的人猫关系,似乎也证明了上述案例并非少数饲主一厢情愿的情话绵绵,猫在历史上尽管曾因被视为撒旦的化身,经历了惨酷的“猫大屠杀”,在文学艺术中似乎也难以完全摆脱邪恶阴森的形象,但它们那难以完全被人类驯服的野性,不把人类放在眼里的某种淡然,却虏获了无数人的心。从世界各地屡屡出现的猫站长、猫店长、猫馆长,都可看出猫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城市中微妙的人猫关系,日本的“小玉站长”、台湾的“黄阿玛”和香港的“忌廉哥”,就是几个为人熟知的猫明星之例。

猫不只以明星化的形象广受欢迎,这些“站长”或“馆长”的出现,最初虽然仍不免带着传统动物利用的功能性目的,希望它们发挥捕鼠的作用,但奇特的是,人和猫的关系中有一项在其他动物利用的历史里从未出现,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跨文化的状况,那就是订立猫的“工作契约”。李仁渊在《猫儿契》一文中,就举了一则元代出版的《新刊阴阳宝鉴克择通书》中的契约模板“猫儿契式”,正中央是猫的画像,契约内容围绕着画像由内而外以逆时针方向书写。兹引其文如下:
一只猫儿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长养,护持经卷在民间。行契××是某甲,卖与邻居某人看。三面断价钱××,××随契已交还。卖主愿如石崇富,寿如彭祖福高迁。仓禾自此巡无怠,鼠贼从兹捕不闲。不害头牲并六畜,不得偷盗食诸般。日夜在家看守物,莫走东畔与西边。如有故违走外去,堂前引过受笞鞭。某年某月某日,行契人某。
契约的两边则写上“东王公证见南不去,西王母证知北不游”。

这则契约是买猫之后所订,虽然以猫的角度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在非自愿状态下被人买卖的“被契约”,若未乖乖捕鼠还要“受笞鞭”,然而猫儿契真正不寻常之处在于,虽然“买卖牲畜动物都有相应的契式,但只有买猫独树一帜,不仅有画像、特别的形制、有行为规范,还需要东王公、西王母来见证。也只有猫儿契是放在需要特别阴阳知识的通书之中,在日用类书里被归为克择门。
猫儿契的契文本身是七言韵文,并写成螺旋状,具有术法的色彩”。中国传说认为家猫是唐三藏往西方取经带回来的,且能在寺院中护持经卷、伏恶降狞,或因如此,要请猫儿工作,还需要借助神灵与仪式的力量,“在人与所有动物的劳动关系中,只有和从佛国带来民间的猫要如此费心”。
不过,猫儿契在清朝之后相当少见,李仁渊遂下了这样的结论:“或许人类在历经数百年的失败之后,已经放弃了以文字或神灵驯化猫的尝试,束手为奴。”这样的看法仿佛呼应了莫斯“猫驯服人类”的说法,但事实上,猫儿契约既非中国“特产”也并未消失,而且似乎还朝着待遇更加优渥的方向发展。在19世纪的英国,每间邮局都可聘用几只“公务猫”,这几只猫必须“通过招募考试”,若灭鼠成效不彰,就“中断薪资给付”;美国在1900年前后,也有300只猫成为邮局的正式员工,邮局局长还需要撰写猫的工作成果报告(毕竟猫没办法自己写,虽然可能很多人会相信它们做得到)。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都有不少知名的“猫职员”,且经过正式聘请的程序,例如俄罗斯的猫咪图书馆员“库加”,每个月就有固定猫粮作为薪水;日本和歌山的猫站长“小玉”去世后,现在已有二代站长接班,还有实习生制度;就算未经过这些礼聘的程序,被收养的流浪猫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备受荣宠的睡在黄花梨双龙戏珠罗汉床上的博物馆馆长。至于街头巷尾一间又一间的猫咪咖啡、猫咪杂货数量之多就更不用说,手持猫地图按图索骥在小店或街角寻猫,也成了爱猫人与摄影师喜爱的城市行脚方式。
这些现象似乎不是用少数人“爱猫成痴”就可以解释的。猫究竟有什么让人情有独钟之处,使它们得到了某种确实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对待方式?但越来越多的猫咖啡、猫杂货,甚至猫街或猫村,究竟是“猫权高涨”的指标,或者反而显露更多动物“观光化”之后的隐忧?这是本章欲着力讨论之处。
以下将由几部以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特别的猫》、朱天心《猎人们》与刘克襄《虎地猫》,作为切入讨论的起点。借以观察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猫的天性如何成为争议的焦点;它们介于野性和驯养之间的特质,如何影响了与人类的互动模式;并以移动性的概念,带入城市空间中动物空间逻辑的新思考;最后则讨论日益兴盛的猫咪观光背后可能隐含的动物福利问题。
透过猫的眼睛看世界
多丽丝·莱辛《特别的猫》,可说是最精彩与经典的猫文学之一,不只写出了人对猫的情感,也生动地刻画了每一只猫独特的性格。其笔下自尊心强、骄傲的“灰咪咪”与另一只“黑咪咪”之间的互动充满戏剧张力,让读者充分感受到猫这种复杂迷人生物的魅力,确实如莱辛所形容的那般灵动美好:“若说鱼可算是流水的具体塑像,那么猫就等于是风的图饰,描绘出那难以捉摸的风的姿态。”
![作者: [英]多丽丝·莱辛 译者: 邱益鸿 <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https://i.aiapi.me/h/2022/11/09/Nov_09_2022_23_54_57_7796761727543019.jpeg)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但《特别的猫》之所以动人,并不在于莱辛对猫的礼赞,毕竟这样的主题几乎是大部分猫文学中的基调,而是她非常细腻地回溯了成长过程中和动物的关系,从而描绘出自身从非洲那样纯粹野性的世界,跨入伦敦这个足以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都会后,对于猫这种生物的理解和想象的变化,以及重新适应的过程。
当我们和莱辛一样,想要探问猫眼中的世界,并好奇它们在观察人们铺床、扫地、打包行李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其实也就等于参与了这场猫与人对“世界”概念的重新丈量:“每当灰咪咪一连花上半个钟头,望着在空中飞舞的尘埃时,她究竟看到了什么?而当她望着窗外迎风摇摆的树叶时,她又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象?当她抬头凝视悬挂在烟囱上方的月亮时,她眼中所看到的又是何种风景?”
都市猫灰咪咪的眼中,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这并非只是莱辛浪漫化的抒情提问,事实上,她确实试着透过猫的眼光去体验城市。当她带着灰咪咪和黑咪咪去结扎时,灰咪咪崩溃惊吓的反应,透露出窗外的车流对于一只猫来说,是发出轰隆怪声、黑压压的巨大机器。漫长的车程让莱辛得以“透过一只猫的眼光,去重新体验现实的交通状况,学到了崭新的一课”。城市猫的世界开启她对猫与自然关系的新观点,也打破了她曾经想要用非洲童年生活中那些理所当然的野地自然法则,来与都市猫相处的尝试。
事实上,灰咪咪并非莱辛饲养的第一只都市猫,当初她想要找的,是一只“坚忍顽强、性格单纯、要求不多,并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猫。……它得自己去抓老鼠吃,要不然就乖乖给什么吃什么……这些条件自然跟伦敦的环境毫无关连,而是我依照非洲的生活所定出来的”。
按照过去的非洲逻辑与成长记忆,没有人会为猫做“去势”手术,对于每年母猫频频生小猫的状况,基于“总得有人动手除掉这些多余的小猫吧”的理由,也被视为必要之恶;尽管这样的事情不代表执行的人会感到愉快,莱辛的母亲就曾经短暂地拒绝过扮演生命仲裁者的角色,但最终对于猫满为患的情况,她也只能“温柔地抚摸猫咪,并轻声哭泣”,在和心爱的猫咪道别后,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而且,就算这场原本可以避免的猫大屠杀让全家人都感到不安,将多余的猫“处理掉”仍然是非洲基本的生死法则。

但是,她很快发现,“都市猫的生活实在太不自然,它们当然永远也无法养成乡下猫的独立个性”,这只会等门、只肯吃“煮得嫩嫩的小牛肝和煮得嫩嫩的小鳕鱼”,最后却因为从屋顶上摔下来而不得不安乐死的猫,从日常生活到死亡,都冲击了她过去对于“我们的老朋友大自然”的想法。或者更直接地说,她终于发现非洲法则不可能适用于都市。
当城市文明提供了其他选项,依照过去的习惯把多出来的小猫“处理掉”就成为一种可怕的诅咒,在经历过一次“诅咒大自然、诅咒对方,并诅咒生命”的痛苦过程后,她终于“下定决心要把黑猫送去结扎,因为说真的,受这种苦真是太不值得了”。尽管她也曾经一度觉得把动物结扎是剥夺它们天性的可怕之事,但在都市法则的逻辑中,这仿佛也成为另一种“处理”的必要之恶。毕竟当生活的地点不再是充满掠食者的野外,但演化的速度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未同步,原先为了应付自然淘汰的生育量就显得缺乏调整的弹性,为动物进行违反天性的结扎也就成为都市法则中不得不然的某种妥协。
而莱辛对于“自然法则”的思考和挣扎之所以别具意义,是因为她恰好身处非洲和伦敦这两个位居自然/文明光谱两端的地方,价值观的差异遂带来格外极端的对比与冲击。但这样的矛盾并非只有在最典型的原始自然或文明城市中才会发生,家猫介于野性与驯化之间的特质,让城市中的人猫关系,必然面临如朱天心形容的:“人与野性猎人在城市相遇,注定既亲密又疏离的宿命。”
猫猎人的形象成为它们在城市求生的双面刃,既是猫族魅力的来源,却也承担了野生动物杀手的恶名。在都市空间和自然野性相遇时,该如何拿捏其中的距离?如果说,在数量控制、安身立命与“活出猫性”之间,如何取舍实无标准答案,透过朱天心的《猎人们》,或可充分理解此一议题何以艰难。
注定亲密又疏远的宿命
在《猎人们》一书中,我们时常可以感受到朱天心试图与猫保持“合宜”距离的努力。对于猫妈妈在生养小猫过程中的某种自然筛选与淘汰——那病弱的、跟不上母亲搬家速度的,总免不了在一胎中折损几只——她一方面用理智说服自己,对于食物来源有限的流浪猫来说,这是不得已的筛选机制,以便养活那最有可能顺利长大的一两只,故忍住不插手不介入;但另一方面,“真遇到了,路旁车底下的喵喵呜咽声,那与一只老鼠差不多大,在夜市垃圾堆里寻嗅觅食的身影,那直着尾巴不顾一切放声大哭叫喊妈妈的暗巷角落的剪影……看到了就是看到了,无法袖手”。
因为看到了,所以无法袖手。这看似单纯的大原则背后,牵涉到的问题却是超乎想象的复杂。首先,这“合宜”的距离出自人类单方面的想象,插手猫的生活,却又勉力维持一定距离,对猫来说也可能造成困惑,猫咪“花生”就是最好的例子。每逢猫猎人“花生”衔回蜥蜴,抢救心切的朱家人总以猫饼干换得她的松口,结果事情逐渐演变成“花生”想吃饼干,就打猎来换,朱家不堪这长期以物易物的交易窘境,决心除了定期喂食之外不再回应“花生”以其他猎物交换猫饼干的行为,冀望如此一来,就能“回到很多人家人与动物的‘正常关系’,冀望她不要那么在意我们(在意我们到底爱吃蜥蜴还是鸽子),冀望她能明白自己是一只猫,属于猫族”。
但这奋力维系的界线,却以“花生”跳窗出走几日后死在地下停车场黯然收场,让朱天心不得不猜想是否正因为她们不再与它进行“好吃又好玩”的交易游戏,才让它受创离去。除此之外,每一次带猫去结扎,也都要经过一番心理挣扎,之后总是几乎毫不例外地“后悔剥夺掉她那最强烈的生命原动力,这漫漫无大事可做的猫生,可要如何打发度过”?但是“一以便空着配额给那总也捡不完的小野猫;二是如此公猫才不致为了求偶而跑得不知所终,回不了家”,即使内心矛盾,却又似乎是不得不为之的“必要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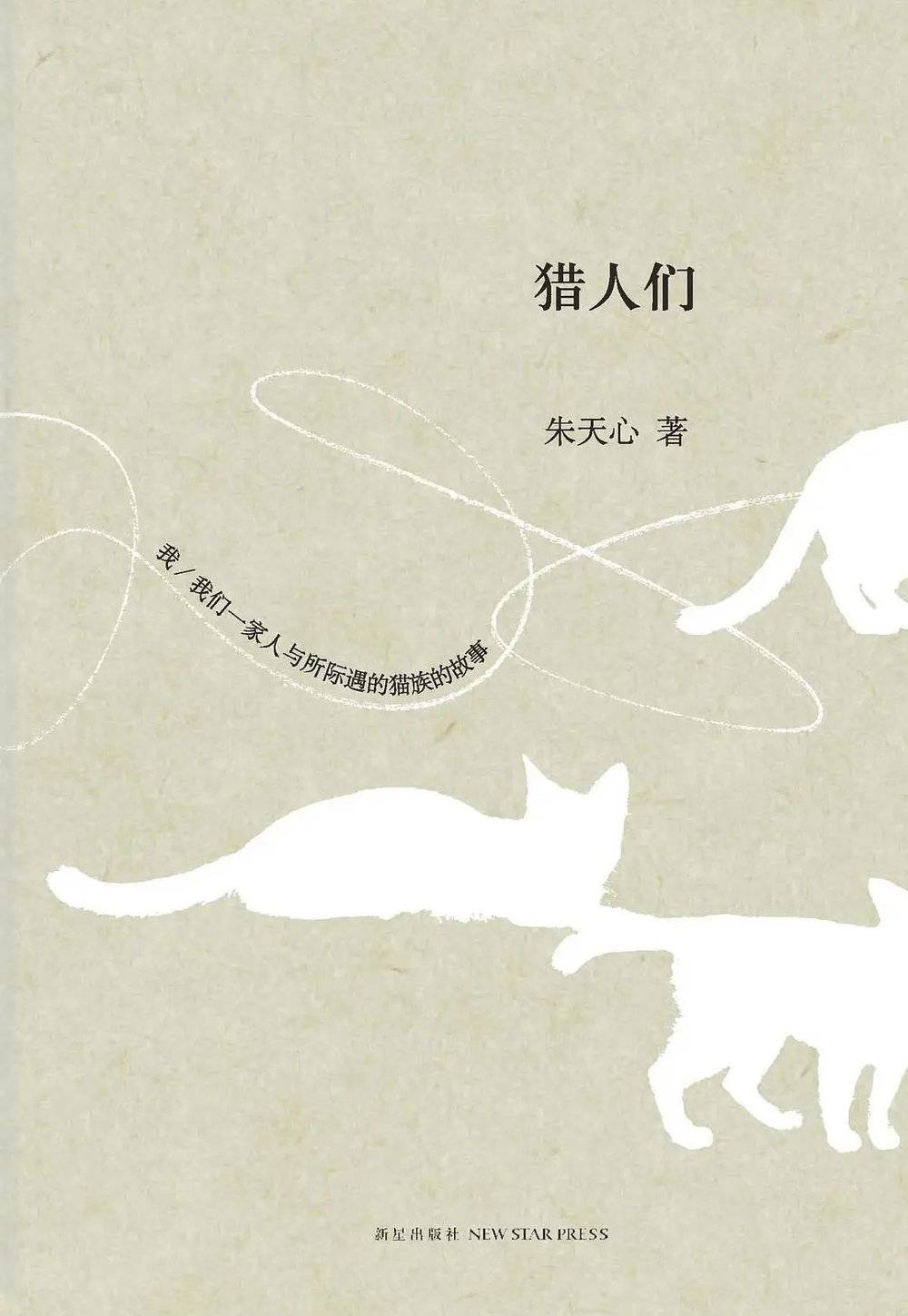
出版: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另一方面,因为介入,因为插手,猫族也可能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地“丧失天性”,例如那些“只要爱情不要面包”的猫,因为爱上了人,日日衷情守候,等待着撒娇拥抱的时刻;(幸运些的)索性进入家庭,认同于人,最后连猫族视为家常便饭的跳跃本能都逐渐失去。对这些猫族赋予的信任与亲爱,朱天心感动骄傲之余,心情却是复杂的,因为这在在说明了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介入和决定,都可能改变一只猫的命运。
我们认为动物应该“活出本性”(flourish),如同本书《导论》中曾提及玛莎·努斯鲍姆的伦理学所强调的,“如果我们承认,生命不只涉及快乐与痛苦,道德的考量也根本不应该局限于此,我们就会意识到,让一个生命尽其本性、以其应有的方式运作、发达,乃是一件具有道德意义的‘好事/价值’”。但是“各种动物的生活要如何才算‘尽性’、动物生命如何才算按照其应有的方式运作,从而我们应该保障动物的什么能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如同绝育放养的街猫,它们既有猎人的天性,却又已被人类半驯养,自然与文明的界线模糊在这类动物身上可说充分体现。“本性”既已难定义,让生命体都能活出本性的理想在落实上的困难,更由此可见一斑。正因如此,种种界线与距离的拿捏,其间的分寸得失,遂显得格外犹疑与艰难。

那么对朱天心来说,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动物空间?她曾以东京镰仓江之岛的状况为例,形容心中的乌托邦:
我喜欢他们的不必理我,不必讨好人,不必狎昵人,或相反的不需怕人,不需因莫名恐惧而保命逃开……他们只是如此恰巧地在生存环境中有人族存在,仅仅如此而已,人猫各行其是,两不相犯,你不吃我我也无需对你悲悯,有闲的时候,偷偷欣赏一眼便可。
无论此种人猫“各行其是”的空间是否带着观光客凝视下的美化,都可看出在这个理想图示的背后,核心精神仍是让猫带着一定程度的本性,与人共享生活空间。但这样的愿景若将其他动物一并纳入,“猫猎人”的身份就可能转变为威胁野生动物存续的“生态杀手”。
猫对野生动物造成的危机究竟有多大?关于这个国内外争议许久的问题,始终没有共识,而且看似单一问题的背后,其实还缠绕着诸多态度分歧的争论,遂让状况变得更为复杂。包括:我们如何看待猫(狗)的驯养过程与饲养方式?TNVR是解决城市流浪动物的最佳解吗?猫狗是外来种吗?若它们是外来种,移除就是把它们“处理掉”的唯一或优先选择吗?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歧异,都会影响最后的态度与结论。
更重要的是,一只在野外活动并捕杀了野生动物的猫,可能代表着从小就在野外出生、乡间放养的习惯、不当饲养与弃养、认为猫应该活出野性而刻意放养、TNVR后再原地放养等各种迥异的原因,每项成因需要对话的对象与解决方式都不相同,换言之,若将其一概而论,回推给部分爱动物人士“任由猫狗在街上撒野”,并以“爱它就带它回家”作为流浪猫狗问题的终极方案,恐怕仍是无法触碰核心、过度简化的想法。

此外,在讨论这类问题时,物种的差异、环境的区隔、个体的状况,也都必须考量进来。刘克襄就曾以自己在香港岭南大学进行猫观察的经验指出,他所观察到的猎杀,对象多半是生病或刚出生不久、缺乏经验的个体,而猫和狗的猎捕状况也会因区域而有所差异:
假如我今天谈的是野地的流浪狗,很可能就无法以都市的流浪狗看待。流浪狗在围捕时,常常有一策略性的围捕,譬如捉浅滩的鱼,一只狗会在这头赶,其他的在另一边埋伏。……这种狗的围捕策略在猫身上就很难出现,或者说猫不像狗,一只狗如果跑进了养鸭的环境里面,它可以一天内把全部的鸭子都咬死。那猫会不会呢?或许在鸟笼里,它有可能,在野外环境恐怕不易。……这是非常区域性的,必须透过很多调查和访问来了解。或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猫跟狗往往有领域性和区域性的,它不可能随便到一个地方就贸然猎捕,它们要移动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要面临到很大的变动,这种情形下应该以个案讨论为宜。
但另一方面,就算基于关怀不同物种的优先序,也并不见得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担心街猫伤害鸟类,与担心街猫在外遇到路杀或虐杀的风险,可能都会导向同意猫应尽量豢养在家中,选择TNVR之后尽可能送养的途径。毕竟对于许多猫志工来说,牵挂自己喂养的猫在街上遭遇风险的心情,可能如同朱天文所形容的:“犹如人质的家属,每只街猫都是猫质。”但因为每个选择的背后,都勾连着不同的原因与价值观,讨论与对话始终如此困难。关于猫猎人究竟是否为生态杀手、又该如何解决的质疑与争议,也就注定在人、猫、狗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共存的现实空间中,持续下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 (ID:sanhuibooks),作者:黄宗洁(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博士,现任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编辑:艾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