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仅三岁时,亚当·斯密就曾遭遇惊险。他被一群流浪的吉卜赛人掳走,家人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才将其找回。约翰·雷曾绘声绘色地讲述斯密走失的故事。“一群过路的吉卜赛人偷了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一直找不到他。忽然有一位绅士说他在几英里外碰见了一个吉卜赛女人背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巡警立即出发……他们在莱斯利森林找到了那个吉卜赛女人。女人一见到巡警就把孩子扔下逃跑了,最后孩子被带回母亲身边。”
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是少儿斯密的历险,更是现代思想与文明的历险。杜格尔德·司徒尔特是斯密的朋友,他对这次救援大加赞赏,因为它“为世界保住了一个天才,他命中注定要扩展科学的边界,并为欧洲的商业政策带来新的启迪和改革”。
然而,对英国学者杰西·诺曼而言,这个故事更像是一则寓言。他在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重写斯密传。他对斯密生平的讲述以其走失为起点,仿佛要告诉世人:在今天,斯密又一次被偷走了,我们需要再一次启动搜救行动,把他找回来。只不过,这次的偷走斯密的是每一个误读斯密的人。

杰西·诺曼
一
在阐述亚当·斯密的思想前,杰西·诺曼意味深长地谈起矗立在爱丁堡街头的斯密像:“今天,如果你沿着爱丁堡老城的皇家大道,从修士门外亚当·斯密故居往上,向海关大楼的方向走,你会经过两座伟大的雕像。第一座是由公众捐款集资建设的亚当·斯密雕像,高大而光辉,矗立在圣吉尔斯大教堂外。他的身后是一把旧式犁,身旁是一个蜂巢,象征着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他的左手捏着长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时间的学术生活。他的右手不怎么显眼,也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搁在一个地球仪上,委婉地提示着观众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野心和世界性的声誉。”
另一座“伟大雕像”是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塑像。它们都是英国当代艺术家亚历山大·斯托达特(Alexander Stoddart)的作品。斯托达特当然没有见过斯密,也无从知道斯密的真实面貌,因为斯密没有留下任何画像。他只能根据世人想象中的斯密身影进行创作,刻画出人们心目中的斯密。
所以,这座雕像是当代人心灵的投射,呈现了今人对斯密的理解。杰西·诺曼解释了长袍、地球仪、旧式犁和蜂巢所代表的隐喻:这些符号暗示了他的哲人身份、世界声誉,及其时代背景。隐藏起来的右手则象征着他的哲思——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如果把其他符号都撤掉,仅仅保留这只“看不见的手”,我们就能把他认出来。对现代人来说,“看不见的手”不只是一种修辞,它甚至变成了一种信仰或意识形态。
杰西·诺曼试图告诉我们,斯托达特的塑像展示了斯密及其学说在当今世界的处境:他被高度符号化了,其思想的真实面貌反而受到遮蔽,变得朦胧模糊。由于《国富论》的盛誉,斯密被人广泛征引和利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声称受到了斯密的影响;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现代经济学分支,从新古典主义到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最近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都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学说。”
在杰西·诺曼看来,此类征引方式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旨在利用斯密来“美化和修饰自己的信仰或论点”(155页)。各派学者从各自立场出发,以各自的方式重新解释斯密,却很少本真地理解斯密。于是,在两个多世纪的思想再生产过程中,人们制造了许多关于斯密的“迷思”。这些“迷思”织成一张巨大的尘网,封盖了斯密思想之本色,令我们越发严重地远离、误解亚当·斯密。
杰西·诺曼归纳了五大迷思:亚当·斯密难题、亚当·斯密推崇自私自利、亚当·斯密为富人说话、亚当·斯密反对政府、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的首要身份。实际上,这五大迷思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将之概括为一个神话,即“看不见的手”神话。它道出了世人对斯密的信仰,或刻板印象:他是一个捍卫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哪怕在这个自由市场里,行为人以自利为原则,竞相追逐财富,制造极端的不平等,斯密仍然要捍卫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
与之相伴,人们还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逻辑基础是“看不见的手”,斯密的最大贡献便是为世人阐明了这只手的作用。所以,世人对斯密的信仰亦即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人们因而相信,“看不见的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引导自私自利的个体在自由市场中实现秩序与公共利益。当然,斯密的批评者也持有相同的刻板印象,认为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始作俑者”。对于亚当·斯密,他的信徒与敌人分享了同一个神话,持有相同的符号化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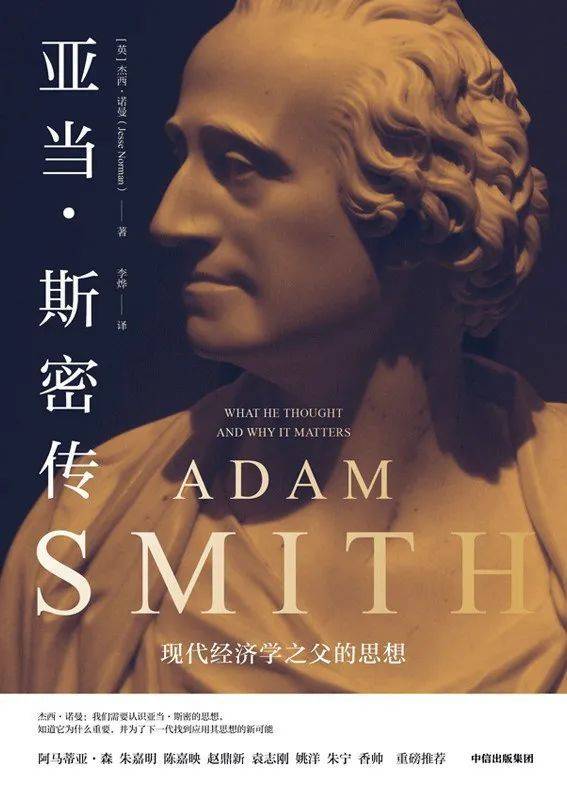
杰西·诺曼著《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二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斯密的符号化认知也折射出他们对经济世界的抽象化理解。杰西·诺曼至少两次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言论,旨在展现当代经济学对斯密的误解,以及经济理论的自我封闭和对具体现实的漠视。弗里德曼致力于将经济学塑造成一门科学。在一九五三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他向其批评者发出挑战:“关于一个理论的‘假设’,要问的相关问题不是这些假设在描述上是否足够‘现实’,因为它们从来都不是现实的,而是这些假设对眼前的目标来说是否能够提供恰当的近似值。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看这个理论是否有效,也就是看它是否能产生足够准确的预测。”
弗里德曼强调,对经济理论而言,“准确预测”的效力比准确描述现实更重要。他无疑认为,经济是一个可以孤绝于其他事物的独立场域:经济有自己的法则,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学也应该成为一门科学。这种科学化的努力很容易忽视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因素,对此,杰西·诺曼不无感慨地评论说:“弗里德曼的挑战表达了他对经济学的宏大期望……但这也起到了转移注意力的效果,使人们不再关注需要研究的市场的具体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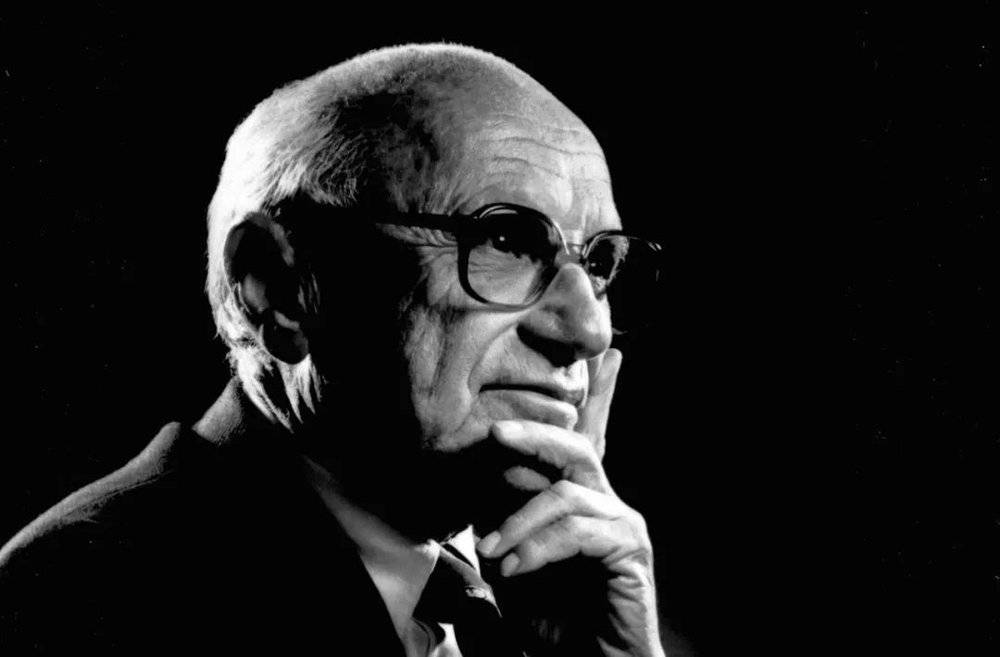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来源:bing.com)
经济学的科学化正在让自身变成一个封闭且抽象的理论系统。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现象是人们对市场的理想化认知。在经济学理论中,“有效市场假设”影响深远。“有效市场假说”将金融市场视为市场机制的完美典范,也完全展现了经济学的市场理想。这一理念相信,只要拥有足够充分的自由,市场就能孕育足够丰富、健康、强大的经济。
究其本源,经济学的科学化目标及其市场理想都立足于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当思想盲从“看不见的手”时,理论便走向自我封闭,漠视并远离现实。思想的盲从将导致政策的盲从,政策的盲从则可能导致社会危机与灾难。
杰西·诺曼认为,究其本源,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思想和知识的危机。“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因为银行业存在有效竞争,所以使放松管制成为可能,并且放松管制可能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这构成了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的关键知识背景。回想起来,那场危机的惊人之处,甚至不在于那之前的十年银行系统令人发指的贪婪自利,也不在于相关政策、法律和执行方面的具体失误,而是自由市场的语言已经对几乎所有方面达成了思想控制,哪怕现实往往非常不同。”弗里德曼和“有效市场假设”都将其理论源头追溯到亚当·斯密。所以,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亚当·斯密不可避免地成为民众发泄怒火的对象。杰西·诺曼忍不住为斯密叫屈:人们对斯密的“迷思”与其真实想法相去甚远,甚至扭曲、背叛了他的思想和精神要义。
杰西·诺曼反复强调斯密学说的经验主义色彩,突出其现实视野。对于市场,斯密也采取了极为务实的态度,从未怀有教条化的乌托邦式信念。“他是一个务实的而非理论化的,具体的而非乌托邦式的,归纳型的而非追求普世规律的理论家,他关注的是具体的补救措施,而不是最大和最小的问题,也不追求一刀切的办法。他对市场是如何出错的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亚当·斯密对市场的局限性也有深刻的洞见,这表现在他对重商主义的著名批判:商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独占倾向,拥有知识优势,洞悉生产与贸易。商人有能力欺骗、捕获国家权力。所以,如果放任市场自由,“裙带资本主义”必将大行其道,商人将主导国家立法,利用政策制造垄断,赢取暴利。社会将陷入不义之境。
于是,贫富分化加剧,阶层矛盾激化,社会将走向分裂和衰落。所以,斯密赞成的“自然自由体系”并不等同于自由放任,亦非让人们为所欲为。它对市场行为人提出了道德上的规范要求,也对政府立法提出了自然正义的规范要求。
针对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杰西·诺曼援引了《国富论》对一七七二年艾尔银行破产案例的分析。在那里,斯密强调了金融市场的内在风险,以及审慎银行政策的重要性。关于激进的自由放任主张,斯密评论道:“可以说,限制私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接受银行家的期票,无论金额大小;或者在他们的邻居都愿意接受时限制银行家发行这种票据,这些限制就是对自然自由的人为侵犯。法律的天职本应该是支持人们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但是,如果少数人行使自然自由权利可能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的话,那么他们都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这种限制与政府是自由还是专制无关。这就如同为了防火而建立防火墙一样,(防火墙)也是对自然自由的侵犯。这里谈论的关于银行业的监管是一样的。”
杰西·诺曼不免感到遗憾:斯密的信徒背叛了斯密,直到二〇〇八年,金融业也没有建立自己的“防火墙”,决策者们甚至丧失了建设“防火墙”的现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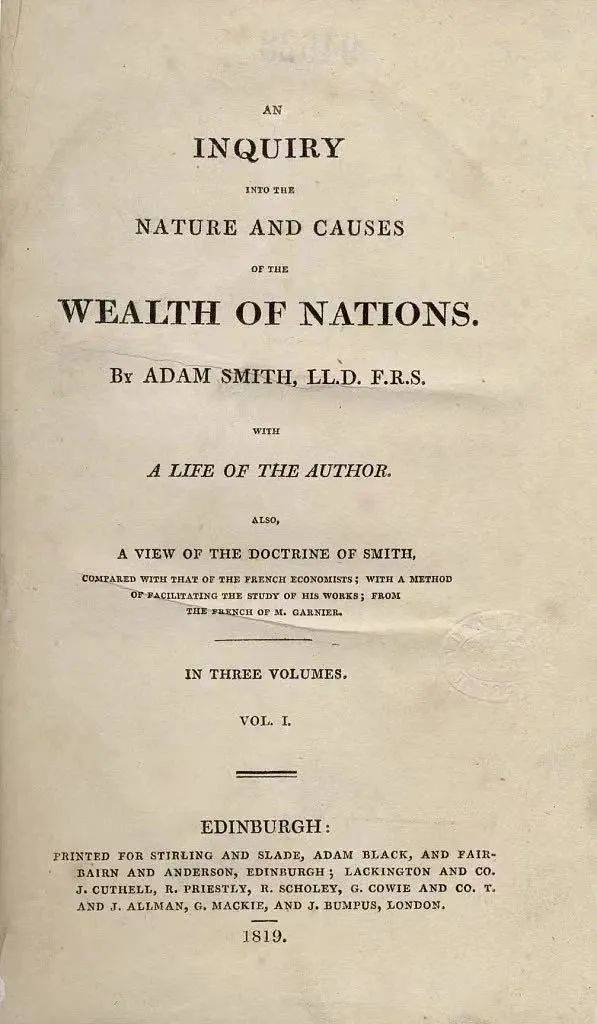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来源:wikipedia.org)
三
关于斯密的经济意识形态封闭了世人的心智,既使我们误解斯密,也阻止我们正确理解现实。既然“斯密迷思”已经成为影响政策,塑造现实世界的理念力量,那么,破除迷思,本真地理解斯密就不只是一个思想史课题,也是重建秩序的行动。
行动的第一步便是找回斯密思想的底色,回归其道德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一思想底色和基本框架就是“人的科学”。杰西·诺曼强调,斯密是培根和牛顿的精神后裔,其学说也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亚当·斯密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建立了自己的‘人的科学’,他借鉴了培根的许多基本假设。像培根一样,斯密也希望构建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理论。事实上,他的野心似乎是,对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包括道德、社会、艺术、政治和商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叙述。”“人的科学”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涉及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从表面来看,斯密的两部著作分属不同的领域(一为伦理学,另一为经济学)。但实际上,它们同属一个理论体系,由同一个逻辑链条连接起来。
按照斯密自己的讲述,他致力于阐发的道德哲学包括伦理学与自然法理学两大分支,而自然法理学又涵盖了政策、岁入、军备等法律对象。《国富论》是对斯密“立法者科学”的阐发,部分实现了斯密写作自然法理学著作的承诺。正义问题则将《道德情感论》与《国富论》勾连起来。“同情”的道德心理机制也为其伦理学与法理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赋予了共通的人性基础。
所以,在斯密的理论体系里,经济学并非一个孤绝封闭、自在自为的领域,而是附属于法理学与道德哲学。在斯密看来,必须结合道德规范、国际情势、国家法律,乃至文明法则来理解经济问题。
所以,经济学必须走出完全抽象的理论沉思,走入现实的生活世界。斯密的理论思考一直保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与此同时,斯密又独具慧眼,能从现实的纷争当中看到秩序的永恒基础,葆有对道德与文明的信心。斯密没有逃避现实社会的冲突与战争,他的心灵对现实世界保持充分开放与关注,没有无视人性中的自私与邪恶。
但是,他也看到,无论人们如何自私,我们都能突破自己,对他人的苦乐感同身受。这份“同情”与恻隐之心正是道德与文明的根基所系。他致力于解释真实的历史与社会,细致入微地分析人类的真实情感,从中发现永世不易的道德法则,向世人展示秩序与文明的机理。所以,他的道德与文明信念接受了现实的检验,也因此具有强大的力量。

亚当·斯密画像(来源:bing.com)
杰西·诺曼写作的斯密传记尤为看重斯密平生经历的叛乱、战争或革命。在杰西·诺曼笔下,斯密的一生与“联合王国”(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的国家建设和殖民扩张历程相伴相随。初生的联合王国历经战火方才巩固政权,通过争夺才“不经意地获得了全世界”。所以,斯密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战乱、纷争不息的世界。战争的意象必然会渗入其理论思考,成为其道德哲学必须回答的重大挑战。因此,斯密才要修改弗兰西斯·哈奇森的社会性理论,并将军备与国防当成最重大的法律问题之一。
杰西·诺曼将斯密的一生分成五个阶段。在斯密人生的每一阶段,英国几乎都经历了重大的战事。一七二三至一七四六年,亚当·斯密由“柯科迪男孩”成长为牛津毕业生,完成大学教育。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经济充满了“混乱与不确定”,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多有纷争。一七四五至一七四六年,联合王国还遭遇了最后一次詹姆斯党人叛乱的冲击。此间发生了残暴的卡洛登战役,王军对叛军大开杀戒。
一七四六至一七五九年,斯密回到苏格兰,先在爱丁堡讲授修辞学与纯文学,后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并出版了《道德情感论》。一七六〇至一七七三年,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巴克卢公爵的家庭教师,陪伴公爵游学欧陆。自欧陆返英后,斯密一直与巴克卢公爵保持密切交往,每年都会去爱丁堡达尔基斯城邦探访公爵。
一七七三年,巴克卢公爵投资的艾尔银行倒闭,斯密帮助公爵处理了善后工作,并在《国富论》中分析了银行倒闭之因由,力主银行应当采取审慎保守的放贷政策。七年战争(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横跨了这两个阶段,它波及欧洲四国(英法及其盟国)和四个大洲。这场战争意义重大,举世关注,斯密定然不会无动于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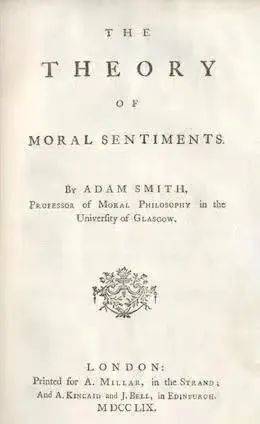
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感论》(来源:wikipedia.org)
一七七三至一七七六年,斯密旅居伦敦,与约翰逊博士俱乐部成员交游,完成并出版《国富论》。在此期间,伦敦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一七七五年,美洲独立战争爆发。一七七六年,《独立宣言》签订。《国富论》于同一年出版,并用了大量笔墨分析美洲殖民地的由来、动乱之因由,以及化解帝国危机之对策。
一七七六至一七九〇年,斯密先后送别了好友休谟与母亲玛格丽特,最终与世长辞。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斯密一直在工作。在此期间,他致力于《道德情感论》与《国富论》的反复修订与再版,也参与了一些海关事务。这十二个年头里,英国与欧洲难称太平,发生了许多大事。一七七八年二月,美国取得萨拉托加大捷。一七九二年,美国军官约翰·保罗·琼斯率领法国中队击毁英国护卫舰,并差点在爱丁堡登陆。美洲独立引发了爱尔兰的动乱。法国政局形势紧张,大革命一触即发。斯密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这些大事件,并在修订著作时融入他最新的思考。
对此,杰西·诺曼评论说:“在抨击重商主义制度时,《国富论》也不避讳以美国独立战争的时事举例,而在阅读《道德情感论》的修订本时,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杰西·诺曼想要告诉读者,斯密的理论思考植根于他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与深刻思索。斯密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务实色彩,如果忽视了他对现实经验的重视,我们必将误解他的学说。不仅如此,斯密生活的时代既是贸易的时代,也是战争的时代。“贸易之忌”(the jealousy of trade)汹涌翻腾,影响人的心灵,左右着国家政策。斯密批判“贸易之忌”,必然对它洞察分明,不会幼稚地认为贸易会自然而然地造就和平,生成秩序。
对他来说,“看不见的手”是一种修辞,意指最底层的自然秩序——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理性。“看不见的手”确实存在,但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它需要哲人和国家的帮助:哲人通过对历史与自然的思考,发现并阐发“立法者科学”;主权者则遵照“立法者科学”之要求,采取行动,纠正错误,化解危机,守护秩序。斯密兼具哲人的智慧与史家的敏锐,他的思想也兼有哲学与史学的特质。
我们误解了斯密,我们丢失了斯密,我们迷失了自己。在这个后危机时代,政治经济世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斯密则是帮助我们顺利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斯密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指引呢?他的著作告诉我们:市场复杂且有局限,商业社会有其道德基础,文明与秩序需要国家智慧。除此之外,他的一生也能够给我们启发:他的理论思考始终对社会现实保持开放,从未让自己陷入某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泥淖。杰西·诺曼仿佛在向我们发出号召:把斯密找回来,重返他的著作,获得他的现实视野。“今天,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极端主义和误解的世界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亚当·斯密,以及将他的思想贯彻到底的智慧。”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英]杰西·诺曼著,李烨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康子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