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港书评(ID:jbsgsp),作者:谈炯程,编辑:伍岭、罗婉,题图来源:《蜘蛛侠:纵横宇宙》
近期,《蜘蛛侠:纵横宇宙》(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Verse)在美国及中国内地上映。这部电影不单以其绚烂、精细的动画技术取得了喜人的票房成绩——美国上映当日,即登上2023年美国首映票房榜首,也同样以它的方式回应超级英雄电影的诸多母题。

《蜘蛛侠:纵横宇宙》海报
不熟悉美国漫画的中国观众,大抵把超级英雄看成一种晚近的现象:我们是在那厚重如一个个无眠之夜的液晶电视前,第一次看到托比·马奎尔饰演的那版蜘蛛侠,贴近看,你就能看到凸起的屏幕上的那些色彩点,正是它们拼合出了托比的形象。如今在人们适应了4K曲面屏的眼睛里,那个形象带有世纪初特有的粗糙与模糊,拓入了我们的记忆:一个平凡人,心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箴言,踟蹰在他的世界里,但他不得不承受生离死别——因为他的私心,他的叔叔班·帕克死于一次抢劫。
不过,其实蜘蛛侠已有将近80年的历史,他由斯坦·李与史蒂夫·迪特科共同创造,首次亮相于1962年8月的《惊人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超级英雄原本单纯的故事变得愈发复杂,各个角色之间逐渐形成一个系谱:这大抵是商业文明的要求,漫画本质上是文化工业链条中的一个产品,因此,串在一起,形成系统的产品可以更快地投入再生产;但这同样也是叙事自然生长的结果,就像溶洞中滴下的露水,早晚会结成乳牙般的钟乳石。
超级英雄与超级恶棍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神话,它不像旧有的神话一样,只在人间以及作为人间复本的神界发生,重叠的空间成为这新神话的基本场景:要么是无数如培养皿般一字排开的平行宇宙,要么像战锤,在凡世之外,还有一个完全异质的亚空间。这样的空间意识,或许只能在网络世代找到它的基础。网络打开了一种空间意识,让人在其中被化约为一个又一个节点。而对多元宇宙的想象,正是这部最新的蜘蛛侠的关键。
在时间的分枝中生长
1941年,由阿根廷文化处举办的三年一度的国家文学奖评比正在进行。一本古怪且难以定义的小书被摆在了评委们面前。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异域的颓废之作”,处在“幻想故事、做作而深奥的博学和侦探小说之间”。这部书名叫《小径分叉的花园》,作者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它最终落选,当年的一等奖,由一部关于阿根廷牧人的小说获得。
博尔赫斯很看重这部小说,因为它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部真正的叙事作品。博尔赫斯以诗歌见长,在写作《小径分叉的花园》之前,他的小说往往由一些精细、微妙的速写构成。但这篇作品,却是布局严密的侦探小说。
小说的核心是博尔赫斯关于时间的沉思,这沉思经由小说角色英国汉学家艾伯特说出,不过其最初版本却归属一个虚构的中国文人崔彭。他放弃云南总督的高位,抛妻弃子,甚至放弃他赖以维生的知识,只为写一部容纳无限的小说。有时,他也宣称他要建造一座迷宫,但他死后留下的荒凉宅邸中,却没有一块砖石属于这预言中的迷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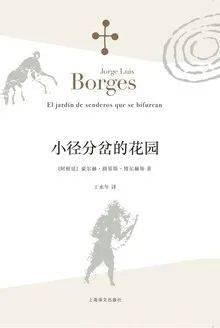
《小径分岔的花园》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著 王永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崔彭的迷宫,并不像米诺斯王在克里特岛上兴建的迷宫一样有形:在那里,探险者们要面对的危险是极为显豁的,他们只需要打败迷宫中央那头嗜食人牲的米诺陶诺斯,只需要用上线团标记自己的行踪,就可以征服这座爱琴海世界最大的迷宫。但崔彭的迷宫就是他那看似散乱的小说手稿,它不单单由文字堆砌、修葺而成,构成这迷宫的真正材料,是时间。
不过,崔彭的时间亦并非经典物理学的线性时间,在线性时间中,人的行为由一个又一个必然性串联起来。当他必须做出选择时,他的选择早已注定,不可回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崔彭的迷宫却是在每一个主体做出选择的时间点分叉开来,它有着没有终点的枝繁叶茂,就像一顶永不停止生长的树冠。
这会是蜘蛛侠们生长的世界吗?存在一个主宇宙,那是最先由斯坦·李创造出来的宇宙,同样,也存在一个被称为“现实世界”的宇宙,在这里,蜘蛛侠是一个永恒的拟像,只以电子的形式被星散在网络空间里。
在《蜘蛛侠:纵横宇宙》中,这些空间仿佛抱在一起的一瓣瓣橘子,当彼此之间的隔膜被打通,人们就会发现,即使蜘蛛侠这样的超级英雄,即使他们来自不同的平行宇宙,他们的性别、族裔也各不相同,他们却也同样被锁在一条固定的时间线上,经历生与死的永恒轮回。
英雄在我们时代的宿命
博尔赫斯在时间之上构架起他的多元宇宙,他的宇宙关乎偶然性,即使最糟糕的可能也会被容纳,故而这多元宇宙的确是通向无限的,从他最微小、孱弱的根系,不断地攀向无尽的天空。
但作为文化产品,蜘蛛侠不能容忍主角陷入彻底的失败,因为失败就意味着产品的终结,就像百年前的英国读者不能容忍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死亡一样,一旦一个角色被纳入大众文化场域,它就不得不接受商业逻辑的规制。《蜘蛛侠:纵横宇宙》在技术上足够绚烂,它的视觉效果,让粉丝联想起美国漫画的黄金时代。
不过,即使是真人出演的超级英雄电影,它们的开头也必然保留着翻动漫画书的快速镜头,这显示出它们来自一个足够有凝聚力,同时也足够开放的传统。美国漫画不同于日本漫画,它们更倾向于成为图像小说,依赖人物对白讲故事。同时,美国漫画更长的连载间隔,更多的制作人员,更充裕的资金,使得它们可以在画风集极精细、写实之大成。进入电影电视的时代,相较日本漫画,它们也更适合改编成真人出演的版本。
正因为在进入影像化之前,诸如蜘蛛侠之类的超级英雄,已经有了深厚的积淀,乃至形成一种角色惯性。故每个时代,都竭力洗去角色身上前一个时代的浮渣。托比的蜘蛛侠就不是斯坦·李笔下的天才科学家,而是一个普通高中生。
在那个著名的场景中,他挡住列车头,用蛛丝拦住正在坠落的列车,蛛丝在他身后一根根绷断,他的战袍也撕裂,他的面具早已脱落,当他最终停下列车,他甚至因脱力而晕厥。列车上的幸存者看见了他的面貌,他们发现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甚至比他们更平凡,于是他们为他戴上面具,为他隐瞒下他的身份。经由面孔的赤裸,他下降为人,而面孔再次被遮蔽,让他抽象成了一个符号,简言之:一个英雄。

正如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神迹一样,我们也失去了英雄,天空变得更高,更不可接近,大地缄默,不再献出它的隐秘。英雄意味着非人性的高贵,向死而生的绝对意志,就像阿喀琉斯与赫克托耳,亦如消逝于历史中的游侠。
超级英雄,有时会沦为与神圣失去连接的时代里的一次漫长的幻肢痛:当它莫名地要像希腊半神一样,超脱于人性时,它就会变得荒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热爱蝙蝠侠、钢铁侠、蜘蛛侠一类的角色,英雄在我们时代的宿命,就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港书评(ID:jbsgsp),作者:谈炯程,编辑:伍岭、罗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