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2020年出版了新书《浮沉世纪》,描绘了美国125年间的历史钟摆现象(“我”-“我们”-“我”),对理解美国历史与今天颇有启发。而在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来回摆动,既是美国的文化周期律,也很有可能具有他山之石的启发。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3年6期,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陈雪飞,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陈雪飞:百年历史的钟摆运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让你描绘当下的美国,它是什么模样?经济发达、科技领先,美国人享有前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物质富足、教育机会和个人自由,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党派极化愈加严重,种族问题持续恶化,经济与政治权力交叠缠绕,很多普通人深陷“绝望之死”的困境。这幅美国浮世绘,其实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其收官之作《浮沉世纪》(与谢琳·加勒特合著)中,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镀金时代”美国景象的描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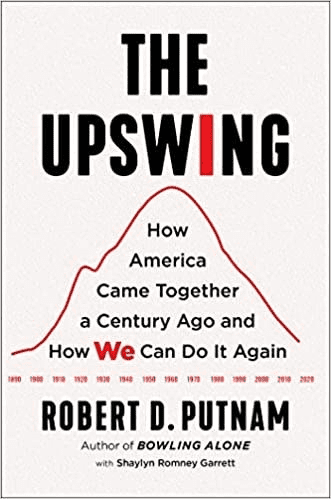
罗伯特·帕特南《浮沉世纪》英文版
是的,美国的当下与之高度相似,不少学者因此将当代美国称为“新镀金时代”,并力图探究其成因。美国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失灵,尤其是共和党对经济议题操控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法学者吴修铭主张,是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反垄断措施走上错误的轨道所致;劳工运动组织者简·麦卡利维则归咎于美国当代社会运动追求的利益太狭隘、目光太短浅,失去了“伟大社会”时期的群众力量,无力推动有意义的社会变革。
尽管归因不一而足,但大家有个共识,那就是美国在六十年代走上“伟大社会”的巅峰,远比“镀金时代”经济更平等、政治更协同、社会更团结、文化更包容,而在那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变得更不平等、更极化、更支离破碎、更个人化,最终走到了第二个“镀金时代”,酿成了当下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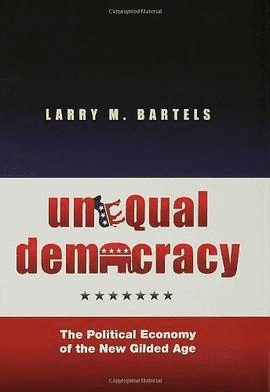
拉里·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英文版
帕特南对“新镀金时代”的研究颇有些与众不同,为了防止人们沉湎于怀旧,他跳出了对二十世纪美国历史的传统叙事,不再把新政和“二战”作为分界线,而是拉长了历史视角,拓展了分析维度,放眼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一百二十五年,品味美国一个多世纪的浮浮沉沉,寻找让美国重回“伟大社会”的涅槃之路。
在这段世纪浮沉中,十九世纪末与当下首尾相顾,进步时代(一八九〇至一九二〇年)是爬坡登峰的上行转折点,六十年代是盛极而衰的下行转折点。这段美国历史就像一条倒U型曲线,而其背后所展示的则是一个从“我”到“我们”后又重回“我”的故事,这条渗透美国生活各个角落的弧线将美国历史变成了一个钟摆,在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来回摆动。过去一百二十五年间,美国如何沿着这条钟摆曲线运动,哪些因素推动过去的美国走出“镀金时代”,以及能否让当代美国走出“新镀金时代”,就是《浮沉世纪》想要回答的三大问题。
一
帕特南的倒U型钟摆曲线,借助了美国人的居住选择、投票模式、家庭模式、流行文化、婴儿起名和代词用法等维度的丰富数据。新旧两个“镀金时代”都在倒U型曲线的谷底,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向着经济平等、政党协作、社会内聚、文化融合持续攀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之后,各个方面都开始走下坡路直至当下。同时,这也是一个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向着更包容的社群主义拉升,而后又向着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急剧下降的过程。
“镀金时代”既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进步,也带来了不平等、两极分化、社会混乱和自我中心文化。面对“镀金时代”的腐败堕落,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开启了全方位的社会实验,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步时代是钟摆曲线的上行转折点,这时的梦想家和实干家们,创造了包括公立高中、工会、联邦税收体系、反垄断法、金融监管、最低工资等制度机制,让美国走上了经济平等之路,为延续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趋同”奠定了基础。所以,帕特南将进步主义视为美国社会改革的根本动力。
为了弥合巨大的政治裂隙,早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州和地方层面就开启了跨党派合作的进步运动,西奥多·罗斯福在一九〇一年意外就任总统又让这场运动获得了国家权力。尽管跨党派联盟在“繁荣的二十年代”(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九年)陷入停滞,但在新政时代重新恢复并得到加强。进步运动、新政改革,以及“伟大社会”倡议所催生的主要法案,都获得了两党多数派和相当多少数派的支持。因此,两次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托马斯 ·杜威说过这样一句话:“各党派的相似性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力量。”
公民组织的建立、教会的发展、工会入会率和家庭组建率等社会团结的主要符号,也都是从进步时代开始走出低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美国公民组织的生发期,政治社会学者茜达·斯科克波等人指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群众性会员组织,有一半是在一八七〇至一九二〇年的五十年间成立的。
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组织的种子”顽强生长,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很托克维尔的美国,即一个“参与的国度”。在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时间里,美国人有组织的宗教参与也越来越多,许多教会不仅是信众的礼拜场所,而且成了社区的聚会中心,这推动人们从个人主义转向社群主义。人们不仅在工会里更团结,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更积极,从“镀金时代”的晚婚不婚、少生少育、交易婚姻,走向强调早婚、多生多育、伴侣婚姻。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法文版
在文化方面,十九世纪末期,推崇个人主义的边疆文化与大洋彼岸传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两相叠加,令许多人认为“镀金时代”的弊病是进步的必然代价。新兴科学与古老偏见融合,放大了“人人为己”的丛林法则,富人理所应当,穷人活该遭殃,伦理秩序礼崩乐坏。物极必反,进步时代的思想家强烈抨击这种丛林法则,他们认为正是个人主义背叛了美国价值观,导致诸多经济社会危机,所以他们努力构建社群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将美国的富人与穷人、外来人与本地人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社群主义在文化议题上的重要体现。
这场朝向理想社会的进步运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半段达到顶峰,之后却戛然而止,世纪早期许多推动进步的体制改革创新开始消退甚至发生逆转,六十年代后半段因此成为美国钟摆曲线的下行转折点。一九六五年前后,教育的增长开始暂停;六十年代中期,减税政策开始导致税收结构加速倒退;一九七〇年开始的放松监管,加快了收入不平等的步伐,等等。
自此以后,美国进入了 “大分化 ”时期。七十年代初,尽管整个经济持续增长,但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停滞。同时,在六十年代末,人们曾津津乐道的跨党联盟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美国政治学会在《走向更负责任的两党制》报告中,嘲讽两党是“双胞胎”党;乔治·华莱士抱怨两大政党“没有一毛钱的差别”。党派部落主义随之重现并加速发展。
到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国会中的两党合作几乎不复存在。美国政治学家尚托 ·延加颇为愤慨地表示: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最重要的断层线不是种族、宗教或经济地位,而是党派归属。社会组织的发展也类似,会员数量在六十年代初达到顶峰,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直至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持续下降。
一个多世纪的公民创造力消失殆尽,美国人成群结队退出了有组织的社群生活,不仅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迅速失去兴趣,而且家庭组建模式也重回“镀金时代”的个人主义婚姻。在美国人的文化心理上,个人主义迅速取代了社群主义,七十年代美国进入了汤姆·沃尔夫所谓 “自我的十年”,人们不再渴望修复社会而只考虑修复自己,影响持续至今。
总之,帕特南发现,在过去一百二十五年中,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都呈现出倒 U型趋势,先从“镀金时代”强调个人主义的“我”,上升到六十年代注重社群主义的“我们”,再折返回“新镀金时代”个人主义的“我”。
尽管这里的“我们”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色彩,但并未将黑人和女性彻底排除在外。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迈向更强烈的“我们”之际,美国黑人也在一些重要方面相向而行。但当美国历史的钟摆转向“我”的时候,黑人首当其冲被排斥在外。性别平等方面亦是如此,绝大多数进步并非始于六十年代的女性运动,在那之后也没有得到加速。但在美国历史的钟摆曲线从“我”转向 “我们”的进程中,女性明显获得了更多的平等和包容,并在六十年代到达顶峰,而在那之后,随着“我们”又回到“我”,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甚至有些方面(比如性别平等态度)出现了停滞或逆转。
二
长期以来,帕特南就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通过社会资本、宗教和教育问题,细致入微,层层剖析着美国肌理。作为其多年美国研究的总结,《浮沉世纪》既与他的《自娱自乐》《宗教如何分裂和团结我们》《我们的孩子》等遥相呼应,又通过在超长时期内跨越多个维度测量社会变迁的广角延时方法,揭示了美国历史的钟摆运动。那么,是哪些力量推动了历史的摆动?帕特南不再像他在《自娱自乐》中那样执着于探究前因后果,而是主张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解释这一钟摆运动,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互为因果,相互激荡碰撞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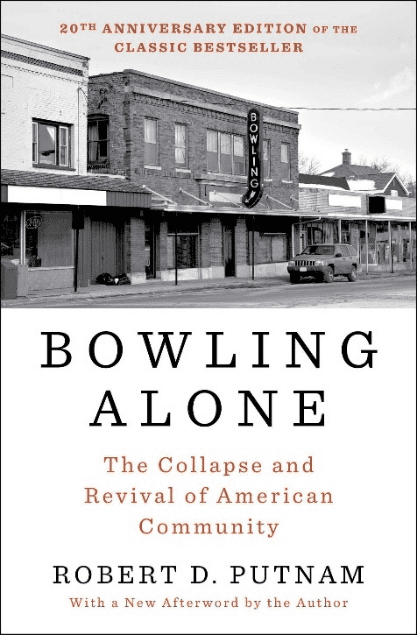
罗伯特·帕特南《自娱自乐》英文版
但是,文化几乎是最显见的推动力,尽管无法证明其是首要因素,却可通过文化的变迁发现钟摆的运行逻辑。不同时期的美国文化对个人和社群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钟摆因此不规则地在两个极点之间来回摆动。在从 “我”到“我们”再到 “我”的钟摆曲线中,“我们”的时代注重群体生活,共享价值观,相信通过勤劳努力可以实现种族和经济平等;“我”的时代关注个人“权利”,人各为己,坚持身份认同的文化战争。知识史学家珍妮弗·拉特纳 ·罗森哈根曾经这样说过:“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家,都想在自我私利和社会义务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都因此挣扎纠结过。”
“人人为己”的原则在 “镀金时代”大行其道,进步主义者因此希望通过各种民主实践将美国文化的规范准则拉升到社群主义一边。到了五六十年代,人们又开始担忧天平向社群主义的过度倾斜会压抑个人精神,那时出版的《孤独的人群》《组织人》《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人》等批评集体压抑个体的大部头作品,相继成为畅销书,整个社会开始为 “回摆”积蓄动能。
这种 “积蓄 ”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 “阿希从众实验”显示,五十年代之前的个体更易在群体中受从众压力影响,而六十年代之后,从众压力的影响已经极大减弱。再比如给婴儿起名字的变化,五六十年代之前,婴儿名字的重合度很高,之后就变得 “异彩纷呈”。还有代词 “我”与“我们”在美国出版物中的出现频率,从一九〇〇到一九六五年, “我”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 “我们”越来越高。
但在一九六五年之后,这一趋势发生逆转, “人人为己”的原则就这样死灰复燃。披头士乐队在六十年代上半期还在高唱团结,下半期就开始讴歌个性。在乐队解散各自单飞之前,乔治 ·哈里森为他们撰写的最后一支歌这样唱道:
我所能听到的是,我我我的,我我我的,我我我。(All I can hear, I me mine, I me mine, I me mine.)
这首歌就像一篇墓志铭,见证着六十年代 “我们”的死亡。
艾恩·兰德(Ayn Rand)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读者最多的书,仅次于《圣经》。这本书引申出一个影响二十一世纪的模因(meme,近似于中文的“梗”):社会由“制造者”和“接受者”构成,接受者通常利用政府权力从制造者那里获取东西,制造者就像古希腊擎天巨神阿特拉斯一样承担着整个社会的重量,只能对无能的接受者们“耸耸肩”。一九六四年,兰德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的那句“我不为自己牺牲他人,也不会为他人牺牲自己”,很大程度上成了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复兴的号角。
当然,文化不是推动钟摆的唯一动力,文化只是为决策者打开了“奥弗顿之窗”。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P. Overton)认为,政策的可行性,取决于特定时期主流人群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不是政治家的个人偏好,政治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做出选择。“奥弗顿之窗”可以让一些政策更有希望、更容易获得认可,或者至少可以想象。
比如,随着文化从社群主义向着个人主义摆动,重新分配税赋这类基于 “我们同舟共济 ”假设的政策变得不可想象,放松监管这类相反的政策就变得合理。因此,文化不只是历史大潮的浮萍,不只是文人墨客或流行文化鉴赏家的品评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动力。正如马克斯 ·韦伯所言,物质利益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但 “观念”所创造的 “世界形象”,常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动力所推动的行动轨迹。
三
美国历史的钟摆,就这样在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两极之间来回摆动,也促使人们对平衡力孜孜以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伯特·赫希曼将钟摆的两极界定为私人利益和公共行动,将“失望”作为反作用力,当人们对某种思维方式不再心存幻想,就失望地转向另一种思维方式。
六十年代是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的转折期。上升下降都可能无声无息,但转折却锣鼓喧天,从一九六四到一九七四年,几乎每年,甚至每月都有一本重要书籍以“改变美国”“震撼世界”或“一切都变了”为主题。整个六十年代繁华与凋敝共存,前半段是“希望的岁月”,后半段变成了“愤怒的日子”。
少数族裔对缓慢的社会变革步伐和落空的民权承诺失望,白人对正在失去的安全与荣耀失望,个人解放运动催生的自我中心主义对“共同梦想”的压抑失望,凡此种种,酝酿了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美国百年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与肯尼迪兄弟、马丁 ·路德 ·金等人被暗杀事件一道,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人的信心。
六十年代下半段,就这样成了美国历史钟摆的下行起点。不仅如此,如果人们继续拉长这一百二十五年的历史,再向前推半个世纪,也就是托克维尔所看到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的美国人通过结社克服私欲,共同解决集体困境,远比欧洲更平等、更富活力,但其后不到半个世纪美国就进入了物竞天择的“镀金时代”。就此而言,美国的发展史不止一个倒U曲线,美国似乎在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陷入了宿命般的浮沉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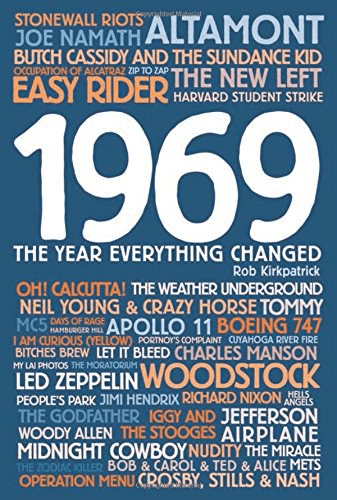
罗伯·柯克帕特里克《1969,改变一切的一年》英文版
但是,帕特南不同意这种借助失望的悲观主义思想方式,也不认为这种历史循环必然无解。他们认为社会生活与物质世界不同,不是在重力法则作用下追求机械平衡,人的能动性和领导力至关重要,历史的钟摆终究是人的力量推动的,并非不可摆脱的宿命,美国在六十年代的转折也并非不可避免。
要想让六十年代中期挣脱钟摆引力逆势上扬,就需要李普曼所呼吁的积极、有创造力、有纪律的公民,来“驾驭”那个“放任”的时代,学习进步主义的衣钵传人,推动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
这些人不是某些聪明的上等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他们是受到三角衬衫厂火灾的震动,为改善女工权益奔走呼告的弗朗西斯·帕金斯;是与伙伴成立扶轮社,致力于提供社会服务的保罗·哈里斯;是揭露南方私刑,为保障黑人权益无所畏惧的艾达·威尔斯;是反思资本主义的贪婪,为提升人们的公共生活而不懈奋斗的汤姆·约翰逊 ……他们在各自范围内积极争取社会进步形成的溪流,汇聚成社会巨变的大江大河,推动 “我”走向“我们”。
这些人凭借共同的命运感组织起来,推动了“镀金时代”的转折,尽管没能成功将六十年代推向持续上升的轨道,但是,如果人们满怀阻止国家继续下滑的强烈意愿,如果人们相信普通公民也大有可为,就很可能会推动“新镀金时代”的转向。

沃尔特·李普曼《放任与驾驭》英文版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未来将由你我开创”,帕特南寄予厚望的,正是那些失望的人们能够重新燃起希望,如果每个人愿意从共同的命运感出发抑制个体私欲,在保障个人的利益、权利、自主,与维护强烈的整体意识、共同目标、共同命运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从 “我”走向 “我们 ”,克服时代的放任,驾驭自身的命运,缩小 “老家伙们”(OK Boomer)与年轻一代的代际鸿沟,设定更清晰的公共议程和战略选择,仍然可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形成打破历史钟摆的必要力量。不过,可以想见,对于当代美国而言,这绝非易事,仍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浮沉世纪:美国如何重现百年前的和衷共济》,[美 ]罗伯特 ·帕特南、谢琳·加勒特著,陈雪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即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陈雪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