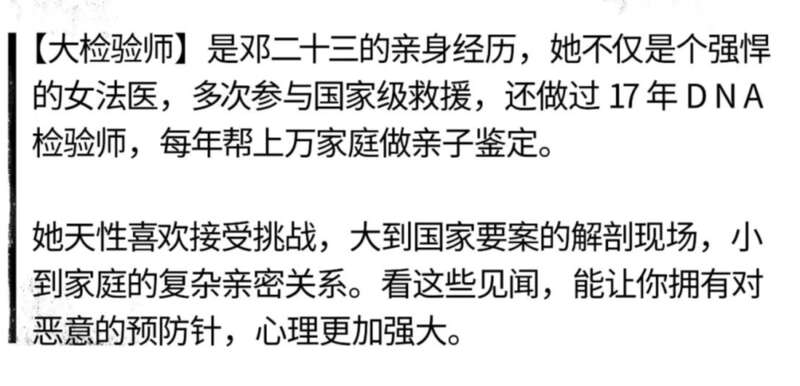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上周六,我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天才故事会,主讲人是大检验师邓二十三。

天才故事会第二期,左为邓二十三,右为猛哥
邓二十三是我认识的最强悍的大检验师,干DNA鉴定的时候徒手拆散了10万个家庭,做法医的时候最高记录一天解剖了60具尸体。
来现场的观众都很热情,有从外地赶来的,还有刚做完手术单腿蹦着也要来的。
为了响应大家的期待,邓二十三分享了自己最厉害的那段经历。那次,她被外交部派去执行一个任务,在泰国解剖3000具尸体。
她在那里看到了从业至今最有冲击力的画面,“闻到了十八层地狱的味道”。
这次任务的最终成果,作为外交礼物,被国务院总理送给了泰国总理。

这是一张2005年的照片,我和泰国总理的一张合影,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左边是我的同事,中间是当时的泰国总理,右边是我
当时中泰建交30周年,时任泰国总理他信也来到中国。我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国务院总理和中国科学院院长,把一份重要数据转交给了他。
7月1日,他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答谢宴,我和一位女同事应泰方邀请出席。宴席结束后,我们和他信留下了这张合影。
我们参与制作了那份重要数据。那份数据来自于一份国家任务,我至今记得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我带着四个队员,被送往了全世界瞩目的灾难现场。那样惨烈的灾难,即便自诩“法医狂人”的我,也不敢想象。
我在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尸横遍野。

2004年12月30日中午12点,我接到外交部通知,能不能立刻出发,目的地是泰国,当晚8点的飞机,5点要到机场。
我说,我倒是可以去,但是我们没有签证。外交部说你放心,签证可以一路绿灯。
我从单位攒了一个团队,除了我还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五个人里有两个人,连护照都没有。
北京的冬天很冷,我却跑出了一身大汗,开车用一下午,把所有人的证件都弄齐了。同时,我还要打电话,让团队准备要带的东西。最后,我们带了14箱子的东西去机场。
在接到外交部电话之前,我差点在北京待不下去。
四年前,28岁的我来到北京读硕士。同时,我还在西安市公安局的一个分局做法医。
硕士读完局长跟我说,你是分局第一个硕士,回来给你一个科长的位置,配个车,配个司机。但我说,我还想考博。
局长不同意,认为我明显是不想回来了,那只有两个选择,辞职,或者停薪留职。
我不想回去,在北京见到更大的世界我心野了。我彻底断了自己退路,辞职,又来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读博。
导师的导师同时会提供一份工作,所以我们管他叫老板。
老板说,现在有测序平台、蛋白平台,还有刚成立的一家司法鉴定机构,问我做哪个?我学了这么多年法医,肯定想做司法鉴定机构。
我只干了一年,就快山穷水尽了。
那一年我一直在亏损,同事嘲笑我,是亏损企业老总。老板可怜我,如果做不下去了,可以做他的办公室主任。
但我可是一个法医狂人,怎么可能转行做行政?北漂漂不下去,西安也回不去,我正左右为难时,看到了那条特大新闻——
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海啸,巨浪高达十余米,席卷了印度洋沿岸。后来确定引发海啸的地震为里氏9.3级,是历史第二大地震。
地震叠加海啸,造成了不可想象的惨剧,事后统计,全球死伤人数超过29万。
我看到海啸发生的新闻时,第一时间就在想,我能不能参与救援,验证一下自己的DNA鉴定能力到底怎么样?
刚好这时候,老板也来找我说,小邓,你有没有想过,在这场国际性的大灾难前你会怎么做?这真是不谋而合。
我立马写好了报告,12月28号把报告递交给单位,当天单位盖章,次日交给了中国科学院。第三天,我就接到外交部电话。
我本想去受灾最严重的印尼,但外交部说,泰国给我们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人援助,听说我们是做DNA鉴定的,泰国没有这样的实力,他们更加欢迎。
从机场出发前,我们老板从家里翻出了四串佛珠,团队里一人给了一串,但我到得最晚没分到。
我能理解老板的心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而他是个科学家,却用佛珠来祈愿我们能够凯旋,可见此行的危险。
他对我说,我要求你必须活着把这四个人带回来。
那时我才32岁,他们更小,平均年龄只有25岁,都是做实验的,从没干过法医。我只觉得我这个“亏损企业老总”肩上的压力重重。

我们被叫作“中国救援队DNA专家小组”,我是组长,此行的目的是提取无名遇难者的DNA样本,并送回北京检测,从而为最终确定身份提供帮助。
那一晚的飞机,我一夜未眠,一直在讨论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做了很多应急预案。
大概凌晨2点,飞机到达泰国首都曼谷,我最后才下飞机。
这时候闹了一个笑话。中国驻泰使馆的张大使,为了表示对中国救援队的重视,走特殊通道跑到了机舱口接我们。
团队中有一个男孩,他年龄比我小,但长得比较老相。张大使看见岁数显大的人,上来就握着手说,邓博士你好啊。
男孩有些尴尬,说自己不是邓博士,邓博士在后边,指指我。

我们刚到泰国和张大使的合影,很遗憾那个“邓博士”没在画面中
出了机舱到了机场里,我更加震撼。
我们要取行李,中国的记者都在那里,使馆特意带来了一面五星红旗,我们在外国的机场拉起了大大的五星红旗一起合影。
新华社当时就把这张照片发回了国内。那一刻我特别光荣,觉得自己是带着一份荣耀和责任来到泰国进行救援的。
救援的地方离普吉很近,我们在曼谷转机,6点钟飞普吉。早晨8点到了普吉岛,当地的领事馆派人来接我们。
他们问,我们这次来主要做什么?我说,我们是做DNA救援的。因为当时是圣诞假期,很多外国人在泰国度假,出现了很多尸体,需要一一个体识别。
灾难已经过去四天,领事馆说,泰国警方给出了一份操作流程。我看完后觉得,这个流程操作不了,我要有自己的流程。
为什么?泰国的专家说。对于没有腐败的尸体,我们可以取口腔拭子(就像做核酸一样)。可是很多尸体紧闭着嘴,怎么取口腔拭子?
泰国专家还说,高度腐败的尸体可以拔头发。但我们看到的尸体是沉浸在血水里的,头发都不用拔,一撮一撮可以拿下来。
后面终于有一个靠谱的建议,说实在不行就取深度肌肉组织。但这就要解剖了,DNA鉴定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污染”,有污染就意味着取样有杂质,后续检测就不准了。
任何流程,都要先制定操作规范。这么一个环境下,如何避免污染,他们都没有写。所以我才说,我们自己做一个操作流程。
领事馆的人说,现在才8点钟,你们准备干嘛?我说,就去受灾最重的地方看看。说完,他们驱车带我们过去。

我们所在的省叫做攀牙府,攀牙沿线就是它的海岸线。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惨的场景,整个开阔的海岸线全是废墟,所有的楼房都坍塌了,汽车打着卷变成了废铁,你想有多惨它就有多惨。
我们当时觉得,这里这么惨,就是在这一直干义工都值得。
开车沿途走,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穿着一次性手术服、戴N95口罩的志愿者,在低头在找什么。
我们问他们在找什么?他们说,在找尸体。
海岸线上尸体一波一波被冲上来。沿途隔一段距离,有一个简单的救助站,他们把尸体捞上来统一码在那儿,再汇集到更大的能停尸的地方。
最大的停尸点是一个寺庙。我们开车到了那里,地上至少有1000具尸体。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尸横遍野,什么叫惨不忍睹,这两个成语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是有裹尸袋的尸体
早来的尸体还有裹尸袋装着,后面再来的连裹尸袋都没有。泰国常年高温,尽管是1月份也有30多度,尸体全都已经腐烂。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开工。泰国已经到了一部分法医,我们跟他们组成一个小组。
我为了实现把他们活着带回去的承诺,要求所有人都穿着防护服,我们叫“猴服”。
我是从国内戴了全套东西。海啸前一年“非典”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经常穿猴服,从脚底下一直到头。猴服为了不沾染病毒,是不透气的。
穿上猴服,戴着N95口罩,戴着眼罩,从头防护到脚。
但跟着泰国人看了两具尸体,我就不行了,要虚脱了,汗不停地往下流。我问他们四个人怎么样?他们也说,真不行,太闷了。
再看人家泰国法医,就戴个口罩,穿个雨鞋和蓝色的一次性手术服。
那好吧,我们也把猴服全部脱掉,换上了一次性的手术服和雨鞋,戴上一次性帽子,以这种方式去检验尸体。
我们要把裹尸袋打开,量尸长,看尸体上有什么衣服,有没有伤口,有没有什么首饰,有没有手术的痕迹,或者其它痕迹。
我们还要拍照,要把尸体翻过来,背面朝上。
裹尸袋一打开,尸臭味就会冲到鼻腔里来。世上最臭的就是尸臭,那是十八层地狱的味道。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反应,胃里边的东西哇就要吐出来。
但是看到在场还有泰国人,我又咽了下去。
几天后,大使馆张大使从曼谷来看我们,刚好有记者拍到我们的照片。我前胸后背全是湿的,脸上流着汗,这就是我们实际工作的样子。
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解剖60具尸体,几乎达到人类能做到的极限。
使馆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从这尸体上他第一次看到什么叫七窍生蛆。其实不光是头上七窍,全身有孔洞的地方蛆都会出来,腿部烂了一个一个小洞,也有蛆。
我干会儿活,就会发现蛆顺着我的胶鞋往上爬,有的恨不得马上就顺着边进来了。
那时候我们吃饭,泰国人吃香米,泰国香米是细长的,粒粒分明的,和尸体上的蛆一模一样。
我们几个中国法医看着香米,面面相觑。还好他们带的冰桶里边有冰可乐,我们只好拿冰可乐,先喝饱再说。
晚上结束工作之后,因为攀牙全部遭灾,没有一个能住的地,使馆比较心疼我们,让我们回到普吉去住,车程大约一个小时。
到酒店里面已经很晚了,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把味道洗了再去吃饭。
跟我同去的唯一一个女生,她是长头发,我们出现场的时候她把头发盘起来,戴了一个鸭舌帽,还有一次性的帽子。
下来吃饭的时候,她把头发散开,坐我旁边。我和她说,快回去洗头。她说自己洗过澡了,我让她回去洗头,她的头发上依然是浓浓的尸臭味。
上菜之后,有一盘是泰式炒河粉,盘子的一角放着绿豆芽,去了根部和头部的绿豆芽,白白小小的,又是跟蛆一模一样。
使馆问,你们为什么不吃?我说,太像蛆了,实在没办法吃。使馆说,那明天给你们准备三明治吧。第二天我们再去干活的时候,使馆就给我们带上三明治。
有时候我们晚上出去走走,走到普吉的广场上,到处贴的是寻人启事,一家几口的合影,或者小女孩灿烂的笑脸。

广场上的寻人启事
我们看到了都说,要给国内打电话,让国内来捐助捐款,实在是太惨了。

我们跟泰国法医干了几天,但是不断有冲突,因为他们说的口腔拭子、头发都没法取样。
泰国警方还说,泰国的指纹库特别厉害,可以看看指纹。但是尸体高度腐败,会出现人皮样手套,一碰尸体的手,整个手皮都会像手套一样脱下来,不可能取得到指纹。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更靠谱的组织机构,这时候发现,比中国去得早的还有个澳大利亚的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上一直有这样一支国际刑警组织,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n,简称DVI,它是进行国际化大型灾难救援的,衣服后背都会有DVI的标志。
国际刑警组织在当地搭了个棚子,给棚子装上空调,按照国际刑警组织一套流程去工作。我想,跟国际刑警组织一起干吧。
我们就开始跟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一起开会,没有人认为我们是中国人,他们看到我们的面孔,问我们是不从日本来的?我说不是,是China。
2005年1月1日,我们到普吉警察局开了一个会,有二三十个国家,围着圆桌坐,澳大利亚的人当主席。
他特别正襟危坐地说,目前我们发现了3000多具尸体,这3000多具尸体泰国人很少,基本上都是欧美或者其他国家来旅游的人,这些人的尸体识别怎么办?
这个检测难度是很大的,常规的样本已经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主席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澳大利亚人自己带来了公司,包括尸体识别、装棺、运回国,公司全部能够处理。但是,公司是要收钱的。
讨论用什么样本的时候,最后大家认定要用骨骼样本。他们报价是一个样本1200美元,3000个人要360万美元。还不算别的费用。
这笔钱谁出?全场默不作声,所有人都低着头。
我本来是特别崇敬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在我当警察的时候,还希望有一天我能到那里去历练,结果现在发现他们是带着自己的利益集团来的,很失望。
大家都在讨论一下,如果很贵,不给这个公司做的话,谁来做?
这时候我壮着胆子说:“我们做。”
我当时英文不好,是用中文说的,让我旁边一个英语很好的男孩翻译一下。
他用非常标准的美式英语说:“我们代表中国,承担此次泰国所有遇难者的DNA检测,包括承担相应的费用。”
全场又一片沉默,所有人都愣住了。
事后,使馆陪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你差点给我们造成了外交事故。我说,什么事故?
他说,你在泰国代表的是国家,你自己怎么能随便把这句话说出口呢,你说这句话谁同意了?
我说,我们单位同意了。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的两位大老板一起把我们送到机场。
我跟他们说,我推测泰国的遇难人数是5000人左右,如果有可能,我想把这5000人的个体识别接过来,你们同意不同意?
老板同意了,说,你可以现场自己做主,费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向国家申请不来,我们就自己承担。
我们到了现场才知道,其实遇难者是3000个,在我承受的底线之内。
当时我预计要花几百万人民币,和几百万美金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觉得我的老板可以承担得起。
而且我们是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这是一个彰显中国大国姿态的一件事情,这会儿你不能怂。
当时全场沉默了至少30秒。突然新加坡的国际刑警组织举手,说,我们相信中国,我们同意中国来做。紧接着,菲律宾人说,我们也同意。别的欧美国家也陆续都同意了。
我看了一眼那个主席,他的脸色很黑。
但紧接着过了两天,美国来了,特别财大气粗地说,为什么要运回中国去做检测,no no no,我们把机器送到普吉岛,帮助泰国建实验室,所有的东西都在泰国当地完成。
团队里英文特别好的那个男孩成了我们的“联络官”,我们去现场干活的时候,每天回来他给我说,美国人要来抢活,哪个国家又说什么。
这时,使馆开始直接跟泰国警方沟通。到我过去的第12天,使馆告诉我飞曼谷,跟泰方讨论合作的细节。
我把团队几个人留下来,自己从普吉飞曼谷,跟泰国高层沟通签署了协议。最后确定,泰国协调所有国家配合取样,由中国负责检测。
所有人都带着怀疑的态度看我们。我们跟澳大利亚的交流很势弱,我们想用肋软骨,他们说NO,要用大腿骨。
大腿骨取的时候很难取,因为腿部肌肉很厚,切开之后还要锯骨头,肋软骨我们轻轻用刀就可以划下来,更容易操作,成本比较低。
澳大利亚人的理由是,肋骨容易污染。我们说没关系,污染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但还是不行,因为讨论过程中,欧美的DNA专家占了优势,说在我们国家就是用大骨头做的。
我们也尝试过肌肉组织取样,但是身部肌肉组织已经全都腐败了,所以要么就肋软骨,要么就是股骨。
到十几天以后,我们准备回北京做检测。
每天都有上百个样本收进来,但是我们第一批带回北京的只有100个样本。其中86个是牙齿,只有14个是小碎骨头,样本不统一,说明之前的流程全都没理顺。

我们第一次带着样本回北京
泰国派了3名警方的高层人士跟我们回北京,号称押运,但是我觉得是监督。
我就把英文最好的“联络官”留在现场沟通,其余四个人带着100份样本,声势浩大地从曼谷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大老板说,小邓你回去休息,这么多天辛苦了。我心里一热。
紧接着他说,这个样本今天一晚上干完,明天就让泰国人拿数据。我说,我可不这么有信心。他说,没关系,你走吧,你不用管我。
都没有等到第二天早晨,凌晨6点天还没亮,我的电话就玩命响。我心头一凉。
老板说,全军覆没,100份样本,一个结果都没出来。

我问,样本是不是都没了?
老板告诉我,我们投机了一下,觉得牙齿可以取牙髓。但他忽略了,尽管被两个坚硬的硬骨包着,但是里边牙髓也腐败了。
反倒是那十几块小骨头,我们自己用研磨机去磨再检测,有了结果。但相当于样本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成功概率,这不好交代。
我说坏了,第一泰国在等消息,第二我不能让泰国人再继续取牙齿了。
我很想埋怨为什么要取牙齿,但我谁也不能埋怨,谁让我在国际会议上大夸海口,我们可以,我们行,现在我说我们不行,特别尴尬。
而且泰国人还来了3个人,怎么办?
老板想了想,出了个主意,说,你陪他上长城,把泰国人招待好。
所以我就问泰国人,你们想不想去长城,中国有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他们说,OK。
他们玩得很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北京太干了,说早晨起来就流鼻血,不能在这待,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一听暗自窃喜,赶紧回去吧。
我把泰国人送走,跟他们说,第一批数据随后就到,或者是我送回去,或者是传回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北京讨论了各种改良实验,最后发现确实无路可走。除了去说真话,去告诉泰国人停止拔牙齿,我别无选择。
泰国人还在拔牙齿,打电话给他们也没用,一直在拔。
那边的“联络官”特别着急,一直问怎么样?我说,全军覆没。他在当地就崩溃了。
你想,一个24岁的中国小男生在运筹帷幄,本来都成明星了,突然被我一头凉水从国内扑过去。
他当时都快扛不住了,气冲冲说,你来,你来!
我去泰国的心情犹如上刑场,但我不得不去,那是我的责任。
我代表着中国承接了这个项目,我去跟人说我玩砸了,不行吧。我只能把整个过程都写清楚,主动去找国际刑警组织交流。
我们老板说,要不要人壮胆,当时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派他跟我去吧。
我们俩去了之后,”联络官“接到我,把我训了一顿。我说我错了,帮我组织一下会议,我说明情况。

我(右边)在泰国的工作照
所有国际刑警组织的DNA专家都在现场。我说,很抱歉,我今天要做一个陈述,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希望换样本,立刻换样本,否则就在做无用功。
我做完陈述之后,全场没人搭理我。
我说,我们必须得有一个结果,我是承接方,你们要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提供样本,不能你们说了算。是谁做这个实验?是我做。
我承担的费用,我出的东西,全都是我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听我的?你为什么要拔牙?你们能不能听我的?
全场沉默了好久。
最后,DNA专家的主管说,我们再送100个样本去北京,这回除了泰国取的牙齿,还送有国际刑警组织取的股骨骨骼样本。
同时,他们要把牙齿样本也送到韩国、澳大利亚,看看是什么检测结果,再做后续打算。

第二次我又带了100份样本回北京。这次跟我回来的不是泰国的高层警方,而是3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
恰值中国新年,我也没敢停。3个专家和我在实验室,我每一步怎么操作,挨个告诉他们,他们看着每一步,最后牙齿结果就是没出来。
我问,你告诉我哪出错了?他们也没办法。现在能怎么办?
最后我们老板说,上长城吧。第二天,我又带着这3个专家上长城了。
等他们也走了,我很关注送去别的几个国家的样本情况。我告诉“联络官”,这段时间你要密切关注这几个国家的消息。
新年过后就是中国的“两会”,马上要开“两会”时,我收到了一封外交部的调查函,请我们去外交部当面解释此次的事故,我们为什么没做出来,造成了如此大的国际影响。
据说,有一个某个国家的报纸说,中国著名的基因实验室竟然没有做出遇难者的DNA。
我们老板开着车陪着我,去了外交部。外交部的人看到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特别高兴,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
原来,就在我带着悲痛的心情想去外交部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封“联络官”从泰国发回来的email。
他说,前三批送到别处检测的样本,纷纷反馈没有结果,或者10个样本只有一个有结果。最后,泰方同意更换样本。
我直接把这封邮件打了出来,带着这封邮件和外交部说,你看我收到了泰方的email,完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现在他们决定换样本了。
从这一天开始,每天都有500个骨骼样本寄到北京的实验室。
骨骼样本操作起来很难,要清洗,还有别的各种复杂操作。我们不能500个一起做检测,得10个、30个,一点一点去做。
如果今天30个能成功27个,另外3个我把它留下来,自己做;然后再做30个,再留下几个我自己做。相当于大家在一个流程里做,我来精雕细琢。
最后,我必须让所有的DNA数据做出来。因为样本是唯一的,做完了就没有了,再也不会模棱两可了。
结果出来之后,30个样本,我让那个长发女孩带去泰国。她带到那之后,我再把数据传过去,他们当天就比对成功9对。
她说,“他们都叫我是中国来的Superstar。”自豪的心情无以言表。
我也特别高兴,每天我就在北京出数据,她在泰国去比对,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所有样本的数据在2005年6月全部做出来。
7月1日,中泰建交30周年,时任泰国总理他信来中国。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把所有的数据刻成光盘,由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代表,转交给他信。
他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答谢宴,我和长发女孩应泰方邀请出席。
我们离主席台很近,他信就在不远处。吃完答谢宴,我告诉使馆的张大使,我们想跟他信合影。刚说完,就见他信起身要离场。
我们顺着一个通道追上去,张大使叫住了他信,和他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他说,我们就是这次DNA援助的人。
他信特别高兴,把我们俩揽住合了一张影。这张合影一直保留在我的电脑里,文件夹叫“海啸救援”。
再之后,我获得了“中国五四青年奖章”、“北京十大杰出青年”、“十大科技进步新闻人物”。
但我仍然记得的是,当初想离开西安,来北京见识更大的世界的自己。
这些年一路走来,我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帮助很多人解决问题,甚至有些是大问题,我在以前都不敢想这些。
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会变,去当那个“解决难题的人”,让自己更有成就感一些。

18年过去了,邓二十三还在做法医,并且开了自己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再是“亏损企业老总”。
很多人会认为,是泰国这次救援让她的人生出现了转折,但我觉得并不是。
远在去泰国之前,她就一直在为此做准备。
24岁刚毕业,在西安做法医的前两天,她就检验了18具尸体。
随着经验积累,她看到一具女尸不用解剖,就能知道她怀孕三个月。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她感到“头发都竖起来了”,因为想法被验证了。
31岁“非典”来袭,她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分离非典病毒。
标准的实验室负压是50左右,同事怕她被病毒感染,把负压调低到了200,那是一个会让人内分泌完全失调,没有月经的环境。
她在里面待了三个月,成功分离出病毒,并进行了传代培养,保证了后续抗疫工作顺利进行。
真正帮助她的,不是一次幸运的机会,而是深爱这个行业,并为之做好一切准备的那个邓二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