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10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楠,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王楠:西部之毒》,题图来自《犬之力》
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犬之力》是今年的话题电影,它斩获无数奖项,并在刚刚颁布的奥斯卡金像奖中荣获最佳导演奖。但对于它的评价,又是毁誉参半,近乎两极。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初美国西部农场的故事,可在王楠看来,坎皮恩的野心恐怕不止是要构建一个不一样的西部,更想彻底解构西部精神的所谓阳刚正气,进而对男权和现代社会发出批判。因此,从“文明”的角度切入电影分析,就是思想史、教育哲学出身的王楠,比较擅长的写作路径了。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曾声称,美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开拓西部的历史。差不多贯穿整个十九世纪,美国文明的潮流,有如海浪一般横越北美大陆,自大西洋向太平洋奔涌而去。无数的拓荒者和冒险家骑着马、乘着大车西进,开辟出无数农田与牧场,建立起贸易站和小镇,推动着边疆不断向西移动。
在特纳看来,这些弄潮儿正是美国精神的骄子。他们征服了漫漫荒野,却又未像东海岸那般,陷入过度文明化的社会。正是在边疆这一荒蛮与文明的交汇线上,生成了美国人讲求实际又粗犷坚强、自由奔放又乐观热情、独立自律又协作共议的生活之道。“西部”也由此成为美国文明的某种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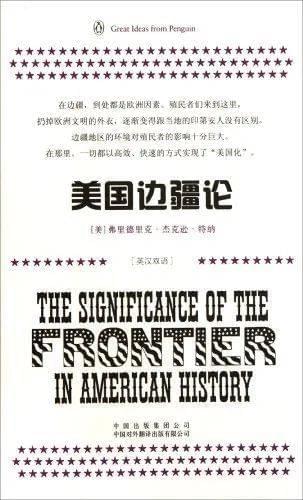
当然,特纳在写下这段话时,十分清楚“边疆”已经消失,自己的使命是让“西部人”定格为美国文明的精神肖像。二十世纪,好莱坞的西部片将它具象为银幕上的牛仔英雄,既提供大众娱乐,也供后人缅怀崇敬。而现实中西部人的生活,仍然在思想与影像之外流动变化。
一九六七年,托马斯·萨维奇的小说《犬之力》,描绘了蒙大拿州牧场中的一段故事。这本书获得了文学界的肯定,在市场上却不受欢迎。显然,无须太高的鉴赏力,小说的读者也能体会到这个所谓的西部故事,与当时流行的西部气概格格不入。约翰·韦恩其时仍在银幕上驰骋披靡。小说虽五次售出电影改编权,却从未被成功搬上银幕。
直到二〇二一年,才由网飞投资,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指导拍摄完成。此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当即斩获最佳导演银狮奖。随后业界好评如潮,各种奖项拿到手软,更赢得二〇二二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十二项提名。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最终只得到最佳导演奖。
刚刚出演了西部剧集《一八八三》的西部片老演员山姆·艾里奥特,更对此片嗤之以鼻,认为简·坎皮恩完全不了解美国西部生活,只不过找了帮人在新西兰拍了部男同电影。坎皮恩反唇相讥,说西部反正是个神话,自己不过拍出了心目中的西部而已。
撇开奖项和言论不谈,这部电影还真挺耐人寻味。坎皮恩的野心恐怕不只是要构建一个不一样的西部,更想彻底解构西部精神的所谓阳刚正气,进而对男权和现代社会发出批判。就此而言,无论是否认同坎皮恩眼中的“西部”,都有必要琢磨一下,这部技巧精湛却又古怪甚至有些变态的电影,到底想要讲些什么?
野性与文明
牧场的主人菲尔和乔治,是一对奇怪的兄弟。虽然同住一个房间,但相互之间既不亲密热情,也没有无言的默契。身手矫健、说话咄咄逼人的哥哥菲尔,总想“教育”矮胖敦实、沉默寡言的弟弟乔治,让他更像个西部的“男子汉”。他讥讽弟弟的体态做派,提醒他莫要忘本,不要忘记当年“野马”亨利是怎样教会了他俩骑马放牧、经营农场,令他们变成真正的牛仔。菲尔还想拉他去山里打猎露营,就地烧烤新鲜的鹿肝,就着烈酒大快朵颐。可弟弟对哥哥的这些言辞和提议,不是敷衍两句作罢,就是默不吭声。
不过,乔治对菲尔也不是逆来顺受、一味忍耐。小说中的乔治,是个内心善良、朴实单纯、实干胜于言辞的牧场小伙儿,虽然不喜欢哥哥的做派,却从未与其直接冲突。电影则刻意加强了两人之间的对立。乔治并非不知哥哥对自己潜藏的依赖和感情,但仍然在暗中对抗他,想摆脱后者的控制与教训,两人相处时充满紧张感。
菲尔一身牛仔装扮万年不改,乔治却在骑马时也穿正装戴礼帽。菲尔不爱洗澡更衣,脸上总是脏兮兮的,浑身散发迫人的气味,只是定期去池塘游泳擦身。乔治一出场就泡在浴缸里,还质问菲尔是不是从来就没在家里洗过澡。乔治明知菲尔十分讨厌镇上的寡妇露丝,却在和她结婚后,才冷漠地告诉他这一既成事实。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州长夫人恐怕会介意他不洗漱就上桌吃饭。很明显,乔治要用自己“文明”的姿态,来对抗菲尔“野性”的做派。

不过,菲尔真的就是个道地的牛仔、天生不羁的乡下糙汉子吗?电影展开到中段,观众才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他其实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主修古典学,希腊文拉丁语样样精通,还是斐陶斐荣誉学会的会员。
这时观众才猛然醒悟,菲尔的“野性”绝非自然而然,而是为了反抗“文明”而刻意为之。一九二五年的美国正处于柯立芝繁荣,《了不起的盖茨比》在那一年问世。即使是蒙大拿的乡下牧场,也早已被“文明”的潮水包围。原著将菲尔随便安排在加州上大学,坎皮恩却大大“提升”了他的学历,暗示这个“野性”的男人其实有高度的文化教养,牧场正是他守持阳刚粗粝的“野性”来对抗腐败又娘娘腔的“文明”的孤岛,而那个处处接受“文明”、整日衣冠楚楚的弟弟,是他最想教育和改造的对象。

一旦看清菲尔这个人物,坎皮恩如何借助电影《犬之力》来解构西部精神,甚至直指菲尔式的男性父权为虚假,就真相大白了。在菲尔的身上,阴柔的内在使他用虚假的阳刚来伪装自己、规训他人,也构成了他渴求阳刚的真正驱动力。手握否定和压制的权威,给了他虚假的自我确信,而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追随,又隐秘地满足着爱欲的要求。
这种阳刚和权威为表、阴柔与爱欲为里、自恋与崇拜合一的辩证法,电影不厌其烦地向观众一再暗示。彼得在湖边的林屋,发现了菲尔私藏的“野马”亨利的色情杂志。在大方展现男性裸体的两本《体育文化》之间,一本女性露出的《艺术期刊》在镜头上一闪而过。乔治和露丝在农场的初夜,备受煎熬的菲尔走进马棚,细细擦拭“野马”亨利留下的马鞍,深情抚摸着昂起的桩头。“野马”亨利教了菲尔许多技艺,可后者却偏偏对编牛皮绳这门不怎么“阳刚”的手艺情有独钟。他将两条细细的生牛皮段编成麻花状,让它们紧紧纠缠在一起,难分难离。这些无言的影像,而不是菲尔的口头言辞和表面做派,才充分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
刚强,却不善良
菲尔这个看似刀枪不入的“硬汉”,最终死在看似文弱娇柔的彼得手里,这一结局实在耐人寻味。既然菲尔极度厌恶“阴柔”,他又怎么会和彼得这个“娘娘腔”搭上线?而后者又何德何能除去菲尔这个“大魔头”?
在旅店的饭堂中,柔弱纤细的彼得和他巧手裁出的美丽纸花,令菲尔多少看到了往昔的自己。或许当年在耶鲁时,他也是这样的文弱书生。彼得的“阴柔”,或许既调动起他恶作剧的冲动,又让他感觉到了什么,戳向纸花中心的手指就是证明。
不过,他对彼得真正“动心”,还是因为露营时看到了后者身上的“勇气”。牛仔们看见“娘娘腔”彼得,准备好好“调戏”他一场。谁知彼得毫不在乎地走过牛仔们的帐篷,对冲自己吹的口哨充耳不闻,随后又镇定自若地原路返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这全被菲尔看在眼里。电影中的这一幕,罕有地几乎全盘复现了小说的场面和气氛,令书中对菲尔的心理描写,足以成为电影未给出的旁白:“哈,值得认可,菲尔就认可。这孩子的勇气不一般。”

如果说菲尔是外刚内柔,那么彼得恰恰相反。这个开场时坐在桌边剪纸花,看似静如处子的大男孩,实际上有极为冷酷的理性、钢铁般的意志。他设下陷阱捕到兔子,哪怕母亲露丝非常喜爱,也仍然毫不犹豫地将其开膛剖腹,当成医学研究材料。露丝向他诉说苦楚,寻求慰藉的拥抱,他冷静地推开母亲的双手,告诉她:“我会想办法,你不必如此。”才刚刚学会骑马,他就独自跋涉数里,翻山越岭去寻找死于炭疽的牛尸,将牛皮小心地割下带回。更不必说他一边眼瞅着菲尔在编绳的过程中染上致命之毒,一边还与其亲密交心,同吸一根烟来达意传情。观众和菲尔,都被他文弱秀丽的外表欺骗。
还是已故的父亲最了解他:“(彼得)他以前担心我不够善良。我太刚强了。(菲尔)你?太刚强?他可错了。”虽然菲尔的感情和直觉没有欺骗自己,外刚内柔的他,或许必然倾心于彼得这种外柔内刚之人。但在意识层面,菲尔才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个表面刚强、内心其实细腻柔软之人,最终被一个真正遏制自己一切温情的刚强者征服和消灭了。
不能说彼得没有感情。但他决不会像菲尔那样,让情感和爱欲来驱动自己。他知道母亲依赖自己,却冷静地和她保持距离。他也不是没对菲尔动情,但面对“如果不去帮助我的母亲,如果我不救她,我还算什么男人”的伦理观念,这种感情也只能弃之不顾。如果说菲尔还能借表面的“教导”来释放自己,彼得才能真正克制一切情感冲动、只服从于冷酷的理性与钢铁般的意志。
可悲的是,虽然菲尔和露丝都爱他和依赖他,以双方对自己的感情为纽带,但居中调和、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这种可能性从未进入他的视野——当然,在坎皮恩的电影世界里,本来也不存在这样的事。既然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母亲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其实就是剪贴本图片里的豪宅大屋,就是母亲与继父的快乐拥吻,那么菲尔不过是母亲幸福之路上的小小障碍而已。最终,彼得在窗前看着“得到幸福”的母亲,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自己真实的感情、欲望与罪恶,就像藏在床下、令菲尔丧命的那根毒绳,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取出,戴着手套来抚摸回味。

西部的毁灭?
菲尔死后,牧场大屋的门前,建起了一座石雕喷泉。可它根本没有水,既缺乏繁华城市中人造流水的勃勃生机,也不像林中清溪那般自在流淌奔涌。它干枯地挺立在砂石荒原之上、凛冽寒风之中,呆滞、僵死而怪异。它是这个西部故事的终点。
在坎皮恩的电影中,西部精神不再是昂扬的生命力与大地般宽广的胸怀和气魄,也不再有滋生它的沃土与山林,而是成了在荒原舞台上演出的一场荒诞悲剧。“野性”和“阳刚”,变成人为了逃离自己和社会,而在头脑中编织出的批判性幻想剧本,支撑权威、自律与规训的则是隐秘的爱欲和冲动。最终,冷酷的理性规划与强力意志护佑的幸福幻象,彻底遮盖了真实的欲望和情感。
简·坎皮恩素有女性电影大师的美名,《犬之力》的主角却都是男性。显而易见,这部充满政治批判意味的作品,是这位女导演送给男人的“礼物”。自问世以来,它获得的大大小小上百个奖项,也表明了它的艺术水平。
不过,在第二十七届英国电影学院奖的颁奖典礼上,发生了一件小小的风波。上台领奖的坎皮恩,面对台下坐着的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说道:“维纳斯和赛琳娜你们真的很了不起,但是不用像我一样和男人竞争荣誉。”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坎皮恩的潜台词是,你们在球场上打败了女人,但厉害如我,能够在艺术界打败男人。这种对自己“阳刚之气”的炫耀,结合电影中对男人“阴柔本质”的揭露,不禁令人觉得,老菲尔也不一定就是男人。批判政治的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彻底解放的理想,何尝不会是一番妄想?批判与革命,如果不能在退场后带人回到真正的生活,而是一再抽象扩张、旧瓶装新酒,最终的结局,恐怕就像那个干涸的喷泉,形态犹在,但生命之水已干。

好在,并不是只有这样的西部电影。不屑《犬之力》的山姆·艾里奥特,二〇二一年不就出演了一部完全不同的西部剧集吗?只要看过约翰·福特、霍华德·霍克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些伟大导演创造出的西部世界,都不会觉得牛仔们就是坎皮恩拍的样子。
虽然这些电影是虚构,但其中的人性与生活以及内在的精神,可不像《犬之力》里的“阳刚”和“野性”那么假。当然,作为批判者的《犬之力》自有其警世价值,我们今天也确实生活在一个幻梦多于真实、虚妄碾压质朴的小世界。但坎皮恩自己也不要落入犬之力的陷阱为好。毕竟,谁说只有雄性才拥有犬之力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