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在学生闻到漂白剂刺鼻的味道,最后没吃下这份咖喱;投毒者半泽彩奈也被警察带走,关到了局子里。 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她交代,漂白剂是藏在包里带进学校的,而下毒的原因是,她本来一直担任班主任,但自4月份开始,学校却没有让她继续做班主任,她很不甘心,遂产生了报复心理,所以在咖喱里加入了漂白剂。
好在学生闻到漂白剂刺鼻的味道,最后没吃下这份咖喱;投毒者半泽彩奈也被警察带走,关到了局子里。 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她交代,漂白剂是藏在包里带进学校的,而下毒的原因是,她本来一直担任班主任,但自4月份开始,学校却没有让她继续做班主任,她很不甘心,遂产生了报复心理,所以在咖喱里加入了漂白剂。  ·半泽彩奈 有日本网友因为这事对本国老师颇有微词,认为老师素质怎么下降了这么多。
·半泽彩奈 有日本网友因为这事对本国老师颇有微词,认为老师素质怎么下降了这么多。  还有人对这种行为表示恐惧,认为怎么能对孩子干这种事。
还有人对这种行为表示恐惧,认为怎么能对孩子干这种事。  半泽彩奈投毒的事件,也让人回忆起了日本教育界始终存在的刑事犯罪现象,虽然数量不多,但每次都能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并被认为是日本教育的通病。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一些小学老师对学生的迫害。
半泽彩奈投毒的事件,也让人回忆起了日本教育界始终存在的刑事犯罪现象,虽然数量不多,但每次都能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并被认为是日本教育的通病。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一些小学老师对学生的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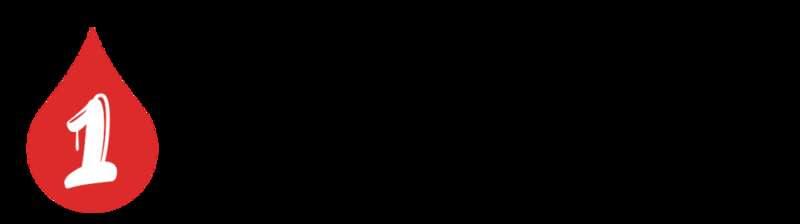
夺命小学教师 2017年3月24日,时年9岁的女童小凛在参加小学三年级毕业典礼的路上失踪了。 等到人们再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具倒在稻田排水沟的尸体。 小凛的死状极为凄惨,下半身有撕裂伤,还有唾液等体液。
 杀害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她就读的千叶县小学监护人会长涩谷康政,时年51岁。
杀害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她就读的千叶县小学监护人会长涩谷康政,时年51岁。  ·涩谷康政被捕现场 所谓小学监护会,是日本小学里通过家长、学校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合作来改善孩子们的学校生活的团体,可以理解成后勤老师。 身为教工人员的涩谷康政,有十分严重的恋童癖,以收集萝莉的色情DVD为兴趣爱好。
·涩谷康政被捕现场 所谓小学监护会,是日本小学里通过家长、学校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合作来改善孩子们的学校生活的团体,可以理解成后勤老师。 身为教工人员的涩谷康政,有十分严重的恋童癖,以收集萝莉的色情DVD为兴趣爱好。  ·中学时的涩谷康政 涩谷康政每个月要花费大概100000日元购买儿童色情DVD。 他时常跟同事抱怨:“日本的规定太多,萝莉控之类的东西流通得不是很彻底。” 在案发前,他曾跟同事说:“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东南亚女孩,她的年龄和小凛差不多。我为此感到自豪。” 和小凛一样倒在回家路上的,还有六年级的12岁学生堀本沙彦。 2005年12月10日,时年23岁的老师萩野裕用刀刺死了他的学生堀本沙彦。
·中学时的涩谷康政 涩谷康政每个月要花费大概100000日元购买儿童色情DVD。 他时常跟同事抱怨:“日本的规定太多,萝莉控之类的东西流通得不是很彻底。” 在案发前,他曾跟同事说:“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东南亚女孩,她的年龄和小凛差不多。我为此感到自豪。” 和小凛一样倒在回家路上的,还有六年级的12岁学生堀本沙彦。 2005年12月10日,时年23岁的老师萩野裕用刀刺死了他的学生堀本沙彦。  ·萩野裕(左)在堀本沙彦(右)就读的补习学校担任老师 因萩野裕的教学手段粗暴,经常辱骂、体罚自己,堀本沙彦跟家人反映了这件事。 随后,萩野裕便收到了一封匿名投诉信。在被校长教训了一顿后,萩野裕固执地认为那封投诉信正是来自于自己经常辱骂的堀本沙彦。 一个杀人计划逐渐浮上他的心头。 12月10日,放学路上,萩野裕先是想用锤子敲击堀本的后脑勺,但没瞄准,失手了。 大为恼火的萩野裕发狂一般地把堀本击倒在地,用匕首在堀本的脖子、脸和头部分别刺了至少10刀。
·萩野裕(左)在堀本沙彦(右)就读的补习学校担任老师 因萩野裕的教学手段粗暴,经常辱骂、体罚自己,堀本沙彦跟家人反映了这件事。 随后,萩野裕便收到了一封匿名投诉信。在被校长教训了一顿后,萩野裕固执地认为那封投诉信正是来自于自己经常辱骂的堀本沙彦。 一个杀人计划逐渐浮上他的心头。 12月10日,放学路上,萩野裕先是想用锤子敲击堀本的后脑勺,但没瞄准,失手了。 大为恼火的萩野裕发狂一般地把堀本击倒在地,用匕首在堀本的脖子、脸和头部分别刺了至少10刀。  独处,是癫狂老师向学生举起屠刀的时刻。 1990年3月26日,广岛县丰田郡一名38岁的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河内武史开车带着自己班12岁的女孩博美去了郊外,并勒死了她。
独处,是癫狂老师向学生举起屠刀的时刻。 1990年3月26日,广岛县丰田郡一名38岁的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河内武史开车带着自己班12岁的女孩博美去了郊外,并勒死了她。  博美被发现时,仰面躺在汽车后座上,身穿红色运动衫和白色裙子,身上盖着一块布。 自1989年9月起,这位老师屡次猥亵博美,最终演变成凶杀惨剧。 博美在小学毕业论文中写道:“在学校,我喜欢学习体育和音乐,进入初中后,我想多打篮球。十年后,我想做一名学校老师。”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了,单拿出几个极端事件就能代表日本小学老师杀学生吗? 但要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自1990年以来,日本最高的谋杀犯罪率也不过是十万分之0.6,这几宗杀人案,每一次都能登上国家级头条。
博美被发现时,仰面躺在汽车后座上,身穿红色运动衫和白色裙子,身上盖着一块布。 自1989年9月起,这位老师屡次猥亵博美,最终演变成凶杀惨剧。 博美在小学毕业论文中写道:“在学校,我喜欢学习体育和音乐,进入初中后,我想多打篮球。十年后,我想做一名学校老师。”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了,单拿出几个极端事件就能代表日本小学老师杀学生吗? 但要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自1990年以来,日本最高的谋杀犯罪率也不过是十万分之0.6,这几宗杀人案,每一次都能登上国家级头条。  而你也可能感到疑惑,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老师为啥会杀学生呢,杀的还是不超过12岁的小学生? 难道是因为学生不听话,天天调皮捣蛋?还是跟家长有仇,想杀人泄愤? 老师杀学生的问题本质,其实是日本教育界较少讨论的校园暴力、欺凌以及体罚导致的。
而你也可能感到疑惑,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老师为啥会杀学生呢,杀的还是不超过12岁的小学生? 难道是因为学生不听话,天天调皮捣蛋?还是跟家长有仇,想杀人泄愤? 老师杀学生的问题本质,其实是日本教育界较少讨论的校园暴力、欺凌以及体罚导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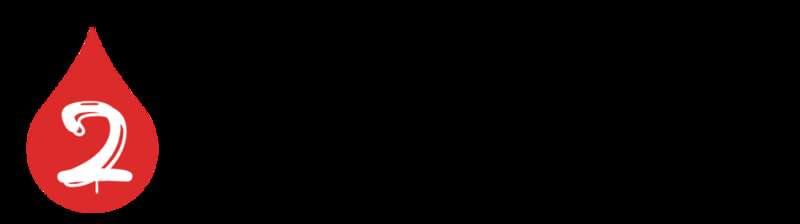
火药桶校园 在日本校园,有两根雷管压在学生和老师的身下,一根是体罚,另一根是欺凌。 根据东京教育委员2020年抽调的数据,体罚率从1990年的40%降到了2020年的5%。
 但这里边水分很大,因为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的规定,体罚的定义是“身体上的纪律处分”。 按照这个定义,“打人”当然是体罚,但“打压暴力学生”是纪律处分,所以不是体罚。
但这里边水分很大,因为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的规定,体罚的定义是“身体上的纪律处分”。 按照这个定义,“打人”当然是体罚,但“打压暴力学生”是纪律处分,所以不是体罚。  ·电影《七岁之后》 所以就出现一种现象,家长投诉学校老师体罚学生,但学校说按照规定你这不算体罚。 拿日本熊本市的学校举例,2018年,当地教育部门收到了来自儿童和家长的大约 50 份关于体罚的报告。其中,学校认定为体罚的案件2015年为1件,2016年为0件,2017年也是0例。 但记者北哲郎2021年采访了当地共500名初中生和小学生,其中有216人表示曾经受到过体罚。
·电影《七岁之后》 所以就出现一种现象,家长投诉学校老师体罚学生,但学校说按照规定你这不算体罚。 拿日本熊本市的学校举例,2018年,当地教育部门收到了来自儿童和家长的大约 50 份关于体罚的报告。其中,学校认定为体罚的案件2015年为1件,2016年为0件,2017年也是0例。 但记者北哲郎2021年采访了当地共500名初中生和小学生,其中有216人表示曾经受到过体罚。  日本的老师,最喜欢击打孩子头部,或是用巴掌扇脸、罚站、用球砸他们等。
日本的老师,最喜欢击打孩子头部,或是用巴掌扇脸、罚站、用球砸他们等。  2019年,东京町田市町田综合高中一名高一学生被50多岁的老师发现打了耳洞,老师把他叫到走廊里,先是骂他:“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是在和谁聊天?” 后来直接拳脚相向。
2019年,东京町田市町田综合高中一名高一学生被50多岁的老师发现打了耳洞,老师把他叫到走廊里,先是骂他:“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是在和谁聊天?” 后来直接拳脚相向。  学生倒地后对着老师喊:“我要在推特上‘烧’死你。”结果又被老师拎起来揍了一顿。 2019年6月,大阪市立小学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遭到教工的殴打: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一个60多岁的老头把孩子压在身下5分钟,大呼骑大马。
学生倒地后对着老师喊:“我要在推特上‘烧’死你。”结果又被老师拎起来揍了一顿。 2019年6月,大阪市立小学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遭到教工的殴打: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一个60多岁的老头把孩子压在身下5分钟,大呼骑大马。  学校不承认,家长难维权,学生求助无门,只能上论坛诉苦。 与日本官方风平浪静的数据相比,在论坛上,有关体罚的求助则是屡见不鲜。 有的孩子说自己被老师揍了,还说老师要杀了自己。
学校不承认,家长难维权,学生求助无门,只能上论坛诉苦。 与日本官方风平浪静的数据相比,在论坛上,有关体罚的求助则是屡见不鲜。 有的孩子说自己被老师揍了,还说老师要杀了自己。  因为留长发和染发,被班主任语言上死亡威胁。
因为留长发和染发,被班主任语言上死亡威胁。  而这种冲突,最后往往会激化成要么学生杀老师,要么老师杀学生的流血事件。 有些学生被骂了气不过,会和老师打起来,比如一名 30 岁的女班主任,在放学后警告三年级学生“一定打扫干净教室”,三年级学生大怒,踹了老师肚子四脚。 在日本课堂上,也经常会出现学生打老师的行为。
而这种冲突,最后往往会激化成要么学生杀老师,要么老师杀学生的流血事件。 有些学生被骂了气不过,会和老师打起来,比如一名 30 岁的女班主任,在放学后警告三年级学生“一定打扫干净教室”,三年级学生大怒,踹了老师肚子四脚。 在日本课堂上,也经常会出现学生打老师的行为。  在爱知县,高中生一把将老师推倒。老师倒在地上,攥紧了拳头又无力地垂下。
在爱知县,高中生一把将老师推倒。老师倒在地上,攥紧了拳头又无力地垂下。  而一个悲观的事实是,这些老师之所以喜欢体罚,是因为他们就是体罚下长大的学生。 在一项4000名教职员工对体罚是否有存在必要的调查项目上,36.6%的老师认为体罚是必要的。
而一个悲观的事实是,这些老师之所以喜欢体罚,是因为他们就是体罚下长大的学生。 在一项4000名教职员工对体罚是否有存在必要的调查项目上,36.6%的老师认为体罚是必要的。  这些体罚的支持者,有70%曾经经历过体罚。经历过体罚的人倾向于认为体罚/暴力是必要的。 体罚,就这样纠缠着日本的学生和老师,让前者从受害者向施暴者转化,让后者从施暴者向夺命者演变。
这些体罚的支持者,有70%曾经经历过体罚。经历过体罚的人倾向于认为体罚/暴力是必要的。 体罚,就这样纠缠着日本的学生和老师,让前者从受害者向施暴者转化,让后者从施暴者向夺命者演变。  而除了体罚,对小学生的畸形之爱,高发的性欺凌也是老师杀学生的诱因。 2020年,日本有200名公立学校教师因性犯罪、性暴力等受到处罚。 在体育馆后面,班主任对小学二年级学生表白,对她说:“我爱你,这不是简单的爱,是真爱,要对你爸妈保密哟!”
而除了体罚,对小学生的畸形之爱,高发的性欺凌也是老师杀学生的诱因。 2020年,日本有200名公立学校教师因性犯罪、性暴力等受到处罚。 在体育馆后面,班主任对小学二年级学生表白,对她说:“我爱你,这不是简单的爱,是真爱,要对你爸妈保密哟!”  随着2019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学生在家只能上网课,但物理上的隔离反而让心里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先是不断有学生自杀。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2020年,日本学童自杀人数总计 499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100 人,创下197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然后是一些老师性欺凌行为的集中爆发。 2022年,1月12日,日本板桥区29岁的小学教师高桥义之被捕入狱。 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间,他曾多次猥亵自己班级的三名女学生。 他经常假装巧合,多次重复抚摸女孩的乳房,或者把女孩带到空无一人的教室抚摸胸部。
随着2019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学生在家只能上网课,但物理上的隔离反而让心里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先是不断有学生自杀。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2020年,日本学童自杀人数总计 499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100 人,创下197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然后是一些老师性欺凌行为的集中爆发。 2022年,1月12日,日本板桥区29岁的小学教师高桥义之被捕入狱。 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间,他曾多次猥亵自己班级的三名女学生。 他经常假装巧合,多次重复抚摸女孩的乳房,或者把女孩带到空无一人的教室抚摸胸部。  津幡町立条南小学的田中干浩老师,在小学女厕所安装了2台偷拍用的小型摄像机,用以满足自己的偷窥癖。 同时,由于信息大爆炸,一些小学生十分早熟,还会向老师告白,加剧了不伦之恋的发展。
津幡町立条南小学的田中干浩老师,在小学女厕所安装了2台偷拍用的小型摄像机,用以满足自己的偷窥癖。 同时,由于信息大爆炸,一些小学生十分早熟,还会向老师告白,加剧了不伦之恋的发展。  六年级女孩爱上学校老师。
六年级女孩爱上学校老师。  以上,便是日本当今小学和其他校园内一个侧面的速写。 整个日本教育界,看似风平浪静,但这种平静,更像是压力过大时所有人都自觉保持缄默的本能。 时间在前进,人类自诩的文明也在进步,而体罚和欺凌等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以上,便是日本当今小学和其他校园内一个侧面的速写。 整个日本教育界,看似风平浪静,但这种平静,更像是压力过大时所有人都自觉保持缄默的本能。 时间在前进,人类自诩的文明也在进步,而体罚和欺凌等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如果日本教育的诸多弊病不从根本上解决,那极端事件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不断累加的压力和恶性事件,让教育系统处于崩溃的临界点。 那个即将来临的崩溃,或许是现在,或许是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