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8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余明锋,头图来自:《理想之城》
近年来,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因几本直指当代社会病症的小册子而名声大噪。其《倦怠社会》一书中大加发挥的“绩效社会”,更是走红。
相比于福柯的“规训社会”,“绩效社会”看似从否定转向了肯定,但实则是直指风行廉价的“鸡汤”和亢奋的 “鸡血”,并落入无尽的抑郁。这种普遍的抑郁既是自我压榨之后松懈下来的无力,也是进一步升级自我压榨的无能,更是猛然省悟到无边无意义的绩效追求之后的内在颓丧。
从他者的否定性暴力到自身的肯定性暴力的转变,因此,自由也变成了一种强制。余明锋对韩炳哲“绩效社会”做了辩证的分析,虽是哲学探讨,但语言并不晦涩,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气息。
一、绩效:词语与现实
“绩效社会”是一个新词,绩效却不然。更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绩效社会”,在汉语世界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绩效”这个词早就融入日常语言之中,渗入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无论是讲授管理学理论的专家们,还是从事管理实践的企业主,甚至医院、大学等各式机构的各级管理者,也都把“绩效”这个词挂在嘴边。绩效或KPI更是精确丈量着每一个“打工人”的日常步伐。
我们已然深处“绩效”的无形支配之中,欲罢不能。而“绩效社会”正是有关于此的一个反思性概念。这个概念的兴起,首先就和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有关。当下社会,特别是一线城市,已然进入到一个绩效主宰价值评价,并且绩效主宰的负面效应已然充分显现的阶段。
一种过于亢奋的、仿佛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和过于忧郁的、仿佛无尽头的倦怠感同时在社会中蔓延。“内卷”和“躺平”这两个词的流行,正是这种亢奋和抑郁之一体两面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
“绩效社会”概念近几年的兴起乃至流行,在另一方面,和韩裔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分不开。韩炳哲一九五九年出生于汉城,后来前往德国求学。他原本的研究领域是海德格尔哲学,他的思想底色中也一直留有海德格尔的身影。近十年左右,韩炳哲发表了一系列对当下社会做出诊断的小册子,并因此成名。
韩炳哲的小册子在全球阅读市场上的爆红,我以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他的论述直指当代社会病症,总体来说可谓一种社会病理学考察,尤其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病理学考察。不过,在一个已然全球化的时代,他的考察不仅在西欧和北美,而且也在东亚等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读者在他的诊断中很大程度上读到了,部分意义上也读懂了自己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的论著篇幅都极为短小,可即便在这短小的篇幅之内,论述也呈现出很强的“片段性”,而这也正符合他所诊断的绩效社会的阅读习惯,满足了这种“浅阅读”“快阅读”的需要。韩炳哲在这个意义上不但做了诊断,而且还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这种诊断。
二、暴力的变形:从规训社会到绩效社会
无论如何,韩炳哲尤其长于以极简的文字做种种社会病理学诊断,而其中最为根本的诊断乃是绩效社会,他对社会、心理、艺术和政治等领域所做出的广泛诊断事实上都围绕于此。
以思想史的眼光看,韩炳哲的“绩效社会”概念是针对福柯的“规训社会”概念提出来的。他在著作中看似常常批判福柯或受福柯影响的当代理论家(如阿甘本等),可其实他正借着这种批判才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才为自己的病理学诊断做了清晰的定位:
“福柯的规训社会由监狱、医院、兵营和工厂组成,它无法反映今天的社会。他所描述的社会早就被一个由玻璃办公室塔楼、购物中心、健身中心、瑜伽馆和美容医院组成的社会所取代。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不是规训社会,而是绩效社会。”(韩炳哲:《暴力拓扑学》,128页)
绩效社会的概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因为韩炳哲而流行,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这个概念并不是他发明的。
事实上,“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在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论述中,绩效社会是一个早已有着很多学术讨论的概念。但韩炳哲做了一种哲学上的概念提纯,通过思想史参照系的建立,将之提升为一种有着社会诊断和时代批判意义的历史哲学概念。
具体来说,“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相应的情态动词是“不允许”(Nicht-Dürfen)和“应当”(Sollen,韩炳哲:《倦怠社会》,16页)。而绩效社会是一个肯定性的社会或积极社会,一个被激励机制所鼓舞的社会,它所对应的情态动词是“能够”(K.nnen):
“禁令、戒律和法规失去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种种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规训社会尚由否定主导,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疯人和罪犯。与之相反,绩效社会则生产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同上)
然而,一个积极进取的社会为何会批量生产“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呢?
韩炳哲的绩效社会论,最重要的在于强调,从规训到激励的转变并非自由的实现和暴力的消失,而是从他者的否定性暴力到自身的肯定性暴力的转变。
也就是说,通常的暴力现象和暴力概念正以否定性和他者性为基本特征(暴力通常是由他者施加的,或者是施加给他者的,并且无论其陈述还是实施通常也都以否定性为特征),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新型暴力,并因其肯定性和自身性而不易被觉察。韩炳哲的绩效社会论因此根本上主张,暴力在当今社会完成了从否定性向肯定性、从他者性向自身性的突转。
相应地,韩炳哲针对福柯的“生命政治”而提出了“精神政治”或“灵魂政治”的概念。“生命政治”的概念之所以要让位于“精神政治”,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由非物质和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所确定的。被生产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像信息和计划这类非物质的东西,作为生产力的肉体再也不如在生命政治性规训社会那么重要了。为了提高生产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优化思想逐渐取代了规训肉体。”(韩炳哲:《精神政治学》,33—34页)
韩炳哲以此又从生产力形态的转变论述了他的绩效社会论。绩效社会不但完成了暴力从否定性向肯定性、从他者性向自身性的突转,而且也完成了从肉身向精神的转变。也因此,《暴力拓扑学》《精神政治学》和《倦怠社会》一起构成了他阐发绩效社会的主要著作。
要言之,暴力并未消失,而是伪装成自由的形态隐蔽地出场。可问题在于,自由何以变成了一种强制?并且甚至是一种比规训更深入、更普遍的强制?
首先,“应当”的形态是触目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能够”的形态是积极的,范围则近乎无限,绩效社会的“能够”于是比规训社会的“应当”更让人不加防备,也更加无可防备。其次,在绩效社会的量化考核体系中,这种强迫是每个人加给自己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自我统治和自我管理,是一种无边的“自裁”和“自我剥削”。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企业主”,沉溺于内在而隐匿的自我暴力。于是,绩效社会在一方面风行廉价的“鸡汤”和亢奋的“鸡血”,在另一方面又落入无尽的抑郁。
这种普遍的抑郁既是自我压榨之后松懈下来的无力,也是进一步升级自我压榨的无能,还是猛然省悟到无边无意义的绩效追求之后的内在颓丧。
“抑郁症和过劳症这些心理疾病表达了自由的深度危机。这些都是今天自由向强制转化的病理性征兆。”(《精神政治学》,2页)
这种亢奋和抑郁的交织正是我们时代典型的内在性状况。韩炳哲又用“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来形容现代绩效主体:
“一只鹫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倦怠社会》,1页)
绩效社会因此也是一个倦怠社会。

三、反思:规训与绩效的交织?
在勾勒了韩炳哲对绩效社会所做的病理学考察之后,我们要指出,他的绩效社会论确实有着切中时弊的洞见,可也有偏颇之处。我们不能停留于介绍韩炳哲的思想,而是要对他的考察做出批判性考察,接着他的洞见去更为深入地分析我们时代的精神现象。
首先要追问的是,我们真的如韩炳哲所断言的那样告别了“规训社会”吗?从规训社会向绩效社会的范式转换,实际上是从政治主导向经济主导的范式转变。就此而言,这个断言在相当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时代的政治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呈现出科技-资本竞争的形态。
可政治并未消失,政治毋宁是人之为人的生存现象,它可以隐匿却并不会消失。当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随着全球化的受阻而愈发尖锐的时候,原本看似消除的对立、原本隐匿的政治又以显赫的姿态回归了。并且这种回归的政治对外不只是贸易的,而且也是划分敌我的;对内不只是绩效导向的,而且仍然是规训的。哪怕发达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在相当程度上也仍然是“规训社会”。韩炳哲的论断因此有着夸大其词的嫌疑。
再比如,韩炳哲对弗洛伊德做了一种历史化解读: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不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存在。它是压迫性规训社会的产物,如今我们已经逐渐与之告别。”(《倦怠社会》,66页)
类似的段落虽然充分彰显了韩炳哲的哲思想象力,可也体现了他过于夸张的断言。公允地说,二十一世纪除了是规训社会,还是绩效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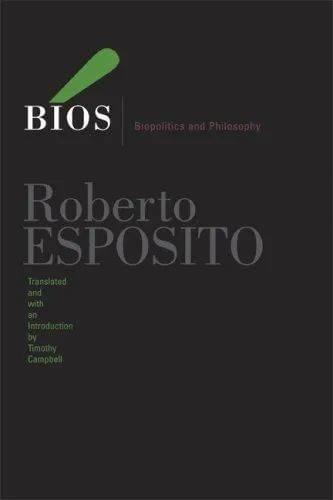
其次,他异性并未真的消失。在《倦怠社会》中,韩炳哲主张当代社会的问题不是对他者的排斥,而是他者的消失。所有的他者都丧失了他者性,陷入了自恋型主体的同一性暴力。他由此反驳当代理论家(如意大利思想家埃斯波西托)从免疫学模型出发的社会诊断。他提出,以否定性为特征的免疫学是二十世纪的范式,“二十世纪是免疫学的时代”(《倦怠社会》,4页)。
而二十一世纪的范式则是由“过量的‘肯定性’”所导致的各种精神疾病,其中尤以抑郁症为代表:“从病理学角度看,二十一世纪伊始并非由细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经元主导。”(《倦怠社会》,3页)规训社会和免疫模式互为表里,相应地,绩效社会也和同一性模式互为表里。
以政治学的语言来说,从规训社会到绩效社会是“内政”上的转变,从排他的免疫模式到同一性模式则是“外交”上的新政。然而,与规训社会过时论一样,免疫模式过时论,同样存在夸大其词的嫌疑。“免疫学范式和全球化进程彼此不能相容”的论断恰足以印证这种夸大其词(《倦怠社会》,7页)。
我们无疑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可近几年的全球化状况充分说明了“他者”的现实存在。新冠疫情更是表明免疫学模式并未真的过时。当然,与民族国家之间乃至不同的文明体之间的冲突相比,当下世界的芸芸众生确实更多地生活在“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肯定性暴力”之下。可否定性暴力并未真的退出历史舞台。
再次,不但绩效社会仍然是规训社会,而且规训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然显现出绩效社会的要素。生命绩效化的年代并非从二十一世纪才开始,而是早已来临。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工业流水线已经是全面绩效化的基本隐喻。只不过当下的技术发展,使得这种自我暴力的手段进一步升级。我们不仅能够称量体重,而且能够计算步数;流水线不仅在工厂里,而且通过智能手机被我们随身携带了。从“流水线”到“平台”和“快递”,我们完成了一次绩效社会的升级。
现代技术带来的绩效考量的无孔不入,确实使得绩效考量升格为时代的精神特征。并且,这种深入现代原子内部的绩效考量也使得外部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变得隐匿化和内在化。因此,尽管韩炳哲的论述有着夸大其词的问题,我们仍有必要明确提出绩效社会的概念。
最后,韩炳哲的绩效社会论忽视了传统绩效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后的政治学、伦理学和福利经济学论述中,绩效首先是一个正义原则。市场导向的社会定然会有财富分配的不均,而绩效原则为这种无可避免的不平等现象做了合理化论证。
用通俗的话来讲,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有冒险精神、他们有经营和管理的才能等等。总之,那是他们的绩效。事实上,以身边的现实来看,以绩效为评价标准的单位,也仍然被认为是比较公平的,至少是让大家都感到无话可说的。这也是我们在深切体察了量化考核的种种弊端之后,仍然不得不奉行之、拥护之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正义原则的绩效有着诸多前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机会均等原则。如果没有机会均等的保障,那么以绩效来做合理化论证,就是掩人耳目的伎俩了。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在大体上落实机会均等的原则,绩效主体又会反过来对“起点”进行残酷的竞争。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就成了绩效社会的另一种景观。当下社会的教育乱象,不正与此颇有关联?
反观韩炳哲,他的绩效社会论虽然有着清晰的批判意旨,可因为他一味强调当代历史的断裂性,这就造成了某种严重的偏颇,反而使得这种时髦的社会绩效论丧失了传统绩效论在分配正义问题上所蕴含的批判性。
四、自由的困境:现代性承诺的落空?
在指出韩炳哲的偏颇和夸大的同时,我们仍然要说,即便夸大其词,可他的诊断仍有切中时弊的意义,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而其中尤为值得深入探讨的,是现代性的自由承诺的落空。
我们现代人的历史意识与现代社会的自由承诺分不开,因为正是这种自由的承诺,使得现代自觉地区分于古代并以进步的姿态走向未来,由此打开了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当中。停留于主奴区分的主人并不真的自由,从事劳动的奴隶反而抓住了自由的契机,历史也将在人格平等的相互承认中终结。而这种终结也就意味着主人和奴隶的一同消失。
冷战结束后,日裔美国政治家福山看到了这样一幅愿景的实现,于是他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可我们今天在绩效社会所看到的,一方面是以绩效考核为导向的工作丧失了解放的潜能;另一方面,则是奴隶和奴隶主并未真的消失,而是内化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现代的自由理解以成功的自我主宰为模型,可自我主宰在现实中显现为一种自我奴役。于是,在前现代社会仍然大量存在的非奴役状态下的自由,在现代社会反而被大规模地剥夺了。
当然,黑格尔仍然致力于推进现代性的自由承诺,他并没有朝这个方向设想自己的主奴辩证法,这也是他和尼采的重大区别。
尼采的“末人说”正是在现代社会的终局看到了普遍的无意义状态,而韩炳哲的绩效社会论进一步断言,这种普遍的无意义状态还是普遍的自我奴役状态。放弃超越性的末人并不如他们自己所以为的那般幸福。
现代的合法性基于一种自由的承诺,而规训社会和绩效社会的论题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承诺的落空。无论福柯式规训社会,还是韩炳哲所谓的绩效社会,承接的都是韦伯以来的合理化命题和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在提醒我们,要小心解放本身带来了新的奴役!
“如果我们将主奴辩证法理解为自由的历史,那就还不能谈论什么‘历史的终结’。我们离真正的‘自由’还差得很远。今天的我们尚处于一个主奴一体的历史阶段。”(《爱欲之死》,40页)
如此说来,我们不再是主人,也不再是奴隶,可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而是“主奴”或“奴主”,是主奴一体的形态,是自由的假象?

无论如何,只有当我们戳破自由的假象,批判现代性过度的自由承诺,才能摆脱现代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焦虑,摆脱由此而来的新的奴役形态。或许,自由人的普遍承认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历史愿景?无论如何,我们还要承认人的有限性、生命必然包含的否定性,和人群无可免除的他异性,并在这样一个人性自然的地基之上重新理解我们的自由。
(《暴力拓扑学》,[德]韩炳哲著,安尼、马琰译;《倦怠社会》,[德]韩炳哲著,王一力译;《精神政治学》,[德]韩炳哲著,关玉红译;《爱欲之死》,[德]韩炳哲著,王一力译。以上皆中信出版集团二〇一九年版)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8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余明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