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 (ID:sdrenwu),作者:斯南,题图来自:受访者
与李继宏聊天,你会惊讶于他语言的高密度性,以及言谈中丰厚的文化底蕴。
与他在译文中表现出的清晰流畅,典雅又富于意象的风格很相似,李继宏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同样用词精准,极富画面感。比如聊到文学启蒙,他三言两语,就将听者拉回那个时空,仿佛和他一起站在家门口,眺望墙上字句:
“我母亲抱着我,坐在我们家那个老房子里,指着墙上一幅字,横的字。那个房子是门朝南,墙上的字贴在东边,她抱着我坐在西边,教我背那一首诗。那是唐伯虎的《落花诗》:“刹那断送十分春,富贵园林一洗贫”,我对文学的最早记忆,可能就是这个。”
但这还不是李继宏身上最吸引人的特质。
他是一个做任何事都非常纯粹的人,一旦投入就要做到最好。他会为了翻译《瓦尔登湖》,花费4000多个小时查阅资料,只为弄清梭罗著作中所引用的东西方经典,以及新英格兰地区动植物的名字;他会为了《傲慢与偏见》中一个不清楚意思的句子,整整三个月不动笔;他也曾为了翻译《喧哗与骚动》,远赴美国,向研究福克纳的权威专家学习。
自25岁那年翻译的《追风筝的人》成为现象级热销书后,李继宏就成了各大出版社争相约稿的译者,他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频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并非文学或翻译专业出身,社会学才是他大学的主业。甚至,他大三时的课程论文,还曾被刊登在《社会学研究》这本行业内的一级期刊,成为该杂志40多年历史上,仅有四篇以本科生身份发表的论文之一。
2003年,李继宏因缘巧合采访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自此开启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兴趣。

时至今日,成为知名译者的他身上被贴了许多标签——“天才翻译家”、“网红译者”......但他对自己的定位,却还是最初那一个:对作品全力以赴,用心负责的翻译人。
2019年6月,李继宏开始着手翻译颓废世代“圣经”《在路上》。这本书的完成是文学史上的一桩惊人壮举,作者凯鲁亚克仅用三个星期,将自己从1947年到1951年间,三次横穿美国和一次南下墨西哥的经历,写成了一部12万单词的作品,不分段打印在画纸上,拼成了一幅37米的长卷。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是一段夹杂着艰难与感动的神奇旅程。李继宏说,这是他在翻译生涯中的第三次失态。译完全书后,年近不惑的他失声痛哭,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
恰逢凯鲁亚克诞辰100周年,经历漫长等待后,李继宏翻译的《在路上》终于正式出版。而十点人物志也得以借此机会,与李继宏聊一聊他翻译过程中那些或艰辛或有趣的细节,透过他本人的故事,我们也得以窥见,热爱与纯粹对人生最终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下是李继宏的讲述。
1. “一旦选择,就全力以赴做好它。”
最早开始做翻译,其实很偶然。
我有一个目前在北大社会学系当教授的朋友,学生时代就认识了,以前经常在论坛讨论一些学术问题。
2004年,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说他有个师姐在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工作,当时世纪文景买了一本外国小说,很难,找不到人翻译,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我本科念的社会学,经常需要阅读英语撰写的社会学著作,再加上我在学校时,常在网上跟人切磋英语,所以他们都觉得我英文很好。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没译过书,试试吧。于是就帮他们试了一下。大概试了一千多字,他们觉得质量很好。最后就帮他们译了《维纳斯的诞生》,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
2005年年底,世纪文景又找到我,让我帮他们翻译《追风筝的人》。这本书出版后,很奇怪地卖得很好,一时间国内几乎所有做外国文学的出版社都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他们翻译书籍。有些先找我的我就接受了,现在看来,也译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书。
就是这样,我慢慢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

但这个时候,我还只是把翻译当一份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当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受管束,可以在家里工作,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虽然并没有特别地热爱这件事,但我很用心地去做,每一本书我都很用心地去做。
2007年我辞职在家,专职做翻译。那时做翻译酬劳很低,一千字六十块钱、八十块钱,书译完一般也拿不到钱,要等书出来几个月,或者半年后才会付款。
这就导致我在2008年的时候生活很艰难,差点放弃翻译工作。
就是这个时候,我翻译了一本书,名字叫《公共人的衰落》。这是一本社会学经典,1972年在美国出版。到2008年为止,已经卖了三十几年,前后出过多个版本。但我在翻译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不少错误——有一些是作者写错了,有一些是笔误,出版社没有改过来。总共大概有几十个错误。
我把所有错误都整理出来,做了一个勘误表。翻译完成后,我把表格寄到作者的电子邮箱,邮件里写道:“我翻译了你的这本书,里面有这么多错误,下回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加印的时候改一改。”
这本书的作者叫理查德·桑内特,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他接到我的邮件后很高兴,他没想到在这本书出版这么多年后,还能被一个中国人挑出如此多错误,所以他一下子就觉得,这个翻译很有水平。
桑内特回信给我说:“特别感谢你,我希望以后我所有的书都由你来翻译”。我给他回信,我说我也喜欢你的书,的确写得很好,但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会饿死的。
那一本《公共人的衰落》,我翻译了8个月,最后拿到18000多块钱的稿费,扣税后只剩1.6万元。他听到后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这样,美国有很多基金会,我去给你申请一笔资助,你把简历发给我。
我将信将疑,做了一份简历发给他。隔了两天,他回信给我,说帮我要到资助了,有一万美元,让我把银行帐号发给他。我虽然心里有些疑惑,但没有多想,还是把银行帐号给他了。
又隔了两天,我的账户就收到了6000英镑,大约一万美元。可我一看不对,汇款人的名字是桑内特本人,这个钱是教授自己汇过来的。
我对他说,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再穷也不能拿。他回信骗我说,你不懂,我给你这么多钱,我年底交税的时候就可以少缴这么多钱。我也不懂嘛,当时的确也很穷很缺钱,就厚着脸皮收了下来。
这笔钱帮我度过了我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桑内特的6000英镑,我今天很大可能不会再做翻译。我后来要还钱给他,他也不要。我觉得欠他很大一个人情,就以较低的稿酬翻译了他写的两本书,一本叫《匠人》,一本叫《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接下来我还会再译一本他的《在一起》。
桑内特帮助我的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原来作为译者,你不仅能对读者有帮助,反过来对作者也有帮助,你可以帮他在国内扩大他的影响,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2009年,我翻译的《与神对话》出版后,有特别多的读者和我反馈,说这本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有的读者说,自己本来是有抑郁症的,看完之后神奇地好了。有一些读者说,本来跟家里人相处不好,看了这本书之后,开始明白怎样去面对与家人的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
这让我感觉到,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除了自己的收获之外,能够帮助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读者。所以慢慢地,我从只是把翻译当作一个工作,变为将翻译当作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热爱的事情来做。

很多时候,可能最初的选择不是你最喜欢的,但你还是要全力以赴做好它。当你全力以赴做好它之后,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也许你会喜欢上它,也许你会有其他职业道路的发展。
无论做什么,两个字很重要:敬业。
不敷衍、不将就,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2. 我们这代人的困境是什么?
动笔译《在路上》,是在2019年秋天的上海。当时新冠疫情尚未开始。
完稿是在2020年5月的美国加州橙县。正值美国病毒肆虐,时局动荡不安。
当时我年近不惑,早已见惯人间悲欢离合,万万没料到译完全书后,竟然失声痛哭,过了很久很久,才平静下来。
我本来就很喜欢凯鲁亚克他们这帮人。
除了凯鲁亚克,还有艾伦·金斯堡、威廉·巴洛兹那一批人,所谓的“颓废世代”我都很喜欢。我反对把他们译成“垮掉的一代”,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不是单纯的垮掉,他们有理想,他们的理想是反战,反原子弹的核讹诈。金斯堡曾写过一首诗《美国》,在诗里,他要求美国用原子弹干掉它自己,不要总想着用原子弹轰炸别人。
在那个时代,他们其实是进步青年,是社会主义好青年,只不过在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下,他们被打压,他们的政治抱负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理想没有办法施展,所以过上了很颓废的、及时行乐的日子。
但他们的思想是进步的。他们追求自由、追求平等,在种族歧视严重的50年代,他们最崇拜的却是黑人,凯鲁亚克甚至说“我恨不得自己是一个黑人”。
2006年,我第一次读到《在路上》原文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很好看。到我翻译之前,我又读了很多“颓废世代”的资料,把凯鲁亚克所有的作品读了一遍,把他的信、他的日记,各种各样的都看了一遍,对他有了很深的了解。有时为了确认某个单词的解释,我会同时看西班牙语、法语、德语、还有意大利语共四个译本的处理。
看到最后,我看到的不再是一本小说,而是仿佛进入他们人生的片段,感觉他们就像是我的朋友。
整本书全部翻译完成,大概花了9个月的时间。
它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作品。不仅是因为从我个人的价值倾向,以及它的文风、文体方面,我很喜欢它。也因为书中讲的那些事情,提过的那些地点,我都非常熟悉。
我是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2015年我在美国各处旅行,书里面讲过的城市我基本上都去过,像纽约、旧金山就不用说了,包括芝加哥、丹佛甚至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我都很熟,都去过。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有种特殊的亲切感。

但翻译这本书时,依然遇到了很多难点。第一,书中用了很多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街头语言,因为不是正式的语言,辞典查不到,所以现在很多美国人都看不进去,读不懂,这需要花费大量的功夫查阅。
第二,凯鲁亚克的父母是从加拿大去美国打工的法裔加拿大人,因此他从小说的是法语。他的英语里有大量被法语影响的痕迹,如果一个人不懂法语,很难理解他书中的内容。
还有一部分中国的东西。凯鲁亚克很喜欢中国哲学,喜欢东方禅宗思想,但他所看的作品,大多是一个叫铃木大拙的日本学者用英语翻译过来的。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铃木大拙、戈达德、凯鲁亚克等人在介绍、传播和接受禅宗思想的过程中,添加了不少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这都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把翻译还原过来。
最后一个难点是文体。这本书的初稿是凯鲁亚克喝酒、吃苯丙胺,在很嗨的状态下,用三个星期写出来的。
凯鲁亚克所强调的那种率真的写作手法,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去改,不要去推敲。但对翻译来说,这种文体很难复原。因为翻译肯定是要推敲的,你硬要推敲,和他不推敲的原文之间,矛盾怎么解决?
这讲起来很复杂,一般的译者很难理解。我的译本就是试图在最大限度上,还原凯鲁亚克想要表达的东西,他想让读者感受的东西,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在路上》这本书读到最后,你会对主人公们特别地同情,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他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但又没有反抗的余地,吸毒、喝酒、听歌、滥交,都是他们发泄的渠道。
凯鲁亚克想告诉我们,每一种癫狂的行为、每一种离经叛道的人,在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颗破碎的心,有一个破碎的、不完整的灵魂,需要我们去宽容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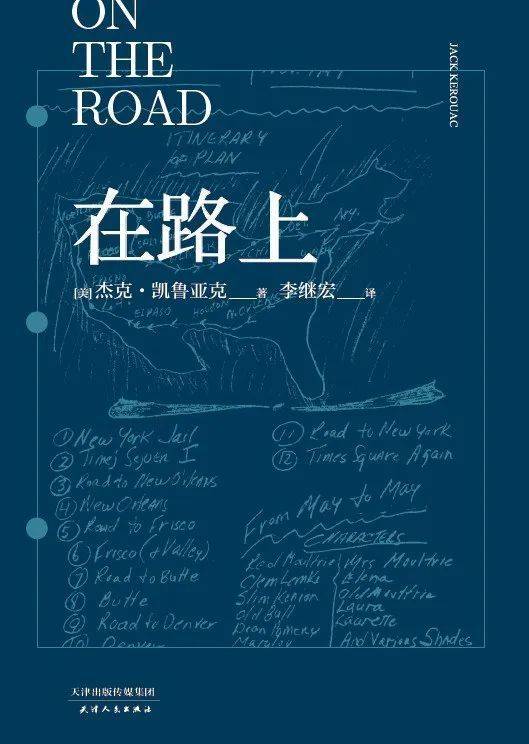
《在路上》真实反映了美国四、五十年代最大的问题,以及凯鲁亚克那代人的困境,而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又不一样。可以想到的,比如气候变暖及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的衰落,比如作为中国人会看到,中国要崛起跟美国霸权之间的问题等等。
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困境是什么,我们可以怎样应对?这是我们现在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应该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年轻读者,我觉得比较大的启发就是在这里。
3. 翻译是一门不能被表演的才艺
我一直强调说,翻译一本书之前,译者应该从知识上去包围这个作者,至少从这个书的范围内包围这个作者。作者看过什么书,写过什么书,他受过什么样的影响,你都要去了解,你才能够很好地理解他在书里要传达的意思。
我做翻译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如何帮读者构建、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让读者能够进去,能够和书中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这样才能够切身地理解他们,体会他们。
工作的时候,我起得很早,大概六、七点起来。然后就一直待在书房里,中间出来吃饭,可能晚上十点多、十一点去睡觉。但我有时候会出去旅行,不会一直在工作,这中间会劳逸结合。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精力很好,译作品很快。到现在我已经42岁,做了十七、八年的翻译,有了那么多的经验,看东西的角度也不一样,所以翻译速度会比以前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没有什么是永久不变的,工作状态也好、你的生活状态也好,什么都好,它都会发生变化。
2013年受到恶评的时候,作品被打一星时,我还年轻。当时的确也很委屈,一下子铺天盖地都在骂你,不止豆瓣,新浪微博、热搜什么的都在骂李继宏。我觉得不是他们说得那样,就会有点过激反应,非常生气,所以我会去回应。
但那不是我平常的样子。其实我从来不发火,我太太说,就没有见过我生气的样子,从早上起来就很开心,笑到晚上睡觉还在笑,她总说我就是个傻子。
发展到现在,我就不管了,就算热搜上有十个话题在骂我,我也不会看的,不会理他们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一个东西好就是好,差就是差,一个好的东西不会因为别人说它不好,它就变得不好。这方面我有百分百的自信,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水平。
从2013年到现在,差不多9年过去了,我在果麦文化(出版公司)出的译著大概卖了800万册,《追风筝的人》等其他译著卖了1500万册以上,很多读者看过我的书,这是不好糊弄的。反正我觉得,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很敬业地做翻译。
我之前跟朋友开玩笑说,翻译是一门不能被表演的才艺,它甚至是一门不能被理解的才艺。因为太专业了,很多人并不真正清楚,这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这一切也都是因为这个行业缺乏规范,没有一个上升通道,没有认证,所以一般读者不知道你水平的好与坏。
最开始我做翻译的时候,千字只有60块钱,当时是行价、公价。后来我与果麦合作,我一直呼吁要提高译者的稿酬。
这两年慢慢的,市场上翻译的稿酬有些可以提高到千字300块、500块,我觉得我是做了一点点努力在里面,有一点点贡献。但这不够,我们需要让整个行业有一些规范,能够让读者很容易地了解,这个译者他是认真的,他在行业内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译者,大家选他的东西有信心、有保障,不会出错。这样一来,整个市场也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
不过这个事情太难了,我尝试跟一些出版机构沟通,跟一些同行沟通,但是做这个事情很难,真的很难。如果这些事情能够被那些管事的人,比如说文联、作协、译协的人看到,他们愿意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会好很多。
这两年里,我没有翻译书,而是尝试了一些新的方向。我在写一本小说,一本讲美国历史的书,希望通过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来讲美国历史。
后续我想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我觉得现在的读者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像《庄子》这样好的典籍,读过的人却连总数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一直想要重新整理一些重要古籍,以现在读者喜欢的、能够接受的形式,去呈现它们。
有一些我想译的作品没有译完,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大多数人并没有理解它在英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不知道笛福所处的环境和背景。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我也会重新进行翻译。这可能要再过一些年,是将来的事情。
我还年轻,没有年纪太大,慢慢地做吧。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事情,慢慢地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 (ID:sdrenwu),作者:斯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