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蹦迪班长 (ID:MrDisco007),作者:肉孜烧烤,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城里的生活总是缺了些季节轮转的实感。
漫步于常青树和钢筋水泥构成的迷宫里,总觉时间也在此迷路,上演着以日为单位的循环。只有当诸如落雪的时刻,后颈上感到的那一激灵,才又叫人真切意识到人类的囚笼坐落在自然界之上,而自然界则片刻不停,不受人类意志左右地周转。
如今已是货真价实的春季,雨下了几场,花开了几片,连日光也变得叫人懒洋洋起来。但仔细想想,春意中总好像少了点什么。
有人说是划过天空的娇小黑影,有人说是窗前的叽叽喳喳之音。最后还是空落落的房檐给出了答案:
你们说的是燕子吧。

最先发现燕子不见的是应该是楼下的环卫工人。
虽然拿着微薄的薪水,可等待垃圾车的冗长枯燥间隙,也赋予了他们大把仰望天空——这件城市里最奢侈的活动——的机会。
“现在的小燕儿可没以前多了,我都好几年没见过燕窝咯。”说罢,环卫工人继续投入扫落叶和果子的工作——把自然从人类社会清除出去的工作。
随后意识到燕子不见的是教室里的孩子。
“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小燕子从南方赶来,为春光增添了许多生机。”
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着课文,讲台下的孩子们面面相觑。一个孩子举起手提问:“老师,春天到了,可是燕子在哪儿呢?我们都没见过真的燕子。”
老师被问住了,就像ta无法回答其他课本和现实相冲突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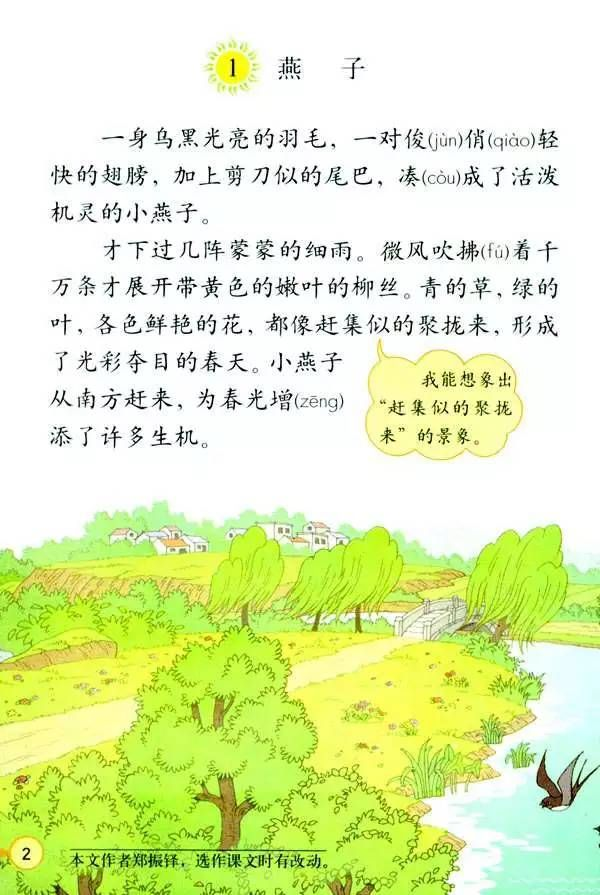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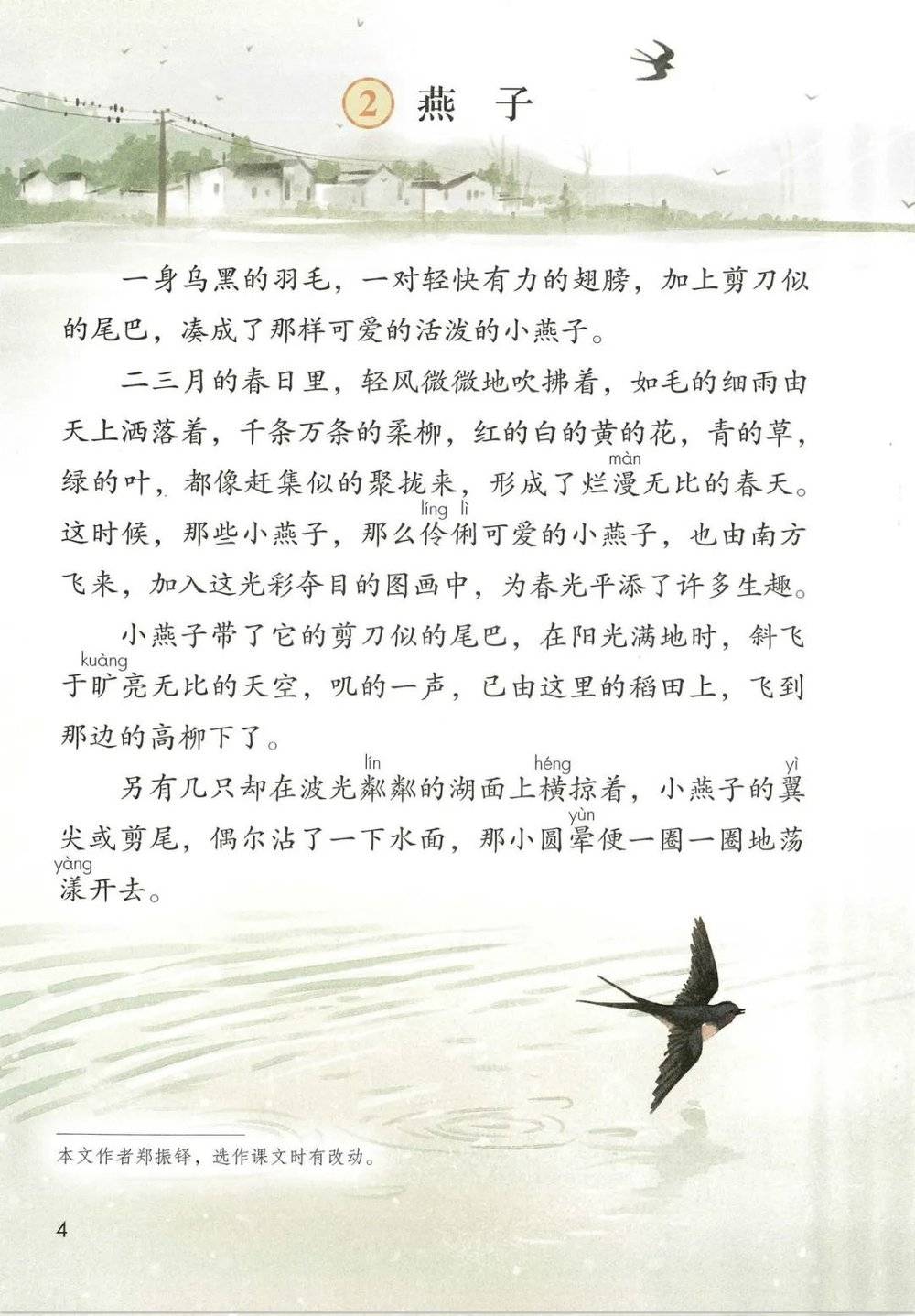
而我,则属于对这一问题后知后觉的那一批人。
即便是这份后知后觉,也得归因于防疫给生活强行按下的慢放键。在缓解时事性抑郁的阳台时间里,我开始关注平日里不曾注意的窗外鸟鸣。
粗嗓门“啊啊啊啊”叫的是“猛禽”喜鹊,趁人不注意就会企图来偷挂在阳台的腊肉吃,暴力驱赶还会招致它的仇恨,没事就往你窗户上喷屎。

窸窸窣窣的声音,八成是“野鸽子”珠颈斑鸠在空调外机上筑巢。因为筑巢相当不讲究以及身影常见多,它最近成了贴吧鸟吧的吧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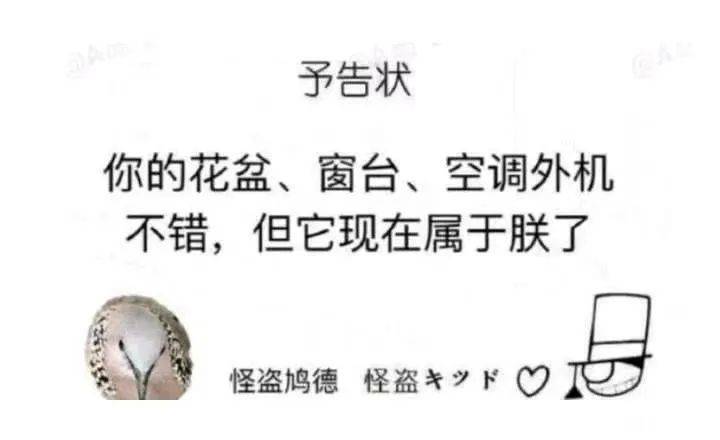
唯独记忆中那话痨般的悠长婉转叫声迟迟没有出现。如此一来,好像春天也没有真正到来。天色阴沉的降雨前夕,也见不到燕子们在低空来回穿梭。
我只得向天空望去,让视线越过那些连成铁链的屋顶,试图望回过去的光景。

1
家中有燕窝,是被神明赐福的证明。
这是每个老人传授给后代的经验包都少不了的一句碎碎念。至于到底流传了多久,老人们也答不上来,总之是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商周时诗经里就有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啧啧,你看那谁家瓦檐下的小燕儿,生了一大窝,长得真好。他们家这是有福啊。”
神选之家总会收获邻居们的连连赞叹。
对于这份上天赐礼,神选之家也会相当珍视,以便尽情享受玄学和现实里免于蚊虫骚扰的双重福气。“不许捅燕窝,不许吓唬小燕子。”神选之家的孩子都免不了此番教诲。
关于打燕子的恶果,不同地区都有各自的诅咒。
有的说打燕子头上会长藓,有的说打燕子会被雷公劈,还有的说打燕子会瞎眼。总之,破戒者关于燕子的记忆,通常都伴着屁股的隐隐作痛。
如此一来,燕子在家中的地位不会低于供桌上被烟雾缭绕的祖先,即使它们高空抛物(粪),人们也不会惊动它们分毫,只是挂上一个“屏风”。
讲究的人家从不在燕子犹在时修缮屋檐,心动的无燕人家甚至会在屋檐下打洞以便燕子前来打窝,一如宋诗《迎燕》所写:“咫尺春三月, 寻常百姓家。为迎新燕入, 不下旧帘遮。翅湿沾微雨, 泥香带落花。巢成雏长大, 相伴过年华。”
不知是做了什么不招神明待见,总之我儿时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望着别人家的燕窝干瞪眼。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衔泥燕,声喽喽,尾涎涎。秋去何所归,春来复相见。”
······
数不清摇头晃脑地背了多少关于燕子的古诗词,终于等到了一对燕子慈善家夫妇光临寒舍,在仓库的房檐盘旋着考察工地。
比起浮皮潦草的珠颈斑鸠,燕子算得上是鸟界的贝聿铭。它们的建筑材料很简单,却又很实用:泥巴、植物的小枝,分别相当于水泥和钢筋。
慈善家夫妇有只灵活的喙,既是搬运材料的推车,又是垒墙塑形的砖铲泥抹。它们找定落脚点,将口中的泥混合着唾液吐出,粘附在墙上,造出一个基点,意味着正式开工。

燕窝最初的模样是个小小的泥球,然后像小碟子,再是小酒杯,最后变成一个背篓的模样。但这还不算真正完工,要等到夫妇产下蛋,幼崽们破壳而出扯着嗓子喊饿,燕窝才从巢穴变成了它们真正意义上的家。

未出巢的小燕像一个不知停歇的合唱团,一旦张了嘴叫声就停不下来。怪的是,明明小燕嗓门很大、吵得很,声音传入人耳确实一种清细悦耳的感觉,令人心情愉悦。
天暖时,我们一家有时会将饭桌搬到院子里吃晚饭。慈善家夫妇往往也在这个时分进行投喂。于是燕子叫声就成了我们家的用餐背景音乐,虽是普通人家,却有种在高级餐厅吃饭,一旁有乐队歌手演奏香颂之感。
燕子入驻的另一个可见的好处是预报天气。
早些年天气预报没现在准,前脚预报晴空万里,后脚就可能掉起雨点。可有了燕子,只要一瞅见它们低飞了,就保准要下雨了,得赶紧扯一嗓子:“妈,收衣服了。”
叶子一黄,秋天一到,跟燕子暂时性道别的时刻也来了。
“秋天到了,小燕要飞去南方过冬了。”家里的大人如是说。彼时的我,想象着燕子在我未曾到过的江南、海南沐浴着和暖的阳光,另择一户人家建起窝。很多年以后,我才了解所谓的“南方”意味着更远的地方,远至东南亚、南非、南美。至今,我也没到过那般广阔的世界。
“小燕儿认窝,明年就又回来了。”大人又教育道。看来,燕子有时比人聪明。
当时附近有家老人得了老年痴呆,有天自己跑出去遛弯了,再也没回来。还有一家的男人在外边喝酒,晚上回家路上醉倒在雪地里,身子是回来了,邦邦硬,气儿没了。
据一位家住村里的同学说,燕子要南飞前会先聚到一块,他家后山那儿就有一块聚集地。到了时间,成千上万的燕子便不约而同的涌了过来,树枝上,电线杆上,都站得满满腾腾。待到那个无形的发令枪响起,燕子便一并飞上天空,翅膀的扑棱声能持续好几分钟,阵仗就像过完年一大堆人去挤客车回城里打工。
我从未亲眼见过那场面,或者说我还没来得及见证,就已经失去了机会——我已成了进城打工大军中的一员。迎接我的是一个人类存在感完全压倒动物的新世界,抬头望天,也不会有大雁一会排成一个人字一会排成一个一字。
2
为什么这些年的春天,你不太能看到燕子回来了?
城里的土地太金贵了。植物种子在地下吸收着汁液,为钻出土层积蓄动力,可建筑总是更快一步。
一道政策批下来,目所能及之处就全长出柏油路、公寓和产业园了。
新出土的建筑,要么披着光滑的瓷砖,要么身着玻璃幕墙。光滑的墙面,苍蝇停上去都要摔折了腿,更别提燕子筑巢了。
建筑们再动动臃肿的肚子,池塘就跟着少了三分,以至于燕子界建材(泥巴)越发稀缺,价格飞涨。再高明的贝聿铭,也只能摇摇头,感叹一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最后再来上杀虫剂和农药这么临门一脚,直接端掉饭碗。
如此一来若是还有燕子能安身,那绝对是燕子界里的生存标兵,搞不好还能登上感动燕国的舞台领奖。为永动机而犯愁的民科们,也终于能露出欣慰的笑容来。
可奇怪的是,泥土上的燕窝接连化作齑粉,水泥里却冒出来一片片。只不过,甭管怎么凑近,窝里的燕子都不飞不跑,用手戳戳,令人哑然一笑:“害,塑料的”。

当然,一笑便罢,没人会再对这个可怜的、自欺欺人的小谎言落井下石,将其曝尸于阳光下,叫众人看个清楚。毕竟脚下走的每一步路,都笼罩在一片欺骗凝成的巨大迷雾当中,我们总能找到点理由做拐杖,代替视觉引领自个儿在迷雾里穿行。即使鸟叫虫鸣没了,还有促销的音乐帮着充盈耳朵。
在迷雾的一角,仍有人拉着窗帘,唱着那首流传已久的童谣: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可歌里唱的“这里”,现在到底又在哪里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蹦迪班长 (ID:MrDisco007),作者:肉孜烧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