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作者:芝士咸鱼,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原文标题:《专访复旦教授梁永安:我们如何缓解工作之苦?》
你是否会经常思考:每天上班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工作让我们越来越痛苦?
据《中国职场焦虑调查报告》显示,高达64.57%的普通员工对工作有“荒废感”,35.54%的白领人士产生厌倦工作的情绪,长期在压力下工作,对人的身心有极大侵蚀。
既然工作让人如此倦苦,我们可以不工作吗?如果必须要工作,怎样才能缓解痛苦的感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给出了他的看法,梁永安出生于50年代,经历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70年代进入复旦大学文学专业,如今是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在和毕业生们的交流中,他发现生活环境的不稳定、职场竞争力过强、个体在工作中缺乏价值感,会让年轻人普遍感到工作很难,他也因此关注这个课题。
梁永安开拓过一门关于“工作之苦”的课程,他认为,虽然996、内卷、35岁职场焦虑等现象近些年才出现,但工作本身是一种劳动,劳动是人类生存史上被永恒讨论的话题。
月初,“十点人物志”联系到了梁永安教授,聊聊“工作”这个与所有劳动者密切相关的话题,谈工作之苦的根源、形态,以及探讨工作不那么苦的可能性。
工作为什么苦:年轻人不怕苦,怕没有价值
我是复旦中文系的老师,1954年出生,经历过文革,也下过乡,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在复旦大学学文学,后来留校任教,主攻比较文学。
从文学的角度看“工作”,倒是不稀奇的。从19世纪开始,很多文学作品都高度关注工作中的劳动者。狄更斯的小说里,常书写孤儿院里贫苦地、被迫做童工的人,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也写过《推销员之死》,都是在写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追求与幻灭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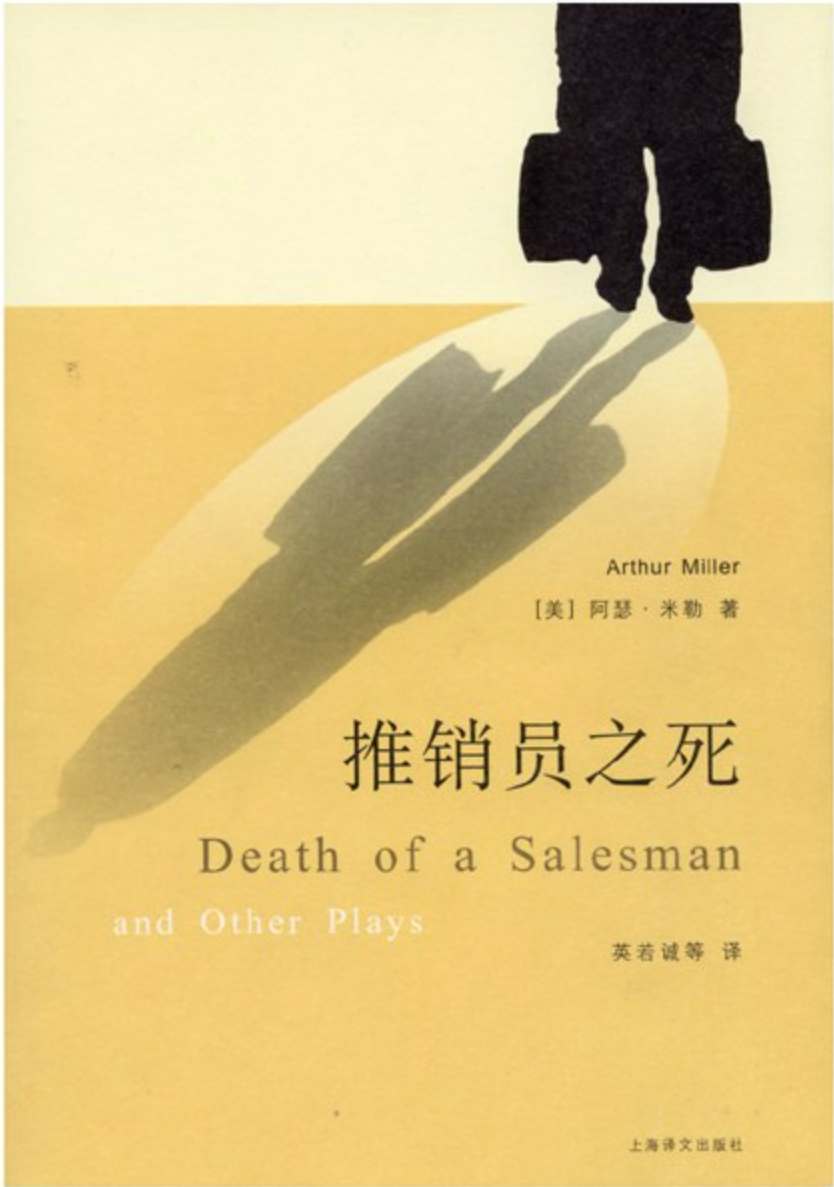
工作本身属于一种劳动,劳动能不能获得应有的价值、人在其中会不会变得异化,成了一个大问题。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所获得的利益和社会认可的差异非常大,不过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与平等,也是从劳动场景里展现的。
关注“工作之苦”这个课题,和我们学校每年毕业生的经历有关。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普遍会觉得很难,其中牵涉很多复杂问题,比如前些年外地学生来上海,需要解决户口问题,很多人为了落户先找个单位定下来,这个单位很可能是自己完全不喜欢的。这样能落户的热门单位,还会有很多人竞争同一个岗位,有时候还挤不进去。
有人只能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待上一两年纷纷跳槽,跳槽后又需要适应期,如何找到自己合适的职位、喜欢的工作很不容易。等到他们毕业几年后,逐渐有了专业积累和工作经验,又会变得有些老练,缺少了点刚毕业时年轻人的冲劲和锐气。
工作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压力不太一样。我遇到过非常努力的女生,她们一直被提醒“女性走入社会后发展空间比男生少得多”“不努力不行”“不努力就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些女性从小学就开始努力,努力读书、努力工作,进入职场你会发现,很多女性能力真的很优秀,但她们的上升空间很小,到了公司的管理层,大部分都是男性。社会也会对女性施加很多工作之外的压力,生活、成家、生育等形形色色的问题。
很多女性努力到最后,会产生疑问:我的价值感在哪里?
男性同样会感受到工作的压力,如果他在学校成绩优秀,出去(毕业)后想获得社会价值和社会的承认,是一个很长的磨练过程,如果他很有个性,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如果他没有个性,又会平庸化。
男性面临的更多是理想与物质的冲突,如果自己一文不名,他的价值焦虑会很大。
我有个男学生,本科学工科专业,读研学比较文学,他自己喜欢写作。他最大的焦虑是:这辈子究竟能不能写出文学界和社会承认的东西?但这是未知的。
如果顺应市场去写作,他会觉得心里过不去,如果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又觉得很惶惑。结果他不得不去考公务员,边上班边写作,当他成为公务员后,又因为看不惯体制内经常应酬喝酒的现象,被逐渐边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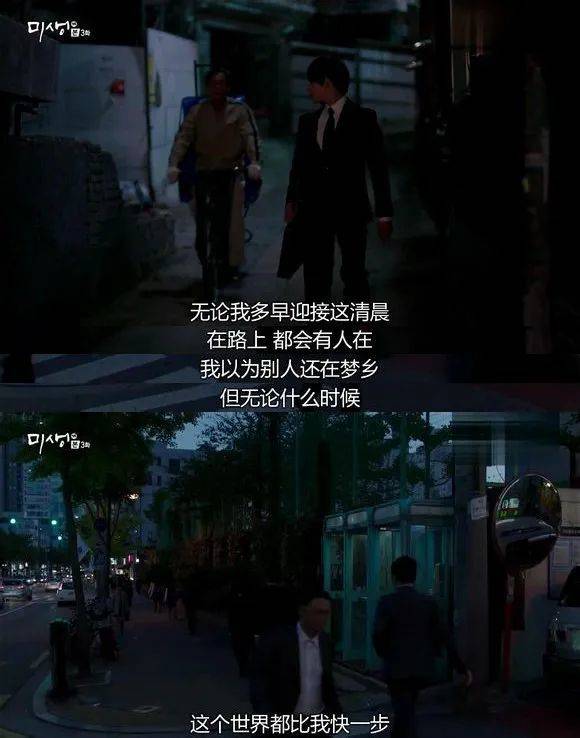
我也遇到过一个女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可以选择公务员,但她决定不去了,去南方的某家知名媒体,我们在电梯里遇见,我问她为什么这样选,她说,“因为你说过,人这辈子还是要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我很感动。
前年武汉疫情,她在一线报道,文章写得非常好。她在工作上一定也有很多困难,写作、采访、挖掘选题等等,需要面临很多职业上的拼搏。苦是苦,但她觉得有价值。
人很容易感到价值感空缺。为什么有工作之苦?很多年轻人并不怕苦,关键苦得要有价值感,身体再苦,但内心觉得值就够了。
这个“值”不光体现在金钱上,也体现在她内心就喜欢这个。
人不怕苦,但怕空。今天年轻人主要的“工作之苦”,来源于精神上。
80年代到今天:年轻人往前走,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近十三四年前开始,年轻人普遍因为工作而感到苦闷。物质发展非常显性,全球化过程里,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和自己目前的生活间有很大差距。
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的苦,但这种苦是不一样的。九零后的父母那代人是农业社会最后一代人,从九零后开始的三四代人是过渡阶段的人,从农业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这是伟大的创世纪,但特别艰苦,苦在前后不搭,文明建设上的空白点非常多,迫切需要“凿空”精神。
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写过一篇《过渡时代论》,讲的就是这种状态:中国几千年都活在过去的格局里,忽然面临世界大潮的启动,社会不得不变革,已经离开了此岸,彼岸却还很遥远。
到了八十年代,那是非常富有激情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面临改革开放,向往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比较刚性也比较具体。人往前走的时候,努力就行,需要的是一种热情和学习性。

那时,个人理想跟国家民族的宏大愿景结合在一起,个人有很大的宏观性。一个人尽管只是个体,但他可以把自己放在宏观的进程里面体会自己,当时的诗歌和各种各样的文学语言、电影语言都会有这种气质。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改革,激活了很多能量,不少人选择下海经商,最关键的是推动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人文积累的人尝试市场化。这时候,人努力的背后,同样有很宏大的梦想来支撑。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更爱追求理想?那时候人们拥有自行车就已经很高兴了,对于物质的要求不是很高;家家户户有了家用电器,开始向往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等,物质条件不断变化,但也还属于基本生活。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产化还没有太大压力,社会普遍处于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环境中。但随着时代进步,城市化在发展,消费主义也在发展。
渐渐地,一个人的生活理念中,房子、汽车也加进来了。加进来之后,现在的年轻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变多,付出的代价也就非常大了。
基本生活实现了,人的社会处境,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变化。他必须强迫自己靠向这样新的现实主义。那么,中产化的压力就来了。
社会中产化以后,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生活要延伸到买房时,压力一下子变大了。西方国家拥有自己的住房平均年龄是在35岁,而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们不太愿意去租赁,农村以前有“几个儿子盖几套房”的传统理念。中国青年拥有自己第一套房的年龄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平均是25岁,比西方提前十年。
这时一切资源向着中产化,但不是全面的中产化。真正的中产化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建立。比如消费结构里面国际旅行、音乐、电影、文学、阅读、社会多种多样的交往、公共空间里面形形色色的文化成分很大。

只实现了资源中产化,人的精神发展空间、艺术发展空间、新型生活方式空间就压缩了,所以过得像个“压缩饼干”一样。整个人生的焦虑都集中在物质上,人的建设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大落后了,他要挣很多钱,要找好工作,要找报酬高的工作,为了解决这些焦虑,爱情和生活空间也被压制住了。
人必须在有限空间里做出选择。你无法自由自在地“挣多挣少都一样”。主流价值还是希望你先有好的工作,再结婚成家。社会环境压力很大,只能在别人的流水线里工作,尽量获得更高的报酬。
这个过程里流失掉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创造性,向往的生活很难实现,你只能去实现老板的理想了。
996与内卷的代价:自由时间的丧失,会造成全面损害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童话《木偶奇遇记》,匹诺曹被骗到岛上变成一头驴,在那里整天干活,被奴役。今天的企业也是这样,如果连员工的基本生命都不尊重,随意支配他的时间,等于把人变成了驴。
一个人不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人,他也是政治学、文化学等多重层面上的“人”。
如果说今天的年轻人觉得苦,只是因为挣钱少,那太表面了,他的自由时间在哪里,在不停加班的时间里,本来8小时之外,你可以逛书店,可以去跟朋友聚会,心灵的需要原本都该在工作外的时间里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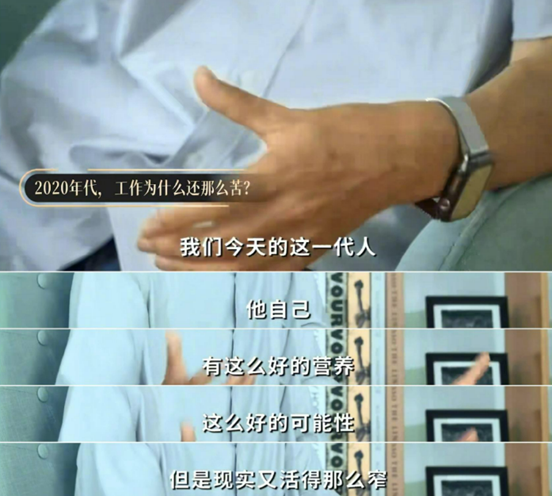
到了现在,年轻人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你向往的生活都没了,活生生地看着,却没法去参与。我们想摆脱当下,但又被当下沉重地压制。
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有这么好的营养,这么多的可能性,但是现实活得又那么窄。这种活得很累的状态,跟我们拥有的这么一个时代之间太不相称了。
以前为什么加班少?八十年代国有企业为主的时候,国企有严格的出勤制度。市场化以后,私企雇佣劳动力更大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但同时呢,也会产生市场压力下的资本逻辑。企业不光是跟中国市场竞争,也是跟全球市场竞争,工作效率牵扯到企业的生死存亡问题。
理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也是探索者和学习者,这样的话不需要996,同样能在市场立足。现实往往达不到,只好靠劳动量的叠加,变相地让员工单位时间报酬降低,形成所谓的996或内卷。

工人史上没有过大规模的996,以前我在工厂干过两年,很严格地遵循时间上下班。如果工作时间长,一般都是两班倒或者三班倒,这就比较合理。我们今天的996可能更适合两班制,把它切换成两个8小时,或者是两个6小时,才比较合理。
996对年轻人来说最大的损失是自由时间,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特别强调,人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是指自己能支配的时间,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天赋都是从自由时间里形成,人生需要自由时间,才能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全国一律不准加班,工时控制在8小时内,社会面貌将会发生很大变化。有个很有趣的例子,1959年纽约突然大停电,忙忙碌碌的人都变得不忙了,外面灯红酒绿也没有了,大家待在家里,这一天生育率大大提高,因为能有个安静的心情了。所以说自由时间的丧失是全面性的伤害,甚至延续到亲密关系、生育率低等各个方面。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就像卡夫卡写的《变形记》一样的,人似乎必须在劳动,一旦不能劳动就失去价值,变成一只甲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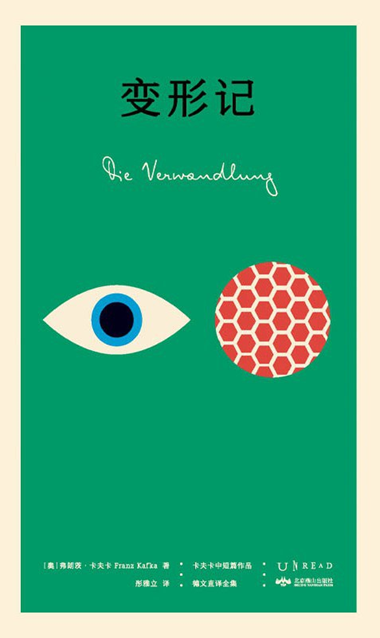
闲暇,不是无能或无价值的体现。青年代表国家的未来,如果青年人的生活质量低,会影响他们的方方面面,人格也会高度单一化。
单一化的人,感情也不可能有很多梯度,对世界的隔绝性很强,精神发展、心灵成长、情感发育都会很差。互相只能比收入、比房子、比车,只能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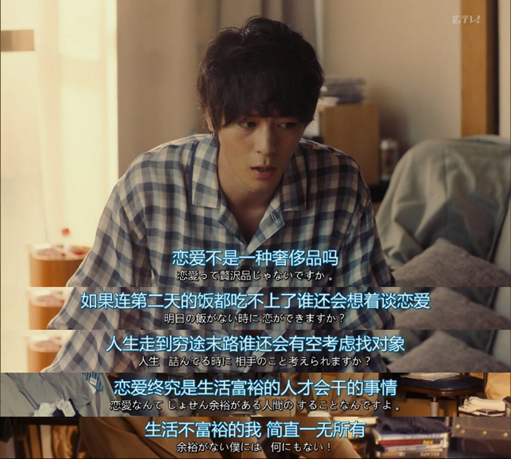
996影响最大的,不光是年轻人个人的未来,从更大的层面看,整个国家的一代人可能会变得偏狭、比较窄。什么叫窄?就是脆弱,不能接受全世界的丰富多元。多元意味着跟自己有差异,如果你只拥有单一性,多元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会产生强烈的自我维护,从而排斥世界的多样性。这样留下的问题就太大了。
我们社会发展的程度还不够,刚刚走出温饱,城市化也在发展阶段,所以年轻人的艰难,也有很大的历史因素。
工作不苦的可能性:个体可以做什么来缓解痛苦?
有人问,既然工作这么苦,我们可以不工作吗?
不工作是不可能的。工作就是劳动,形态是多样的。哪怕你不去某个企业工作,但在做创造性的事情,也是工作。
现代社会是交换体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益,再去交换购买其他物品和服务。
历史上只有贵族不工作,那是身份社会,人与人天然不平等,一旦你意识到现代社会是平等的,你就必须得工作。

哲学家罗素说,人性有四种欲望:占有欲,竞争欲,虚荣心和对权力的欲望。工作像是一个平台,人把自己的价值和欲望放进去,就会生出很大的推力。人一生总的来说,更大程度上是在精神世界里生活,工作本身给我们带来一种自己的价值感。
我觉得这个社会分为三种人。一种处于时代的火车头,是时代的领跑者,有动力去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另一种是坐在车厢上整天发牢骚,放大自己的欲望。
还有一种人属于火车的车轮,愿意被火车头带着走,轮子也承受着一定的重量。他没有火车头那么强劲的动力,但是他愿意跟着走,很朴素地希望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用劳动获得自己的生活,这类人占了大部分。
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渴求安稳的人,一届届的学生都要找工作,有些人就想找个稳定工作,过自己的小日子。
有些人会把生活看作一个程序,每天都可以预计到自己在办公室里一年年老去,以降低风险来实现安全性,这样也行,无可厚非。但会缺乏一点冒险精神,社会发展充满风险,而风险中还有很多机会和成长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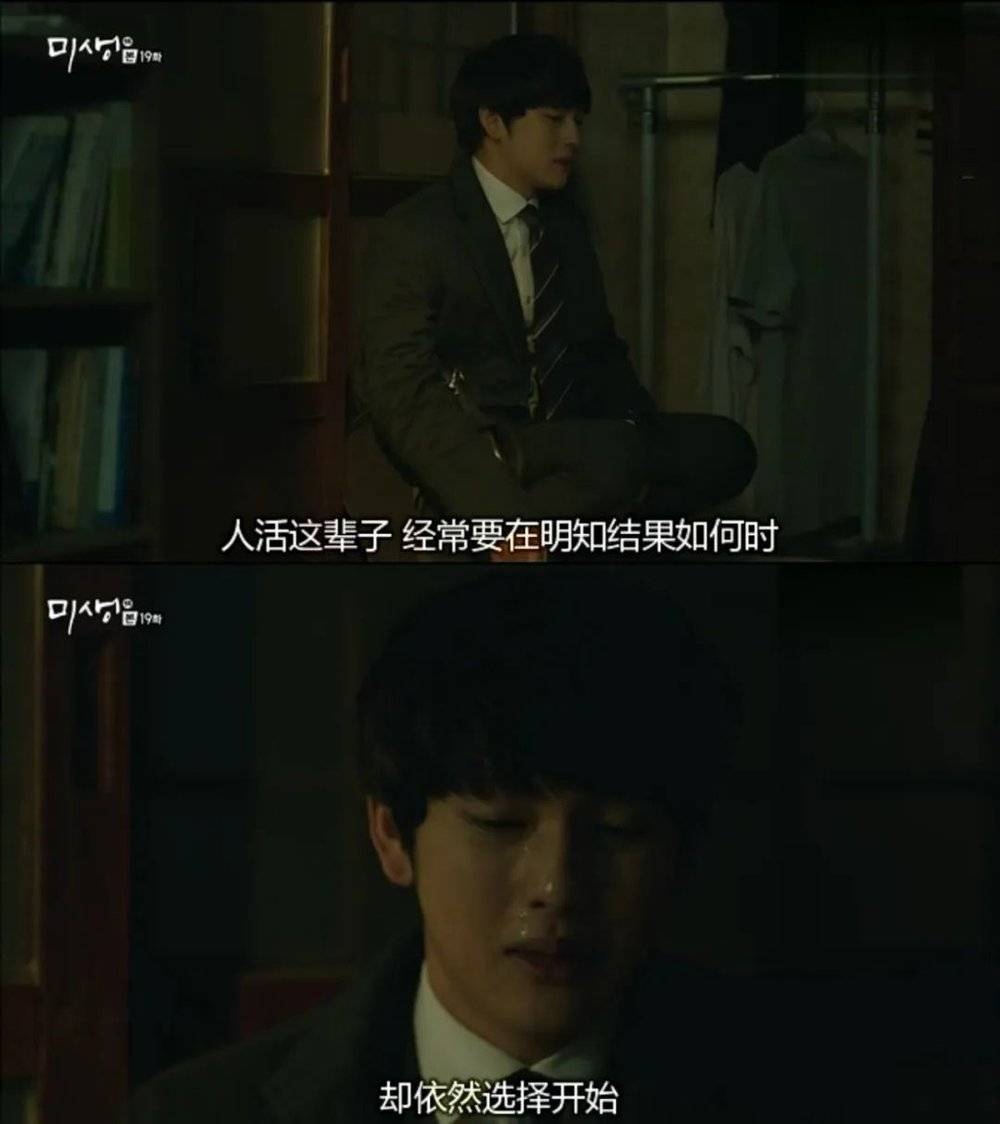
我更主张大家要找喜欢的工作,这非常重要。什么是好工作?是富有活力,能在时代永葆青春的工作。人不是机器,工作质量完全看自己的内心,对工作有深厚的激情,才会有创意。
有些事情你原来觉得不喜欢,深入进去发现里面有很大的创意空间,后来爱上了,这也是专业化的过程。
人对某种事物的热爱要从小建立起来,如果你喜欢文学,文学里的一些书籍作品会成为你的巨大支持,艰难的时候拿出来再读一读,就会成为支撑。如果你喜欢捏彩泥,一旦特别烦心的时候,拿出来捏捏做做,会有情绪释放的作用。魏晋时期嵇康内心不平的时候会打铁,浑身打得冒汗,这也是一种排解。
归根到底,人一定要寻找到建设性的自我支撑,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越发能体会自己内心深处渴望什么,痛苦里面有一种建设性的自我建构、自我疏解,这样才有持续性。
不管是哪个领域里面,你要不断地努力,有自己的生产力。哪怕最后没有特别成功,但是在过程中,你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很好。真正的有为青年,不是获得了社会承认或者得到一笔财富,而是他享受了生命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相遇,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云南下乡劳动的时候,在山坡上种南瓜,它长个小芽伸出藤来,藤要长好长才能开出黄花,黄花越来越大,花谢了,长出了绿绿的小点,小南瓜出来了,再长上一两个月,最后才长成大南瓜。
年轻人要生产出“大南瓜”来,光是开花的环节,或许就要爬很大一截藤。爬藤是很孤独的,看不见花也看不见果。唯一能体会的是自己内心的向往。前方不是必然开花,也并非必然结果。但很多人是过不去这一关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ID:sdrenwu),作者:芝士咸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