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纽斯河泥螈和其他蝾螈身上始终有一个谜题让科学家感到困惑,直到今天才初现眉目。这种动物的奇特性状源于一副隐藏的重担:它们的每一个细胞内都挤满了DNA,DNA中的碱基对比人类细胞中的多出近38倍。
纽斯河泥螈的基因组是地球上所有四足动物中最大的。大部分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鱼类的基因组大小的变化范围不大,一般包含5亿~60亿个碱基对。这些碱基对串成长链,构成了基因,而众多的基因构成了动物的基因组。可是蝾螈基因组大小的变化范围却很大,少的有100亿个碱基对,多的达1200亿个。蝾螈的基因数并不比其他动物多,但是它们的基因组中塞满了类似于寄生DNA的片段,这些片段失去了控制,不断扩增。蝾螈巨大的基因组支配了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它们推上了一条极慢的生存车道。它们拖着发育不全的身躯、结构简单的脑和纸袋般薄弱的心脏艰难求生,有时却可存活上百年。
或许是因为这副重担的代价,蝾螈得到了一种奇妙的能力:再生。它们不光是四肢能再生,就连脑部在切除四分之一后,也能长回来——这种能力太利于生存了。

纽斯河泥螈在水下生活,到地面上就显得笨拙。它们只会在昆虫恰好游过身边时捕食。
膨胀的基因组
关于巨大基因组的疑问是在几十年前的一段重要时期提出的,当时生物学家还刚刚将DNA认定为生命传递遗传信息的分子。研究者起初认为,那些身体结构复杂的高等物种,例如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理应携带较多的基因,并因此拥有一个较大的基因组。
但是到1951年,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艾尔弗雷德·米尔斯基(Alfred Mirsky)和汉斯·里斯(Hans Ris)推翻了这个成见。他们测量了几十种动物细胞DNA的碱基对数量,结果惊讶地发现,一些巨型蝾螈细胞基因组中含有的碱基对竟比人类、大鼠、鸟类和爬行动物多出了几十倍。
所有这些物种的DNA链都会缠绕成香肠形状的结构,这种结构就叫做“染色体”。而那些基因组较大的物种的染色体看上去也被放大了,就像一个吹得太鼓的香肠形气球,整条染色体上似乎都缀满了额外的DNA。
在几十年间,对巨大基因组的探索始终进展缓慢。科学家辛勤地对果蝇、线虫和人类的基因组做了完整测序,但他们大多避开了蝾螈,因为蝾螈的基因组实在过于庞大,操作起来如同一场噩梦。直到2011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蕾切尔·米勒(Rachel Mueller)才终于跨出了一大步。
米勒和同事锁定了6个无肺螈物种和美洲大鲵(Cryptobranchus alleganiensis)。分析结果证实了人们的猜想:蝾螈的基因组里塞满了转座子。许多相同的转座子同时存在于无肺螈和美洲大鲵基因组内,说明这些寄生DNA最初是在2亿多年之前,在所有现生蝾螈的祖先体内开始不受控制地复制的。

蝾螈庞大的基因组使这类动物拥有了一副婴儿般行动不便的身体,但也赋予了它们再生四肢甚至部分脑组织的能力。
胚胎般的大脑
巨大的基因组常常会导致蝾螈长成“巨婴”。在766个已知的蝾螈物种中,有超过39种完全无法从水生的幼体长成可以生活于陆地的成体。它们像纽斯河泥螈一样,长着幼体的鳃和软弱的四肢,终其一生只能困在水里。
它们中的许多还缺失脚趾,因为它们的四肢始终没有发育完全。纽斯河泥螈的后足只有4个趾(大部分蝾螈有5个);两栖鲵属的物种每只脚只有1~3个趾;而居住在美国东南部的鳗螈科(Sirenidae)物种,甚至连后腿都没有。
这些发现源于两位科学家的合作,他们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蝾螈生物学家戴维·韦克(David Wake),和当时在德国不来梅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格哈德·罗特(Gerhard Roth)。他们发现,蝾螈的脑部结构大多比蛙脑简单。用韦克的话说,蝾螈的脑神经细胞是“胚胎状”的:外形较大而圆,并且分化程度较低。

图片来源:ElisaRiva/Pixabay
在这些现象中,罗特惊讶地发现了一个普遍规律:蝾螈脑部所缺失的特征,都是那些在发育晚期产生的。这看上去好像这些动物的时间太紧,它们的脑部来不及发育成熟。这种规律很容易解释得通,因为当时刚好有另一位科学家揭示了蝾螈的巨大基因组和它们发育缓慢之间的联系。
斯坦利·塞申斯(Stanley Sessions)现在已经是美国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的荣休教授。他曾是韦克的学生(本文中有好几位专家都是),当时正在研究蝾螈四肢再生的特殊能力。塞申斯切断了27种无肺螈的右侧后腿,计算了它们重新生长的速度。这些动物的基因组中包含130亿~740亿个碱基对,是人类的4~24倍。果然,他发现基因组较大的物种,断肢再生的速度比较慢。它们的未成熟细胞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分化成肌肉或骨骼这样的特化组织。
韦克、罗特和塞申斯的研究也为理解另一个问题提供了基本依据,那就是为什么基因组最大的那些蝾螈,会失去脚趾、后腿甚至变态的能力——它们“笨重”的基因组拖慢、阻碍了很多发育过程。大家想当然地认为,蝾螈发育受阻的原因很简单:基因组越大,复制所需的时间越长,因而细胞也分裂得越缓慢。但是到2018年,基因组学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进展,让科学家开始批判性地思考这一问题。
那一年,研究者首次公布了一个完整的蝾螈基因组的数据,来自墨西哥钝口螈(Ambystoma mexicanum)。这种动物能长到接近一个人的前臂那么长,有着铅笔似的细腿、披着绒毛的鳃和其他幼体特征,但它的基因组“只”有320亿个碱基对,比纽斯河泥螈的1180亿少了许多。这项研究指出,墨西哥钝口螈的转座子不只是单纯地散布在基因间,而且还大量存在于基因内部的内含子(intron)区域中。
这个小细节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一个基因表达时,其包括内含子序列在内的整段DNA,都必须复制成一条RNA链。接着内含子必须被修剪掉,然后RNA链才能作为模板,生产可以指导细胞发育的蛋白质。墨西哥钝口螈的内含子序列长度可达人类的13倍,原因是其中塞满了转座子。于是,它们的RNA就要更长时间才能生成,引导细胞分化的指令也要更久才能生效,久到用塞申斯的话说,这些蝾螈“永远也不会真正地长大”。
除了发育缓慢,基因组过大还会产生另一大冲击。虽然科学家在150多年前就碰巧发现了这个现象,但它的重要性直到现在才刚刚被认识到。
纸袋似的心脏
19世纪初,一位名叫乔治·格利弗(George Gulliver)的英国军医一边周游世界,一边追随自己的兴趣。每到一处,他都会采集当地物种的血样,拿到显微镜下观察,并测量其中的红细胞。格利弗发现了迄今已知最大的红细胞,属于三趾两栖鲵(Amphiuma tridactylum),这种动物的四肢退化、极为细小,看起来就像一条鳗鱼。它的红细胞体积比人类的大了300倍。红细胞大小仅次于三趾两栖鲵的,则是一些蝾螈和一种肺鱼。
我们现在知道,细胞大小和基因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DNA越多,细胞就越大。为了容纳大细胞,有的蝾螈直接长出了硕大的身躯。比如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俗称娃娃鱼)能长到1.8米长。
硕大的细胞构件还会堆出结构较为简单的身体。试想你要组装两部完全相同的玩具车,一部用较小的积木,一部用较大的积木。如果车的大小固定,那么用较大积木组装的那部整体结构就会更简单、更为棱角分明——蝾螈的身体似乎也是这样。
20世纪80年代,如今在哈佛大学工作的詹姆斯·汉肯(James Hanken)为这条原理找到了一个经典例证。当时,汉肯正在研究索里螈(Thorius)的腕“骨”(实际上是未硬化的软骨)。这些物种是世界上最小的蝾螈,隐居在墨西哥的深山老林中,有一些小得能直接放在一枚硬币上。索里螈的几十个近缘种都有同样的8块腕骨,虽然它们在演化中已经分别了几百万年。但是汉肯发现,在索里螈中,这8块祖传的腕骨却发生了部分融合。更惊人的是,就连在同一个物种内部,这些骨头的排列也会出现差异。有的个体只有4块腕骨,有的有7块。还有的甚至左腕和右腕的骨骼排列都不相同。汉肯表示,这种差异“非比寻常”。他认为,索里螈因为身子小细胞大,所以在胚胎阶段没有充足的细胞可以调用来形成腕骨。
汉肯的结论(即大细胞会导致身体结构简化)吸引了米勒和她的博士生迈克尔·伊特根(Michael Itgen)。但是两人怀疑,对于这些动物,这一点是否真的会造成什么影响。2019年,他们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课题,想揭示细胞大小的差异是如何影响心脏结构的。他们考察了9种无肺螈,它们基因组包含的碱基对数量从290亿个一直横跨到670亿个。
无肺螈没有肺,通过皮肤呼吸。而且它们只有1个心室,不像哺乳动物一样有2个。当伊特根在显微镜下观察时,他惊讶地发现无肺螈的心室竟如此特别。对于那些基因组十分小的物种而言,心室壁很厚且肌肉发达,心室腔内只留一小块空间让血液流过。随着基因组变大,它们的心室会越来越空,周围的肌肉壁也越来越薄。对那些基因组最大的物种而言,心室更是如同一只空空的袋子,周围只有一层薄膜似的肌肉,有时甚至只有单层细胞那么薄。
伊特根不清楚为什么更大的基因组会塑造更空的心脏。他猜想,或许那些基因组较大的物种的心室需要更多空间来容纳较大的血细胞,而血细胞的大小会影响血液的黏度。又或许是因为个体在发育时细胞分裂得不够迅速,所以它们的心脏缺少肌肉,变得很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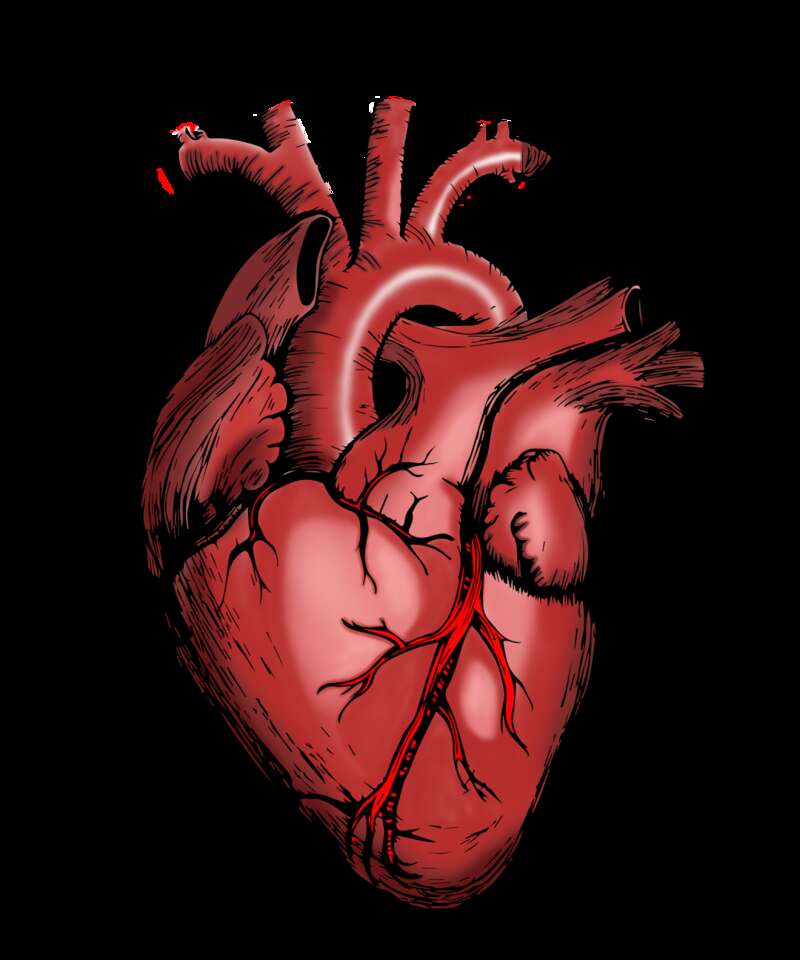
图片来源:mandrakept/Pixabay
无论如何,这种“粗制滥造”的结构都会带来沉重的代价。亚当·基科(Adam Chicco)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心脏生理学,他发现这种纸袋似的薄心室,与严重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相似:心肌细胞变少,心室壁被拉伸而变得更薄,心脏泵血的功能越来越弱。
蝾螈如果是人类,已经走到鬼门关前了。韦克曾在2020年告诉我:“拥有庞大的基因组会在方方面面带来高昂的代价。”然而蝾螈已经生存了2亿年。“所以那肯定也有什么好处。”他又说道。在寻找这些“好处”的过程中,科学家已经收获了一些惊喜的发现,它们冲击了传统的观念,有可能颠覆我们对演化的理解。
难以理解的畸变
韦克曾在2020年和我交谈过两次。他已在2021年4月逝世。但在死前,他和塞申斯终于在一个他们求索了几十年的问题上获得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了蝾螈和肺鱼如何从巨大基因组中受益。这个理论萌芽于一次大胆的实验。
塞申斯和他的本科生尤里·马塔耶夫(Yuri Mataev)麻醉了几只火焰蝾螈(Notophthalmus viridescens),然后剥开它们薄薄的颅骨,将每只蝾螈的脑组织摘除了近四分之一,摘掉了负责嗅觉的脑区。对蝾螈来说,腿被切断后再长出来是很容易的,但塞申斯想测试一下这种再生能力的极限。果然,“不出6个礼拜,它们的脑组织就重新长了回来。”塞申斯说。
这次实验表明,即使蝾螈失去了通常在自然界中不会丧失的部位,它们也能启动再生。这一点违背了演化论的基本原理——某种能力的产生,是因为环境压力的推动。塞申斯猜想,蝾螈演化出再生能力,或许只有一部分原因是要应对外界的应激源,而巨大的基因组帮助它们加强了再生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最终成为了一种有益的“副作用”。
韦克和塞申斯的理论揭示了,那些遗传物质里的“寄生虫”深刻地改变了蝾螈的生物学特性。包括人类在内,许多长寿的物种都会在发育完成之后限制剩余的干细胞数量,这是演化上的一种权衡,其目的是降低一种时刻存在的风险:细胞分裂失控,从而引发癌症。而蝾螈却拥有更多的干细胞,其干细胞受的约束也小得多。
韦克和塞申斯的理论未必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蝾螈能忍受巨大的基因组。虽然如果在极不巧的情况下失去了四肢,能够使它们再生确实很方便,但蝾螈每天还是需要与畸形的心脏、脑和身体相伴。2021年年中,米勒、伊特根和汉肯进行了一场对话,他们从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中,推测出可能存在一种惊人的真相。
3人在Zoom上通话,讨论空洞的心脏可能会对蝾螈的生存带来什么影响。“我的观点很极端。”汉肯说,也许一颗空洞的心脏“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这个观点听起来奇怪,但米勒和伊特根却认为它挺有道理。蝾螈的生长和移动都很缓慢。在迄今发现的脊椎动物中,它们的代谢率和氧气需求都是最低的。伊特根和米勒研究的无肺螈更是连肺都没有。伊特根说,或许蝾螈能够忍受空洞的心室,“是因为它们对心脏功能的需求实在很低。”
的确,当塞申斯开展再生实验时,他曾将12只火焰蝾螈仅有的心室(两栖动物成体的心脏只有1个心室)都切除了一半。当时蝾螈血液喷涌、心脏停跳,但都活了下来,并长出了新的心室,这说明它们可能并不像哺乳动物那样依赖心脏。

纽斯河泥螈可以通过鳃呼吸,以此弥补它孱弱的心肺功能。虽然体内塞满了垃圾 DNA,这种蝾螈仍找到了生存的方法。
蝾螈似乎也没有为它们奇怪的骨骼付出代价。汉肯认为,索里螈能忍受结构简陋的腕骨,是因为这些动物身体很小,对关节施加的压力微乎其微。索里螈同样不需要有猎豹那样设计精巧的四肢,因为它们不追捕猎物,只是静静趴着等候昆虫经过身边。
罗特补充说,既然蝾螈只需要等待猎物上门,它们的整个视觉系统都可以简化。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欧洲和美洲的网足蝾螈(Bolitoglossa)。由于脑部的简化,它们失去了50%~90%的视觉神经元,因此无法区分一只爬过身边的昆虫和一颗滚过身边的闪闪发光的金属球。不过,网足蝾螈拥有地球上最快的舌头之一,韦克说它们就像“举着一把上好膛的枪在行走”,只要短短几毫秒就能击中一只昆虫。
如果你也长了这样一条舌头,如果你不需要多好的视力,如果你能够长时间蹲守,你的身体就会卸下许多压力,那么你也可以只要一个简化的脑子、一颗空洞的心脏和几块奇怪的腕骨了。“那样也没什么妨害,”米勒说,“真是挺深奥的。”
看到纽斯河泥螈的样子,你很容易对它产生怜悯之情。迟缓的发育不仅使它无法变态,也可能阻止成年个体断肢再生,真是残酷的讽刺。因为无法穿过干燥的陆地,这种泥螈只能被隔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2个小河流水系中。农业和开发使这里的水质每况愈下。2021年6月,美国政府将种群大小不断萎缩的纽斯河泥螈列为“受威胁”(threatened)物种。虽然蝾螈这一类群已经生存了2亿年,但是对纽斯河泥螈这一个物种,我们仍禁不住要认为它的庞大基因组已经将它推向了灭绝的边缘。
对此塞申斯并不太确定。这些臃肿的生物已经一次次证明,说到适者生存,我们对“适者”的认识总有偏颇,会优先考虑力量和敏捷。基因组中的寄生者拖慢了纽斯河泥螈的发育、撑大了它的细胞、扭曲了它的身体。这种反常的境遇将这种动物推入了演化之旅中一条奇特的小道,在这里“适者”被重新定义,使强壮的心脏和复杂的脑都成了次要考虑。火灾、洪水和小行星撞击抹去了那些覆着皮毛、羽毛和鳞片,看起来适应性更强的物种,然而不知怎的,纽斯河泥螈却传下了血脉。
“这些蝾螈,”塞申斯说,“都是顽强的生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