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邓中华,责编:施杨,原文标题:《欺诈盛行可能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头图来自:《小丑》剧照
《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Fraud:An American History from Barnum to Madoff)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美国社会并非净土,至少在商业欺诈这件事上,一直如此,恐怕将来亦是如此。不过,如何有效地反商业欺诈,从清除广告中的不实之词,识破信息披露中的滑头花招,揭穿资本市场的割韭大法到让庞兹骗局、会计丑闻的操弄者锒铛入狱,美国商业社会的摸索、经验以及教训不失可资镜鉴之处。
一、 “精通人性的所有弱点”
虽然在道德上审判欺诈易如反掌,但在法律上界定它却非易事,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有证据表明虚假陈述是既有事实,而非推测;(二)欺诈实施者知道该主张是错误的,并有意误导;(三)对手方在评估虚假陈述的合理性时采取了适当的努力,然后相信了欺诈者的陈述,并据此采取了行动。换言之,法律不保护或无力保护盲目轻信者,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懒汉或巨婴。
不过,欺诈实施者的基本脚本却是一以贯之的。《骗局》关注的是组织欺诈,即商业机构对供应商、债权人、客户、投资者等施行的欺诈行为。作者发现,有四个领域重点体现了欺诈的关键模式:销售投资机会;商品零售;教育培训、就业或信贷等个人经济机会的营销;管理层对公司的掠夺。
例如,在投资机会的销售方面,有两种经久不衰的模式,一是“庄家”操作;一是庞兹骗局。再比如,在零售领域,欺诈者通过极为诱人的交易条件——超低的折扣、难以置信的质量和服务承诺,将消费者引入彀中,然后开始转向,将其引入昂贵的替代方案,或者在合同中埋伏了不易察觉的“坑”。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上当呢?仅仅是因为骗子太狡猾吗?尽管这是事实,“精通人性的所有弱点”,但重点是我们究竟有什么弱点。首先,“商业欺诈历史一再出现的一些心理冲动反映了人类情感中普遍存在的欲望或焦虑”。
譬如,一夜暴富的梦想,以及为了一夜暴富而产生的赌博天性;再比如,在老年群体中,对抗衰老无疑是焦虑中的“王者”,所以,保健品公司和养生鼓吹者很容易从这个群体赚到钱。其次,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人的认知存在很多偏见和抄捷径的特征,例如,牌桌上的人们常常会认为,自己输了多次,下一次赢的概率会变大,但事实上,下一局的牌面仍然是随机的。
有意思的是,历史长河中的人们似乎不太长记性,无法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什么,所以,“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每一次投机热潮都引发了金融欺诈”。君不见,只要股市的指数开始上涨,开户入市的人数就急速攀升,因为“每当资产价值上涨时,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不切实际的暴富梦想,投资者会看到周围人快速积累财富的证据”。
除了对经济事件的记忆在代际传播中不完美的解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商业欺诈从来不需要一直欺骗所有人,只要有一小部分人上钩”,足矣!
例如,在南北战争之前,受害者多是来自乡村的新客户,宰他们的是虚假拍卖行、礼品企业以及“便宜货”商店;此后,移民则是重点关注对象;在镀金时代,“在家工作”骗局盯上的是贫困妇女;二战后,是城市贫困人口;20世纪后期,金融和电话诈骗则对老年人紧追不舍。

交易的关键是赢得信任,欺诈者深知这一点。他们通常用三种方法来赢得信任。首先,“山寨”。《骗局》作者爱德华·巴莱森称之为“社会模仿”,它包括:盗用成功者的名称和地点,例如,一家注册在中关村名为高科技实为骗子的公司,就比注册在甘肃某个地方的高科技公司更像高科技公司;模仿成功者的商业形象,例如把办公室装修得非常豪华。
其次,“官僚化中的个性化”,又被称为“亲和欺诈”,充分利用同类、认同的影响力,在欺诈推销者与受害者变为自己人、好朋友之后,再鼓励其挖掘自己的社交圈,或可总结为“熟杀+杀熟”。
第三,“偏转”,也即贼喊捉贼,在公开打击欺诈行为的背后隐藏欺诈行为。
二、“买者自慎”还是“卖者自负”?
一个社会如果黑白颠倒,就会认为欺诈是正确的,或者是必要的。善良的人常常以为,欺诈者会备受道德谴责的煎熬。事实上,欺诈者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例如,即便是善良的人,也喜欢看诸葛亮演空城计“忽悠”司马懿,也热情地为球星用假动作晃过对手而喝彩。其次,只要一个人坚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成王败寇,欺诈就是一种生存策略,就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从积极的一面看,欺诈盛行可能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景气,所以乐观;因为乐观,所以轻信。在周期的低谷之中,机会微渺,竞争会趋于残酷甚至不择手段,因为人们会面临更多的零和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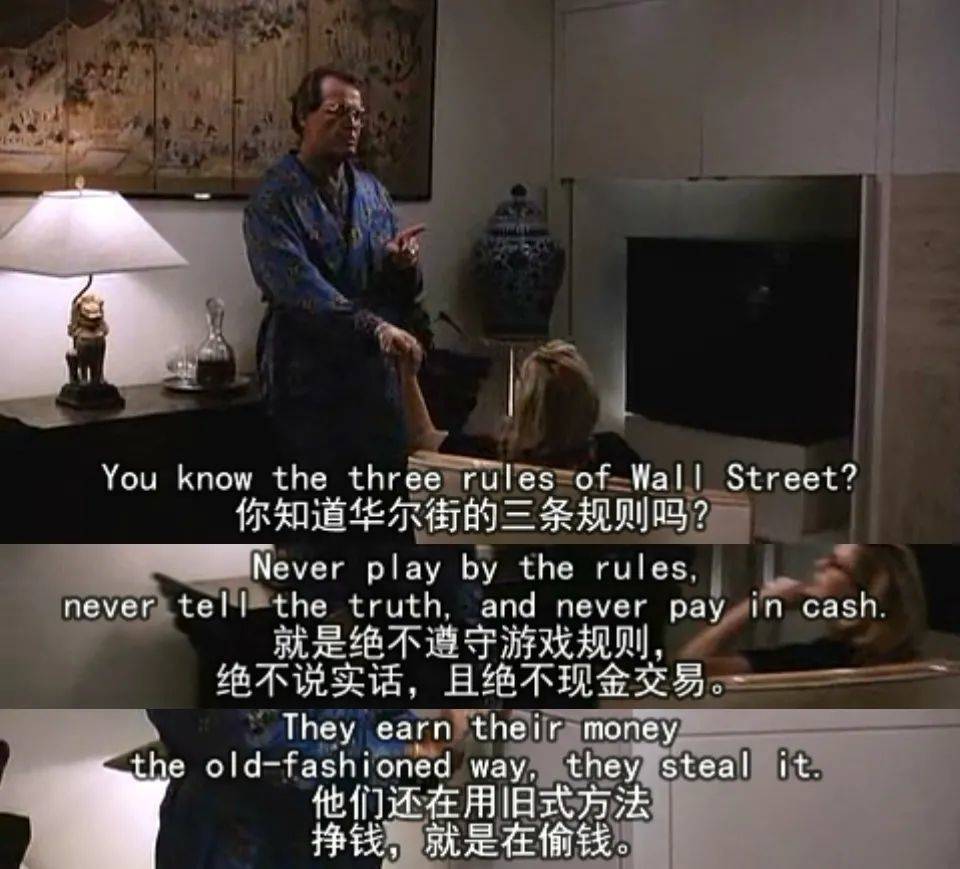
但是,它毕竟是错的,是违背经济公正的。所以,只要有欺诈,就有反欺诈,二者是相爱相杀的。自19世纪初以来,美国商业社会对组织欺诈的战斗已历经五个阶段。
19世纪10年代~19世纪80年代:购者自慎
“19世纪的美国经济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的商品、伪造证券、冒充合法商业代理人的骗子,最重要的是,还有假币。”
然而,这个世纪也是美国赶超“老大哥”英国的世纪,是“自由放任的堡垒”。虽然法律允许提起民事及刑事诉讼,然而,购者自慎的商业文化,使得大多数上当者选择“愿赌服输”,放弃起诉,以避免被公众羞辱;起诉则常常被巨大的举证成本阻遏;就算是赢了,不仅定罪率低,而且给欺诈者的惩罚也是最轻量级的。
虽然行政力量也参与其中,例如制定标准、进行检查,但批评之声不绝如缕,例如不够专业,或更关心收费而非坚持质量标准,任命过程不乏黑幕、裙带等等。新闻媒体在曝光骗子和提醒人们小心方面发挥了关键角色。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30年代:对购者自慎的挑战
一方面,随着阴谋和骗局的增多,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中投机商人以次充好带来的严重后果,让越来越多的精英认识到,这威胁了一体化、复杂的国内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曝光不足以胜任反欺诈的任务,加强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

呼吁者包括寻求巩固其地位的企业主、强化社会地位的专业人士以及主要政党中的社会改革者及其盟友。监管涉及的领域包括谷物检查、肥料标准、食品药品、企业会计核算、证券营销等等。邮政反欺诈成为其中的亮点。邮政局长发出的终止令与当今断网、封号类似,杀伤力巨大。
与此同时,企业主们出资组建的非政府组织——商业改进局日渐崭露头角,并以专业机构酣斗欺诈者。这些行为虽高效,但也不免误伤创新者,引来批评和质疑,因此,不得不在其彰显正义的活动中引入更多的“程序正义”,但这削弱了它们的效力。
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卖者自负”
经济大萧条成为凯恩斯主义的春天,行政直接参与经济取得了“合法性”,新政由此展开,政府权力日益扩大,成为反欺诈的关键角色。同时,1960年以后的消费者运动,民选官员为选举而迎合了这股社会热潮,推动了企业在“卖者自负”(卖者小心)指引下披露更多的信息。例如,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便是在罗斯福上台之后成立的。

20世纪70年代~2008年:“购者自慎”的回潮
对于家长式的监管,美国社会从来不乏批评者。一方面,过于强大的行政权力是否值得信任是一个问题,毕竟执掌权力的人很可能并非忠于信念的门徒,也不时是有利益诉求的俗人,因此,他们很可能成为大公司的手套,成为创新的窒碍;另一方面,为打击而打击,意味着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很可能带来一个效果,消费者、投资者疏于审慎,恰如投保之后的懈怠。
随着经济陷入滞涨,美国社会放松监管的呼声日渐高涨。里根的上台,标志着市场开启了反击。但是,这也为欺诈重开了方便之门。这个阶段最让人震惊的是,不仅边缘企业欺诈,一些大型企业也不顾惜自己的羽毛,声誉制约机制失效,并最终导致了波及甚广的金融危机。
2008年至今:“卖者自负”复兴
大企业让人怀疑,使得政府权力再一次找到了舞台,民粹主义日渐得势。特朗普这样的共和党总统,其手竟然伸到了具体的商业交易之中,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当然,这个阶段的反欺诈制度仍在演进之中。

三、启示:有效反欺诈之未济之旅
区块链技术的拥趸常常吹嘘它对反欺诈的价值。有这样天真想法的朋友,有必要好好读一读这本书。美国的商业欺诈史,是一个欺诈者拥抱时代潮流、不断推陈出新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新技术的“发烧友”。
巴莱森总结道,“欺诈者不仅表现出冷静、精于计算和自我控制,还表现出一种自我提升的热情,一种能精明地应付工业化社会文化需求的能力,以及对时局瞬息万变的适应能力”。电话发明后,他们创造了电信诈骗;互联网时代,他们是网络诈骗者。除了买下新闻媒体,他们还能利用揭批他们行径的媒体,先故意让媒体报道自己准备好的烟雾弹,等报道出来后,再标榜与之不同而大显身手。

粗梳美国反欺诈简史,就会发现其间的摇摆和反复:弱监管下,一方面是创新的繁荣,一方面是欺诈的横行;然后,监管的力量——可能是民间自发的商业组织,也可能是得到授权的NGO,或者行政力量,向欺诈宣战;随着权力的扩张,对权力的任性和高效带来的错杀引来如潮的批判,这使得它们引入更多程序,纠正错谬、惩治腐败,但也降低了效率,等同于日渐放松了监管。
如此循环往复,其驱动力是两个矛盾:经济正义到底如何实现,是快速惩戒,还是要遵循程序正义的流程?监管权力到底可信不可信、聪明不聪明,会不会在遏制欺诈时让创新也喘不过气来?
同时,美国的反欺诈制度创新遵循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演化过程。从媒体、邮政局、商业改进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到国会,从专栏作家到科学家再到州长、议员直至总统,权力的构建日益登堂入室。这对后发经济体采用什么策略来反欺诈颇为重要,对于东方社会强调顶层设计的经济体尤其如此。
反欺诈,就像任何治理一样,都是有其成本的。信誓旦旦地反欺诈固然受人尊重,但成本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制约因素,一个社会究竟愿意投入多少人力、物力、精力去实现“天下无诈”?这是否得不偿失?此外,如果物极必反是真的,一个大同社会会不会同时也是一个大伪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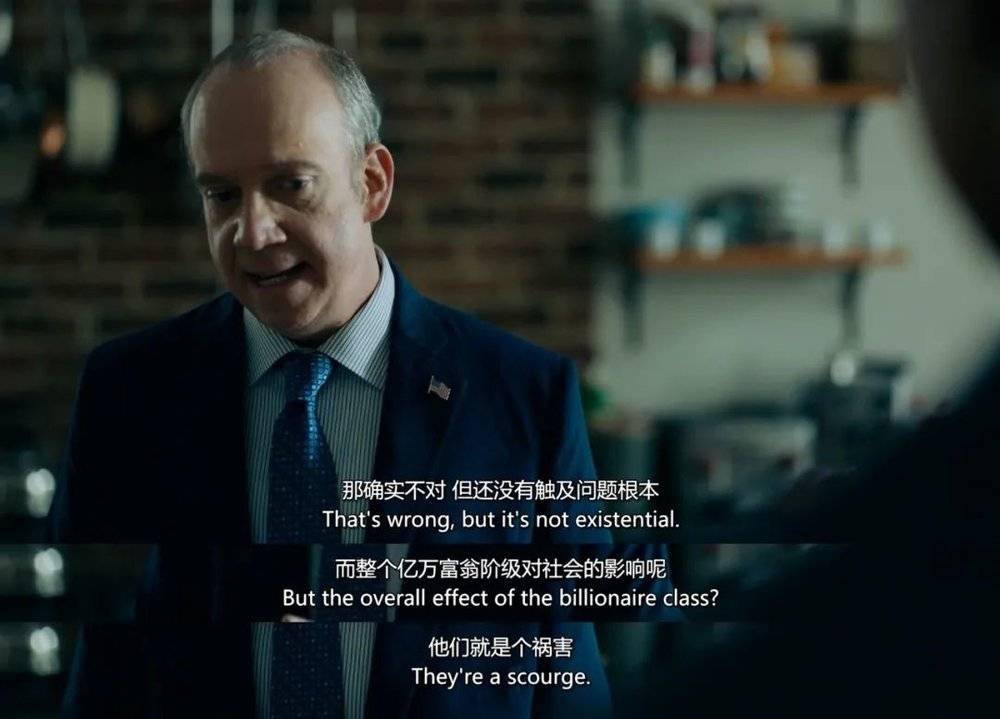
其次,一套反欺诈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多个要素,尤其是受众实际的文化认知。几年前,P2P行业还被当成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而被人们津津乐道,如今已是过街老鼠,只待最后的晚钟。
在这过程之中,监管方试图兜售的“买者自慎”似乎未曾起到显著的效果:面临清退中的损失,投资者不是诉诸法律,而是希望以更激烈的方式来施压政府出手,至于个人是否有责,只有少部分人自省,甚至有人希望新投资者接盘,从而反对清退。
因此,即使精英有足够的智慧来做顶层设计,也要允许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茁壮成长,充分利用企业、媒体、专业看门人、NGO等角色的意愿和能力,唯如此才是智慧的。
反欺诈生态的衰败和失灵,一个关键的表现是不同角色日渐同一化。这种同一化很可能引起系统性的坍塌。在安然、世通等公司的丑闻中,一些中介机构的同流合污让人不胜唏嘘,究其原因,“这些商业服务提供商开始强调自身的盈利能力,削弱了对专业责任的专注,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破坏了对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的承诺”。
教育是根本之策,但也任重道远,反欺诈似乎永远在路上。幸运的是,欺诈者在进化,反欺诈同样如此,“创新治理能够跟上旧游戏的所有新花样,杜绝最严重的欺诈行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邓中华,责编:施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