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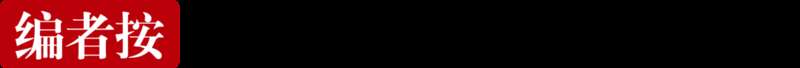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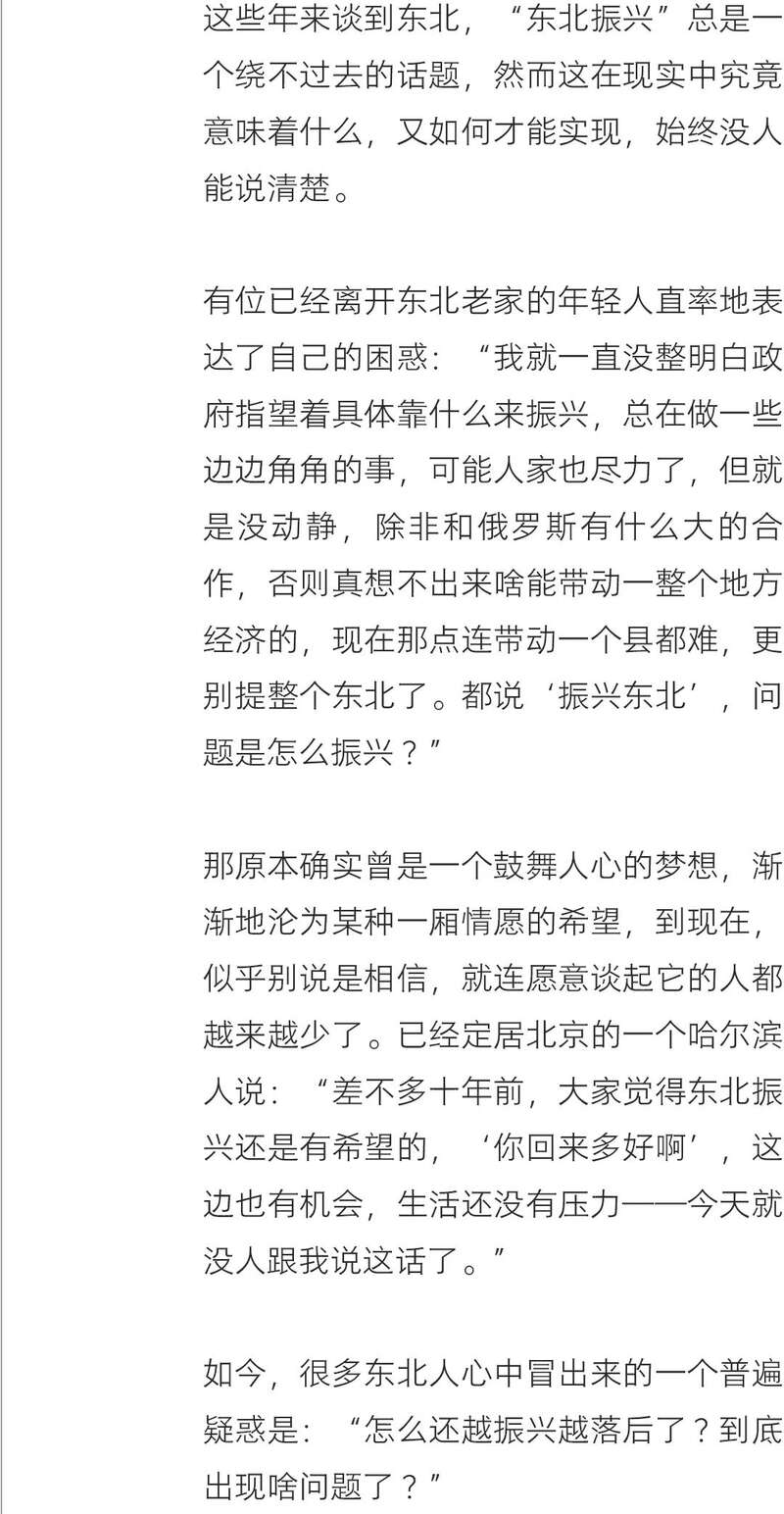
撰文 | 维舟
责编 | 翟梓然

东北振兴,怎么振兴?
但凡对东北的现状有所思考的人,都不能不回头看它的历史。有东北人回忆起多年前,第一次离别故土南下,她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见外面一车车的木材、煤炭,情不自禁地一阵心痛:这片黑土地不缺资源,也不缺人才,“共和国长子”也不是白叫的,怎么就混成了这样?
东北确实辉煌过,常有人提到“1945年东北工业总产值曾占到全国85%”,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名副其实的领头羊:“一五计划”期间150个苏联援建项目,56个落在东北,占了三分之一强。虽然多年来东北二人转、小品输出的都是东北的农村文化,但事实是:直到1990年代,东北的城市化水平都是遥遥领先于全国的。

◎辽宁东北老式蒸汽火车铁轨交通运输
无论东北人多么想要重现往日辉煌,但无情的现实是:曾经让东北兴起的那个特定地缘政治环境或历史条件,早已不复存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纯内循环,但现在打破之后,东北的资源并不存在稀缺性,市场体系、价格计算都已不一样了。东北确实是公认的“老工业基地”,但在现在确定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版图中,东北只剩下沈阳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长春市汽车集群,也就是说,即便在工业上,东北也已被边缘化。
然而,过往的历史记忆往往左右着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很多东北人在说起“东北振兴”时,不管信不信,潜意识里以为的“振兴”都像是“回到过去的好时光”(类似特朗普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很少人细想过,这是要回到什么时候的东北——是建国初期那种国家计划经济?还是近代时期对外开放的那种?更好的未来就是回到过去吗?即便想这样,那又怎么回得去?
很多人确信,“东北曾经辉煌过,所以也一定会再度辉煌”,那样的好事,没有道理不能再来一次,如果有什么问题,那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有一位已经南下的东北人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一美梦:“我也相信东北一定会振兴,但有些人可能对时间尺度没有概念——30年后也许可能,而且不是完成,是开始。对于大部分人的人生来说,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多大意义,只不过是一种难以证实的信念。”
一位本地学者在回顾近代以来的“东北问题”后,诚恳地对我说,他相信只要在新的历史机遇下重新定位,东北一定能复兴,理由呢?“它的资源还在。”这是一种工业时代的思维,相信财富来自于资源的开采——不论是什么样的资源。当场就有一位本地年轻人对此表示怀疑:“我做个极端的对比:非洲也有丰富的资源,但它依然很穷。”
如果说东北过往的繁荣有赖于特定的外部条件,那重新创造这样的条件不就得了?此时,有些人想重现的是近代那个开放的东北:那时的东北是东北亚跨国网络的枢纽,是全国铁路网的中枢脉动,现在却变成了末梢,原本那个国际化的东北经历了漫长的地方化乃至边缘化。然而,这样的外部机遇太难了,一位东北官员私下说:“邻居也很重要啊。现在外贸不行了,我们毗邻的俄罗斯在打仗,朝鲜、蒙古经济都很弱,朝鲜发射导弹跟放二踢脚似的,怎么把产业放这里?”
更多人想重现的外部条件,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布局。许多东北人抱有一种执念:只要国家重新重视东北,振兴是分分钟的事,一位当地朋友就说:“东北人总觉得,我们有过好日子,现在穷,都是国家不给钱、不给政策,这种话还特别能引起东北人共鸣,但‘东北振兴’战略也给钱给政策了,为什么东北还是没好起来?”
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东北振兴”原本就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量国家注资把本来已经僵尸化的老国企又救活了过来,而当时好不容易冒出来的一点民间经济活力反倒被扑灭了。亲历了这些年变迁的一位企业高管辛辣地说道:“都振兴20多年了,振兴意味着啥,给点钱?资源都枯竭了,唯一的资源就是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李强就曾提出“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他说,浙江没什么矿产、森林、黑土地,“浙江经济的成功是把浙江人自身变成了资源”:“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浙江最值得珍惜的资源。新的资源观,最不能丢开的是人这种资源……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很重要的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机会有更大的作为。”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或许可以借助一时的形势、资源、政策,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人。从这一意义上说,“东北振兴”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应当振兴的不是东北这个地方,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你究竟爱的是这片土地,还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只是谈“振兴东北”,普通人也根本无感。一个老家长春的个体户尖刻地说:“上面发个烧饼,到老百姓手里能落下粒芝麻就不错了。你投的这些钱,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些GDP上去了,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以地为本”,而是“以人为本”,那就应当看到,“振兴东北”其实是手段,而非目的。应该做的不是振兴这个地方,而是让人感到希望,活得体面和尊严。这就好比“乡村振兴”,村民的幸福才是目的,当然你可以“通过振兴乡村来使村民幸福”,但如果农民进城才能得到这些,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留下?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留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希望和机会在哪里?

思想上的换血
东北不缺人才。作为一度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教育资源配置很好的一个大区,东北的人才足以自给。谁都知道,东北在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没有人”,而是“留不住人”。

◎沈阳:EX未来科技馆
这次去东北,我的一个深切感受是:东北人受困于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系统,缺乏主体性——也就是,他们做的事,自己无权决定,常常也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甚至也谈不上是为了地方利益,而是为了国家。诸如一汽、大庆油田、哈工大,它们只是碰巧坐落在东北,但从根本上都服务于国家战略。诸多大型国企连本省都没有管辖权,不是当地能自己说了算的。1980年代初大兴安岭火灾,连烧剩下来的木材也全都火车押运走,当地无权处置。
在哈尔滨,一位当地的经济官员向我强调,市场化并不是一切:“东北振兴,经济意义远远小于国家战略意义”,黑土地上的三江连通工程更多的是着眼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就此而言,“黑龙江的战略地位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所以仅仅从经济意义上来衡量黑龙江,对它不公平——超市里的东西你可以挑选不同品牌,但大国重器,你少不了啊!”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止东北,但在东北尤为严重。在南方,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赚钱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东北,人们似乎觉得为国家才名正言顺的,必须“服从大局”。如果一个人不是对其自身负责,而总是对上面、对集体负责,那结果就可能导致无人负责。正因为人们长久以来都不是在“为自己做事”,因而很多东北老人都抱有一种非常不市场经济的思维——“我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为什么不给我这样那样的待遇?”
即便是人们怀念那些“过去的好时光”时,也给我这样一种感觉:那与其说是东北人自身的努力所致,倒不如说是“赶上了好时机”。在一百多年的东北近代史上,各方势力争夺这块黑土地,东北的命运都不能自己做主,人们似乎长久以来也缺乏这种意愿。东北人很愿意批判社会,但也不太去反思这事应该怎么样,不去想改进的方法,顶多说一句“唉,现在的社会不就这样嘛”。
也正是这种主体性的缺乏,让许多人认定,东北振兴只能自上而下推动:人们不相信单靠自己微弱的力量能改变什么,而期望着“政策”能带来神奇的转机,似乎只需要家长给东西,而无须自己为此积极主动地去推动,但恰恰是这种“等、靠、要”的心态阻止了本地发展,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力,总是取决于无数市场主体自发的行为,毕竟任何组织的发展都是小个体或局部的试错、优化选择,才带来整体的发展。
现在回头来看,当下东北的问题,其实在它辉煌的年代就已种下了前因:计划经济时代的现代化,只是以工业化的方式把人组织起来,却远不是“人的现代化”。正由于人们长久以来过着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生活,市场化的转型才尤为困难,而当系统崩溃时,人们也更无所适从,最终是无数普通人默默承受了这一阵痛。

很多人都提到1990年代的下岗潮是东北盛衰的转折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全国都下岗,却唯有东北社会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回想那些年时,南方的叙事重点是“我们怎么发家的”,但东北却是“我们怎么落魄的”。这种集体记忆的不同,至今决定着社会的价值选择:体制外不是被看作机会之地,而是危机四伏,这又反过来让人们宁可不去自己闯荡,而是转身依附于强大的体制。一位长春的企业管理人员感叹:“东北是本末倒置了,好一点的工作都在体制内,都想考公,搞得头重脚轻,应该反过来才是。”
市场化改革多少年来想要打破的“铁饭碗”,在东北仍然是香饽饽,普遍的社会心态是:赚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稳定的工作——前些年哈尔滨招聘457个环卫工,一度都引来1万余人报名。当然,公平地说,这远不止是东北的问题,不乏有人断言“整个北方的年轻人目标都是考编制,想的都不是去搞钱,而是去分钱”。如果说南方有什么不一样,那只是因为商贸相对发达,发展出了产权,而在东北乃至整个北方,要想保护你得到的财产,就得进入体制,获得权力——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年来全国都在“东北化”。
一位已南迁多年的东北人和我说:“其实我们老师那时不鼓励我们考出去,因为你还是要回来考公务员的——这还是学校里好老师说出来的话。东北的选择很单一,如果你没有人际和实力,就很难有上升空间。所有人都羡慕稳定、清闲又有权的官位,所以东北产生特殊的社会氛围,以进入体制后低劳动强度的无所事事、无法无天为荣。所有人被嵌入这个体系,固守着刻板的制度,还要面对那些做梦不想干活的员工,这就是一个系统化堕落的闭环。深度体制化的结果,就是东北现在这样,不管多大年纪,都是嗷嗷待哺的巨婴。”
东北要真正复兴,就必须打破这种体制思维,恢复人的主体性,真正释放人的潜力,但问题是怎么做呢?我遇到不止一个人坚称,东北需要“思想上的换血”,“要等到死守着旧思想的老一辈都死光了,才能发展起来”。也正因此,一位对东北的现实极为悲观的朋友,又同时抱有相当的乐观,因为她相信:“现在最破败的地方,也将是可以最快得到重生的地方。”

自己从土里刨食
虽然这些年来媒体上总说“东北衰退”,但一位东北官员强调:“其实和我小时候那种灰突突的相比,生活质量是在优化。你要批评一个地方,你要先了解它,越了解就爱得越深,不能因为现在有点问题就否定它的进步,只是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在疫情放开之后,黑龙江第一时间也提出了“变冬闲为冬忙”,做好前期服务,以便一旦开工就能做起来,而这就需要“怎样既能激发社会活力,又能发挥国企央企的作用”,说到底,“东北振兴,主要还是看老百姓腰包鼓不鼓、脸上笑不笑。”
如果说那种试图再现计划经济时代繁荣的思路是“往回走”,那么这相当于是“慢慢走”,但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有点等不及了。一位很有想法的年轻公务员跟我吐槽:“东北也开始接受海洋文化思想了,但掌权的仍是大陆思维的。东北体制内中年人的普遍想法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感觉有希望但又看不到希望。对于像我们这样前端执行的人来说,想要推动一点改变太难了。”
东北还有希望吗?有。疫情过后,东北财政缺钱了,这是危机也是契机,但怎么改?唯一可取的道路,是从行政驱动改为财税自支的绩效驱动,财政支出要和收入平衡——如果东北没多少转移支付,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这首先就打破固化的体制思维,让老的一批更新淘汰;其次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不换人的情况下,推行新的做法;但最重要的,还是放手让人们去做事。

◎2023年3月16日,在长春的中国一汽红旗制造中心繁荣厂区,全自动机械手臂在装配轮胎
东北的希望在哪里?在我看来,既不来自上面给政策,也不来自外面的客商过山海关来投资给钱,归根到底还是要释放东北人内生的力量,“自己从土里刨食”。
哈尔滨的文化人老孙是闯关东的第四代了,一直在推动一些本地文旅资源的创意,在他看来,改变说到底事在人为:“东北当下的衰落,可能也只是历史的尘埃,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我们现在是比南方落后,但这不是说一定要照搬它,可取的谋生之道不是生搬硬套、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看我们争取什么样的机会,找到不一样的形态,看看我们能改变什么、影响什么。”
另一位已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哈尔滨人,极力主张现在的步子还太小了:“政府的改善,是跟自己以前比,那不可否认是有进步,因为它以前很差,但你要横向比。现在是城市竞争的时代,跟南方比,你怎么才能吸引到年轻人才?比如哈尔滨落户政策,有变化吗?有。有用吗?没有。早几年也罢了,现在各地都放开落户了,哈尔滨市的户口,比深圳更有价值吗?”他说到这里断言:“不弄点深圳特区那样革命性的政策,没辙。”
然而,这又有点像是“要政策”,似乎在那个时机到来之前,做什么都没用。有东北朋友说,他一度也相信有形之手的神奇魔力,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兴起不过是伟人在那里“画了一个圈”,“但经历了这些年,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人不行,那就算当年在东北画十个圈都不管用。”
这些年来,他在各地也算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只有你自己从土里刨食的时候,你才是独立的。我父母都有下岗经历,让我见识了体制的不稳定,所以在我眼里,体制从来不是稳定,而是牢笼,一旦离开,连生存都会成问题。我之所以能抓住机会,也是因为我是体制外的,没得到任何好处。我就像是东北的南方人。”
所谓“南方人”,在这里的意思是适应市场,并且人与人之间能通过契约合作共赢。在东北,往往自己捞一票就走了,极少能看到像华南宗族社会那样亲族一起团结打拼的,因而南方还能先富带动后富,东北是先富先跑,行事和决策都是“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如今遍及全国的张亮麻辣烫是2008年创立于哈尔滨的,据说他从亲戚杨国福那里得到了配方(这些故事版本众多),起家的那些人都来自阿城的同一个村子,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在农村而非城区,因为只有在农村社会还存在像南方那样的自发联合,毕竟你要成功,除了配方,还得有团队合作,组建不了团队就不行。这种社会资本在南方很普遍,但在东北就成了罕见的例外。
东北经济的活力,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无数人成为能自主的市场主体。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秘诀,说到底就是打破体制内思维,把普通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求取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解放思想”那么重要,因为这与计划经济的逻辑刚好是反着来的:在国企这样的大型组织内部,一颗渺小的螺丝钉往往是无权也无责的。深谙这种组织文化的一位东北朋友一语道破:“你只能干领导要你干的事,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激励机制,也没什么自由行动的空间,都是一环控制一环,老人控制年轻人,自主权很小,所以没劲。”在看破这些之后,他一年前“跳船下海”了,因为“我宁可当一条野狗,也不要当一条被抛弃的老狗”。

◎哈尔滨,参观者观看展出的连续化电化学法制备可膨胀石墨生产装置模型。当日,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动哈尔滨高新区专场启动。本次路演以“科技赋能东北振兴,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为主题,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高端装备、新材料与新能源四个领域81项科技项目亮相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能仅仅寄望于个人敢闯敢干,毕竟当外部不确定性增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抱大腿。市场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因而任何市场主体的行为都是一场探索,本质上都是“看见不可见的未来,踏足没有路的领域”,这不仅需要“关系”这样的社会资源,更关键的是要有市场信息,个人的勇气、自信和合作机制,还需要公共机构为他们提供公平、法治化的市场环境。
在更年轻的一代东北人那儿,这正在逐渐成为新共识。一位30来岁的黑龙江朋友说:“我爷爷去世前曾经说过,他和我爸爸这两代人都没有机会了,不是因为环境,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环境的一部分。但从这个逻辑推论下去,新的一代也有很大可能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机会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取决于个体如何与环境互动,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只要更多人这样想、这样做,那就有改变的可能。”
是这样,当东北人能为自己负责、肯为自己未来努力的时候,就有未来。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有位东北的民营企业家感叹:“我相信东北一定有未来,但我不一定看得见了。”另一位则更犀利:“我也觉得有未来,只不过不在东北。”——同样是个人努力,如果在别处更容易获得成功,那为什么一定要在东北?这就需要东北下决心营造一个能让人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的制度环境。
留给东北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