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员出访世界,自然是一次次的文化碰撞。若能考辑他们的日记、笔记、书信等材料,这些交谈、观察、思考,乃至材料中的“见与不见”,都对历史深处的探寻大有裨益。何况,外交官们这次出访见到的人中竟有日后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除上述重大问题外,童年罗素是何模样,他与中国结缘起于何时,以及西人姓名考释等,本文都有相当新颖的推进。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2年1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丁,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事情的缘起,为一八七七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清朝驻英公使馆一行四人应邀前往罗素公爵家拜访。事后三位参与者留下记述,分别为正副钦差大臣郭嵩焘、刘锡鸿以及翻译官张德彝。所谓童年罗素,就是后来成为大哲学家、获得一九五〇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他是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勋爵的次孙。因为人物的外语译名古奥隔阂,迄今为止,似无人注意到这里有关于童年罗素的情节,特撰此文试为揭明,或可为近代中外交往与罗素的中国因缘增一谈助。

郭嵩焘的记述
光绪三年二月十一日(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在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的居间策划下,清驻英公使郭嵩焘携副使刘锡鸿及翻译张德彝、马格里,一行四人,驱车二十余里,去访问英国一家老贵族:
(光绪三年二月十一日)礼拜。罗尔斯勒斯夫人约茶会。勒斯为三十年前宰相执国政者,年八十五,住里登门地方。所居室曰:布洛得叱,一小结构,树木环抱,多数千百年古树。来陪者罗尔斯佛得思里。勒斯言,约尔克海口有大教堂,为英国最著名者,不可不一往视。情意恳恳,自言今日读辣丁古文字书,年老而学犹勤也。孙二人,皆纯良文秀,小者四岁。问其年,曰:“佛尔珥叱。”佛尔者,译言四也。珥叱者,年也。问其名,曰:“白尔思兰阿克威林石。”问何以名字如此之多,始知其以三名合成文也,大率白尔思兰名,其正名。(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五,岳麓书社二〇〇八年版,141页)


右图:“罗尔斯勒斯夫人”:罗素的祖母
“勒斯为三十年前宰相执国政者,年八十五”一句显示,郭嵩焘造访的主人家就是罗素勋爵(John Russell, 1st Earl Russell,1792-1878),一八七七年正是他的八十五周岁。他于一八四六至一八五二、一八六五至一八六六年间两次入相组阁,掌御大英国政。他前后两次结婚,第一任夫人阿德莱德(Adelaide)于一八三八年病故,留下两人共同的一对女儿。三年之后一八四一年续娶弗朗西丝(Frances,昵称Fanny),给公爵生下三男一女。“约茶会”的自然是Fanny老太太,也就是小罗素的奶奶。
“里登门地方”,郭嵩焘的译音用字不准(或许“登”为“齊”的讹字),据下句提到的罗家宅邸实际所在,可以确定所指即是Richmond Park,今译里士满公园,是伦敦的御苑之一。罗家大宅“布洛得叱”即Pembroke Lodge,今译彭布罗克山庄,是里士满公园的十大建筑之一,曾于一八五七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赐赠给时任首相的老罗素,供他一家终生居住(Pamela F. Jones, Richmond Park: Portrait of a Royal Playground. London, 1972, p.41)。
这座庄园坐落于一片坡地之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泰晤士河谷和温莎宫苑。首相的长子夫妇不幸早逝,遗下两男一女,由祖父祖母监护。小罗素一八七六到一八九四年在此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二十二岁。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后来罗素在回忆录中写道:“久而久之,开阔的地平线,无遮无挡的日出日落,在我眼里就是理所当然的事。”(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1914, Boston/ Toronto, 1951, p. 13)

文中提到的两个小男孩,就是老罗素长子的遗孤,分别是斯坦利·罗素(John Francis Stanley Russell)和本文的主人公伯特兰。长孙当时十二岁,已经入学,平时住寄宿学校,周末回到爷爷奶奶的庄园。《罗素自传》对大哥有一些记述。郭嵩焘的日记显示,他特别注意了在场众人中最小,可能也是最活泼的成员——那个四岁的小朋友,问了他年纪、名字。小家伙显然不惧生害羞,有问有答,让钦差大人甚是欢喜,印象深刻。有关郭嵩焘和小罗素的英语对话,待下文分解。
张德彝的记述
陪同郭嵩焘往访前首相罗素一家的,还有汉翻译官张德彝。在他的日记中,对当天的行程见闻及罗素祖孙两代均有描述:
(光绪三年二月)十一日丁酉晴,凉。申初,同马清臣随二星使乘马车过泰木斯江长桥,西行三十余里,至立墀满村大囿旁,拜公爵勒色喇。屋宇建于山头,四望无际,树木参差,花卉繁盛。入内见其妻,七旬老妪也。其次子勒慈,暨其长子勒萨所遗之子女各一,皆八九岁。继入内室见勒公,年八十有五,鹤发童颜,床头危坐,言语温恭。坐间又来男女六七人,皆左右邻也。各饮茶一杯,面包几片。临别,其孙女勒阿姒请署名于簿。(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二〇〇八年版,363页)

把罗氏宅邸所在的Richmond译为“立墀满村”,译音用字比郭嵩焘的“里登门”准确。“公爵勒色喇”,即Earl Russell。在场的“次子勒慈”,即威廉·罗素(George Gilbert William Russell,1848–1933)。“长子勒萨”,即安伯雷子爵(John Russell, Viscount Amberley,1842–1876),在一八七七年中国客人造访罗家之时,他已去世一年有余,其妻去世更早。以上信息与罗家的成员情况符合。
但是,张德彝说“所遗之子女各一”,却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夫妇俩生了二男一女,二男已见上文郭嵩焘记述部分,一女鲁克丽霞(Rachel Lucretia,1868-1874)已于三年前病故,另有一个孪生姐妹,出生时即夭折。所以,张德彝所能见到的小孩只能是Francis、Bertrand两兄弟,一八七七年之时分别为十二岁、四岁零八个月,因此张德彝下一句“皆八九岁”,也有失笼统。
至于提到的女孩“勒阿姒”,名字显然一依张德彝的外国人起名法:姓使用Russell的第一音节勒。但阿姒(A-Si)所指不明,有可能是老首相的另一个孙女,属于罗家的哪一支不得而知。前述郭嵩焘记录的是“孙二人”,没提到孙女,的确是当时罗素家只有二孙的实情。同住的女性成员中有一位颇为活跃的“阿加莎姑妈 ”(Aunt Agatha),为罗素的姑姑,老首相的女儿,但与“其孙女”的说法不合。
刘锡鸿的记述
三十年前宰相曰专勒士者,年八十五矣,寓李志门(地名)之偏布禄罗址(里名),相距二十四里,嘱威妥玛致意,订期来相访。以其年高,不欲劳之,于十一日特往就见。其人步履虽艰,目光荧荧,尚能读书,日以著述为事。自谓幸延残年,得见中国名下士,告别时犹恋恋不舍也。(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二〇〇八年版,135页)

这是此行记述的第三个版本,作者是清驻英副使刘锡鸿。他心目中此行的主要人物只是八十五岁的前宰相“专勒士”,即John Russell。见到他,就达成宗旨,对同一天见到的其他家庭成员不着一笔,可谓公事公办,见到满大人兴奋不已跑前跑后的小孩子及其与郭正使的对话,更不值一提。这颇可体现刘锡鸿冷淡的性格特点,也是他与郭嵩焘不睦的又一个表现。他的记述比前两个记录唯一值得称许之处,是他提到此行的幕后牵线人是威妥玛,起初的会见动议,是来自老罗素勋爵主动表示愿意到大清使署来拜访,清使馆答复表示要往拜长者。往复沟通之后,这才有了郭嵩焘提到的罗素夫人的家庭茶会邀请。
罗素本人的回忆
罗素在七十九岁的时候出版了自传第一卷,写的是他生命旅程的前三分之一:一八七二到一九一四年,从出生到出名。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童年、少年时代,在幼年先后失去妈妈、爸爸的经历,在罗素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孤独”是他经常提到的词,但他童年的整个基调还是欢快、幸福的。《自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历历在目的记忆,是我在一八七六年二月到达彭布罗克山庄时的情景。”(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1914, p. 7)新来的小主人带来了不小的骚动,山庄的仆人们对他好奇备至,各种特别照顾,让他大惑不解。家庭教师、仆人们给他带来不少快乐。幼小的他,当时也不晓得上至在任首相、女王的各种枢机官,下至贵人名流,都曾对他加以仔细端详。
他记得,他被接到山庄,是在一个融雪的季节,那时他四岁;他记得四周岁生日那天,吃了生日蛋糕,喝了茶,得到的生日礼物是一件乐器,一把小号,他爱不释手,吹了整整一天(同上,p.32);之后是上幼儿园,从四岁到五岁半,那段时光给他带来不少乐趣。他提到,祖父家里有不少大名流、各国大使来来去去,具体是哪些,在四五岁的小童记忆里当然是难有名有姓的。小罗素一定是个活泼、多动的孩子,一次家中安排四岁的他照相,摄影师无论如何也没法让他静下来不动,无奈之中,向他许诺,如果他乖,就会得到一块海绵蛋糕(sponge cake)作为奖赏。拍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在晚年仍然耿耿于怀的是,大人们不守信用,他配合了照相,奖品却没有给他兑现(同上,p.19)。

现存一幅据说是摄于一八七六年的小童罗素的半身照,我愿意相信,这就是当年大清客人郭嵩焘一行在彭布罗克山庄见到的“白尔思兰勒斯”的当年模样,跃跃欲试的体态显出有点淘气,头发乱乱的,但眼睛明澈,透露着聪颖和无穷的好奇心。
有关一八七七年的中国来客,看来罗素并没有形成一个概念性的印象,否则以他的中国之爱——《罗素自传》有专门的“中国”一章,记述他在中国讲学之旅、社交圈子——他一定不会不写上一笔奇装异服的满大人出现在他家庄园里引起的轰动。按张德彝所记,拜访过程当中,“坐间又来男女六七人,皆左右邻也”,这应该是闻讯赶来的好事邻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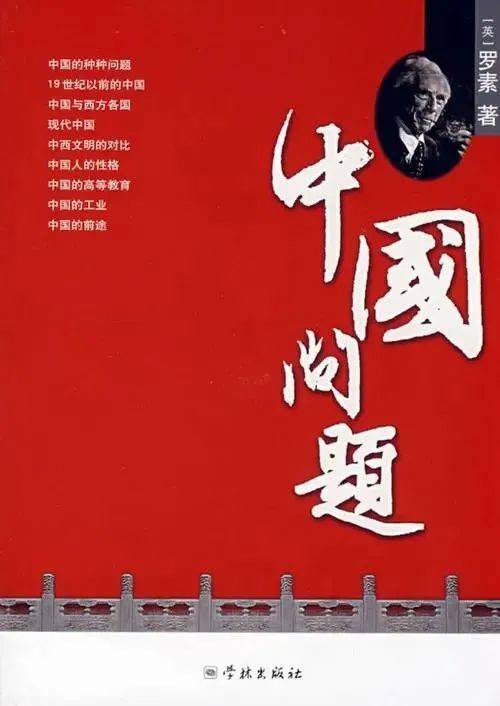

当年的四岁小童“白尔思兰勒斯”,后来以数理逻辑改造哲学,成就了以“语言学的转向”为特征的二十世纪新哲学,驰誉国际,大哲学家罗素的种种著作舶来中国,赢得追随者无数。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间,他从任教的剑桥大学请研究假,应邀偕女友勃拉克(Dora Black)访华一年之久,除了在北大进行逻辑、哲学的讲学、研究,还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写出一本《中国问题》,当中他写道:“吾之往中华,本为讲学授徒。然居华愈久,则愈感吾所能为师之处少,应请教于中国人之处实多。”这种谦逊除却个人方面的客气,实际的意义更多在于为西方文明的主流地位、强势态度做修正。当时“一战”刚过,欧洲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惶惑期。罗素以一个做数理哲学出身的哲学家而关心入世的思想、社会问题,身体力行,力促西方走出自我中心,在“中国问题”中为西方求镜鉴。
见闻异词
据目前所知,在公开出版的西文书刊报章中,未见对中国外交使臣这次来访留下的文字记录。前首相罗素本人生前写过一种政治回忆录(Recol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1813-1873),出版于一八七五年,时间还在中华客人到访之前。

当年去罗素家做客的四人,洋翻译马格理(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没有自己写过回忆录,一九〇八年出版的《马格理行述》(D.C. Boulger & J. Crichton-Browne,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London, 1908)对此没有一字提及。另外三人,正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翻译张德彝,各有记述,情节在详略取舍上颇有异同,要在均有独特信息,可以互补,把这一场星期天英国贵族之家下午茶复原到一个比较有细节的程度,事件、地点、风光、建筑、家庭成员关系、过访的邻里、简约的茶食、临行时要署名留念的访客登记簿。
姓氏Russell的汉字化,三位记述者各有自己的写法,郭嵩焘“勒斯”,刘锡鸿写了John Russell全名“专勒士”,张德彝用了最复杂的方式:在保持一家人同姓的情况下,做出三个名字来“勒色喇”“勒萨”“勒慈”。这是他的常见做法,为外国人名字汉语汉字化闯出一条新路来,颇具匠心。

Russell这个姓氏在英语世界不算稀见。清末在中国活跃的美国商社“旗昌洋行”(Russell & Co.)东主Samuel Russell,当时的译名为“剌素”。本文的主人公罗素的爷爷、英国政治家John Russell曾经在马克思的笔下出现过,编译局译为“约翰·罗素勋爵”。他的侄儿利奥波德(Odo William Leopold Russell,1825-1884)是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德意志大使,在李凤苞《使德日记》中以驻柏林使团的领袖人物、热心承诺为英中关系穿针引线的面貌多次出现,名为“卢赛尔”(见拙文《大清的朋友圈——李凤苞记录的诸国驻德公使名单》,载《语藏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132、146—148页)。
郭嵩焘对这次访问的记录细节最多。日记里的“罗尔斯”,是英语Lord“爵士”不准确的音译。在“日记”中郭嵩焘在更多时候译写成“罗尔得”。“佛尔者,译言四也。珥叱者,年也”,写的是小罗素回答问他几岁,正常的英语说“四岁”,是four years (old),绝无four age(s)之说。“珥叱”之为“年”,谓age“年岁”。不通的four age,想必是郭嵩焘自己或者是他的某些英语欠通的文案编造的,小罗素不会犯这种生来就说英语的人(native English speaker)永远不可能犯的错误。对罗素名字发音的记录“白尔思兰阿克威林石”,与原型Bertrand Arthur William相差比较大,不能逐个音节对得上,“思”不如“忒”,“克”不如“色/瑟”,“石”是赘余,人家原名是William,而不是Williams。“白尔思兰名,其正名”,字句不甚顺畅,友人艾俊川认为原文或为“白尔思兰为其正名”。这些出入,在英语不通、自己口音又有根深蒂固的湖广话干扰的郭嵩焘的“还音”实践中属于正常情况,读者心知其意,综合判断可也。

一八七七年这次郭嵩焘一行前往彭布罗克山庄对前首相罗素的礼节性访问,在中英外交史中并没有很重要的意义。罗素本人当时年幼,没有留下记忆,但这次会面事实上成为他与中国结缘的序幕。当年六十岁的郭嵩焘帮他留下了记录。此篇小记如能为未来的《罗素传》增加一条不仅时间地点人物确定,而且情节也亲切有趣的材料,则英语汉诂地看明白这几段外交官日记就有了历史的意义。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九日于上海衡文公寓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