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k Dychtwald ,90后,在美国加州长大。他曾在中国旅居,香港教父给他取了中文名“戴三才”。在成都、深圳、毕节等地的青旅,戴三才认识了一帮中国的同龄人,写成《中国后浪》一书。这本书英文版首发时,在欧美颇受关注,对于英语世界来说,书中的中国是一个更新鲜、更当下的现代中国。这本书也是中美两国年轻人,相互打量、相互碰撞的一种见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作者:施敏珠,摄影:李知诚,编辑:陆莹,头图来自:出色WSJ中文版
“我已经快两年没有回到中国了。”
戴三才说起中国,用的动词是“回”。
2020 年 1 月戴三才为了一个和视频网站合作的项目回到美国,当时的预计周期是两个星期,他利用这段时间安排了一些演讲。疫情发生,两个星期变成两个月,最后变成两年。在这期间,他的书 Young China 中文版出版,出版社译作了《中国后浪》。
2011 年左右,在香港、深圳,乃至成都、毕节,在校园里、青旅里,戴三才认识了很多 90 后的中国朋友,他把他和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写成了这本书。
他把笔尖对准从 2012 年定居国内后认识的中国年轻人,剩女、学霸、“小皇帝”、“房奴”、性少数群体纷纷出现在他的书里。为了采访,戴三才在成都一家青年旅舍里一住就是半年。
对于一些他的采访对象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在毕节,他到一家本地餐馆吃饭,餐厅的服务员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为了避免尴尬,朋友只好介绍戴三才是少数民族。在此之后,戴三才明显感觉到这位服务员抽了一口气,缓解内心的局促。

接受采访的时候,戴三才用的是普通话。除了有一些语调上的问题,他的中文算得上流畅。他甚至能听得出中国不同地方的口音,却也不自信,笑着说回到美国一段时间,普通话都退步了。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还会把“杯子”说成“辈子”。
离开中国的两年时间,戴三才时常会跟出现在《中国后浪》的主人公联系,他在后记中说:“对所有允许我将他们写进这本书的人,我都要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2011 年,戴三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将自己交换的地点选择了中国,报了香港大学。当时,他身边的同学大多选择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学校,但戴三才翻起那些学校的宣传页,仿佛像是在看一本老旧的历史书。而中国大学的宣传册,让他想起了曾经读过的科幻小说:一个东方国家将在未来被科技改变,成为世界强国。当时科幻小说家们的想象对象大致上都是日本,而戴三才知道现在可能是中国正在被科技深刻改变。
港大读书期间,戴三才去了一趟深圳。他发觉,自己看到的中国,完全不像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媒体们描述的那样。在深圳,他明明看到了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庞。
2012 年毕业后,他决定只身搬到中国来,住在成都一家青年旅店。写作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青旅认识朋友,去到朋友们的家乡,听他们的故事。他到苏州做英文老师,又在网上认识寻找新的采访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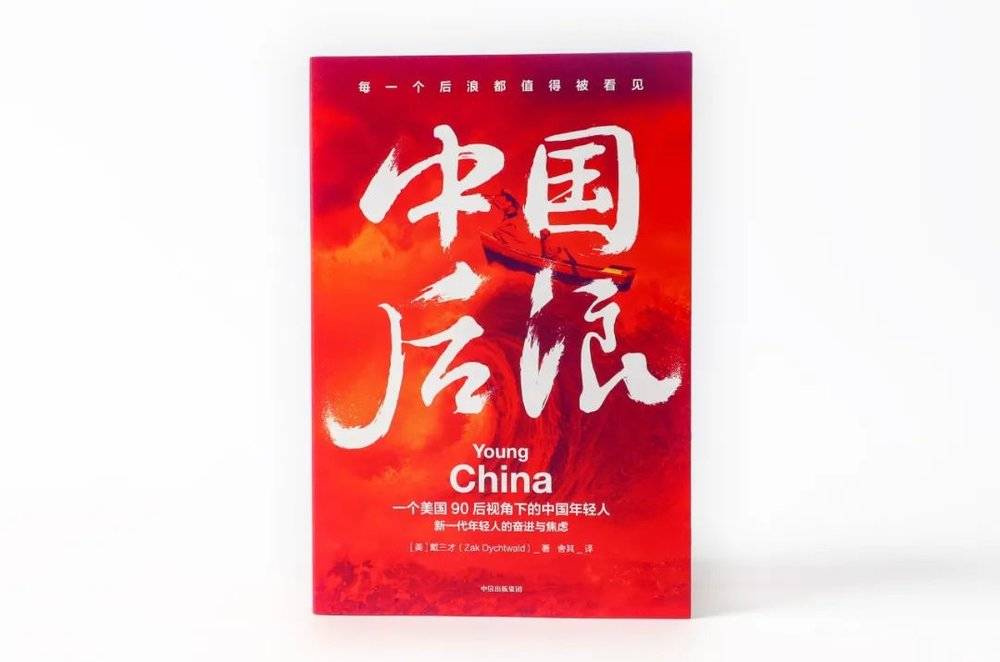
如果梳理出一条来自国外的中国写作者线索,1990 年出生的戴三才是最新的一代,他的写作对象也是更新一代的中国人。《江城》的作者何伟、《打工女孩》的作者张彤禾、《鱼翅与花椒》的作者扶霞、《长乐路》的作者史明智、《再会,老北京》和《东北游记》的作者迈克尔·麦尔都在中国和国际上得到了关注。
戴三才不太敢把自己和这些人相提并论,他甚至也不敢说自己做了一些“更新”前人作品的工作。戴三才说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媒体,可以更自由地“乱跑”。他也不想做一个消失在采访对象背后的写作者,而想更有深度地去一起跟他们过生活。
在加州,提出“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就住在戴三才家附近,他的父亲甚至认识马斯洛。戴三才习惯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今天的中国,“我更多是从群体的角度”,在他看来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当赚钱赚得足够生活了,物质也不再匮乏,消费已经不再有吸引力,年轻人开始思考一些更形而上、自我认同的问题:“我是谁?”“我为了什么而存在?”“我要到哪里去?”。而中国年轻人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会对世界产生影响。

以下为《WSJ.》与戴三才的对话,采访以普通话进行。
《WSJ.》:是什么原因让你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当时你对中国的想象是怎么样的?是一个相对落后,甚至有点神秘的东方古国吗?
戴三才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于普通话一点兴趣都没有,是我爸逼我学的。刚开始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很差,到现在这门课程都是我整个学生生涯成绩最差的。
但通过学习中文,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有一门课程是中国现代文学,需要看中国最近 50 年的文学作品,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即便这些故事里的比喻我都看不懂。虽然看不懂,但让我产生了探索的欲望。当时我读了《骆驼祥子》的英文版,很喜欢。
我特别喜欢看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吸引我的是,科技的发展怎么影响一个社会。20 世纪 90 年代时,很多西方的科幻作品开始写未来有一个东方国家会变成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写的都是日本,那时日本发展得很好,我觉得他们所描述的未来特别有意思。
在哥大,我们可以选择到另外国家的学校做交换生。看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学校资料,让我想起那些科幻小说描述的一个未来世界强国的样子。我当时从来没有去过亚洲,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是要去法国,选择跟历史相关的专业。我想跟他们不一样,选择了港大。还好被录取了。
在港大的时候,我对于中国的兴趣变得更认真一点。我开始一个人去深圳。我发现我所接触到的中国,跟西方媒体描述出来的中国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样我就决定我大学毕业了以后,要一个人来中国开始认真地学普通话,了解中国文化。
《WSJ.》:《中国后浪》这本书里你写了很多 90 后同龄人,英文原版的名字是 Young China,其实翻译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后浪”因为一个视频网站的演讲有了特殊的指涉。你怎么看书名的翻译?
戴三才 :Young China 在中国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含义,它是一个 100 年前的社会运动(编注:学术上有说法指,晚清时期,Young China 指称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最著名的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大部分美国人不知道这个,所以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他们就取了年轻人正在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国家的一个意思。
“后浪”那个演讲我看了,我觉得它忽略了中国年轻人心里都有的焦虑感。虽然现在中国不可否认比之前好很多,尤其在赚钱、发展的机会上。但很多年轻人觉得虽然他们能吃上火锅,能吃上肉,心里还是充满了焦虑感。
《出色》 : 那么,你认为现在中、美年轻人的焦虑,有什么不同吗?现在中国的后浪跟美国哪一代比较像?
戴三才 :要分层次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消费者的层次来说,中国的 90 后有点像美国“二战”后的那一代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很强,所有人脑子里都只有消费,拥有强大的购买力。而他们的消费,又会带来很强的蝴蝶效应。
中国年轻人跟美国年轻人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可能在和上一辈人的代沟上,中国年轻人和父母的代沟是更大的。这一代年轻人因为社会快速发展,生长环境和上一代人是很不一样;而我跟我父母差别没有那么的大,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我爷爷和我父亲就存在较大的代沟,因为我爷爷的成长过程经历了“一战”后的大萧条。我爷爷所长大的环境是物资匮乏的,他们对于未来有非常多的焦虑,甚至是生存的考虑。
《WSJ.》:你的书中也不断提到消费或者说是物质的变化,是具体怎么影响了这个 Young China 这一代人的?
戴三才 :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可能比较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理论来看中国不同代际的人对于需求的定义。之前中国物质条件不好,对于年轻人来讲,赚钱是被放在首位的,成功和开心这两个概念也是放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一代物质环境变好了以后,马斯洛原理说的金字塔要往上爬,年轻人就越来越面对着更抽象的问题: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为什么而活?我觉得这是自我认同的问题,是身份性的问题。
而对于上一代中国人来说,“享受”是一个很遥远的词,是一个根本不会考虑得到的东西,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当然可以找到一些快乐和乐趣,但是不像现在年轻的一代有那么多享受生活的机会。
有一个概念叫“选择悖论”,就是说对人们来说选择越多越不开心,有种 formal 的感觉。人们总感觉自己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这让人们心里变得很压抑。
《WSJ.》:其实美国的年轻人其实更早地接受到了消费主义,但现在也许不是发展那么快,但美国的年轻人依旧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你有没有见证过快速的物质变化带来的影响?
戴三才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一样,在那么短时间内发展得那么快,所以真的想做一个对比的话是很困难的。中国家庭很多是隔代教育, 所以中国年轻人跟他们爷爷奶奶讲话的时候,他们知道苦日子离得不远,就可能在自己家里头有一个人接触过,或者自己经历过。
我爸是 1960 年代自己开摩托车,从新泽西开到加州的,他是很经典的一个嬉皮士,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于物质文化的反抗。我不知道把嬉皮士运动和“躺平”相比是不是合适,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运动。我把它说成一个运动,我不知道合不合适,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沉默的反抗。年轻人对于拼命奋斗的文化,要做自己的反抗。
我爸的那一代人可能有类似的反抗,轮到我的时候,我从小就听到他说金钱不会让你快乐。我们都知道需要赚钱,要赚个够,但光赚钱是不够的。

《WSJ.》:你说中国的千禧一代是“观察的一代”,他们看美剧、追赶西方时尚、关心西方政治,你认为他们认识的西方跟你所处的西方,在你看来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西方人对中国其实有一些认识的局限,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西方一种误解呢?
戴三才 :我觉得在互相了解这件事上,中国人有一个优势:你们小的时候觉得美剧好看,所以你们都很愿意看看美剧,也都愿意看外国电影,从不同的渠道来了解美国和其他国家。
而我在美国的经历不同,除了很年轻的时候看过李小龙的那些东西外,很多美国人认识中国是通过媒体,而这些媒体都是更政治化的,会关注更宏观的东西,甚至有些冷战的味道。所以美国人特别容易对中国产生抵触情绪,而中国人则通过更多的方式与信息来源来观察美国。我觉得这一点有点讽刺。
《WSJ.》:你怎么找到你的这些采访对象的?
戴三才 :我第一次稍微深入一点地融入中国年轻人社会的时候,是在重庆一个青旅。那个时候没几个钱,我每次都会住青旅最便宜的床位,住很久。所以我认识了一些背包客,包括一个来自贵州的朋友欢欢。我们当时聊得很好,后来我去了他的家乡毕节,在书中有一个关于房价的章节是关于他的。
我当时普通话学到了一个沟通没有很多障碍的水平。我们第二天一起要搭车到到成都去,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看到一个外国人的脸,就不太愿意让我们搭顺风车。我们最后选择坐火车到了成都,我跟欢欢又去住一个青旅。
当时那个青旅里面全都是年轻人,而且是从中国各地来的。我们一开始大概跟二、三十个人一起住了一个星期,聊各种各样的话题。这基本上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一个外国人。后来我在这个青旅住了六个月,这期间我开始收集故事。当然你在这么一个青旅里面待着,接触的中国人可能不能说代表全国。
因为住得时间长了,大家都渐渐地放下了心里的屏障(barrier)。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国人的时候,大家都把戒备稍微放低一点。那个时候开始,我想我可能有一些能写的东西了。
我出发来到中国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写书的想法。我喜欢看书,但写书真的非常的头疼,就写书的人我觉得都是有病,这真的非常难。
去哪儿我都会认识新的朋友,中国人特别热情。他们都愿意把我带到他们自己家里,说自己家里的事,喝了一两杯就开始说得稍微透明一点。当我累积足够的故事,我开始知道就是哪一些故事有代表性的。我也会看一些社会学的研究,来证明我所发现的事情是不是真正有代表性的。
《WSJ.》:听起来你所接触的这些年轻人相对来讲是同质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是中产、城市的,他们可能是从一个三线城市或者说从一线城市到成都和重庆去玩。你觉得这些人能代表绝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吗?如果有可能,你还想跟什么样的中国年轻人进行对话呢?
戴三才 :只待在青旅里面采访人的话,我觉得的确没有太大的代表性,所以我出来了。如果说还想采访什么人的话,我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农村里。虽然我在贵州还有成都的农村是有待过;还有就是台湾,我在台湾待了六个星期,采访了五十来个人,但是我觉得我所收集的材料不够我写一个章节。另外,创业特别成功的人我没认识太多,后面是有采访五六个人,但我不觉得我有了解到他们心里的一些真实想法,他们太会面对媒体了,所以我也没有把他们给写进去。
《WSJ.》:非虚构作家何伟很早也从美国来到中国,他也写成都、重庆,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什么?你怎么看待他的写作?
戴三才 :何伟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人,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写中国写得比他好。我在港大的时候,一个教授送给我了一本《江城》,这本书让我知道可以有稍微接地气一点的方法去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人。
坦诚地说,我不是那种特别热爱写作的人。在何伟之前,很多外国人写作所描述的中国都是在迎合外国人口味。直到出现了何伟这样一个角色,去写现代的中国。
我去了成都和重庆,第一次去重庆,就可能感觉最大的感觉是何伟描述的重庆已经不存在了,这让我很失望。我就决定要稍微更新他的工作,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和尚般”的一个角色,当然我不能把自己跟他相比。
我觉得我的角度跟他的稍微不一样,可能我稍微敢一点,因为我不是任何杂志的员工。他当时要写中国的时候,他已经是《纽约客》的雇员。我又不是任何的一个学校的老师,我不受他们的限制。我可以到处走,甚至可以说是乱跑,我没有很多成见要去挖掘,我只想就是真正的去探索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认识朋友的人,而且特别喜欢二、三线城市。我觉得这个区别也蛮大的,很多人都会写上海是什么样子,北京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会特别怀念老中国的逐渐消失,感觉特别可惜。我觉得反正可惜归可惜,但是这就是现实。我想写现实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不带任何情绪地去写。
《WSJ.》:你说何伟是一个“和尚般”的人?
戴三才 :何伟是 1996 年到的中国,当时他 27、28 岁样子。他是交了朋友,但是感觉他个人生活从来没有干扰他的工作。
我 22 岁开始想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可能更多地去参与我所描述的人的生活。我不是一个完全消失在他们背后的一个记者般的角色,我可能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成长过程,更有深度地去跟他们一起过生活。
我看何伟的书的时候,可以看得出他富有特别强的同情心,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一点。我感觉他是心里非常踏实的一个人,而且能够在中国度过那么多年。而且很奇怪,他看起来就没什么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而且写得非常好。
《WSJ.》:《中国后浪》有 12 章,你现在觉得哪个人物是印象最深刻的?
戴三才 :我觉得可能是贝拉的故事,就是一个努力考研最后失败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年轻人。她可能就是大家说的“中国后浪”,她很乐观,也特别拼命地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她没有那么多的态度,也没想过反抗。她不想躺平,不想过非传统的生活,她想考中国最好的翻译专业的研究生,每一年有 6000 人报名,最后只录取 14 个人。她的梦更有代表性,但后来失败了,贝拉选择了创业,跟着时代的变化去改变自己生活的轨道,适应能力非常强。
在高速增长和变化的中国,人们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必须要适应环境的改变。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如果环境变得没那么快的话,你的适应能力自然会弱一些。
中国人没有选择地只能去适应所处的环境,贝拉让我觉得非常认真,甚至有点天真,但是非常乐观和努力的。她充满了一种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会,也一定要主宰命运的态度去面对世界,这让我印象非常深。我后来一直跟她保持联系,还参加了她的婚礼,也讲了一些话。
《WSJ.》:你在书中说,青年人会决定中国在现代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希拉里也提到自己受到了嬉皮士运动的影响,这个运动深植在了美国人的这种观念里。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你父亲和自己的影响。你觉得在中国,年轻人的多样选择会带来什么?
戴三才 :我记得我在成都青旅的时候,他们放的电影就有《在路上》,这是一部根据反映嬉皮士运动的杰克·凯鲁亚克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家都爱听的歌也是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也跟那个运动有关系。嬉皮士们面对世界的态度也对于很多中国年轻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甚至和现在躺平文化有关系,来源于大家对于世界的规则、社会的压力有一些不服。
上一代中国人影响世界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制造业。今天问一个普通美国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答案可能是效率,每个周、每个月会制造多少样东西。但这一代人很不一样,中国现在变成强国了,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和之前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
上一代中国人想影响世界,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允许的。各个国家都有年轻人,但是大部分没有影响世界的潜力。而中国不一样,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可以影响世界了,决定这件事的因素在我看来,首先是购买力。
通过资本主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不得不注意中国人的自我认同问题,包括中国人到底喜欢什么东西,这都是资本或者大公司认真考虑的问题。要开发中国市场的话,你必须要了解中国语言,这个跟 20 年前非常不一样。
虽然这么说有点俗,随着资本的影响力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后果。中国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会变成世界上的一些大问题。很多大公司在 20 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希望在中国发展业务,比如肯德基开了很多家餐厅,但没有针对中国的一个大策略。
因为庞大的市场,中国人的意愿甚至变成了一种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这是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对于大公司来说,它们有了不一样的动力,来了解中国年轻人到底想要什么,之前他们不需要听中国年轻人在想什么、说什么。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你们百分之百地一定会影响全世界,而上一代中国人是没有这种力量的。上一代年轻中国人要赚钱,这一代中国人肯定第一也是要赚钱,但他们还想在世界舞台上有不一样的话语权。但用这个话语权来说什么,我觉得还得打一个问号。
《WSJ.》:疫情给全世界都带来了一些变化,《中国后浪》这本书现在看来让人觉得恍若隔世。你还在持续观察疫情后的中国和世界吗?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跟书中的人物联系,他们和在书中相描述的比有出现什么变化吗?
戴三才 :当然有,还保持联系,我都有他们的微信,每一天都会跟中国朋友或者合作伙伴联系。面对疫情,中国的表现让他们快速地回到自己生活里面,这和其他国家相比要好很多。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自己的政府感觉很失望。
我感觉中国的中产更焦虑了,虽然中国在经济上恢复得非常快。但是我觉得很多普通人,就像我书里面的人,他们过得比之前要压抑多了,希望寻求稳定,在追寻某种稳定的感觉。
对于他们来说,工作没有之前想象中那么稳定。只能选择在大公司里面工作,因为大公司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小公司完全有这个可能。另外一方面,很多人觉得不一定要打工或者在公司工作,因为非常辛苦,人生苦短,想多多享受,想躺平。
这是两个对于疫情不一样的反应,一个是渴望有更多的稳定,因为疫情把生活当中一些不稳定的东西凸显出来了。另一个是,很多人对于他们本来的生活开始觉得不满意,认为很多大公司把他们当成一个一次性的东西来用。很多人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生活:人生那么简短的话,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WSJ.》:你说过回到美国之后重新卷入了“国家认同的漩涡”,具体指什么?你怎么理解所谓的后特朗普时代和后疫情时代?
戴三才 :对于当下的美国来说,从特朗普的阴影中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特朗普是美国“患上分裂症”的一个症状,而不是根源。国家就体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分裂,是不能通过下一任总统来弥合的。
中国的崛起反映出很多美国的弱点,有的美国人感到自卑,有的美国人感觉要和中国竞争,有的美国人则越来越相信美国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的概念。但总体来说,我们要对政府有越来越多的怀疑。
特朗普就代表那种怀疑的声音,他的上台反映出很多美国人生活在非常大压抑与焦虑中。但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右派觉得美国应该当一个更强、更霸道的国家,所以对于现在的美国感到失望;左派觉得美国是一个既卑鄙又欺负其他国家的国家。两边的人现在都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极端。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会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很难从特朗普的阴影中走出来。我觉得他代表了一个运动,虽然他是一个特别奇葩的人,但我觉得不能完全只怪他一个人,因为我不觉得仅仅是他一个人就给美国带来了这样的改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作者:施敏珠,摄影:李知诚,编辑:陆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