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名场面 但大白菜们显然不会被掩埋在冰雪中,在享受过几天深秋的日光浴后,它们最终会消失在东北人民的大缸里,两个月后再以酸菜的姿态被炖进东北人民的大锅中。 而这也是最具有东北特质的饮食符号。


食物之所以经常能完美地区分各种人群,有时候是因为价格,有时候则是因为气候。 酸菜就是因为后者。 腌渍与发酵食物的历史可能和人类的饮食历史一样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区各自“进化”出了带有本土特色的“风味”。 温暖而湿润的南方,蔬菜易得而宝贵的蛋白质难以保存,入冬前各种腊味往往会挂满各家的阳台,在肉价高企的年份甚至能成为财富的象征。

而过去,在东北漫长的冬日里,室内虽然是暖气或者火炕,肉却可以直接冻在室外,拉开门,就像守着冰箱一样样吃。 但这个“冰箱”能冻梨冻肉,偏偏保存不了绿叶菜。
而地窖的出现依然不能拯救东北人单调的冬季食谱:白菜与土豆,炖汤或者炒,炒或者炖汤。 于是乳酸发酵的蔬菜成了高纬度地区人民冬季里共同的“不冻产”。 在这一点上,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两个相距万里的继承者,东北与德意志都做出了极其相似的选择。 甚至搭配的肉食也几乎一致,唯一的差别是一个用白菜,另一个用圆白菜。

就像没人知道谁第一个做出了闯关东的壮举一样,也没人知道这种古老的农作物以及食材处理方式,是如何在这片长期被北方游牧民族控制的广袤雪原中落地生根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酸菜抢在辣椒之前征服了这批新东北人的味蕾,并帮助他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严酷的冬天。 当一锅热气腾腾,搭配着五花肉、血肠与粉条的酸菜端上东北人的餐桌时,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北美洲清教徒们感恩节大餐里的火鸡。



一群人是如何成为一种人的?答案之一是让他们吃同样的食物。 相同的饮食习惯背后往往意味着相同的集体记忆。 比如富庶的浙江偏偏有不少干咸发臭的食物,绍兴有霉干菜,上虞有霉千张,宁波还有一种臭冬瓜,以至于鲁迅经常怀疑浙江人祖上是不是遭受过什么大灾荒,才能接受如此重口味的食物。

·宁波三臭,闻起来臭,吃起来……· 这种记忆在东北酸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便是与时间捆绑在一起的气味。 在日光下轻微脱水的白菜所散发的独特气息对东北人来说是深秋即将终结的信号,而缸中弥漫出酸菜在盐水中发酵的味道往往意味着年关将至。 在计划经济尚未解体的时代,对于一切都与计划与体制挂钩的东北人来说,只有“积酸菜”这件事才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从囤菜到腌菜,这是东北人民一年中少有的非官方集体行动。

但就像欧洲的奶酪、红酒与火腿一样,任何细微的差异都足以让每一缸酸菜发酵出不同的风味。整齐划一的白菜一旦入了各家的大缸,便立刻演绎出百家百味。如果给东北的酸菜认证法定产区,那每一栋居民楼里都能出现若干个酸菜AOC(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

·
每家都有祖传的石头、酸菜缸和手艺 同时,酸菜的制作方式往往也因家庭结构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东北人也并不是家家都腌酸菜。 在结构紧密的大家庭中,腌酸菜的工作往往由你爷、你奶以及你三叔和二大爷等长辈承担,几百斤白菜积一缸,想吃的时候去捞两棵都是顺带的事儿。 而从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另立门户”的成员,如果不愿意或者不方便蹭吃,那就只能在“自己动手”与“不吃”之间做出选择了。 因为购买“外卖”酸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少从健康角度来说不是,你并不清楚哪一棵酸菜是在铺了塑料布的露天大坑里腌出来的。

尽管酸香开胃的酸菜可以搭配多种食材,但是在缺少现代物流与保鲜技术的时代,依然无法改变东北人餐桌上的匮乏。 简单的炖煮与包馅儿终归只能做出有限的排列组合,就像二人转里光棍儿与小寡妇的故事,听多了早晚会厌烦。

所以东北的酸菜在自我进化这条道上一直没有停下过脚步。 在炖煮之外,酸菜炒粉就是烹饪方式上的一次突破性改变。

·加醋的都是异类 而锡纸烤酸菜则是判断一家东北烧烤店是否足够“东北”的标准之一。

酸菜火锅看似异类,实则直接终结了人类在油碟与麻酱上的论战,它用实力证明了简单的汤底本身就是最好的蘸料。

尽管在不断进化,但是东北酸菜从未改变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特质,如果世上有哪一种食物无法用来区分阶层,那一定是酸菜,这是一种属于全体东北人民的食物,不分高低贵贱。 冒着热气的酸菜一上桌,不管是给主任当司机的你三舅,还是当个体户小老板的你二姨,在这顿饭的时间内,大家都要短暂地做一回东北一家人。 而所有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分化,也都会在这一口锅里迎来终结。


劳动者们的饮食方式常常与工业化的进程紧密绑定在一起,当社会生产的面貌改头换面,饮食也随即被重塑。

东北曾经是全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而常年占据东北人冬季餐桌的酸菜不仅一直保持着“计划外”食物的身份,作为一种大众食品,它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实现过工业化生产,自然也不会像涪陵榨菜一样远销全国。 它太过普通,只是在每年“十月一”前后由农民的驴车或者三蹦子拉进城,腌进缸,最终再被端上桌。 酸菜,没有享受过计划与体制带来的辉煌,但似乎也没受到计划与体制的诅咒,在这一点上很不“东北”。 它伴随着移民从山东半岛与华北平原来到更北方的大地,在缸中静静发酵,由碧绿转成金黄,然后在东北人民的铁锅中静静地沸腾,同时也看着这片沸腾不止的辽阔土地。 闯关东、张家父子、伪满洲国、共和国长子、知青建设北大荒、工人大下岗、东北振兴,酸菜比烤串和网红见证了更多变幻的风云。

酸菜的味道始终没变,但是时代却在飞速的变化。 工业化生产的酸菜问世,干净又卫生,传统的手艺在年轻人中逐渐失传。 连当年那句给全国人民洗脑的歌词“翠花,上酸菜”,一晃都已经过去20年了。

一批又一批吃着酸菜长大的东北年轻人又重新踏上了当年祖辈们走过的路,而这一次,他们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远离了故土的他们也许不必担心吃不上家乡这一口菜,不用说在海南,即使在遥远的台北,你也能在吉林路上吃到东北酸菜白肉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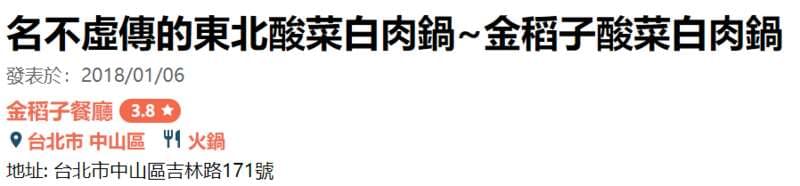
而网络与快递小哥更是能让远在黑龙江的一棵酸菜朝发夕至,虽然一棵菜的价格可以在东北买一缸菜。

·一棵酸菜背后可能是8000+东北人 但是新的“关东”又在哪里呢? 它在地理上的界限早已模糊,在人们心理上的空间远未成形,带着东北味蕾的年轻人们也注定背不走老家的那口大缸。 酸菜依旧,不知翠花今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