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作者:谢祎旻,编辑:Lyra,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 中文播客听众与消费调研》显示,中国的播客用户有将近 7 成生活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但是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小镇青年也开始做播客了。
小镇青年里的这帮先行者,大多曾在大城市读书工作,有海外留学背景,回到小镇后感到与周遭格格不入,对自身处境有强烈的表达欲,但暂时难以突破,普遍处于对未来迷茫的人生阶段。
而播客的出现,让他们发现远方的微光,从听播客到做播客,从播客重度爱好者到独当一面的新手主播,播客成了他们安顿自身或开启人生的一个通道。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听了100个小时
Masa 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在离家 60 千米的招商局工作,每天有 5 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
偶然的一次机会,他从一位豆瓣网友口中得知某款中文播客 App,从此“便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听了 100 个小时。
日本留学回到青岛后,他苦于身边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大部分)在所谓的体制内工作,平时不怎么读书,晚上刷刷抖音、陪陪孩子,周末(和兄弟)喝酒吃肉吹牛逼。”这样的饭局 Masa 参加过一两次就不再去了。
Masa 没想到,在播客这个平台上,有这么多和自己有相同困惑的人,在认真讨论诸如“内卷时代如何突围?”“帮我摆脱焦虑的自洽逻辑”“如何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些在二线小城无处诉说的人生问题。

那段时间,Masa 最常听一档名叫《逆行人生》的访谈类播客,主持人林安是“只工作不上班”生活方式的推广人,常常在节目里对话“数字游民”“即兴戏剧创业者”“绳缚师”等过着“非主流”生活方式的嘉宾。
Masa 从这档播客里第一次知道,国内有一帮人在实践 FIRE(财务自由,提前退休)理念,听到 35 岁的山东济宁老乡翟峰辞职卖房,带着家人去航海的故事时,他备受鼓舞,“心进行自我解脱以后,物理空间都不是问题”。
没过多久,Masa 就有了自己做一档播客节目的念头。他在豆瓣仅有的 3 个播客兴趣小组上发布了召集令,“有趣的家伙,我也只能在网上去寻觅”。
召集令一经发出,前后有三四十人来联系,有学生,有社会人士,“大城市比小城市的人多一丢丢”,但基本上聊了几句就没下文了。

直到还在读大学的咕咕发来私信,约好第二天晚上语音沟通。咕咕从小在深圳长大,喜欢游戏和社会学,当晚两人热烈地交谈了两个小时,“一拍即合”,挂电话后 Masa 兴奋得心脏怦怦跳,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在上海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云树也加入了,三个人敲定第一期播客聊 2020 年终总结。Masa 记得,第一次录播客,他和咕咕都比较拘着,刻意放慢了语速,生怕说得太快显得卡顿。“可能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原因吧。”Masa 说,相比起来,做互联网运营的云树就自如得多。
青岛留得住我的肉体,留不住我的心
开头几期他们聊游戏、读书和南北方差异,播放量并不好,云树也因为工作原因退出了。Masa 偶尔也会感到失落,但比起自己,他更担心小他 7 岁的咕咕,“不要做着做着半途而废了”。因此,他一看到听众评论和平台推荐就转发给咕咕,稳定军心。
后来,Masa 尝试往更多音频平台分发节目,选题上也学着蹭“摸鱼”“吐槽大会”“高考”这样的热点。结果不到半年,就出了一个全网播放量四五十万的小爆款。
那是 6 月初,趁着高考的时间节点,他和咕咕聊了聊两代人的高三,“天才少年”咕咕高三忙着思考人生意义,最快乐的事是解数学题,而已为人父的 Masa,高考前夕紧张得要服安定剂才能睡着,在节目里懊悔当年做题只懂死记硬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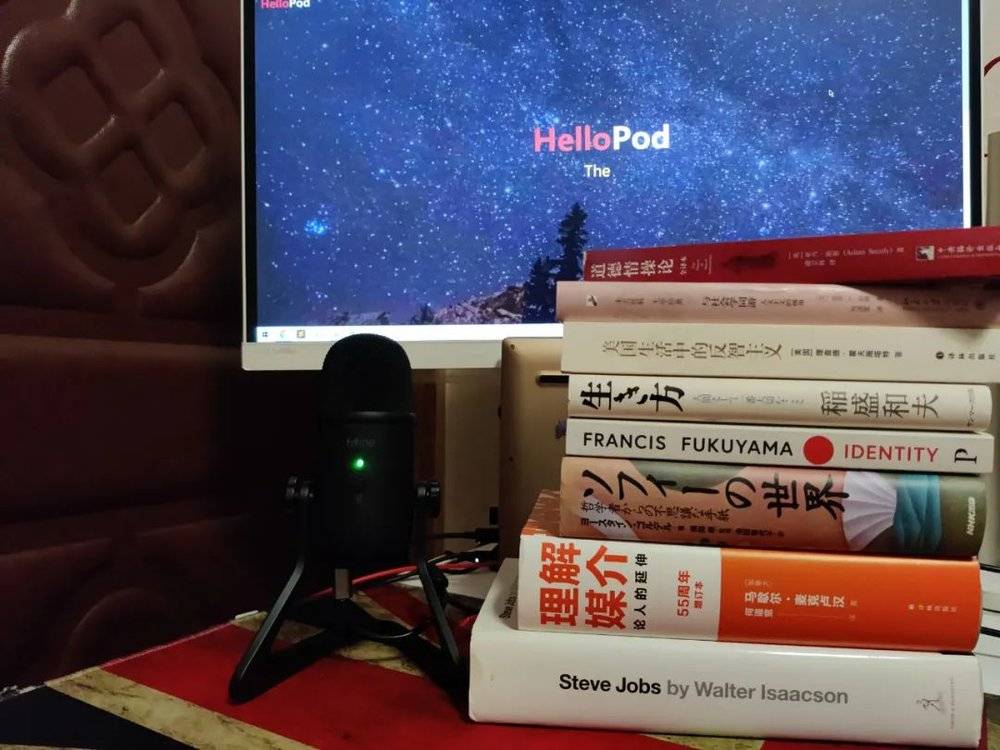
看到播放数据的瞬间,早就做好打持久战准备的 Masa,感到一丝不真实。后台涌入了一堆陌生 ID 的私信,有高中生,问 Masa 高中生活如何过得更有意义,有播客新手请教要如何从零制作一档播客,还有闻讯而来的新晋奶爸,向他讨教带娃经验。
“做这事儿不仅自己开心,还能帮助到别人。”Masa 觉得年轻时那个热衷表达和连接他人的自己回来了。
读书时,他是留学生里积极的活动家,创办了首个专门面向留学生的社交平台,那会儿认识的朋友“大部分留在了日本,进微软、IBM、谷歌那种顶级公司,回国的也都在北上广(互联网行业)做特别好的工作”。
富有社会情怀的他还应聘过海洋保护的公益组织,薪水待遇都谈好了,却因为家人反对而不得不放弃,在传统的山东父母眼里:“做公益不就是献爱心吗?”退休了有大把时间做公益。
而通过播客,他不仅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和志同道合的拍档讨论,还能给予有相同困惑的人一点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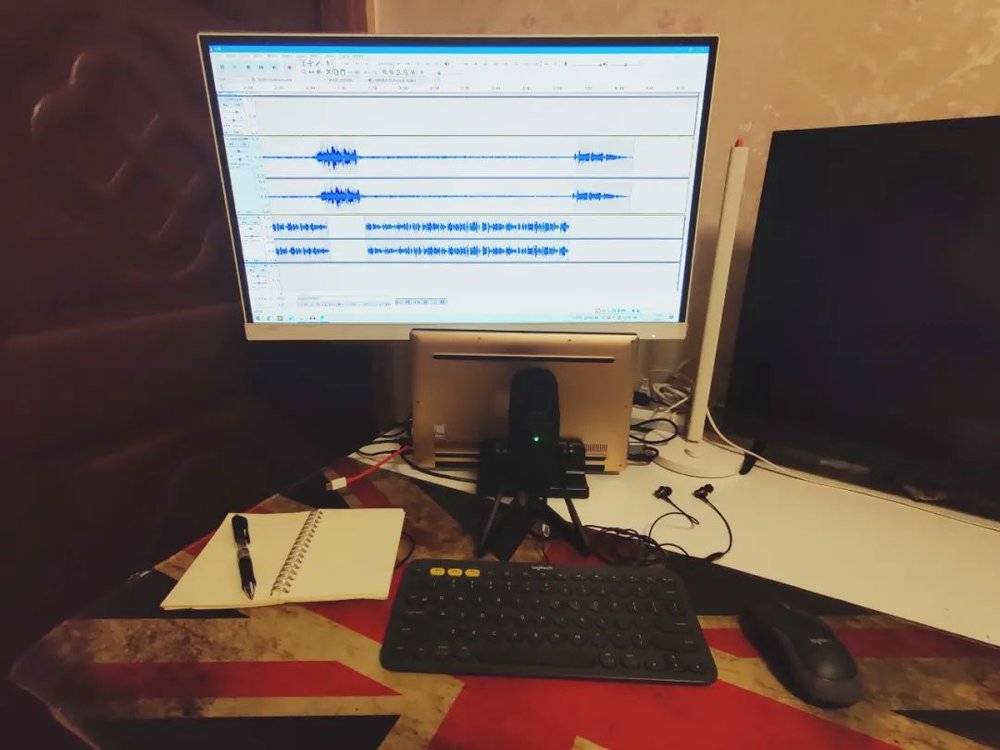
“青岛留得住我的肉体,留不住我的心。”Masa 说,自从做公益的想法在家人那儿碰壁之后,他就收敛起了那些在他们眼中不切实际的计划,每次录播客,他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说要开会,或者借口外出见朋友,家人至今都没有发现他在做播客。
7 月份,他和家人说去北京出差,其实是特地飞去北京参加播客节,两三天里他几乎和到场的播客 KOL 们聊了个遍,“算是半只脚踏进播客圈了。”嗓子都聊哑了,遇到了十来个自称是他节目的忠实粉丝,都在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工作,逮着空 Masa 还去 abC 艺术书展逛了一圈,结识了几个做独立出版的文创青年,正筹划着请他们来录几期播客。
Masa 现在觉得:“没有播客的人生怎么会是我的人生呢?”
意气风发的他正在尝试扩大自己的播客版图,不仅孵化出了第二档播客节目,还创立了自己的播客品牌“Hellopod”,有偿给新手主播提供从零到一的辅导。

原来有那么多年轻人在讨论自己关心的议题
阿鲸是 Masa 在北京播客节认识的播主,在青岛一家书店做新媒体。
在国内,播客以 UGC(用户生成内容)为主,大部分播主遵循 Masa 的路径,从听众转化而来。而阿鲸则是误打误撞去北京参加了一档播客的听友见面会,萌生出“我也行”的想法。
阿鲸今年 26 岁,山东淄博人,在青岛念的大学,就留了下来。她学的是播音主持,但涉猎广泛,喜欢文学、诗歌、艺术,读书时她就对填鸭式的学校教育不满,平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疫情发生后,她开始关心国际政治,热衷思考“疫情下各国的责任”“如何防范疫情在全球的扩散”这样的公共议题。
2020 年 12 月初,她应邀去北京探访一个生态环保组织。当晚,刚认识的朋友问她要不要一块去参加播客《不合时宜》的线下见面会,阿鲸没多想就答应了。
那是位于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一家工业风咖啡馆,场地视野开阔,灯光温暖明亮,开场大家在轻柔的爵士乐声中,自愿结对跳 swing dance,一曲终了,三位主播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听友们三五成群,像朋友一样平等地交换各自对“美国大选”等政治议题的看法。
“我大为震动。”阿鲸说,“原来有那么多年轻人在讨论自己关心的议题。”而在她平时的交际圈中,很难找到愿意花几个小时去谈论公共议题的朋友。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其实已经)在青岛文艺圈里面,他们蛮嬉皮士的,有自己丰富的业余爱好,摄影、诗歌、古董收藏、潜水爬山,不太关心公共议题。”
当时阿鲸就觉得播客这个生态圈太棒了,从北京出差回来后,做一档播客的念头一直在她脑海里盘旋。
恰好十几天后的平安夜,她上崂山一家朋友开的有机餐厅,认识了一帮从一线城市回来的年轻人。
老板娘原来在上海做英语老师,前几年返乡后在村子里开了这家餐厅,成了青岛归巢青年们的聚集地。年轻人有的去学了陶瓷,有的在村子里开咖啡馆,厨师长着一张标准东北大汉的脸,私底下却酷爱思考哲学问题。
那天晚上,一桌五个人酌着小酒、大口吃饭,一边探讨各自对哲学、美学、宗教的看法。阿鲸置身其中,感受到久违的思绪飞扬。她忍不住偷偷拿手机,录下了这场饭桌上的闲聊,整整 5 个小时。征求朋友同意后,她按主题剪成 3 段,美学篇就成了阿鲸播客的第一期节目。

“开了头之后很自然而然就做起来了。”阿鲸说,播客名字《循环往复》也是她下了班在公交车上 1 分钟之内想到的,取自能量守恒定律,“比较符合我对世界的认知”。
“我最想过的生活就是隐居在小树林里”
录制前三期播客的过程中,阿鲸充分体会到了自我表达的快感。
第二期,她和一个同时开设个人播客的好友,天南海北地聊了 1 个半小时,她们同样关心国际政治和环保,说到病毒、极端天气和粮食安全对人类处境的威胁,阿鲸顺带提及前段时间探访北京和福州生态家园的见闻。
回听这期播客,阿鲸觉得找到了某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哇,表达得蛮有逻辑,观点挺新颖的”。播出之后,有一个做教育创新共识社区的朋友辗转联系到她,后来成了第三期节目的嘉宾。
到了第四期,阿鲸自觉转变成了提问者的角色。那期请来了两位前豪华游轮随行摄影师,他们都是阿鲸当时玩古董相机的男朋友介绍认识的,原本只是定期聚餐打麻将的酒肉朋友。那阵子刚好赶上疫情复发,出不去,阿鲸灵机一动,请这两位朋友聊聊“在豪华游轮上工作是什么体验”。
当阿鲸只是提问和倾听,“更多版面交给嘉宾”时,她才发现,原来一块吃喝玩闹的朋友,思想这么有趣,涉猎之广,视角之新,阿鲸觉得很幸运,“重新认识朋友,了解彼此的精神世界”。
这之后阿鲸的好奇心一发不可收拾,触角逐渐从文学艺术领域延伸到了科技与性别话题,聊的话题也五花八门,有高空跳伞和潜水爱好者、社会对女博士女程序员的刻板印象,最新一期请来了一名艺术与旅行爱好者,聊面临消失的中国唐代古建筑。
“本来我以为(做这个播客),和青岛当地圈子的文化人,聊聊文学诗歌,没想到后来几乎每一期的嘉宾都是我刚认识不久的朋友。”

生活里,阿鲸不是一个在人群中感到自在的人,朋友聚会她常常抽离于热闹的气氛之外,聊到一个话题时,她总是过分认真,有时还会说出“感觉不到这样喝酒有什么快乐”的话,把局面弄得尴尬。
但在她构建出的播客世界里,阿鲸可以完全地做自己。从选题到发布,阿鲸是整个过程的主宰者。选题阶段,她会反复拷问自己,是真的有话可说还是为了填充内容,谈到敏感的性别话题时,她还特地加入了男性视角。每次录专业性强的播客前,她都要看大量的论文和书籍,就像她最崇尚的达芬奇,“纯粹为了运用知识去学习知识”。
“如果可以,我最想过的生活就是隐居在小树林里,不问世事,专心去研究一些东西。”
“我这个研究生算是白念了”
与此同时,地处东北十八线小县城的丸子一心渴望去到一线城市工作。
她在北京读的硕士,毕业之际手里有一个新零售集团的管培生 offer,本来要留在北京,碰巧吉林老家的县城发布新的人才引进计划,她抱着试试的心态去考,没想到阴差阳错拿到了一个名额。家人都劝她回来,县城国企工作轻松又稳定,“人家想进都进不去的”,丸子也觉得机会难得,而且业余时间多,可以做副业,就从北京回到了老家。
“回来之后会觉得大城市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生活。”丸子在单位负责文书机要,用她的话说,平常工作有一部分就是“穿针引线”,用一根细线把厚厚一沓文书紧密地缝在一起。
正式工作没过多久,丸子觉得这活儿高中毕业也能做,“我这个研究生算是白念了”,她也曾试着建议领导采用效率更高的工作方法,但领导总是不置可否,“再看看吧”。
久而久之,丸子觉得生活陷入了一种机械和重复,“工作上很循规蹈矩,每天做的事情差不多,(小县城)文娱活动不够丰富,什么话剧、艺术展、脱口秀,这里几乎没有,去同好会遇到的也都是认识的人”。
“生活缺少一些新鲜感”,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到一线城市工作,最好是在年轻人扎堆的互联网行业。

一次机会,她听到了两位在北京做互联网工作女生的播客《贤者时间》。丸子是资深播客听众,大学时就会从 Spotify 上下载一些对谈类播客练英语听力,去韩国交换时,也接触了几档音频类综艺。
但《贤者时间》让她耳目一新,“蛮治愈的播客”,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两位主播之间的友情,她们的一些对话、措辞特别吸引我,不由得会有笑声”。
听得多了,丸子和坐在对面工位的 Mody 提议,“其实我们也可以做”。Mody 比丸子小两岁,但早她三年进这家单位。两人同样是从北京读书回来,又在一个小房间里办公,朝夕相处了大半年,早已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Mody 一开始有点犯怵,市面上都是强观点输出的成熟播客,她担心自己积淀不够深厚,直到偶然间听到一档家庭播客,主播是教社会学的大学女教师,不定期邀请家庭内部成员来对谈,包括孩子的成长历程,甚至还有家庭内部的争吵,她一下子就有了信心:“这样都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每天4点30分下班,是什么样的体验?”
2021 年 2 月份丸子再和 Mody 提起时,两人一拍即合,开始思考播客的名字和定位。Mody 脑子转得快,脱口而出一个“鱼摸鱼”,随即又否定,摸鱼这件事不特别,在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里也司空见惯。
那她们的特色是什么呢?Mody 想到了一个名称,“县里限外”,意思是讲述县城里尝试突破限制的年轻人们的生活。丸子觉得很准确,敲定了名字后,她们花了两个月才设计出最终的 logo。某个中午,丸子和 Mody 在饭桌上和毛毛谈论起这件事。
毛毛是在另一栋大楼办公的同事,温柔又仗义,三个人常常一块在单位食堂吃过午饭,驱车去附近商场的咖啡馆聊天、午休。得知丸子和 Mody 的想法后,她没多想就答应了。饭后三个人找了一家有包间的咖啡馆,用手机录了第一期:“今天的归巢青年是何模样?”
那期节目散发着一种县城独有的慵懒气息,三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孩在工作日的午后,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聊了各自从大城市回到县城的原因,对县城生活的不满和共通的迷茫。
三位女生个性分明,丸子是热情洋溢的乐观主义者;Mody 古灵精怪,工作 5 年来总是陷入恋爱;毛毛心思细腻,又有执行力,是三个人里月收入最高的。

播客起步之后,丸子自觉承担了 leader 的角色,在三人小群里催促大家想选题,召集大家开会,每期节目三个人轮流当主持人、后期剪辑,剩下两个就负责文案和运营。开头几期播放量寥寥,丸子记得有一期她们聊着聊着就无所顾忌,“反正也没什么人听”。
没想到两个月后,她们简单聊了一期“每天 4 点 30 分下班是什么样的体验?”火速出圈,订阅量从 10 来个变成 1000 多人,整整翻了 100 倍。
走红后三个人既意外又纳闷,那期选题是 Mody 下班后在车上想的,节目里也只是各自说了下班后的生活。“聊得很平淡,背景音乐还太大,收听体验并不好。”Mody 说。三人分析了一通,得出结论:选题正好切中了大城市 996 年轻人的痛点和盲区,另外,要归功于丸子,节目发布后特地转发给了好几个主流音频平台的运营,这才上了首页推荐。
丸子对播客最上心,走红当天晚上激动得睡不着,每隔 1 分钟就在群里播报一次互动数据,直到凌晨 3 点,“第二天早上 7 点钟还要起床上班”。毛毛打趣丸子,“以后要是特别火了,不得把你熬死”。
“别人在飞,我在原地踏步”
随着流量增多,压力也越来越大,丸子是最焦虑的那个。她对标《贤者时间》,仿照互联网行业的惯例,给团队定下了一年内达到 1 万订阅量的 KPI。
最初,Mody 和毛毛有点望而却步,但抵挡不住丸子激情燃烧,把年度目标量化到了每期涨粉多少,一个月达到多少,还定期组织复盘。
“在丸子的带动下,我们也激情了起来,觉得可以实现了。”Mody 说,播客能有这么多听众,她和毛毛都挺知足的,“这个阶段主要是帮丸子实现她的梦想”。
Mody 和毛毛都在大城市碰过壁,一个在北京金融行业实习,曾加班到天昏地暗,一个在郑州的教培行业辗转到沈阳,又回到县城,“慢慢往家挪”。
在对未来的规划上,Mody 和毛毛都觉得自己“拼不动了”,两人约好一起去省会城市长春安家,找一份有编制的工作,她们很清楚自己寻求的是安稳之上尽可能有趣的生活。
只有丸子还执着于要去一线城市。前段时间她专程飞去深圳面试,2 天内集中面试了 10 家公司,面试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不仅脑子跟不上,还丧失了对时代的感知。
一个 HR 问她想过 35 岁在职场上要做到什么位置吗,她第一反应是 35 岁怎么了?年龄是个问题吗?还有面试官直接告诉她,“你太严肃了,可能是在国企待太久的缘故”。最后没有一家公司有下文,丸子感到很挫败。回到县城后三人聚会,毛毛说,“欢迎回到现实世界”。

丸子一直想做个女强人,大学时她的榜样是一个走路带风、雷厉风行的学姐,当初丸子决定回老家时,学姐就劝她不要回来,肯定会后悔。
读书时的好朋友在大城市做咨询,偶尔两人聊天,丸子觉得“她谈吐清晰,讲话一针见血,很有气场”,是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那种“别人在飞,我在原地踏步”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丸子想去互联网行业工作,但苦于没有经验,她希望播客可以成为一块敲门砖。
“做播客的过程就像在做一个产品,等到 1 万粉丝的时候再去投简历。”丸子说,“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一块精神自留地
同样是县城青年,来自成都大邑县的小败画风清奇,他既不关心热点,也不讨论公共事件,播客对他来说,更像一块精神自留地。
他的播客名叫“加班Radio”,乍一看以为讲的是互联网大厂年轻人的 996 生活,但实际上,至今更新的 10 期,邀请的嘉宾都是小败朋友圈里的大邑县本地人,有刚认识的业余脱口秀演员、县城咖啡馆老板,还有他定期聚会的老朋友们。

每期播客从选题到录制都随性而为,第一期播客是农历新年的晚上,七八个县城里的朋友来小败家里做客,临时起意录的,每次录制结束后,小败几乎不做剪辑,因此,听众会在某期节目开头听到一个长长的嗝,在好几期节目里听到嘉宾拿起手机接电话的应答声。
小败从小在大邑县长大,目前是一名自由职业者,身上有一股成都人特有的乐天气质。从四川一所学院的设计系毕业后,他先去成都市区一家设计工作室做助理,工作上没有成就感,他就用业余爱好来填补。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都会去住处附近跑步,生活也过得去。
一年后,刚好老家一家自媒体公司在招活动策划,他就回到县城。和几个同公司的朋友挖掘本地有趣的人、事、物选题时,小败意外拜访了村子里一家夫妻合开的书店和建筑工作室。那家建筑工作室接了不少振兴乡村的公共建筑项目,小败和主理人聊得投缘,留了下来,一做就是 4 年。
正是在这期间,小败养成了边工作边听播客的习惯。“做设计画图要长时间对着电脑,我习惯听点东西,既不影响我画图,又能解闷。”

有段时间工作室接了一个项目,小败平均每天要开六七个小时的车,将近 3 个月的时间,他把一档节目全听完了,这还不是最疯狂的时候,2020 年疫情刚爆发那阵子,小败和工作室的四个伙伴,在成都市区租了一家宽敞的民宿办公,因为工作时间长,听播客的时间也变长了,“一天听 10 多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晚上偶尔去公园散步,甚至睡觉前,他也会戴着耳机听。
“主要听一个潮牌旗下和讲嘻哈音乐的播客。”小败对市面上扎堆的观点输出类播客无感,“我喜欢轻松的,太多讲大城市年轻人生活的播客,观点输出量比较大,听起来有点累。”
这样得劲地听了半年后,小败觉得播客这种形式可以“为我所用”。作为一个装备党,“装备不行会打击我的兴趣”,他先买了一个自带录音功能的调音台、监听耳机和 4 只麦克风。

除夕那天,吃过年夜饭后,小败喊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们来家里坐坐。他们一伙八九个人,因为某段时间恰好都没有工作而熟识,闲来无事就聚在一块喝酒、吃烧烤、打狼人杀,之后也定期聚会,小败见证了其中好几对情侣从初识到结婚的全过程。
“有好几个聊着聊着真的哭了”
老朋友们陆续到了小败家,小败提议,“我们今天录个东西玩一下”。
他没有提到播客,因为“县城 100 个人里 99 个人是没听过播客这个东西的”,只说是做个记录,对着话筒讲讲过去一年,自己生活里发生的重大事情,和对新一年的期待。
朋友们听了,都很捧场,有两个推辞说普通话不好,小败也不勉强。

这帮老朋友们的人生已经开始分野,有结婚了的,有准备生孩子的,还有相亲五六年仍孤身一人的,有公务员、老师、家庭主妇,还有自己做生意的小商贩。
小败觉得,相亲多年的那位高中女同学,是最能代表县城年轻人生活现状的一个。她学编导出身,毕业后在成都电视台工作了一两年,就回到县城,“接受家庭的安排”,在父母和姨妈所属的医院宣传科工作,每天走路 5 分钟就到单位。亲戚们从那时起就张罗着给她介绍男朋友,她也从不拒绝,生活里没有太多烦恼,“主要焦虑就是结婚”。
进到设备间后,小败问她过去一年有哪几件重要的事情,女同学第一反应就是相亲。性格大大咧咧的她,笑着分享自己最近被一个相亲对象强吻的故事,小败只能跟着乐呵。
“换作大城市的女孩,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性骚扰了,但在县城,人们没这个意识,说的人当笑话讲,听的人也当八卦听。”
小败没想到,此前从没进过录音间的老朋友们,面对麦克风,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他这才知道朋友们平时聚会时藏在心底的那些郁结:做语文老师的女性好友,骨子里就文艺,年底刚刚离婚;看起来恩爱的那对夫妻,过去一年共同经历了一次流产;还有一个哥们考公务员五六年都没考上,“有好几个聊着聊着真的哭了”。
但走出房间后,朋友们又都恢复了正常,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嬉笑怒骂。那期播客剪出来后,只有几个女性朋友听了,但反馈也都是“谁谁谁讲的挺好玩”,有意识地不去触及彼此生活里那些沉重而真实的部分。
“话筒是有魔力的。”小败说。当朋友来到录音间,面对主持人和话筒,成为那个狭窄空间里的主角,“很快就会变成放松的状态,能聊出很多日常聊不到的东西”。

在做播客的小镇青年里,小败无疑是个颠覆人们刻板印象的异类。他喜欢热闹,经常是攒局的那个人,即使他喜欢的前沿设计、嘻哈音乐和播客,在县城里找不到同好,他也不觉得忧虑。
自由职业了一段时间,他常常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偶尔和老友喝酒扯皮,没钱了就接点私活,“我现在连工作的想法都没有”。
大部分时间里,他享受作为一名小镇青年的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作者:谢祎旻,编辑:Ly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