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中国
北京东三环,车需要在东大桥掉个头,高佑思坐后排,挤在一位编导和一位记者中间。他向司机师傅发出指路提醒,人高马大,口音微弱,“不在这里调头,直行,从前面调”。一个外国人乘客指路?师傅闻后不语,跟着车流继续往前蹭。高佑思继续说话,仿佛只是跟同事聊天,“前面还有一个口,大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次在这里调头堵过半个小时”。车行缓慢,师傅不情不愿,并入最左侧道之前最终挤了出来,上了中间车道。
掉完头,高佑思松口气,显然他是对的,“我经常从这里走,熟悉,导航只懂指挥从第一个路口调”。他已经迟到了。他要赶去找一个意大利女生,拍一条“网友提问”,“怎么样逼一个意大利人吃菠萝披萨”(因为意大利人非常讨厌吃菠萝披萨)。

高佑思是以色列人,过去近15年都生活在中国,现在没人使用“中国通”这么老土的称号了,但以高佑思在中国生活的资历,实在当得起。他最常做的事情,是到五道口和三里屯,街采其他外国人,问他们这样一些问题:你在淘宝上都买过什么;你听过哪些中式客套话;你在中国KTV有过什么样的奇葩体验,诸如此类。
这些街采视频在B站、抖音、youtube等多个平台、以账号“歪果仁研究协会”发表,目前,它在全网有3000万粉丝。而高佑思,出现在这个账号的大多数视频里,不折不扣,是这个账号的符号性“形象”,也是“会长”。
“歪果仁研究协会”的所有账号下,“外国人讲中文”的相关话题效果最好。比如,“用毒毒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啊”,“明明明明明白白白喜欢他,但他就是不说”,请外国人给它们断句。有个小哥回答,“毒毒”可能是像“包包”那样,是卖萌的说法。B站观众特别喜欢这些桥段。再如,小高是“会长”,但这个会长,中文讲得并没有另一个外国人,也就是副会长星悦好,“为什么星悦中文这么好,却是老高当会长”,这听上去就是个好选题,他们于是专门拍了一期。

论相貌,28岁的小高肯定属于中国人眼里长得帅的那款外国人,身高1米82,头发颜色接近中国人,而且很浓密,眉毛更浓,像两捆柴横伏在脸上。但网友喜欢他,长得帅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视频里,有一种“憨憨傻傻”的形象,甚至有时讲中文出点岔子都成了他讨喜的原因。如果说网络红人都得有一个人设,那么高佑思的人设大约可以总结为:“经常去街上采访外国人的以色列人”、“一个富二代,但没过过好日子”,以及,“努力学习但中文水平总比不上星悦的外国人”——或者用他们团队CEO方晔顿的话说,高佑思是一个“精神混血”,不像胡润他们那一代来中国的外国人,成年以后来探索发现中国,亲近的同时实际与中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感,而高佑思从青春期就到了中国,大学时代又受北大熏陶,其精神与气质与中国更亲密。

“歪研会”其实是一个内容创业公司,其内容属性,可以归类为“跨文化交流”。高佑思是这个创业公司的发起人,他有三个合伙人,除了担任CEO的方晔顿,还有负责内容的刘祺和如今正在拓展海外渠道的张希曼,都是地道的中国年轻人;后来星悦也加入了,她是大家街采时碰到的美国人,中文异常流利,今年甚至还去参加了一期《脱口秀大会》。
高佑思是以色列人,2007年底跟随做投资的父亲到达香港,2012年来到北京,经过两次备战,2014年以留学生身份考入北大。上北大第一年,他就张罗着创业,他先找到方晔顿,比他高几届的学长,张希曼最初加入是实习,她当时还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体育管理专业的二年级。刘祺稍晚,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社会学硕士。那是2014年。
那是中国互联网创业最火热的几年,其中戴威和他创立的ofo小黄车风头正劲,创业风潮一度席卷北大。现在回看,高佑思他们那个小团队,也属热血沸腾中的一员。
7年前这个非常年轻的创业团队,到今年已经扩充至近五十人,成长为一家MCN公司(且已有相当多海外业务),而“歪研会”这个账号,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他们获得关注与成功,与他们在“外国人如何看中国”这个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分不开。某种程度上,即便对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是理解中国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中国,与90年代胡润、何伟这一代深入中国的外国人所观察到的中国,已截然不同。
“自从”
高佑思他们是从“街采”起家的。
创业的想法最初来自高哲铭,高佑思的父亲,一家风险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及管理合伙人,2007年,他带着全家人从特拉维夫搬到香港,原因是认为中国“在各方各面都有极大的增长前景”。2014年,共享经济如火如荼,高哲铭跟他儿子说,这一块很适合年轻人来干。他觉得自己的儿子,一个以色列年轻人在中国,经历独特,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发挥。如果高佑思不做,他也会投别的年轻人。
高佑思还真做了,就像当初考北大也是高哲铭的主意。高佑思的创业最早是从兴趣出发,做内容他没有媒体人的包袱,作为足球迷,他的第一个点子是去“采访一个英国球迷的体验”,也就是足球向的内容,目标受众非常精准,就是中国球迷。

高铭哲为儿子提供了办公室、法律上的支持,并带他去见了一些投资人,还帮他招了一些实习生。他们的方法是去其它国家寻找驻站记者,中国留学生也好,能讲中文的外国人也好,总之他们能去街头采访球迷,特别是在慕尼黑、巴塞罗那、马德里这些城市。欧洲杯期间, 这些城市里充斥着大量激动的球迷,赛后上街去采,一逮一个准。他们就做了一个叫“fanTV”的账号,让他们感受母队海外球迷的力量。
fanTV做了两年多,欧洲杯和世界杯期间,有几个视频在微博达到过上亿播放量(按照微博的计算方法)。甚至中国国家队都邀请他们为中国男足的球迷拍摄视频,请他们记录十强赛。
但是2016年,几个大赛一结束,他们发现流量没了,掉落了足有80%,这令他们非常失落。改变来自同一年江苏卫视上的一档节目,叫《世界青年说》。圆桌式聊天,棚内录制,每期一个小话题,请外国人讲讲他们国家的风俗习惯,有时也讨论热点话题。节目组邀请了11位各国青年才俊,高佑思也是其中之一。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档节目实在过于浮皮潦草,既不搞笑,也没有深度,但也有不少观众喜欢,因为节目有个点非常准确,即中国观众对那些“中文非常好的外国人”永远有好奇心,同时,对海外生活也有好奇心。

受此节目启发,高佑思和他的团队开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在这里学习语言,融入文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适应与不适应,有很多话可以讲。更何况高佑思本人就是一个“歪果仁”。
那时,高佑思与张希曼二人刚从巴黎拍摄欧洲杯没多久,“请欧洲球迷吃辣条”是所有视频里最火的一条。张希曼就发现,法国人没见过这个东西,辣条包装简单,而且那个红色,一看就特别辣,“这东西能吃吗?”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试了,接着是比较害羞的朋友——球迷聚集起来,都来吃吃看。这个视频传回国内,被国内网友津津乐道,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年轻人认可的 “跨文化”了。
事实上,中国电视确实有制作跨文化内容的传统,央视90年代开播的《正大综艺》,正是无网络时代的中国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无论是外景主持去体验异文化的风土人情,还是很多人印象深刻“真真假假”竞猜,本质上都在满足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

电视节目往往做得一本正经,形式大于内容,高佑思的团队取其精华,去掉了那些一板一眼的流程,直接上街街采,就在中国找外国人采。他们就在五道口,系统地找外国人聊,一天10个小时,连续3天,加起来能采访到几十个人,输出一个3分钟的短视频。
在B站火的第一个视频,聊的话题就是外国人发微信红包。微信红包这个主题浮现出来时,有一个特点非常突出,即,这是“只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的东西,是外国人在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时的戏剧性时刻,这些时刻,很受目前中国网友的喜欢。
循着“微信红包”,他们拓展出了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一整个系列,包括“自从这群歪果仁入坑了美颜神器”、“自从这群歪果仁开始逛淘宝后”等,效果都挺不错,在B站上的点击都有近百万。三个月后,他们在B站的新账号获得了第一个百万粉丝。
“别见外”
一直以来,高佑思采访的都是外国人,街采的问题也是零碎的、闲聊式的。当他更深入地去体验中国生活,他需要去“深入内心”。刘祺在团队里负责内容,相当于主导所有视频的选题与方向,也经常与高佑思一起出外拍。据他观察,这些事,对高佑思来说难度还挺大。“基本都是带口音的中国人,事实上他可能只能听懂50%,或者需要处理一段时间,这使他很难形成一种及时的交流”。
另一个层面,交流难度又是降低的。“如果中国人听你努力讲中文,他还是会非常欣赏你的,他会觉得你好厉害,或者你很可爱,尤其是不会说英语的人,他们会觉得很舒服,跟你没有距离感。所以你努力用一半的中文跟他讲,大家可能会不明白你,可是会更喜欢你”,高佑思很清楚,这是他的优势。

到2017年底,“歪研会”已经做了80多期街采,刘祺已然感觉到,不管提什么选题,两年前肯定有人提过。横向主题没有太多可拓展的,那么或许可去探索更深的内容。他们试过《西游记》这个话题,作为四大名著,中国人想当然地以为,在中国上学的外国人肯定读过它,结果是,几乎没有外国人读过它。
刘祺是学社会学的,他想,既然他们的内容一直受限于当下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水平,那么打破困境的路径,或许是“行动并参与观察”。他想出的新思路,是让高佑思去体验不同的职业,外国人的不适应与新奇中,会有很多潜在的文化碰撞。
第一时间,他们想到的是外卖员,和收共享单车的人,这群创业者,仍然首先将思路粘连在互联网上。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职业体验大概可以做出三四十期来。在刘祺心里,这个方式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摆脱选题枯竭的危机,拓展“外国人视角下的中国”之广度和深度。
他们为系列起名“别见外”,英文名是“don’t be shy”,名副其实,它需要高佑思将自己进一步地融入中国,最好完完全全当个中国人。

第一期,他们联系了美团。高佑思刚上手两三天,跟不上那种快节奏。当然也骑得相当快,摄影师要跟着他跑,有受伤的,还有摄影师吐了。“真的很危险,包括我自己也崩溃了”。高哲铭也露了个脸,团队委托他在美团上下一单,又联系美团,通过系统特地把这一单派给了高佑思。匆匆赶单的高佑思,奔到楼底,在他父亲投资的这栋大楼里叫保安拦住,不允许上楼,就像许多外卖员会遭遇的一样。正在交涉时,他父亲笑嘻嘻地下楼来取餐了,镜头给高佑思一个特写,他脸上有惊讶和惊喜,最主要的还是心事重重,送餐任务太难了,他没有时间停下来跟父亲寒暄。
他们还拍了一家早餐店,拍完两个月,店就被拆了。“本来店里有很多老朋友经常来,很开心,那个阶段算是好阶段,后来就‘依旧在路上’,每一年或两年的,要被赶出去,生活就发生一次变化。”除了规定给他的“观看中国”,高佑思自顾自地总结说,“好像人都一样”。
他说,“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想过好的生活,吃好吃的食物,工作一天能回到一个温馨的家庭。不管什么人,出生不同,文化语言不同,但心里想的是一样的,都需要安全感,都想过简单的生活,都需要有点开放,都是有朋友或没有朋友,都有不好的时候。体验过别人的生活后,你会有点羡慕,你会觉得大城市里的压力是不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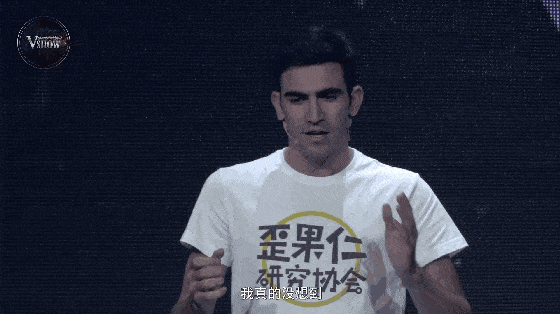
方晔顿不会跟着所有的拍摄,但外卖员那一期的拍摄,他全程都参与了。拍摄之前,他跟大多数人一样,认为算法和技术是美团最大的秘密,但参与到实际的工作中,他感受更深的这些站点的组织协作能力。比如他们去的那个站点是五道口,几乎是全北京最繁忙的外卖站点,他看到,这里的每个人都非常有战斗力。或许,这才是中国这几年移动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基础,而非算法和技术。
有时看拍出来的视频和弹幕的反馈,方晔顿也会思考,这不只是一个外国人在观察中国,也是一个类型的年轻人在观察中国,只不过,他们用了外国人这个比较讨巧的入口而已。
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外国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眼里的中国之间,或许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是一条多大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