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角落的夜晚》,嘉宾:刘擎、周濂、梁文道,编辑:林蓝,监制:猫爷,原文标题:《当代年轻人,夹在“难”和“太难了”之间》,题图来自:《喜剧之王》
焦虑似乎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鸡娃”、“内卷”、“躺平”、“逃离北上广”...这些流行语的出现,好像把所有人都赶进了一个笼子里。里面的人要么盲目竞争,要么消极抵抗。
当代年轻人,时常夹在“难”与“太难了”之间。学生时代追求分数,进入职场追求财富,我们的快乐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在看理想出品的谈话节目《角落的夜晚》中,哲学教授周濂说,“年轻人应该是可能性大于现实性的,只有可能性大于现实性你才有希望。”除了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人生路径,我们自己也要学会远离无尽的攀比,专注于已经拥有的生活,从中寻找意义。
正所谓别人卖瓜我种花,你去大厂我回家。从设定好的赛道中偏航吧!愿我们永远不放弃扑腾,这样就能杀生活一个措手不及。
年轻人,为何不快乐?
1. 今天的年轻人,格外不快乐吗?
梁文道:今天要聊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我最近看到一些数字,应该来自某份中国心理健康白皮书,里面说中国大概有27%的年轻人有心理问题,主要表现是抑郁。
二位都是教书的,你们在学校天天接触年轻人,这种感觉强烈吗?
周濂:很强烈。我身边有不少年轻人去找心理医生咨询,比如说毕业前,因为论文压力,很多学生需要导师,甚至是团委书记进行开导。我相信刘擎兄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刘擎:我的夫人是做心理咨询的,她说现在给学生的心理咨询从无限免费到只有八次免费了,因为排队的人太多。有心理问题的年轻人正在快速增长。那天夫人还告诉我说,统计到有7%的人的心理问题很严重,其中还有人有过自杀行为或倾向。
梁文道:所以你认为,现在年轻学生的心理亚健康比以前更严重了。
刘擎:非常严重。
梁文道:我一直有个想法,但极有可能是错的。我一直在想,今天的年轻人比以前的人面对着更大的心理危机,是不是一个被夸大的代际差异呢?其实以前那代人也可能有很多心理问题,只是当时没有被辨认出来。
不瞒你们说,我中学的时候也想过自杀,好几次上过顶楼。因为我的学校是所高度纪律化的男校,非常压抑。我也不想学习,我只想读自己喜欢的书。当时就觉得人生如果这么苦,而且最后都要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死?当然,最后我因为没有勇气,没有跳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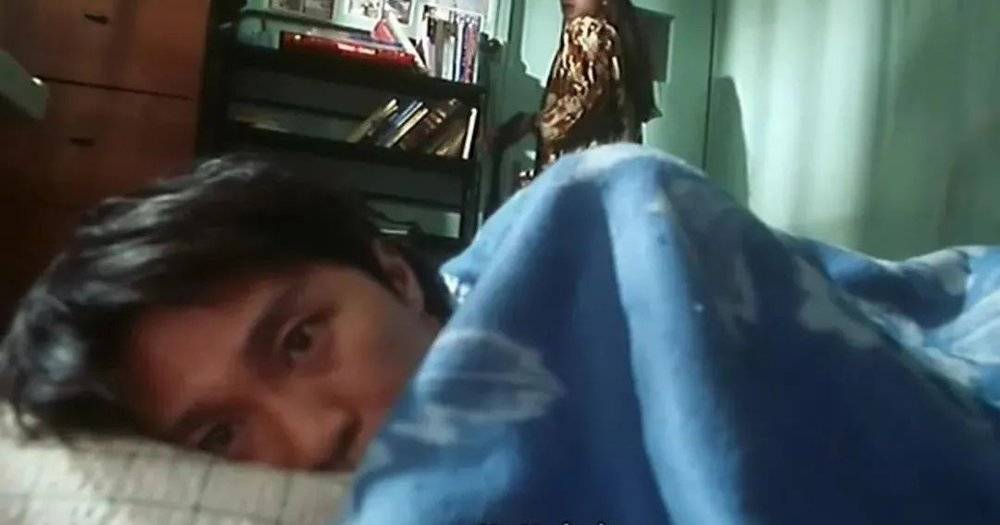
刘擎:有这样的因素,但我觉得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80年代,要干的事很多,机会也很多,你不会时时刻刻以一种自省的态度来看待自己,想那么多自我的事情。
梁文道:你的眼睛在往外看。
刘擎:是的。有好多事情在激励你、推着你,生活的洪流是巨大的。现在的孩子,包括那些说工作上要“躺平”的人,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期待,但他们同时会想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其中的挫折等。
周濂:我大致倾向刘擎兄的判断。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知识上的考古学。80年代、90年代的年轻人的状态,到底是比现在的人好,还是坏?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年轻人总是会忧郁的。他们会对社会失望,会对自我感到焦虑。这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我觉得可能还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变量。
刘擎:无论这个征兆是时代的征兆,还是青年青春期的征兆,它们都是叠加在一起的。但是,在不同代际的青春期所有的共性之外,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新时代的烙印。
梁文道:也有可能就是青春期的共同表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2. 社会需要给年轻人提供“掩体”
周濂:谈到现在的年轻人跟上一代的差别,我经常跟我女儿说,你们一周有两天休息,多幸福,我们当年只能休息一天。后来我一反省不对,孩子们虽然有两天休息,但周末其实有各种课外班。
我还经常和她说,爸爸以前经常考双百,你呢?后来一想不对,我们当年的厂矿子弟小学只有一个班,女儿现在的小学有八个班,而且面对的是智商非常高的小孩,竞争压力极大。
刘擎:你好讨厌。

周濂:没有没有,我是会自我反思的。
梁文道:真是个“鸡爸”。
刘擎:她才二年级吧?
周濂:对。有一天我女儿回来跟我说她特别不想上学,想休息。她还说她们班上有同学希望上两天学休五天,我当时就被他们的焦虑程度震惊到了。
我女儿还迷上了一种减压玩具,叫“squishy”,捏了之后能释放压力。这种玩具在小学生之间很流行,文具店也卖着大量减压日记、减压笔。
梁文道:这原本是发明给那些在硅谷的白领和程序员用的。你孩子的小学是地狱吗?
周濂:不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
刘擎:我自己认识一个本系的同事,他初三的孩子已经到了不能去学校的地步。那个孩子每天早上八点进学校,四点回家,一天在学校八个小时,对于孩子来说像是生活在地狱。因为他在班上排名倒数。
后来孩子就选择不上学,心理慢慢开始恢复。这是我身边的真实经历,而且孩子的父母都是教育程度很高,当教授的人。
虽然国内开始实施减负了,年轻人的心理并没有变健康。因为那个所谓的赛道非常明确,好像当学生的时候我们把分数放在第一位,工作以后,就是财富第一位。
梁文道:没有任何中段。
刘擎:我那天跟陈嘉映老师谈,他说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被数字化。比如你本来弹个钢琴吧,挺好的,但你要考级。所有事都通过数字化而变得可以被比较了。
梁文道:因为数字化才能管理嘛。有考级,还可以催生培训机构。
刘擎:我觉得当生活全部数字化,可以被标明、划分等级,那些暧昧不清,野蛮生长的领地就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那才是人可以躲藏的地方,可以逃逸的地方。
梁文道:我感觉很多小孩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被父母教训了,在学校不开心,会找个地方躲起来,或者找个树洞倾诉什么的。
这种躲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件事,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关键是我们的社会有没有一个机制,或可能性,能让人有个躲的地方,你可以与外界暂时告别,做什么也无人打扰。
刘擎:就是你有掩体。
梁文道:比如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蚂蚁搬家,可以一整个下午都在看蚂蚁慢慢走。我意识到时间的流逝都是因为天黑我看不见了,才知道该回家。那一天我可能就逃学了,虽然会被骂,但第二天又元气满满。
刘擎:这在今天是多大的奢侈。
周濂:因为今天的时间管理已经精确到分钟或秒钟了。我还是觉得, 如果今天的生活中,年轻人可以获得承认的途径多一些,是不是情况就会好一点?
我讲一个小例子,我的同事有对双胞胎,面临中考的压力。老师对孩子的评价是,表现一直很稳定,但进步空间很大。
刘擎:就是稳定在低水平(笑)。
周濂:真的是语言的艺术啊。然后我问,你作为母亲不焦虑吗?你的孩子不焦虑吗?她说不,因为她的孩子们在别的地方找到了自信。首先她们情商高,人缘好。她们还会做手工,卖得特别好,甚至有足够的资金请妈妈吃冰激淋。
我觉得就作为父母也好,或者整个社会环境也好,重要的是我们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更多可以被承认的渠道。
刘擎: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不是特别支持。很有趣的是,在一些欧美国家,一个孩子读书优秀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梁文道:那是会被歧视成书呆子或者娘炮(笑)。
刘擎:大家都羡慕那些打篮球好或者擅长课外活动的人。
周濂:我们当年进北大的时候特别变态,入学第一天就开始比高考分数。我处于中间,所以心态比较平和。
当年有个朋友比完发现自己的分数和别人天差地别,就坐着发呆发了一晚上,但是后来他大学四年过得意气风发,因为他运动好,还会打麻将,能带着哥们儿一起疯玩,后来还和最漂亮的女生谈恋爱。我想说的是,其实生活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刘擎:另类选项的空间还是需要拓展。
3. “太爽了”与“太难了”之间
梁文道:我们刚才都在讲学生,但感到不快乐的青年其实也包括刚入职场的人。
我回看当年的很多同学,的确有的人刚开始工作是不太开心的,但有个前提,就是他们大学四年非常愉快,不像周濂你们北大那么变态。我那时的大学有多样性,就像刘擎兄你当系主任的时候和学生讲的,这四年应该是欢乐的时光。

刘擎:对,就是不被体制和工具理性完全占据。
梁文道:而且是这一辈子唯一一次。
刘擎:探索自己的最佳机会。
周濂:听起来也是个恐吓。
梁文道:因为大学前都在应试,终于上了大学,再出去职场。这四年你再服务于任何目的,只为了自己。
以前的学校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所以从这种学校里出来后进入职场,人又重新回到小时候熟悉的那种怎样都要往上爬的轨迹,他一定会不开心。但是今天的青年,无论是念本科还是研究生,已经不再是那么欢乐的时光了。
周濂:因为职场的逻辑已经全面侵入社会。
刘擎:功利和目标都很清楚。
梁文道:从幼儿园开始到老去,生活的逻辑是一致的。所以今天的青年进入职场后的压力,是在延续大学,他没有一个break。我很难想象,这就像一辈子都在跑一个没跑完的马拉松。
刘擎:从分数到财富,这都是完全单一的目标。这对年轻人的压力很大。他们本可以工作后,领一份还行的薪水,然后就开始玩,探索生活了,但现在的环境让他们必须要有房有车。社会设定的目标很明确,而且路径给钉死了。
像80年代的时候,好像我们的方向也很明确,但路径是不清楚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还不够成熟,没有提供如今这么现成的赛道。
梁文道:由于路径不清楚,也充满着各种机会。
刘擎:现在的赛道都很清楚,你要么考公务员,要么创业,要么进大公司。但是意义感的缺乏很普遍。
周濂:就是道路是被人设定的,且非常有限。我们总说年轻人应该是可能性大于现实性的,只有可能性大于现实性你才有希望,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是现实性大于可能性。
刘擎:我觉得那种焦虑来源于他们通过电影、电视、互联网看到了很多生活的样态,各种可能性看似唾手可得。
现在的年轻人夹在“太爽了”和“太难了”之间。爽指的是你好像可以离开任何一个城市,你可以换国籍,甚至还可以换性别。但难在,现实中要达到任何一个目标,能力都特别有限。进入他们视野的东西越多,越容易让人感到渺小和卑微。
我们小时候由于媒体不发达,好不容易去趟上海或北京,会觉得实在是太好了。但现在的人们因为有智能手机,从小就知道生活有多丰富精彩,期望和现实的落差会大很多。
周濂:就是你看过那些生活,但同时知道很难去经历那些事,那不是你的生活。
4. 即使系统的控制无处不在,还是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刘擎:几年前有“逃离北上广”这个说法,但后来又说小城市和家乡也回不去了。人们安不下心过小镇生活,好多人仍然不甘心。
他们处于一种状态,就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好。这个不够好有时是现实,有时是攀比。攀比是一个无尽的游戏,你当下总觉得不够,当你提高了,比如说年薪能赚到20万,你对比的人又会上一个阶层。
梁文道:就总觉得我值得更好的东西。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谁值得什么呢?这是个分配问题。
周濂:这的确是个问题。前几年我了解到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指数”。《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都知道,盖茨比是一个从底层奋斗到上流阶级的人物,阶级流动的经典。
所谓“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指的是横轴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意味着说贫富差距越大。然后纵轴是代际收入弹性,听起来很学术,其实就是“拼爹指数”,你爸有钱你就有钱。那么越往右上角,那里的年轻人的希望就越少,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就越高。而中国和美国都在右上角。
刘擎:经济学家匹克迪说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基尼系数很像欧洲,后来跟美国比较像。
梁文道: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轨迹。
周濂: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从社会正义的层面去谈,还有一方面就是去想个人或家庭应该怎么办。我们家庭内部的观念需要转变,自我认知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其实所谓的“躺平”或者“逃离北上广”,都是一种反抗。
刘擎:或者说另类选择。在现在的竞争游戏里,你可能多多少少还是需要竞争,但内卷也不要卷得太深,你就微卷,然后卷出可能性。
梁文道:“花卷”。
刘擎:将“微卷”“花卷”当成一种暂时的对策,打开眼界看看别的可能性,注重你已经获得的东西。当你不老跟别人攀比,你可能会发现它的意义。
周濂:其实是有现实例子的。我有好多学生现在就去高中当老师了,也有的选择去四川当个小公司职员,过悠闲的生活,读想读的书。
刘擎:我在《人物》上读到陆庆松老师的故事,他本来在体制内,是清华的音乐老师,他后来就全辞职了,在北京郊区租房子,每天练琴养花养草。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个好的钢琴家,但他也不那么急。
他就完全不按照社会路径来走。有次丢了身份证,警察都不相信他的履历是真的,这竟然是个放弃了清华大学教职,然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但就是这么一个“极端”的人,他生存下来了。
我就特别感慨。在躺平和内卷之间,还是有位置的,人还是能在一个庞大的系统里找到机会。
周濂:我始终相信这一点,哪怕这个系统的控制力已经无处不在了,但依然还是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梁文道:我们虽然都可能在如来佛的手掌里,怎么翻都翻不出去,但还是努力一直翻。

周濂:如果翻不了我就撒泡尿。
梁文道:哎,《人物》也可以采访采访我啊,我也是这种典型的人啊,从小成绩很糟。
刘擎:你已经太成功了,人家陆庆松老师很贫寒,但自己很有定力。
周濂:不,你不可能成为普通人的样板。
......
*本文经过编辑,原内容请观看视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角落的夜晚》,嘉宾:刘擎、周濂、梁文道,编辑:林蓝,监制:猫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