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建立100周年,这篇文章,正是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在常怀颖看来:年轻而小众的学科,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迅速博得学术界的青睐?又会以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未来?作为中国考古学从业者中年轻的一员,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前景的焦虑和危机感,还是一颗纯然的好奇心,都不由自主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虽然仅过了百年,和最初的样态相比,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化显然超出了学科出现时的预设,发展也远非线性,以工作目标和学科进展为线索,粗线条勾勒学科发展的路线图,回望来时路,了解当下瓶颈,为未来保存过去,或许是解题的一种方式。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1年7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常怀颖,原文标题:《常怀颖:由碎而通:中国考古的路线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百年前,初春四月,瑞典人安特生骑着毛驴二进仰韶村。他定想不到,一百年后考古学在中国这般地欣欣向荣,他更意识不到,自己接下来在仰韶村的工作,会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那时,考古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还不足百年。这门以物质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非常年轻,但自诞生即迅速被知识界理解和接纳,进而影响史学界修整固有认识。这在讲究积淀和传承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多见的。
年轻而小众的学科,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迅速博得学术界的青睐?又会以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未来?作为中国考古学从业者中年轻的一员,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前景的焦虑和危机感,还是一颗纯然的好奇心,都不由自主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虽然仅过了百年,与最初的样态相比,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化显然超出了学科出现时的预设,发展也远非线性,以工作目标和学科进展为线索,粗线条勾勒学科发展的路线图,回望来时路,了解当下瓶颈,为未来保存过去,或许是解题的一种方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考古学起步之时,从业者少,在梁思永回国以前,甚至没有真正具有田野考古发掘经验的科班毕业生。职业工作人员少,工作重点就一定得拣最紧要的干。陈星灿和孙庆伟在总结这一时段学术史时不约而同注意到,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均着意于“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而最核心的工作目标,是傅斯年所总结的“材料最重要”。
可以说,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中国主动性考古工作,如西阴村、城子崖,以及殷墟和斗鸡台的调查发掘,无疑都是基于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这一问题展开的资料积累性探索。
以新材料带动新问题,再通过解决新问题寻找新材料,进而“有现代科学的发生”。对考古学来说,发现与研究之间往往并不匹配。对各类遗存的认识和理解滞后于发现,理论的凝练与提升更需在若干认识和理解沉潜之后方能产生,研究的突破不会一蹴而就。
按照傅斯年的设计,选择殷墟发掘,是因为它“是考古学上最好的标准时期,便于研究的人去比较……以殷墟发掘的陶器做标准,推出其他地方陶器变更的情形,及其时代关系,可以推定其时文化是什么样的”。
虽然殷墟时代性质明确,但由于发掘所获的陶片、石器等资料零散,且因当时的发掘技术水平低、规范程度差,所以发掘资料很难真正被利用起来。
一九四九年之前,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效工作时间不多,夏商周以外各时期遗存的田野工作并不系统,对新发现的文化多样性关注严重不足。但当年的第一批中国考古人,却对这些考古资料充满信心。
殷墟、斗鸡台的发掘不仅在实践中基本确立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发掘与整理方法、流程,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基础,还培养了人才队伍,组建了中国考古学的人员班底,对一九四九年以后考古学发展影响深远。
后冈和城子崖“三叠层”的发现给他们极大的鼓舞,散碎的资料已经能看出编缀的可能。李济对这些看似零散资料的意义十分看重,提出未来要将各类发掘资料“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家所做的第一步工夫。他们的第二步工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这几年中国古史所辩论的完全是如何联缀起来这些地下出土的若干新资料”。
以傅斯年、李济的既定目标衡量,初创阶段的中国考古成就有二:
其一,是确认了仰韶、龙山、小屯的早晚关系,形成仰韶、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的学说,并由此衍发出夏、商、周三代文化并非一脉相承的新认识;
其二,明确了殷墟作为中国考古学物质文化辨识基点的地位。
在李济的心目中,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过程应当有三个阶段:“一、如何把这些材料本身联起来;二、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三、如何把它们与整个的人类史联起来。”但他没有想到,这个目标将在后续的九十年中缓慢而持续地指引现实工作。
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年之间,“考古工作,是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推动下进行的。田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对各地古代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由于主动的和配合基本建设抢救保护性质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工作集中在长江和黄河流域,所以这一阶段考古工作重点和最大成就,在于初步辨识上述两区域主要考古学文化类型。通俗地讲,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在较大的范围内“认东西”。
一九五三年,夏鼐就当时的考古工作现状提出今后几年内努力的方向,其中“除了配合国家建设工程发掘地下文物加以整理研究之外”,主动性的研究“应该以新石器时代、殷代和两周为重点,尤其着重西周”,同时应学习苏联,做大规模的完善的发掘,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解决考古学问题。
类似半坡、庙底沟、屈家岭、大溪、二里头、药王庙、丰镐、汉长安城等新发现遗址或新开辟的工作地点,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甚至在华南、西南和北方草原地区,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认识到这些地区原始文化十分复杂。
与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新的考古发现已不局限于几个遗址点,而是以区域甚至流域展开。这些新发现,是完成黄河、长江、西辽河等地区以考古学资料进行考古学文化编年“拼图”的主体材料。
但同时,新发现也带给考古学家新任务,他们需要给这些新发现以正确的时空定位,并对其相互关系做出解释。因此,考古学家的首要工作,是构建中国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坐标网,识别各类新发现。
但以当时的研究能力,还不足以对这些新发现的文化差异和相互年代关系做出准确与全面的结论。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定稿付印的、代表新中国十年考古成就的总结性著作《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重点就只能做到介绍各地新识别出的新考古学文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研究不关心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那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不承担具体田野发掘任务,但却因为教学和科研的双重需要,在苏秉琦等人的统一设计下,利用考古学资料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尝试构建不同时空的物质文化格局。
一九六〇年七月,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由师生合编的《中国考古学》(初稿)讲义铅印发行。这份讲义是中国考古学年代最早、最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讲义中,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尝试对当时可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给出相对细致的时间、空间定位,并尝试对它们的关系进行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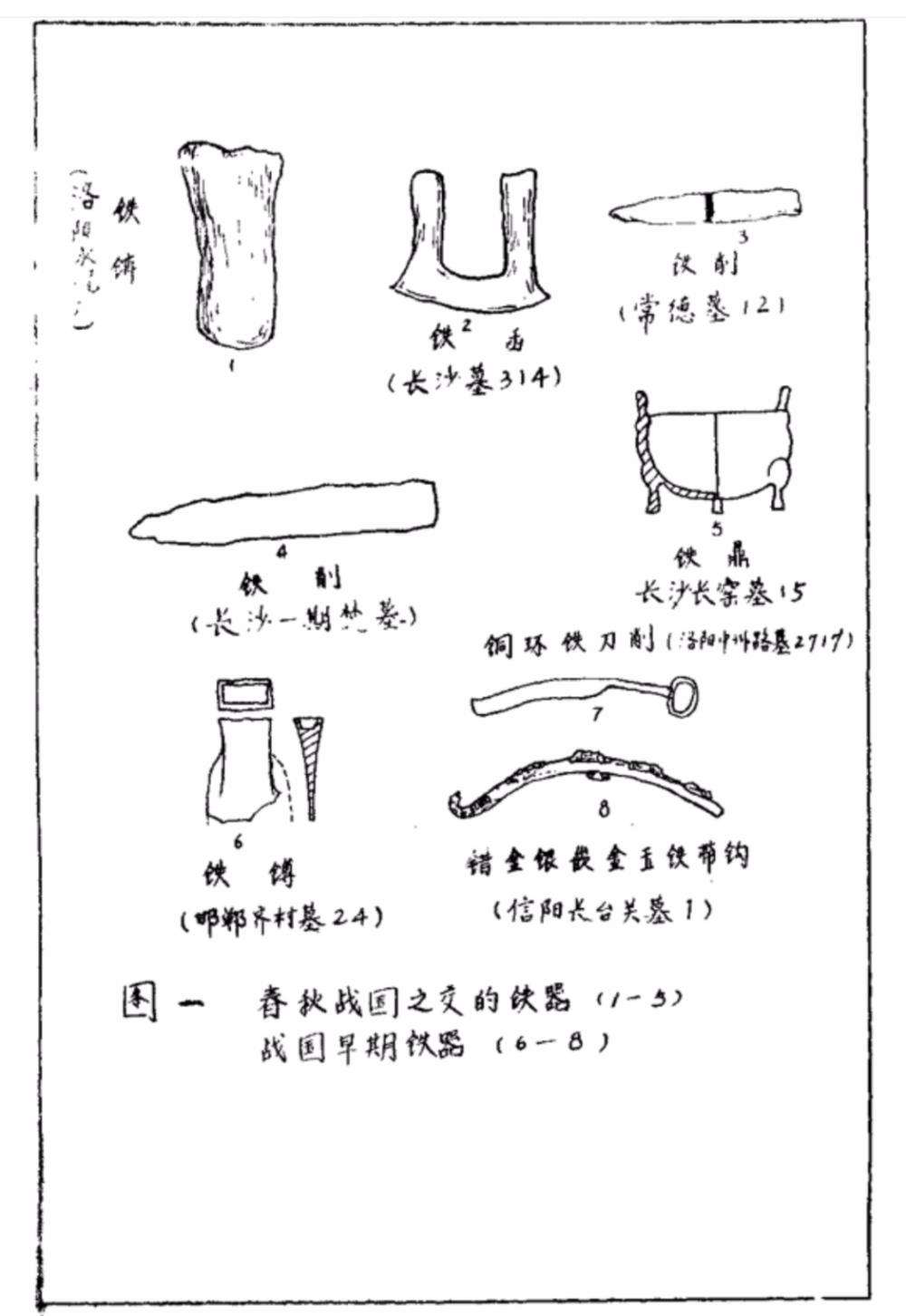
其实,当时以苏秉琦为代表的考古学教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构建各时段考古学遗存的谱系,进行区域化的分析,而非单独处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问题。比如,苏秉琦主撰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已开始对不同地区的战国至秦墓葬材料相对年代关系进行排比,并分别将战国、西汉、东汉时期的遗存划分为不同的区块。
同一时期,严文明对仰韶文化,邹衡对夏商关系,俞伟超、高明对东周秦汉墓葬,宿白对六朝隋唐墓葬、石窟寺,不但自己亲自动手,研究年代与地区框架与差异,还有意识地组织高年级学生以毕业论文方式分时段、分地区进行“阵地战”式的逐个清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以后成熟的各种区系类型研究方法,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基本上都已经在北大师生群体中有了初步尝试。这个过程,加速了对中国物质文化遗存时空框架的“拼图”过程。接受系统训练的学生,毕业后星散各地的同时,也将“缀合碎片”的方法和理念带往各地,引导了全国的考古工作,解决了各地最迫切的需求。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七年间,整个考古学界研究基本停滞。但由于生产、生活并未停歇,田野考古工作虽然受到了极大冲击,但并未曾中断,甚至于有妇好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这样的重要发现。一九七二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坚持和引领下,重要遗址的主动性工作,陆续恢复并持续进行。
到一九七六年之前,还有一个并不显见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即科技检测分析的团队组建和研究准备,通过各种科技手段,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扩充各类考古遗存的信息范围,使各类无“拼图”价值的零散资料焕发新的意义。
考古所和北大不但拥有了自己的碳十四年代实验室,还有了多种科技分析手段,甚至出现了利用卫星、飞机航拍寻找遗址,利用“蛙人”搜索沉船的考古工作。夏鼐对此感慨万千,乃至于引用傅斯年的期盼,强调当时的工作“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考古事业在沉静、稳妥地前行,对新发现的解释和分析却相对沉寂。然而,研究低迷不等于终止,许多学术问题也因之有足够的时间在学者胸中沉潜和积淀,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一九七七年开始,中国考古学的工作基本上恢复正常,学术活动也陆续展开,学术讨论、论辩逐渐常态化,学术研究活力逐渐增强,学者们期盼了十多年,可以自由讨论、活跃与绽放的时代终于到来,学术讨论、论辩逐渐常态化,学术研究活力逐渐增强。对于夏鼐和苏秉琦而言,如何利用好研究环境,引导学科的发展是当务之急。
按照苏秉琦的想法,数十年积累的考古资料已经显示各地“古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是连绵不断、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不是一刀切的,也不是一条线发展下来的”。因此,在一九七九年,他就提出考古工作改革有三件大事时不我待:
“一是全国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二是原始社会的解体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还有)一点希望是:全国分区开展学术活动。”这个想法,与他在五十年代对全国秦汉遗存的分区研究方法一脉相承,也被后人形象地比喻为“画圈圈”。
一九八一年,他将这一思路概括为“区系类型”学说,提出“‘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做了全局性的归纳和划分,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转化为历史演进的框架构建。
这一学说,迅速引起了全国考古学界的极大反响。他的学生张忠培、李伯谦等将这种思路进一步阐发,分别提出“考古学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法”和“青铜文明结构体系”研究。甚至远在西南地区四川大学的童恩正,也在这一学术路径上提出广受中外学者赞誉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这些理论探索,无疑都是在探索考古学与其他学科联结的方式,并赋予考古资料以历史意义。
随后的二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进入了多点开花的阶段,一系列新发现令人耳目一新。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将不断涌现的零散、新见考古学资料“系谱”化、“体系”化,寻找各地时空框架的空白,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认识其意义,成为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识。
田野考古资料积累到这个时期,开展聚落考古研究已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聚落内部格局与历史演变、不同聚落之间的关系研究,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遗址中展开实践。而在考古学编年体系研究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对于考古资料的认识程度自然深化,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
严文明在这时开始率先意识到,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圈的形成与各地的自然环境相关,背后决定因素,是因环境而产生的不同经济生产类型差异,而不同的经济形态造成了中华文明的演进道路与模式会有不同。
这些变化,在经历了新世纪前二十年的考古实践与研究后,逐渐显现出学术影响力。类似良渚大城、石峁、金沙、东山村等遗址在新的发掘和研究理念下有了突破性进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细节信息,令人叹为观止,纠正了不少过去的猜想。不但国外同行能与中国同行深度合作进行研究,中国自己的考古队也已坦然开始走出国门,在二十多个国家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与一百年前相比,中国考古学有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学科发展至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三个显著的变化:
其一,是学术议题凝练,细密构建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选择代表性遗址进行农业起源、聚落演变探索和开展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成为学术界最为关注的课题;
其二,是国门开启,考古学家与国外同行开始交流,从研究内容上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众多学术问题需要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进行调整;
其三,是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特别是将现代科技广泛应用于考古实践,以期获得更多的信息。
这二十年中,考古学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探索“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农业起源”“中国古代文明、国家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研究重任。以物质文化资料为基础,“重建史前史”甚至先秦史已成为考古学家的共识。
考古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思考古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经历了与其他文明相似的道路。换言之,古代中国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古代文明体发展阶段的研究理论、模型甚至术语。这种思考影响下的“多线进化论”在新世纪逐步由考古学界扩展到整个中国学术界。
同时,考古学家已经将对社会的“定性研究”,转入对社会的过程研究,思考遗存物化形态的背后,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转、交流过程如何,社会样态与运行机制究竟如何,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演进模式与过程等问题。
也正因此,非传统史学底色的“小历史”、社会史话题在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话题中也正积极尝试。这些研究范式和观察视角的变换,带来了两个直接问题:考古资料所见的中国古代社会与文献记载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契合;国外既有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实际。
这两个尖锐的问题,带来了近二十年中国考古学的两个主要分歧。针对传世文献,有两种态度:
一种倾向认为传世文献多不是“共时”记载,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真相,因此提倡尽量不使用文献而回归“考古学本位”或“纯粹的考古学”,摆脱考古学“证经补史”的取向;
另一种态度则认为,不能以普适性的否定态度对待所有文献记载,文献记载哪条有问题,就具体分析哪条,在“历史语境下”和史料甄别基础上与考古学资料互动研究。
对国外既有理论,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主张采用或借用国外既有理论来总结中国问题;而另一种,则对由具体问题、具体材料的分析所得的规律性认识更为执著。如果以个案说明,则近两年围绕中华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夏文化研究两个议题,可以看到这两大分歧的针锋相对。
十余年来的论争,目前未能达成共识。但两个分歧的背后,实际上都隐含着一层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或者“对话”的意味。毕竟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理论的话语权仍在西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终究需要面向全世界开放,并得到评判。
赵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相当清醒,他提出“产生在西方资料基础之上的概念在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中国文明的性格方面,是大可怀疑的”,认为与其在概念的笔墨官司上耗费时间,不如通过对考古资料研究作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历史理论。考古学大发展到了当前,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也遭逢“林中路”的彷徨与挑战。
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对物质遗存的研究,正在李济所期盼的第二、三阶段间行进。各地看似散乱的资料已经纳入了文化发展史意义的时空框架之中,考古学者已经开始从不同角度考虑这个格局如何与中国古史对应,以及它们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作用问题。
可以预见,再过二十年,中国考古在重大议题上的认识、理论发展、多学科信息提取以及数字信息化方面必然会有长足发展,结论与成果的多元也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但无法预测的是,在原始资料体系化,文化发展与格局认知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多元理论带来的多元阐释体系和堪称海量的新信息,在未来将会如何重组?在不同或零散或断裂的片段甚至体系中,历史的整体形态和意义如何表达,“个案”如何关联“大局”?以既往一百年的发展观之,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阶段,但理论整合与跨学科的话题疏通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可能正是考古学认知模式和理论建构的必经阶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常怀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