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余华x梁文道,题图来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最近有一个文学相关的Meme(模因)流传很广: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活着》无疑是国民认知度很高的一部,在各大售书平台的销量榜上常年霸榜。
作者余华并不高产,目前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6部长篇小说作品出版。
《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的出版时间间隔了10年;《兄弟》后7年,才出版了《第七天》。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文城》,则是在《第七天》出版8年之后。
不过他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此降低,《文城》上市三个月,印量就突破了100万。
畅销与争议并存,《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余华的每部作品出版时,都伴随着读者的批评之声。
《文城》的争议也不少,“为什么要写民国时候的故事?”“人物扁平没有发展”“《文城》是重回了《许三观卖血记》的那个创作舒适圈”“不再是写《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的那个余华了”......
在今天的对谈里,余华和梁文道聊了聊对这些争议的看法,以及他对于创作的信念。
“只要每一部作品保持在某种水准线上就够了。至于哪部作品更成功,那不是作者的选择,那是读者的选择。”
1.《文城》回到了创作舒适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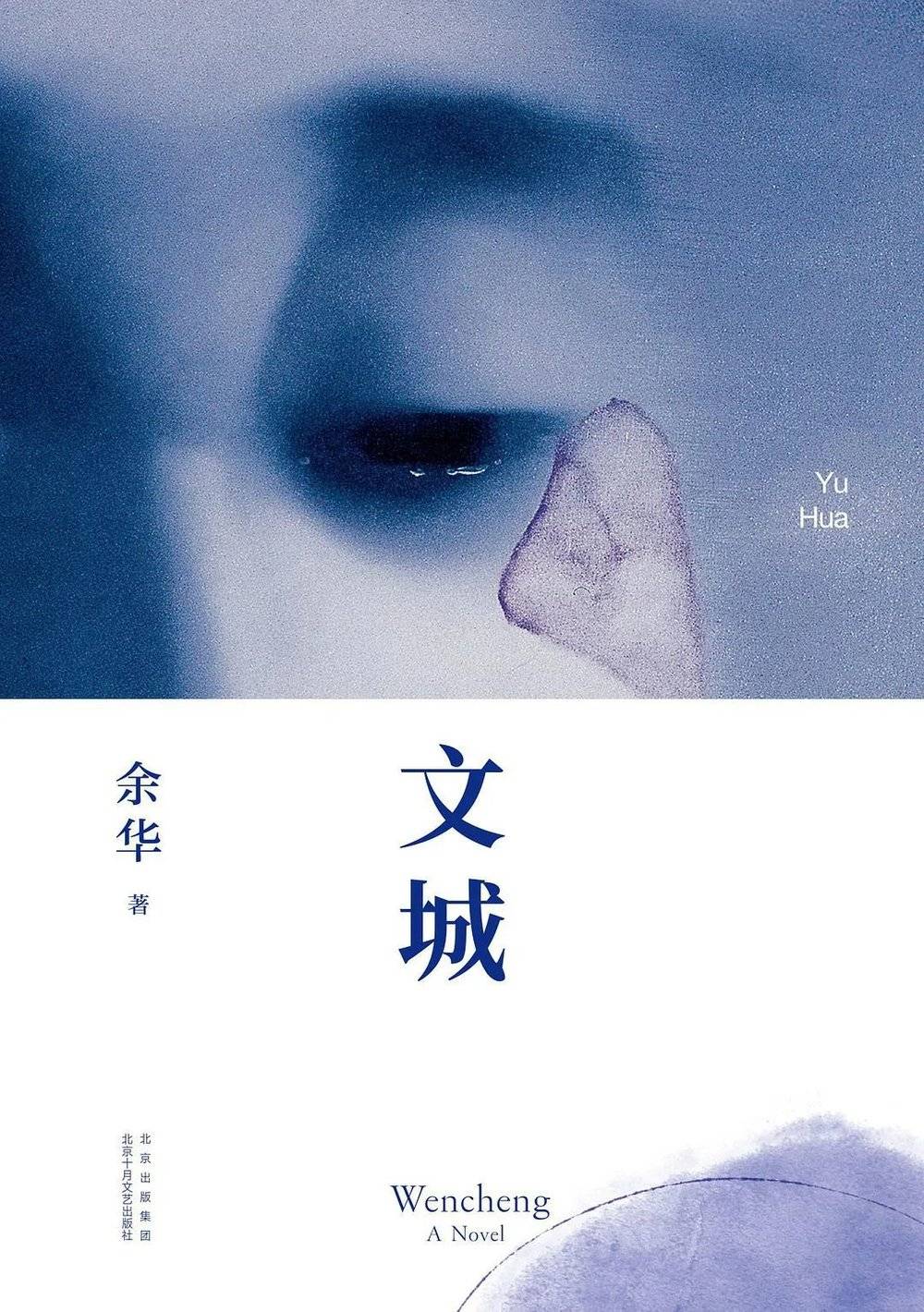
梁文道:《文城》这部小说,我第一次听你谈它是好久以前,也就是说,这个小说你是断续写了很多年?
余华:很多年,1998年、1999年开始写。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在《收获》发表,96年我开始写了《兄弟》的开头,然后1998年、1999年开始写这本,因为《兄弟》当时没有写下去。
《文城》的计划是写一个很长的、(跨度)一个世纪的小说,结果写了20多万字就写不动了,太累了。我当时去读了《静静的顿河》,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它的4卷本也就写了不到10年的时间,而且它的写法也是很细腻的,比《文城》还要细腻。
《百年孤独》是跨越式的细腻,所以要想用《文城》那种方式一直写100年的话,可能得要200万字,我觉得那会耗尽我的一生,然后我就停下来,重新把《兄弟》写了。我在《兄弟》后记里边说到,曾经有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指的就是它。
当我把《兄弟》写完以后,我就知道这个小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写100年了,因为《兄弟》已经把其中40年里很重要的事实给写了。
梁文道:你写《文城》的时候,还在写《兄弟》,后来还写《第七天》,这几部作品风格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你这种在几部书之间来回跳动的写作方法,会更容易意识到每一部作品的特别,反而凸显了两部书的差异?因为有的人写作会担心如果同时写几部作品,它们的区别会模糊,会相互影响。
余华:写长篇跟写中短篇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完成以后,对我的情绪控制时间比较长,可能会长达半年到一年。我只有把前面那部长篇小说完全忘记以后,才能够去写新的。
我之所以老是这么跳跃着写,其实是因为我当时找到一个方式,就是我去写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小说,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被它控制了,换一个题材换一种叙述,就可能换一种心态,而且也换一种世界观。

梁文道:《文城》出版之后非常畅销,然后跟着有很多的评论。有人认为《文城》是回到《许三观卖血记》那种状态了,你还是回到舒适区了,远离了《第七天》那种和现实贴得很近的写法。
我觉得这种讲法好像不是太合适,因为你的写作基本上是这几部书同时在开展的,几个世界观和叙事的模式都在进行中。你怎么看别人说你回到舒适区这个问题?
余华: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种评论。因为《文城》只是我6部长篇中的一部,当然它目前来看是出版时间最近的一部,但根据我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自信,我觉得不会是我的最后一部。
我想他们说我回到舒适区的意思可能是,我的写作离现实远了,但是,难道过去的现实就不是现实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点我们刚才也说了,我的写法就是不断写新的,然后又搁置在那儿,情绪来了又把它写完。
假如我之后还有3、4部长篇小说,都是《文城》这样的,那他们的说法可能是成立的,如果这个说法是针对我的写作和现实的关系。但是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接下来还会写出什么东西,是去舒适区还是危险区。
梁文道:我觉得那种说法的出现,是因为你上一部小说《第七天》,它的写法跟这部的差别非常大,跟《兄弟》的差别也很大。有人觉得《第七天》里你在处理的是一种跟现实的关系,和别的作品不一样,好像是想要有一个突破,是要做一个很实验性的东西,但是后来那个“实验”没做完,又回来了。我想他们大概是这个意思。
可是因为就像刚才讲的,《文城》其实写得很早,甚至在《兄弟》之前,所以很难这么讲舒适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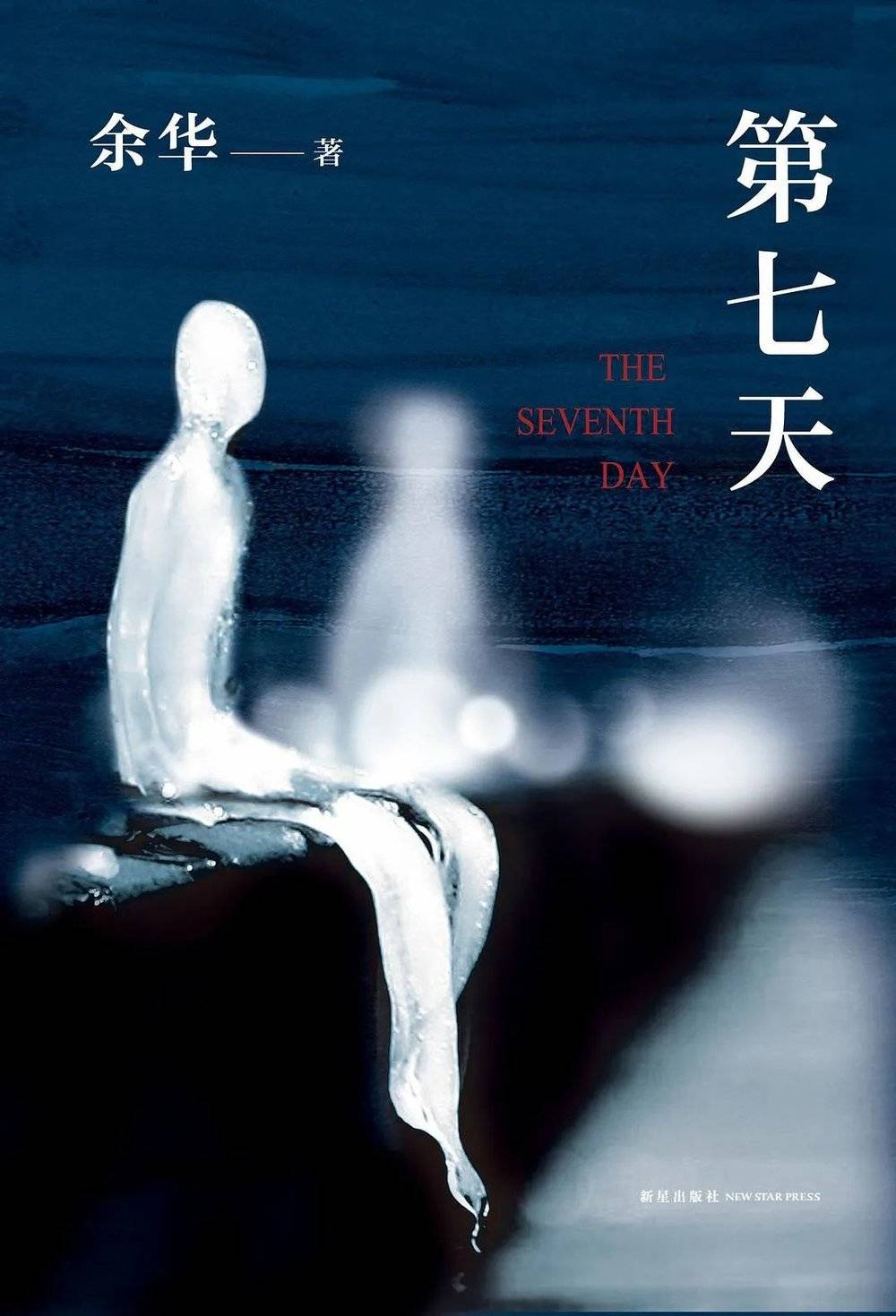
2. 超越自己,没有必要
梁文道:《文城》这部书,我第一遍看的时候,觉得它的整个结构整个感觉就像个传奇故事。我注意到很多人评论说,里面的人物不够立体,没有发展,人物出场是这个性格就这个性格了。
我倒没这个感觉,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个传奇故事,而传奇故事的人物就是要上来戏剧性就很强烈,不是像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深刻描写人物怎么发展,那是另一码事儿。
所以这种写法也是一开始就想好的?还是我猜错了,其实你并不是这么想的?
余华:因为很大部分的读者,他们了解的是我的长篇,对于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那些中短篇小说,他们并不熟悉。其实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武侠小说,还写过才子佳人那种古典爱情小说。
所以我确实有想要尝试传奇小说的愿望,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到了写《文城》的时候,我觉得它具有了写传奇小说的特征,因为传奇小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无法写当代,除非是科幻。传奇小说只能写过去。
我当年读了《基督山伯爵》之后,就想什么时候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就好了,当然《文城》跟它完全不一样,不过就是类似这样充满了传奇性的小说。《文城》是完成了我的一个愿望。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是,这辈子一定要写一部纯粹的喜剧。《兄弟》下半部虽然是喜剧,但是它的基调还是悲剧。
梁文道:为什么?
余华:都是年轻时候喜欢的。就好比回老家,突然看到一条街上在卖小时候吃的东西,虽然你已经感觉到不好吃了,但那个时候你在为自己的童年而吃。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愿望,我努力一个一个去完成它们。
梁文道: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就对喜剧这种形式感兴趣?
余华:对,我年轻的时候读《莎士比亚故事集》,就想搞一个狂欢式的喜剧,像《暴风雨》的那种。

梁文道:那你的写作是从题材出发,还是在题材之前先决定了类型呢?
余华:我觉得可能还是情绪的变化。我要换一种情绪,然后自然就会去换一种题材了,因为要摆脱前面那个作品对自己的控制。但是我做得很不好,我的书写得少。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我有个观念,可能有些作家同行未必同意,就是我觉得写多了没用,为什么?好多作家被人广泛阅读的书只有一本,虽然他可能写了几十本上百本。所以写太多了,好像最后只有研究者会把你的作品读完。
梁文道:所以这是个因果关系,由于你要摆脱某种情绪状态,这个过程对你来讲很困难,所以也导致了你的低产,然后你的低产又回过头来,要求你在状态的把握上要更严格更高。
余华:对,因为压力更大。比如说《兄弟》出版的时候,已经10年没有出新书了,而且那时《活着》已经比较受欢迎了,读者的期待很高。
现在我的小说在完成之后,拿出去之前,我会把之前出版的小说拉出一个平均值来,只要达到这个平均值了,我就拿出去发表。当然,要是到作品里面去找毛病,哪部作品里面都可以找到,但是我自己心里边有一个平均值,当我感觉到这部作品可以拿出去了,就拿出去。
我觉得超越自己,没有必要,只要每一部作品保持在某种水准线上就够了。至于哪部作品更成功,那不是作者的选择,那是读者的选择。
梁文道:我同意,比如说,我们今天回想卡夫卡,有谁记得他的那些书,哪一本先出,哪一本后出,然后哪一本书超越了前面?
而且我总觉得,期待一个作家要超越前面的作品,这是个很现代的古怪,我之前也讲过好几次,如果曹雪芹活在今天,也会被记者访问,《红楼梦》大获成功这么多年,下一步将要写些什么?会不会要有什么突破呢?
我觉得这可能跟现代文学和市场的关系有关,大家都期待一个作家要一本比一本好卖,一本要比一本不一样,就像拍电影不能一直拍同一类型的东西,得不断地推陈出新,这是个很市场经济的想法。
3. “想把20世纪写完”,这是一个很执着的信念
梁文道:你这么多年在北京居住,然后写回南方,像《文城》里的这样一个典型的江南城镇。你现在对南方是什么感觉?是会觉得原来的南方已经不在了,所以你要在文字里面把它抓回来?
余华:我觉得在《文城》里,我的南方回来了。前两天在车里面听罗大佑的一首老歌,他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南方了。我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到上海再到嘉兴,再从嘉兴坐汽车回海盐,一路看,南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长得一模一样,气候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接近。
文城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写的全是我记忆中的南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绍兴。小时候过年去绍兴外公外婆家,要坐乌篷船,那里有大片的水域。后来到了1979年到1980年,我在宁波进修牙医的时候,有几次回绍兴,就发现水域一点一点在消失了。再过几年去看,原来的河道全部变成公路了。

梁文道:今天的江南的很多地方,水域都变成被保护起来的景点区域,不再是生活中的一个出门就碰到的东西了。所以只能够在小说里面把它复活。
那么你想写清末民国初这段历史,从九十年代末就开始写了,是对这段时间有点特别的想法吗?
余华:这可能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作家才会有的一种很执着的信念,就是想把20世纪写完,如果不能在一部作品里完成,就在多部作品里完成。
我之前写的年代最远的是《活着》,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写的,所以我的小说里从清末民国初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空白。所以不管怎么样,一直想去把之前也写到。因为20世纪,尤其是前半叶,不仅对中国人,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苦难深重的。我们这一代作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是没有办法的。
梁文道:你的作品一直都很受欢迎,《文城》这部书也非常畅销。今天大家看你,很多时候都觉得你是中国畅销作家的代表,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身份?
余华:其实这些都是《活着》带来的,所以我一直说《活着》是我的幸运之书。
《活着》是1992年在《收获》发表的,我当时写完《活着》以后,最大的愿望是《收获》能接收,能接受我风格的变化,因为我之前是先锋文学的,还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希望《收获》给我发一个头条,那是我当时对《活着》的全部愿望。
结果《收获》不仅接收了,确实也发头条了,编辑们都觉得我的风格转变得很好,我当时觉得这部小说对我来说已经是成功了。

梁文道:所以你觉得你的畅销作家的身份纯粹是《活着》赋予的。那么像你这么成功的作家,无论是从创作上还是销量上,会怎么给年轻一代作家建议?
余华:首先是,根本不要去想你这本书写完以后会怎么样,你就全力以赴地把这本书写好就够了。
至于这本书出版以后能不能获奖,读者是否喜欢,能不能畅销,那是它自己的命运。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后来发现每本书也有它的“人生道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余华x梁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