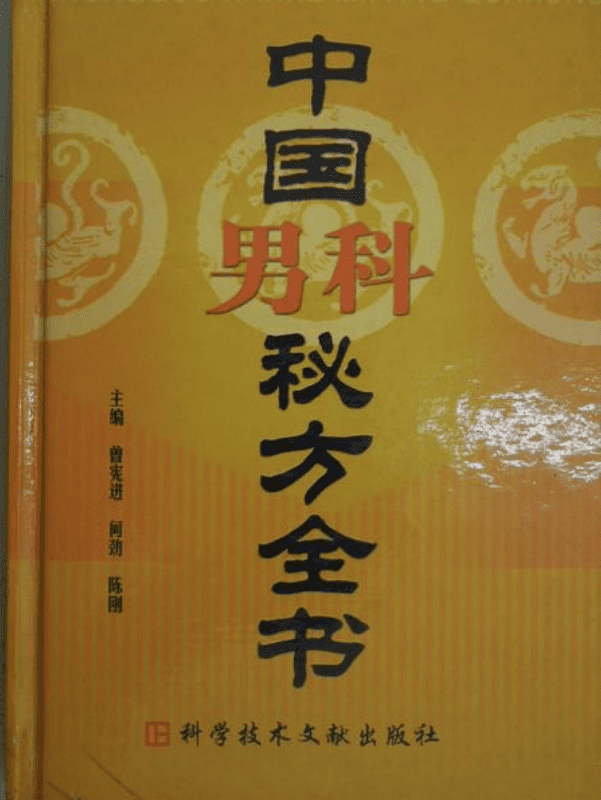
彪子是我的高中同学。五年前,我曾跟他一起在重庆贩卖无限极。我们双双破产之后,我开始进军文化产业,他则是在去大理散心的路途中突然换掉了手机号,从此人间蒸发,了无音讯。
“是你?你也开始不行了吗?”昨天,彪子站在装潢奢华的客梯门口,突然对我讲道。
这是我们自重庆分别以来,彪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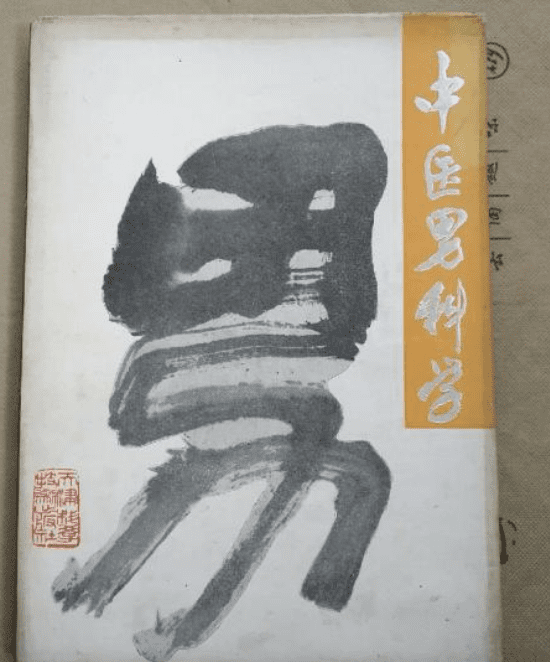
“我反正是不行了,”彪子不等我回答,只是自顾自地讲道。
“你知道的,男人的不行向来很突然。可能昨天还是生龙活虎的野狼——野狼在白日休憩,在夜晚觅食,它们似乎应该永远地在荒原制造恐慌与传说。但可能就是一天的时间,”彪子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悬吊在天花板的那盏硕大轻奢的欧式吊灯,然后用一种悲凉凄楚的语气继续说,“可能就是一天的时间,男人就会从野狼变为一只兔子,一粒碎石,一杯无人理会的劣质啤酒,就变成这些该死的破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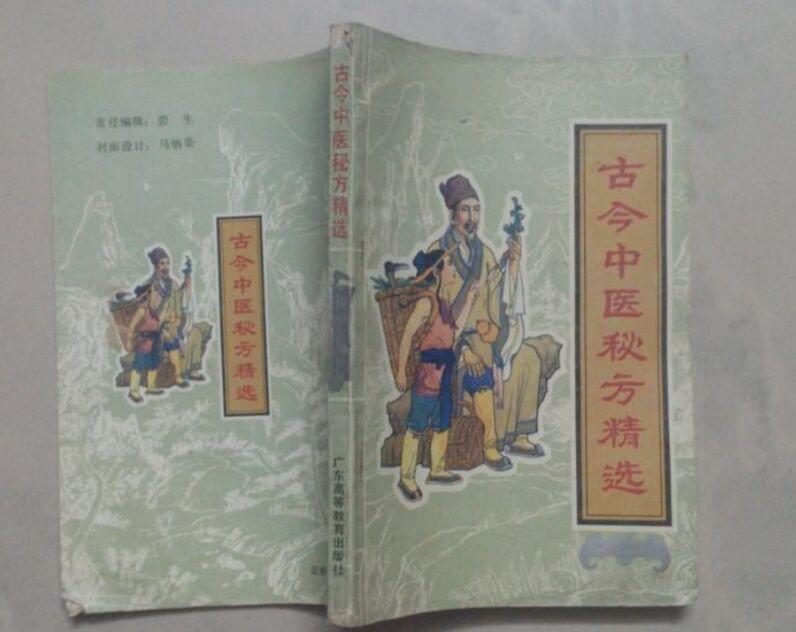
“是这样的,有些事情我们终究无法躲掉,”我随口说道。
而彪子却立马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不要打断他。仿佛我是他这么多年以来,遇见的第一个可以交流的活人似的。
“这种变化太突然了,可能就是在某次新闻联播结束之时,或是在一次平平无奇的腹泻之后。怎么说呢,或许就跟我们上次在重庆破产那样突然。”
“破产那次不是因为所谓的网友把你的……”
“不提这些,已经过去了。”

彪子摸了摸裤兜,思考了一会儿,旋即掏出了一包软塌皱褶的中华烟。这包烟看起来就像是在他的兜里藏匿了至少三个月。
他捏出一根稍微还像一根烟的烟发给我,然后从耳朵后面取出一根崭新的白沙丢进自己嘴里,最后示意我跟他去楼梯间好好聊一下。
“对了,好久不见,”他背对着我,率先走向了楼梯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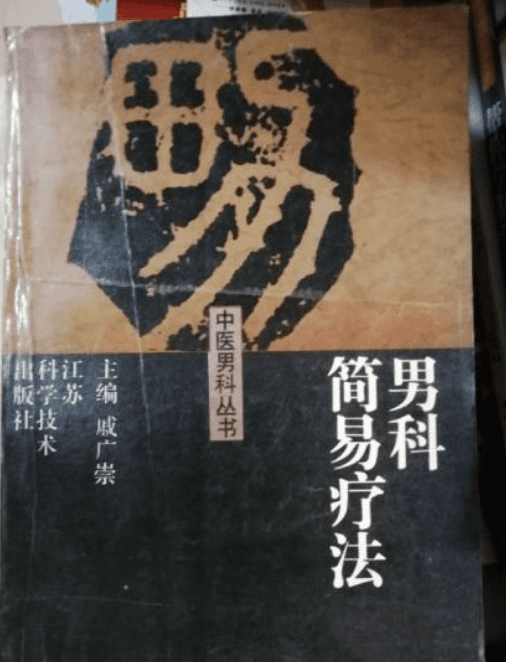
“我做过调查,也问过病友,其实这种病不是绝症,我们要相互鼓励,一起痊愈,然后再次与命运搏杀”,彪子点燃了香烟,烟雾弥散在不大的楼梯间内,而我与烟雾报警器同时保持着一种不谋而合的沉默。
我看见地板上满是大大小小的烟头,似乎每个不行的男人都在这里抽过几根过肺的香烟。

我问彪子这几年干什么去了,他摇了摇头,只给我丢了一个重庆富侨洗浴中心的打火机。
昏暗的应急灯光照射在彪子的脸上,这导致他的面孔始终笼罩在一片祥和的绿光之中,宛若一颗发霉的西瓜。
他挠了下鼻尖,顿了一顿,然后解释说他这几年都在云南打拼,他骗过人,也被骗过,他爱过女孩,也被女孩爱过。他一边赚钱,一边在红尘里翻滚,他在昆明的凌晨里与人相拥,也在洱海的旁边被爱情的债主追杀。
“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不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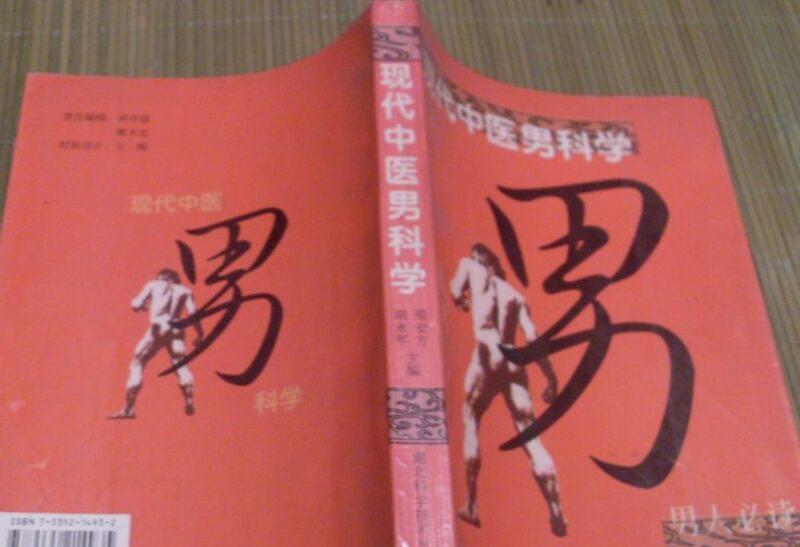
彪子的不行是从两个月之前开始的。
最开始,他只认为那是一场小小的意外,可能是那晚的泸州老窖过于上头,以至于让他几乎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干出合适的事情。不过缓慢的启动过程被他用国际地缘政治分析搪塞了过去。
当天晚上平稳且安详,没有人会觉得太阳已经落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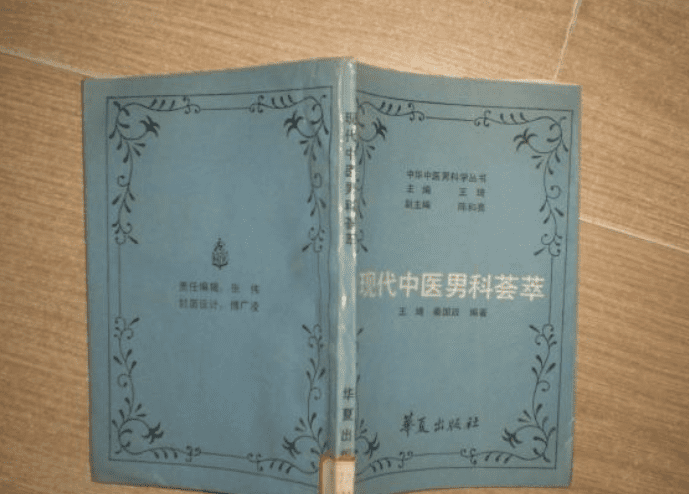
后来,事情却变得越发不可收拾。
彪子的启动时间越来越长,他不得不从政治谈到文学,从宇宙谈到沙尘,他依靠过去三十年的人生经历来为自己争取时间,他开始给对方讲自己的故事,包括当年在重庆的经济纠纷,以及读书时被同桌投毒的过往。
即便如此,他也因此错过了很多个良夜。至少有三位可人儿误会他要趁机借钱,并在随便胡诌一个借口后迅速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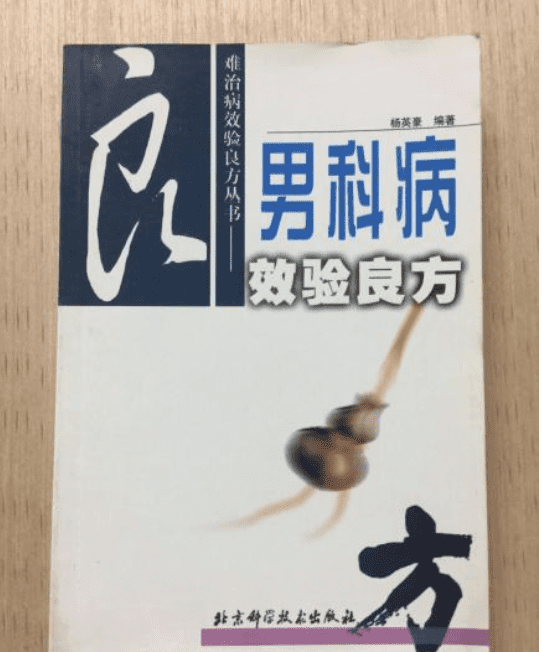
然后彪子又开始尝试服用药物。
“实打实说,药物确实有用,”彪子抖了抖烟灰,又胡乱整理了一下自己那件早已褪色的优衣库格子衫,“但是压力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一颗药一百多,一个月怎么也得上千块,你应该多少知道我的经济状况,我的欲望正在杀死我,我在每一个清晨为自己落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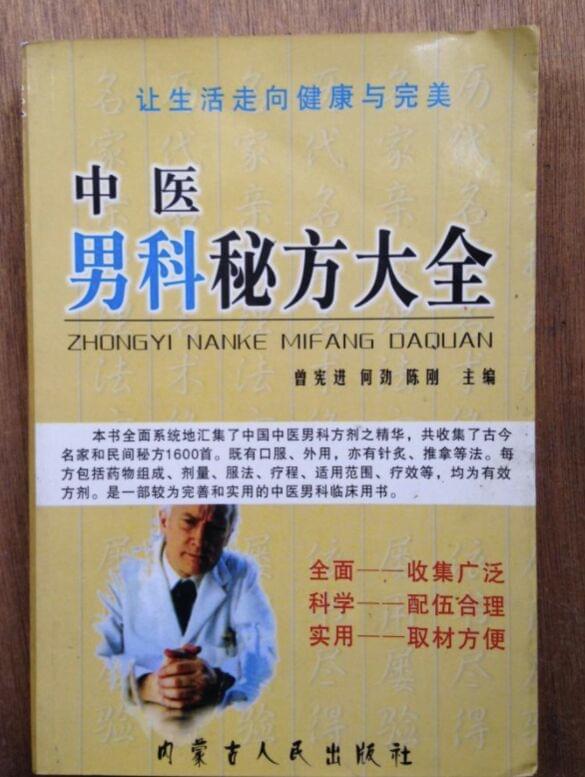
彪子说,他最后都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四天前,当他在出租屋里翻阅微博文学BOT的推文用以收集启动素材时,他突然关闭了电脑,因为他终于看透了一些东西。
他说哪有什么博闻强识的中年人啊,他们口若悬河地点评这个社会,拍着肚子指点江山,在酒桌与双人床上瞪着眼睛发表社论,不过因为他们不行罢了。可惜多数中年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人体的一种代偿机制,当一个男人不行时,他就会妙语连珠,侃侃而谈,并且对所有异性与年轻人都抱有一种肤浅的歧视。
“你是指所有男人吗?”我问。
“至少来这家医院的男人都是这样,包括你。”彪子掐灭了香烟,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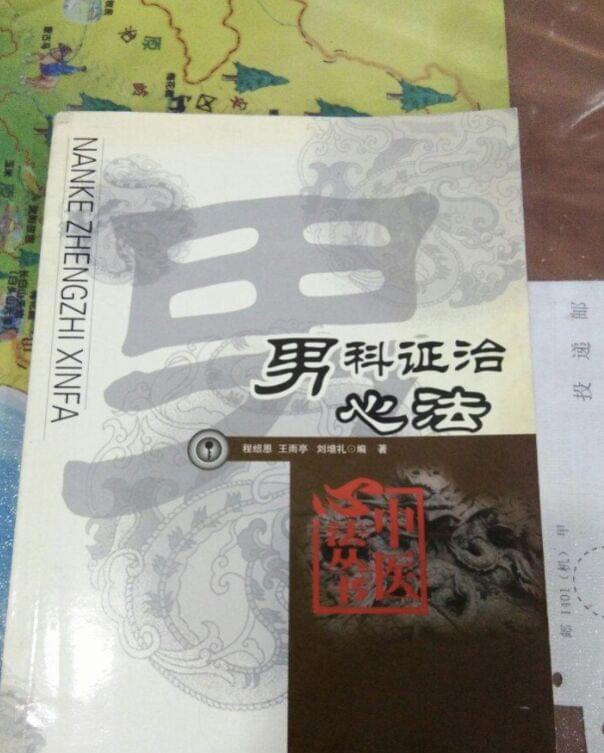
“昨天我就有一种预感,我猜我会在这里碰见你,”当我们再次回到了电梯口时,彪子说,“你也是去三楼吗,挂的黄医生?”
“不不不,我是来接我女朋友的,她在这里上班,”我笑着说。
“也罢。”彪子丢下这句话便自个儿乘上了电梯。
他的背影沧桑且伛偻,跟当年在重庆奋斗时几乎判若两人。也许我也一样。

